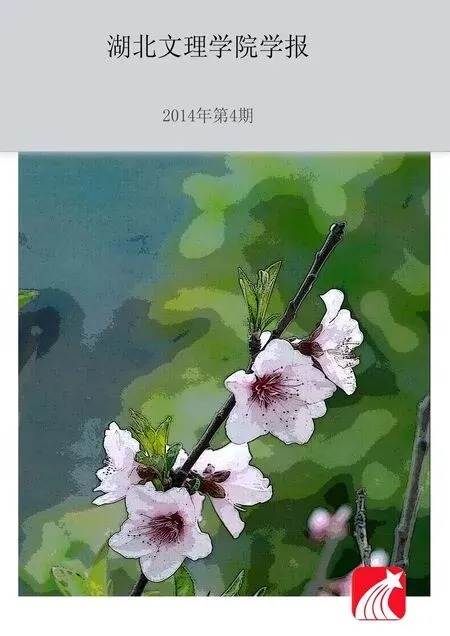关于“里份”的武汉想象
——方方、池莉新世纪“汉味”小说合论
马 英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在城市的文学想象里,上海少不了张爱玲的“公馆”与王安忆的“弄堂”;北京多的是“胡同”和“四合院”;武汉的方方和池莉则书写了各式各样的“里份”。里份是武汉人对里弄的称呼,是汉口开埠之后西方低层联排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的结合体,在老武汉的记忆中,里份曾经一度辉煌,是富足乃至奢华的代名词。现今的里份在旧城区改造的风潮中逐渐显得破败起来。人口的增加使里份拥挤不堪;公用厕所水龙头使生活极为不便;墙体的风吹日晒使里份的外观日渐破烂,里份数量也由兴盛时期的200余条锐减为现在的几十条。里份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一个城市永远的历史记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武汉作家来说,“汉味”文化就是滋养她们的温床。正如方方所言:“当我开始写小说时,这座城市就天然地成为了我的作品中的背景。”[1]在池莉的眼中,老武汉是一个“远在江湖的城市”,[2]它具有灵性、冲动、火辣、自由、散漫等特点,在池莉和方方的汉味小说里,“里份”是一个重要生活场景,对里份小人物、里份风情乃至里份性情、里份语言的生动描画,均唤起我们对老武汉的文学想象。
一、里份风情
方方、池莉对里份的书写,还原了里份的过去和现在,具有深切的历史感,展现了活色生香的武汉生活。在方方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中女主人公水滴的童年时代,里份还居住着不少富贵之家。水滴的亲生父亲生意做得不错,在汉江边经营着茶园,又在里份置办了家产、娶了两房太太,水滴的母亲就是二房李翠。文中有关于水滴的母亲李翠居室的描述:做工精致的花床、满床的绫罗、松软的铺盖、丰盛的早餐,正是因为舍不得里份生活的体面与富足,李翠才狠心将水滴送给一个下河人。小说伊始便展现了里份辉煌时代独特的俗世景观——“下河”。水滴的养父就是一个下河人——每天到汉江清洗他所管辖里份的围桶。水滴从小陪伴养父下河,因之她的童年记忆就从里份开始。水滴看到“富人家的描金围桶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亮”,这样壮观的场景使水滴发出了长大以后也要下河的感叹。“住里份,坐包车”曾几何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社会上层才有可能住得起里份,里份生活充满一份令人羡慕的祥和与富足。行走在里份的水滴从小就感觉到了黑漆大门背后的权势,见识了有钱人家少爷的霸道与专横,里份也因此成为水滴的心结。所以在她成名后,梦中竟然看到有个女人“满处看房。她从英租界走到法租界,看完洋房看里份”。优越与富足的里份生活成为童年水滴不可想象的美好世界。
方方的另外一篇小说《出门寻死》中的何汉晴也住在里份,然而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置换了,里份的文化意蕴、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到了《出门寻死》,里份成为底层市民的聚居处,下岗工人、小摊小贩集结于此,经济情况一般也颇为拮据。何汉晴就是一个生于里份、长于里份、最终也将老死里份的普通居民,小说通过她的日常活动展现了一个生活在里份的中年女性最典型的日常生活图景:每天早上到里份口为一家三口买早餐:“公公婆婆要吃面窝和豆浆,刘建桥喜欢吃热干面,小姑子建美交待过这个礼拜吃油条。何汉晴自己则只花一毛钱坐在摊子上喝一碗稀饭”,平日最大的娱乐就是和里份的婆婆嫂子聊天,用的是里份的公共厕所。这样的里份生活与水滴的童年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少了一份舒适与优越,多了一份平实与拮据。一家人挤在里份的逼仄房屋里,日常琐屑的烦恼淹没何汉晴并最终滋生出一颗出门寻死的心。到了池莉的《她的城》,则更增添了一份辛酸的调侃:“在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大道水塔街这一带,每大早晨,就连前进五路路边的那座公厕,都比太阳重要,附近几个里份,有多少人起床就奔过来,盯着它,排队,拥挤,要解决早晨十万火急的排泄问题。这座公厕历史悠久到好几十年了,好几十年里水塔街早晨的太阳就硬是没有这座厕所重要。”在这样的叙写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现今住在里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空间的逼仄。里份再也难回到从前的那一份富足与优越,而充满了困难与窘迫。
这种困窘的生活方式也孕育了粗糙与世俗。所以,何汉晴的郁闷心情不会引起家人的关注,她的苦闷所招来的不过是插科打诨。逢春因赌气去做擦鞋女也没能让丈夫体会到她的良苦用心。不过里份生活却也不乏一份浓浓的亲情:《出门寻死》中何汉晴热心帮助刘太婆,刘太婆对她说的一段话也让她“倍感温暖”,文三花和丈夫吵架,何汉晴撇下家里的事情立刻去调停。小说最后,出门寻死的何汉晴蓦然看到里份“温暖的灯光”,想起了无数琐碎却不乏温暖的日子而再度回到里份。《她的城》中逢春遇到难事,请同一个里份的蜜姐帮忙,里份有红白喜事大家都会派“红包”,里份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这就展示了里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信任与紧密。如果说文学中的上海“弄堂”更多一份世俗和精明的话,武汉“里份”更多的则是一份亲情和温暖。
小说中的里份具有“家”的含义,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激荡,也无论自己的内心曾经经历过多少隐痛与伤痕,里份始终能够留给人一份安全感,它给的不是一份光亮耀眼、万众注目的生活,而是一份家长里短、平实安稳的生活。当很多人渴望走出去向往喧哗与骚动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们喜欢停留、追求安稳与静谧。当何汉晴出门寻死未果返回时,里份那些闪烁的带着晕味和暧昧味道的灯光让她倍感亲切,也让她对生活、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给了她生活下去的念想和勇气。《她的城》中的蜜姐丈夫癌症去世后,她把自己的店铺就开在自己家里,因为在蜜姐看来,“这是她祖孙三代的街道,她熟悉得没有一点怕,只有亲。更不能离开,除非死。”在这里,方方和池莉都写出了“里份”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里份是生养她们的地方,更是她们的精神家园。虽然空间狭小,却自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这,正是无数市民在里份中生活的真切体验。
二、里份性格
《水在时间之下》中晚年的水滴终于住进了里份。然而此时的里份已今非昔比,它“幽深阴暗,狭窄杂乱。它们有混乱的线条,没有人能够缕清。”这就是武汉的里份,没有北京胡同的方方正正,它网状交织最终通向长江。就是这样日渐破败的里份,却隐藏着许多像水滴这样的人,经历过阔大场面和风云人事,如今却隐匿在里份深处。正是因为它经历了大风大雨,所以才有了一份豁达的性情与博大的胸襟。因此,武汉的里份既经历过奢华也惨遭蹂躏,既大家闺秀又小家碧玉,它本身就是复杂的综合体。日夜与里份厮守的居民濡染了它的精神特质,在“最是时间残酷无情”的感叹里有了一份“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无奈与坚韧、一份俗世的泼辣与精明,也蕴藏着一份仗义与率性。
比如蜜姐(《她的城》)就具有典型的里份性格。丈夫宋江涛罹患癌症,蜜姐没有被击垮,像往常一样照顾老人、带着儿子做生意,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自己振作起来,这是她的豁达与顽强。面对逢春的求助,蜜姐爽快答应,那是她的仗义;看着逢春“顺眼”,才“允了下来”;发现逢春红杏出墙,蜜姐不去拆穿却处处暗示,那是她的精明;见逢春避而不谈,蜜姐与逢春彻夜长谈,并毫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心交心使得两人之间有了“无言的共同秘密”,那是她的率性。何汉晴(《出门寻死》)对朋友、邻居都非常热情,看到老人有难极力帮助,在出门寻死的过程中看到别人寻死,抛开自己的烦恼前去劝说。生活在东亭的阿东(方方:《声音低回》)遇到了困难:母亲去世、弟弟弱智、父亲残废,而自己还要完成大学学业。在这种情况下,左邻右舍给予了他许多帮助:母亲去世的时候,大家都去帮忙张罗丧礼,罗爹爹帮助照顾弟弟阿里、罗四强帮助阿东的父亲进货,这都是底层百姓仗义、率性的表现。就连弱智的弟弟阿里也熏染了这种品格,所以他才会几乎是出自本能地要扶腿脚不灵便的罗爹爹。不过这种里份热情也是留有余地的,不能侵犯自身利益。比如,阿里放哀乐影响到日常生活邻居也会出来阻拦,也有人会不顾形象地跳出来骂街。罗爹爹和阿里早上一起去东湖边放哀乐,实际上也是各取所需:罗爹爹需要阿里的搀扶、阿里需要罗爹爹的看守。蜜姐对逢春的帮助也是以不损害自己利益为前提的,“逢春如果是个不懂事的,蜜姐最多容忍她三天。三天的容忍够长的了,这也就是给街坊邻居的面子”。如果逢春的存在影响了她的生意,她会毫不客气地请逢春走人。
通过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具有里份性格的人们,方方、池莉写出了武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里份性格对他们的濡染。他们的生存智慧,他们的生活哲学都深深地浸润着里份文化的精髓。方方曾经如此表达她对武汉人性格的理解:“武汉人精明,但却不像上海人那么能算计,那么利己;武汉人聪慧,但却没有广东人那样深藏不露的沉着和灵活多变的花样;武汉人仗义,同燕赵之士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有所不同,往往为自己又留着点余地;武汉人直爽,与没遮没拦的东北人相比,这种直爽又直得有限,难免不带上点小弯弯;武汉人天真,见朋友什么事都连兜带底地说出来,但最要紧的事也总还能压在喉咙管里……”[3]这就是典型的里份性格,既“精明泼辣,又务实洒脱”[4],将仗义、直率、天真、热情与算计、粗糙、精明紧紧杂糅在一起。
三、里份语言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普通话的几率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使用方言的几率则越高。与那些住在高楼大厦的白领相比,生活在里份的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下,更多人使用别具一格的汉味语言。方方和池莉的这些小说以居住在里份的市民为表现对象,与此相关,“泼辣、粗鲁、夸张、幽默”[5]的里份方言已经成为她们小说中的独特风景。在她们的小说中,“蛮累”、“晓得”、“邪货篓子”、“老干巴”、“扯皮”、“苕”等武汉方言比比皆是,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的同时显得非常俏皮。
《出门寻死》中年妇女何汉晴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下岗失业,生活拮据。好朋友文三花关于“活的蛮累人”、“心里烦”这样的话语像影子一样跟随了何汉晴,让她也产生了寻死的念头。她和丈夫倾诉,然而丈夫认为“天下人都死绝了”,何汉晴都“还剩在屋里”。何汉晴从心底深处生发出来的对人生的感悟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共鸣,面对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这位全家日常生活的调理者知道自己即使要死,也要把饭菜做了再去死,当她把饭菜做好没有食欲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时,公婆、小姑子和丈夫却一起取笑她。丈夫没有任何劝慰之词,听后劈头一句便是“莫耳她”,对于何汉晴的寻死,他“一个字都不信”,认为“她这种喜欢到处岔的人最舍不得死”,“就是小鬼把她捉到了阎王爷跟前,她两脚就把阎王爷踹在地上,自己跑回来。”《声音低回》中巴西的母亲要替巴西改名字,警察听说巴西智商有点问题便说,“是个苕?那就改吧。免得把巴西队也搞苕了。难怪他们最近有点苕样。”这一方面表现了武汉方言乃至武汉人的幽默、油滑的文化性格,同时也表现了武汉市民的粗犷、粗糙、敷衍乃至刻薄等负面性格。
池莉说:“文学本来就是俗物,所谓小说就是‘大街小巷的说法’,是大雅与大俗的集合。古代有多少好诗是从青楼出来的,流传下来的文学关注更多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寻常生活。”[6]基于这种认识,《她的城》表现的就是生活在一个里份两名女性的寻常生活,寻常生活中充满了市井俚语俗语,用最纯粹的语言表现最本真的生活状态。小说中蜜姐对逢春说:“只要顾客想买什么,我什么都卖,我就给他两个字:敞——的!”“我请朋友吃饭,他们问:怎么点菜?我也就给他们两个字:敞——的!”“我儿子,我给他也就是只能两个字:敞——的!他就是想吃我的心,我立马拿刀子挖给他,冇得二话!”小说最后还专门对“敞”标注了读音,“敞”是武汉非常典型的方言,意思就是说帮助别人没有任何附带条件,这一个字就将武汉女性直爽、热情、果断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
参考文献:
[1] 方 方.阅读武汉[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4.
[2] 池 莉.天生的江湖城市[J].作家,1999(9):98-100.
[3] 方 方.武汉人的性格[J].武汉文史资料,2013(8):49-51.
[4] 樊 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6-37.
[5] 樊 星.当代女作家方言小说特色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2011(1):98-102.
[6] 庄 园.池莉:文学就是俗物[EB/OL].(2000-10-18).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32/20001018/2769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