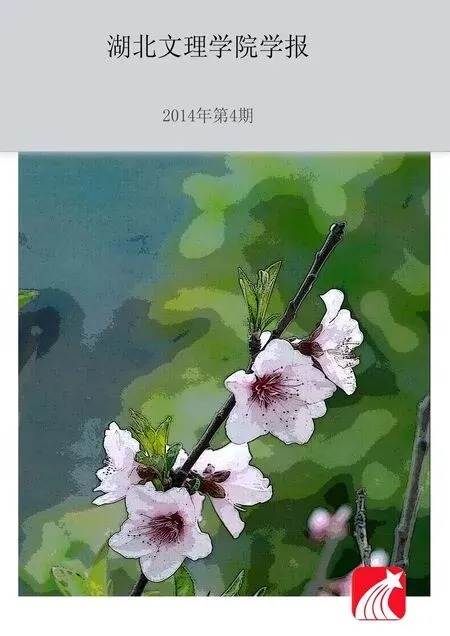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二下)
——湖北钟祥调查报告
刘 刚,关 杰,王 梦
(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
二、关于“宋玉是否是钟祥人”与“宋玉到未到过钟祥”的讨论
近当代钟祥本土学者力主“宋玉为钟祥人”之说,其论辩主要见于民国版《钟祥县志》和1990版《钟祥县志》,兹录如下:
民国版《钟祥县志》卷四《古迹上·序》:
古迹必有事实可稽,足供后人凭弔,而又确在封域之内者,始足与山川并寿。旧《县志》于春秋战国时代,大半泥于“郢”之一字,取《渚宫故事》过事铺陈,其汉以来,又往往阑入安州境内,沿革不明,舛误滋多。本编既量为删削,然关于宋玉遗迹独备载之,说者或疑借重名贤,不无傅附之词,不知兰台为玉赋《风》之处,今固巍然在望,而《阳春》《白雪》本玉歌曲,都人士取以名楼名亭者,亦千余年,于兹观于宋建郢州学,当时指为宋玉故宅,宅内有井有石。王之望《舆地纪胜》、石才儒(按:湖广通志作孺)《郢州土风考古记》皆详著于篇。由斯以论玉所生地,虽不敢确定所在,《水经注》以为宜城县南人,较为可据。宜城县南即今钟祥,说详篇内“宋玉宅”条下,无容赘述。
民国版《钟祥县志》卷四《古迹上·宋玉宅》:
按《史记·屈原列传》但称宋玉楚人,王逸楚辞注亦同。楚地广,玉所居属荆属归,迄未能详,惟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云云。据是,则玉所居之地在后魏时为宜城县南。然石才儒《郢州土风考古记》有云:宋玉之宅,两石竞秀;王象之《舆地纪胜》于《长寿县·人物》(按:考之是书,作《郢州·人物》,此引擅改)内称:宋玉,郢人;《古迹》内载:宋玉石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又载: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又载: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即玉侍楚襄当风处,又有阳春楼诸名胜。据是,则玉所居之地,在宋时为长寿,而后魏时之宜城县南,宋时之长寿在今则钟祥也。窃尝考之钟祥,北接宜城,在西汉为郢县,自东汉郢省县,无专称,逮宋明帝泰始六年始立苌寿,中经四百余年并入何县,虽无明文,然以《陈志·马良传》考之,殆以一大部分划入宜城。按马良所居地,今称马良山,在县境西南,《志》称,良为宜城人,实东汉并郢入宜城之确证。《水经注》谓,宜城县南有宋玉宅,既称“县南”,故决其在今钟祥也。当道元时苌寿甫立,其名未著,道元北人,未及深悉,故仍以宜城称之。前《志》谓,郡学宫即玉故宅,盖沿唐宋以来之旧说,其由来固已久矣。
民国版《钟祥县志》卷十九《先民传》:
宋玉,楚郊郢人。师事屈原。原弟子著籍者,有唐勒、景差之属,而玉之词赋独工,至以屈宋并称于后世。当怀王时,原遭谗被放,玉作《九辩》以述其志,赋《招魂》以致其爱。后因其友见于顷襄王,王无以异也。玉让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也。”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左夋右兔),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虽卢不及(左夋右兔),若蹑迹而纵緤,(左夋右兔)亦不及卢也。”他日其友又曰:“先生何计画之疑也?”玉曰:“君不见夫玄蝯乎!当其居桂林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悲啸长吟,龙兴鸟集,及其在枳棘之中,恐惧而悼慓,危势而蹟行,处势不便也。夫处势不便,岂可量功效能哉!”玉尝侍襄王游兰台,作《风赋》;游云梦,作《高唐》《神女》二赋。唐勒及登徒子妬其能,短于王。王问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词。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凤鸟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非独鸟鱼为然,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一日,同唐勒、景差,从襄王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泰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罘罳。”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能小言者,赐以云梦之田。”景差曰:“载氛埃兮乘飘尘。”唐勒曰:“馆蝇鬚兮宴毫端。”玉曰:“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视之渺渺,望之冥冥。”王曰:“善,赐之以田。”玉休归以著述自见,后世裒录所作有集三卷。
1990年版《钟祥县志·考证》六《宋玉生平考》:
宋玉是战国末期著名文学家。宋玉是哪里人?这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史记》说宋玉与唐勒、景差同时,是屈原以后的辞赋家,没说他是哪里人。《汉书·艺文志》只说他是楚人,《襄阳耆旧记》说他是鄢人,《太平寰宇记》说他是郢人。只有《水经注·沔水篇》记载较详:“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明正德年间,宜城县给宋玉修了墓,据说有3个墓冢,清朝嘉庆年间还树了墓碑。《太平寰宇记》说宋玉墓在河南唐河东北泌阳县。我们认为不能以墓来定其生平,比如屈原是湖北秭归人,却死在湖南汨罗江;王昭君也是秭归人,却葬于内蒙古。
宋玉当为钟祥县郢中镇人。其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自东汉初至南朝刘宋泰始六年止,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钟祥没有设县。《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北魏人,在他那个时代,钟祥北部地区属鄀县(今宜城)南境地。所谓“宜城县南有宋玉宅”,具体当指今钟祥。钟祥有没有宋玉宅呢?有的,据清康熙《陆安府志》记载,明代唐志淳作有《陆安州儒学记》,陆安州儒学即“宋大夫之居”。民国《钟祥县志·古迹》载:“宋玉宅在兰台之左,相传郢学宫即其遗址。”(郢学宫今为县实验小学)。宋玉宅门前还有宋玉井,今保存完好。《安陆府志》所载清李棠馥《重修宋玉井碑记》云:“郢学宫为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数武,有泉冷然,相传为宋玉井云。”
其二,宋玉生前的政治活动在郊郢。据《中国诗史》记载:“宋玉生于顷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照这个纪年推算,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时,宋玉年仅13岁,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可能是从屈原习辞赋。宋玉任过楚大夫,随顷襄王到过郊郢兰台之宫(详宋玉《风赋》)。宋玉的老师屈原任过三闾大夫,屈宋二人是师徒关系,共事顷襄王。屈原以犯颜直谏,终于被顷襄王放逐江南。蒋天枢的《楚辞论文集》说屈原被逐江南是在顷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69年),投汨罗江自沉是在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中国诗史》说是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自沉。宋玉曾经受到顷襄王的器重,赐给他云梦之田。到考烈王时,宋玉便不得意了。至于宋玉的政治活动则主要是在郊郢。
其三,宋玉的文学创作高峰在郊郢。他的作品富有想象力,善于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事物,其著名作品《风赋》、《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等,对后世辞赋影响很大。顷襄王驻跸郊郢时,宋玉曾随侍在侧,每作赋,唐勒、景差都不及。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载: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对楚王问》有客有歌于郢中者,……遂谓郢人善歌。这一记述,涉及了宋玉作品与家乡郊郢的密切关系。
以上的论述,明显地带有“借重名贤”的主观意识,因为其只选用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而回避不利的证据,甚或不顾学术规范与诚信,篡改相关资料,这就使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概括上述论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宋石才孺《郢州土风考古记》和王象之《舆地纪胜》等文献与宋玉宅、宋玉井等文物遗存论证“宋玉为钟祥人”;二是以兰台遗址与宋玉《风赋》和钟祥故称郢与宋玉《对楚王问》论证“宋玉行迹到过钟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一)宋玉是哪里人
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宋玉为宜城人,在宋代以前并无歧说,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载:“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习凿齿襄阳人,其先祖襄阳侯习郁(一说为习凿齿兄)在宜城别筑宅院,其对宜城当特别熟悉,其说最为可信。郦道元之说当本于习凿齿,又在习说“宜城有宋玉冢”的前提上补记了宋玉之宅,可见亦作过精心的考证。迄至宋代方出现不同的说法,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郢州》:“宋玉,郢人。”又《太平寰宇记·襄州》:“宋玉,宜城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襄阳府》载:“宋玉,宜城人。”又《舆地纪胜·郢州》载:“宋玉,郢人。始事屈原。原既放逐,因与景差事楚襄王焉。”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襄阳府》:“宋玉,宜城人,有宅在城内。”又《方舆胜览·郢州》“宋玉,郢人。”显然,宋人“宜城人”说是承习凿齿、郦道元之说,而“郢人”说为后起。凡难决断,则两说并存,是史家存疑的通常做法,体现了史家客观记史的传统精神,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这后起之说从何而来,且所据为何?乐史、王象之、祝穆三人均未交待。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唐时在今钟祥设郢州后,其称谓被固定下来并沿至两宋,在此地又有旧传的宋玉宅、宋玉井以及兰台等与宋玉有关的遗址和遗物,从而推测宋玉为郢人。其实这种推测并不可靠,因为其所依据的仅仅是传闻。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记述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如其所记:“楚贤井,在城东,旧传即宋玉宅。俗名琉璃[井],亦名宋玉井。”“兰台,在州城龙兴寺西北。旧传楚襄王与宋玉游于兰台之上,清风飒然而至,王披襟当之。即其地。”“宋玉石,凡二。唐李昉守郡日得之榛莽间,今移在白雪楼前。”你看,宋玉宅遗址是根据“旧传”;兰台遗址也是根据“旧传”;而宋玉石只是唐人在榛莽中的发现,作为佐证也缺乏公信力,因为此石本身是无法证明发现者为其命名的可靠性的。若那片榛莽即是“旧传”的宋玉宅遗址,那么,又是以“旧传”来确认石之身份。这一切均来源于“旧传”,终难以将问题证实。因此,《大清一统志》在“兰台”条下指出:“按楚郢都非隋唐以后之郢州,此台殆属附会。”且在《陆安府·人物》中不列宋玉之名,而只在《襄阳府·人物》中首举宋玉,并明确说明:“宋玉,楚宜城人。”果断地消除了不足征信的说法,消解了两说并存可能造成的歧义。这是《大清一统志》作者在清人重考据学风影响下,经过翔实的考证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民国版与1990年版《钟祥县志》重提“宋玉郢人”之说,然而所举例证,均无法支持其论点。例如,在论说中,将《水经注》“城南有宋玉宅”改写成“宜城县南有宋玉宅”,企图使其说得以立足。这便犯了偷换概念的常识性错误。郦道元是在叙说秦将白起水灌故宜城的语境中提到宋玉宅的,句前说“其水自新陂入城”,句后说“其水又东出城东注臭池”,因此,其所说的“城”指的是汉代宜城县治所在的宜城故城(即古楚之鄢郢),按郦道元标出的方位,宋玉宅当在宜城故城内南部某个地方,退一步说也应在城外南部近处。若将原文的“城”改成“宜城县”,的确可指其县辖区的南部,假若当时古之钟祥隶属古之宜城,那么也可以指距宜城治所近一百公里之遥的钟祥,但是这样篡改原著实在太不严肃了,如果说得严重些,则是跨出了考据学的学术底线,若不是不懂考据原理与基本方法,那只能是“别有用心”而为之。又如,民国版《钟祥县志》辩称:“当道元时苌寿甫立,其名未著,道元北人,未及深悉,故仍以宜城称之。”此辩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狡辩之词。郦道元虽未用“苌寿”的地名,但使用了“石城”的名称,石城、苌寿均是今钟祥的古称。郦道元按照沔水的流经,在叙说宜城、鄀县而后便说到了石城,“沔水又南经石城西,城因山为固,晋太傅羊祜镇荆州立。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按《水经注》的体例,“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若宋玉为刘宋之苌寿或晋之竟陵即今之钟祥人,郦道元必定要像记述“羊祜”“晋惠帝”一样在“石城”下言之。这与郦道元是否“深悉”“苌寿甫立”毫无关系。更何况郦道元所举今钟祥的古代行政隶属是西晋元康九年(299年),比民国版《钟祥县志》追溯的刘宋泰始六年(470年)还要早171年,岂可妄言“道元北人,未及深悉”。要之,郦道元确认宋玉为宜城人,则不可能在“石城”下提及宋玉事。再如,1990版《钟祥县志》引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并据之说:“这一记述,涉及了宋玉作品与家乡郊郢的密切关系。”其引证,实为断章取义,任意歪曲。《梦溪笔谈》原文为:“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这明明是沈括援引世俗人的说法,以用来供自己批判,因此下文批判说:“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仅止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岂非大误也。”“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以此知,沈括的看法是,郢州不当以“白雪”为楼台命名,理由是:一、郢人“不知歌甚矣”;二、沈括时代即宋代之郢州,不是宋玉作品提及的古楚都之“郢中”。沈括对郢州白雪楼现象的批判,如何能说明“宋玉作品与家乡郊郢的密切关系”呢!若一定要以此来证明,那么就沦落为沈括所批判的世俗人的浅陋和无知。
据此,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宋玉是宜城人,而不是钟祥人。
(二)宋玉到未到过钟祥
宋玉到未到过钟祥呢?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先搞清楚钟祥在先秦时期的称谓。《郢州土风考古记》说:“(郢州)谓之郢,实郊郢焉。”《方舆胜览·郢州·建置沿革》说:“春秋属楚,为郊郢。”《湖广通志·安陆府·沿革表附考》说:“元志郢城在安陆州,乃古之郊郢。”而杜预、孔颖达注《左传》仅说郊郢为楚地,并未坐实其所在何处。所以张正明认为,“这个郊郢,无疑在楚与郧之间,旧说在今钟祥县境,但也可能在今宜城县境。所谓‘郊郢’,看来是个复合的地名,郢是邑名,郊指邑外。”今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对于今钟祥在春秋时期标为郊郢,在战国时期标为竟陵。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又认为“竟陵为春秋楚邑,其地在今湖北钟祥县。”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竟陵)故城在郢州长寿县(今钟祥)南百五十里。”从所引的古今各家之说看,问题比较复杂,尚无定论,但大致情况还是清楚的。今之钟祥,在先秦或称为郊郢,或称为竟陵;而郊郢或竟陵所在的具体地点,或在今钟祥市区,或在今钟祥辖区之内。
有了这个前提,接下来就可以考查在宋玉生活的时代,在秦楚战争中,钟祥地区隶属的变化,从而来判断宋玉到钟祥有无可能。《史记·楚世家》:“(楚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史记·白起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秦昭王)廿七年,攻邓。廿八年,攻(鄢)。廿九年,攻安陆。”《战国策·秦一》:“秦与荆大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综合上面的引文并参考相关之文献,楚与秦的战争得失是: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北纪南城),在夷陵(今湖北宜昌西)烧毁了楚先王的陵墓,又向东攻取了竟陵(今湖北钟祥南)、安陆(今湖北安陆),又向南攻取了洞庭、五渚等江南地区(指位于江南的洞庭湖及其周边小湖泊的沿岸地区)。楚襄王只好向东北退守陈城(今河南淮阳)。楚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在楚国节节退败的形势下,楚襄王不得已与秦王会于襄陵,割让了青阳(今湖南长沙)及其以西的大片国土,才获得了喘息之机。楚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楚襄王才重整旗鼓收复了“淮北之地十二诸侯”和“江旁十五邑”,所谓的“江旁十五邑”,当指汉江下游潜江至武汉段与长江大致平行的江、汉两岸的楚国城邑。此后,楚与秦在军事上对峙了四年,公元前273年,用春申君计“复与秦平”,又于公元前272年,“入太子为质于秦”,才稳定住了局面,得以与秦在江汉平原一东一西隔云梦而治。公元前262年,楚襄王去世,考烈王即位,“纳州(今湖北沔阳)于秦以平”,秦便全部占领了江汉平原,版图拓展至云梦的东部。这就是说,钟祥地区(即古之竟陵、郊郢地区)在公元前278年已被秦攻占。《史记》说秦将白起“遂东至竟陵”,指的就是楚收复“江旁十五邑”后,楚与秦对峙的疆界,亦即秦设南郡的东部边界。
在公元前278年,今之钟祥古之竟陵或郊郢被秦人占领之时,宋玉的情况如何呢?前辈学者游国恩认为宋玉生于公元前296年,陆侃如认为生于公元前290年。按游说,此时宋玉年龄18岁;按陆说,此时宋玉年龄12岁。假定宋玉是钟祥人,在这个年龄之前,宋玉入仕做为文学侍从随王伴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今之钟祥古之竟陵或郊郢被秦人占领之后,宋玉侍于襄王之侧在游赏中作赋助兴,那就更不可能了。就算有这种可能,那还要满足另一个条件,就是古之郊郢或竟陵亦即今之钟祥是否有兰台之宫,这是宋玉《风赋》中明确交代的,也是楚王驻跸游赏的必要条件。若有,则宋玉随王伴驾于古之钟祥尚可能获得一个佐证;若无,则宋玉到古之钟祥就没有了考据学的学理支持。
关于兰台之所在,《史记·楚世家》有“綪缴兰台”句,唐张守节正义曰:“兰台,桓(恒)山之别名。”明董斯张《广博物志》曰:“北岳有五名,一名兰台……。”此非兰台之正解。唐张九龄《阳台山》诗曰:“楚国兹故都,兰台有余址。”认为兰台在楚都城附近的阳台山。宋石才孺《郢州土风考古记》有“兰台避暑之宫”句,认为兰台在宋之郢州今之钟祥。明董说《七国考·楚宫室》曰:“兰台之宫,《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楚世家》‘楚有人谓顷襄王曰:王綪缴兰台,饮马西河’。兰台一名南台,时所谓楚台者也。《湖广志》:楚台山在归州城中。旧传楚襄王建台于此,因名。又杜诗注作云台之宫。”认为兰台在归州城中楚台山。今人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取《七国考》的说法,认为:“兰台即是楚台,楚台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城中,盖山以台为名。”由此可见,问题也颇为复杂,由于名为兰台的地方本有多处,所以究竟哪里是楚宫之兰台,各家对其遗址考实不同。这里只说今钟祥之兰台,虽然其地称兰台“由来已久”“亦千余年”,但要证明这里是古楚国的兰台之宫,既缺乏文献资料的佐证,也缺乏考古发现的支持,仅凭“旧传”立论终显得太过单薄。既然钟祥兰台是否是古楚兰台之宫不能证实,那么对于宋玉在今之钟祥作《风赋》也就不得不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更何况此时的宋玉还不满18岁,甚至不满12岁。因为在宋玉18岁或12岁之时或之后,今之钟祥古之郊郢或竟陵已经是秦国南郡的属邑了,楚王既然去不得,宋玉也就无法随王伴驾去那里了。
至于“郢中”是楚国都城的别称,《春秋大事表》提到的“长驱入郢中”,指的是春秋时的郢,即今湖北宜城南之楚皇城;《史记》提到的“郢中立王”,指的是战国时的郢,即今湖北荆州北之纪南城;宋玉《对楚王问》提到的“歌于郢中”,当指楚襄王迁都后的陈郢,即今河南淮阳,因为宋玉作赋时荆州北之郢都已沦为秦邑。即便今钟祥春秋战国时确实名为郊郢,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不能称之为郢中。至于后世人以“郢中”命名此地,那是后世人的权力,然而进行历史考据,则不能“以今释古”。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说:“昔楚丘之纷纷聚讼,郊郢之讹为郢中,历代之沿革变迁所系非细,岂可以圣人之大经漫曰不求甚解耶!”据此,宋玉记述的唱和《阳春》《白雪》的地方,不可能在古称“郊郢”的今之钟祥。上文在讨论宋沈括《梦溪笔谈》引文问题时,已涉及了这一问题,下面再举一例: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宛委余编五》说:“郢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纪南城,所谓南郢也。《阳春》《白雪》之倡在是矣。今之承天,初为安陆,萧梁、唐、宋为郢州,所谓北郢也。其在楚非都会地,然则郢曲仍当归之江陵,乃为当也。”沈括和王世贞说宋玉提及的“郢中”指江陵,虽与我们的意见不同,但其否定《阳春》《白雪》之唱不当在今之钟祥,则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同。退一万步说,今之钟祥古之郊郢可以称为郢中,但在其被秦人占领之前,谁能相信,一个不满18岁甚或不满12岁的孩子,会被楚襄王称之为“先生”,会遭来“士民众庶”的“不誉之甚”,会写出被《文选》收录、被《文心雕龙》称颂的好文章——《对楚王问》。
据此,古之郊郢或竟陵即今之钟祥在被秦占领后,宋玉不可能到过那里,也不可能如1990版《钟祥县志》所言:“宋玉生前的政治活动在郊郢”抑或“宋玉的文学创作高峰在郊郢。”
三、余论
宋玉既然不是钟祥人,随王伴驾到过钟祥的几率也非常小,那么钟祥涉及宋玉的遗迹与传说就很值得怀疑了。考查古代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宋玉宅、宋玉井、兰台等宋玉的遗迹和白雪楼、阳春亭、阳春台等以宋玉文学创作命名的景观,大多肇起于唐代。这当然与今之钟祥在唐代被定名为郢州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与有唐一代崇尚复古的文学思潮和喜好游赏的文化风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生活在唐之郢州今之钟祥的骚人墨客,以及宦游到此的文人雅士,因此地唐名郢州而自然联想到先秦的楚国郢都,由此地兰台的地名自然联想到在文学创作中提到过兰台的宋玉,于是相关的一系列遗址与景观就被创造出来了,而并不介意历史的真实,或未加深考。这就像苏轼写《赤壁赋》一样,以一篇文章创造了一个为后人激赏的文化景观——东坡赤壁。但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知道,东坡赤壁不是当年“火烧赤壁”的古战场,因而以“文赤壁”和“武赤壁”加以区分;然而今天的人们全然不知,钟祥涉及宋玉的遗址和景观,也是一些文人雅士依据“旧传”用笔墨创造出来的,却未能加以甄别。尽管这些被创造的宋玉遗迹与景观,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宋玉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文化背景没有多大的帮助,甚至会带来些许误导和歧意,但若是从作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研究宋玉,却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文物史料价值。因为就这些遗迹与景观的本身来说,无疑是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物,比如宋玉井就至少是唐代的古井,阳春台就至少是唐代阳春亭的遗址,虽说兰台不一定是楚之兰台之宫,而在那里兴建的兰台书院却是清代早期的古代建筑,还有那些因被创造的宋玉遗迹与景观而题写的诗词歌赋、金石碑刻,也是一笔珍贵的古代区域文化遗产。这些被创造的宋玉遗迹与景观,承载着自唐代伊始,历代钟祥人对于楚国先贤宋玉的由衷景慕与对于战国文学家宋玉的别样情怀,同时也成为了历代宦寓钟祥、赏游钟祥的文人雅士,缅怀宋玉的凭吊场所和观照历史的游览胜地。为此,我们不仅不能轻视这些文物,反而要像对待其他文物一样,珍惜它们,保护它们,从而在当今的时代充分地利用与发挥它们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为此,我们也不必刻意在地志上或宣传上作违悖历史真实的文章,非要把宋玉的户籍落到钟祥,而应该换一种思维,将这些被创造的宋玉遗迹与景观,打造成为像东坡赤壁那样“虽非历史真实却是文化真实”的古代文化景观。
(续完)
参考文献:
[1] 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钟祥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2]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乐 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王象之.舆地纪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 祝 穆.方舆胜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大清一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华地图学社,1975.
[9] 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10] 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1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 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 董斯张.广博物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董 说.七国考·楚宫室[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5]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7] 游国恩.楚辞概论[M].北京:北京学术社,1926.
[18] 陆侃如.宋玉评传[J].小说月报,1927(6月号外):22-25.
[19] 刘 刚.“江旁十五邑”与陈郢至云梦之路[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22-25.
——兰台人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