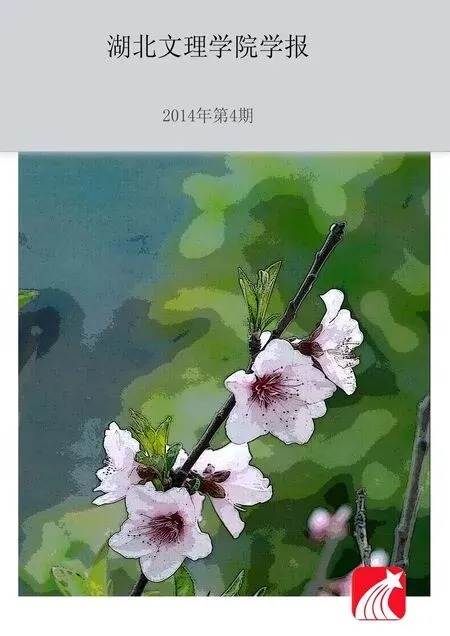价值观视角下的欧盟共同外交政策
——以对华政策为例
李明月
(1.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欧洲一体化是二战以来极具历史意义的世界性事件,其中由1993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确立的欧盟共同安全政策是支撑欧洲一体化的三大支柱之一。由于特定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地缘因素的影响,欧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在国家政治中,“观念因素”可以对行为者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重大影响。[1]在某种程度上,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可以说正是欧洲价值观念的延伸。
一、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由来
欧洲国家对欧洲的安全环境有着共同的认识。他们认为,原东欧苏联的局势是威胁欧洲安全的首要因素,全球化的发展也给世界安全威胁的性质、表现方式带来了新的问题。[2]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处理上述难题,因此欧洲国家必须共同行动,实行共同外交政策,以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
(一)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1958—1970)
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EC Foreign Policy Activity)是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初始形式,产生与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和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苏联的军事发展和部署使欧洲的不安全感日益加深,欧洲也对美国保卫欧洲的决心心存疑虑。这些都使欧洲意识到必须要联合起来,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以保卫欧洲安全。1957年由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署的《罗马条约》明确界定了欧共体的宗旨之一是“通过实行最终包括共同防务政策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3]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大环境和指导思想下孕育了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
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充分保护成员国的海外共同利益,并对世界对欧共体的要求和施加的压力做出回应。[4]这促进了成员国针对共同体以外的外部世界政策和行动的形成。但是,这种外交政策行动从根本上讲是松散的,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外政策。成员国在政治外交领域的合作是非正式的:并没有成文的、得到各方认可的法律来保证实施,也没特定的机构来保证执行。但这却充分证明,欧共体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影响力。
(二)欧洲政治合作机制(1970—1991)
在20世纪70年代,欧共体政治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交政策上的政治合作。欧洲政治合作机制(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是后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雏形。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与是与欧共体六国外长会议1970年10月批准的第一个《达维尼翁报告》直接相连的,该报告为欧洲政治合作建立了政府间的机制。达维尼翁政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政治合作的第二个报告在1973年7月由扩大后的共同体九国外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通过,这就是《哥本哈根报告》。报告强调,凡涉及欧洲利益的问题,在未磋商之前成员国不作最后的决定;并规定共同体“应当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参加到世界事务中去”,“用一个声音说话”。[5]
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建立后,欧共体越来越表现出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这就显示了欧共体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但是这一机制仍旧只是一个磋商和协调的机制,并不能进行决策和采取共同行动。成员国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外交政策,对时局和重大国际事件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只是被动的反应,并没有约束力。
(三)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1992至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的终结不仅使得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而且使欧洲地缘政治环境产生了深刻变化,这客观上为欧盟的发展与合作提供了契机。欧共体在政治和军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无力进一步凸显了推进欧洲政治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992年2月7日,成员国正式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着这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的出台。1997年10月2日,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是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修订,《阿姆斯特丹条约》与1999年5月1日生效。该条约的付诸实施有助于改善欧盟对外部事态变化做出反应的速度,同时也表明了欧盟在政策立场上将尽可能寻求一致。《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共同外交政策上有两大革新:一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政策规划和早期预警小组(PPEWU),以帮助欧盟解决外交上的危机;二是为CFSP设立了一个高级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盟与各成员国之间在外交政策领域合作的连续性和效率。为提高欧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委员会与2006年6月8日发布了名为《世界中的欧洲》的文件,重点探讨了加强欧盟外部行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该文件可以被看作是2005年6月《欧洲宪法条约》批准受挫以来,欧盟对其对外政策行动的一种新的审视,对欧盟今后的对外政策走向有重要的意义。[6]
二、价值观思想与欧盟共同外交政策
从安倍、麻生曾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到默克尔强力推行价值观外交政策,从中国与波兰等国因价值观差异而形成长期冷淡关系到外国政要频繁接见中国异议人士等一系列的外交现象,都揭示着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所推行的、不同层次国际政治角色都参与其中的价值观外交时代的到来。价值观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与国际交往实践中以其国民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诉求为指导而形成的外交方式。[7]在国家政治的演进中,全部的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行为都是一种价值判断与道德选择。西方国家通常以人权、自由与民主等传统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原则,其外交实践行为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
(一)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
在对外关系方面,基督教与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传统有直接关系。这种传统强调欧洲在观念上的“正统性”,在此基础上,论证自己对非正统地区有一种“使命感”。在欧洲历史上,普世主义强调的价值内容有很大变化——从古代的基督教福音,到近代的工业文明,再到现代的自由民主。但是,它在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和“使命感”方面却没有什么变化。“强势文明”一般都带有价值普世主义的色彩,欧洲的特点就是将“普世价值”与对外扩张联系起来。例如,古代带有宗教色彩的十字军东征,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的殖民侵略,到现代在外交的“新干预主义”中强调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可以说,价值普世主义是欧洲价值观外交的基础。
作为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代表,欧盟一直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把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观念视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将是否遵守这些原则作为衡量是非的基本标准。冷战结束后,欧盟更是加大了这种价值普世主义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1991年6月,欧洲理事会在卢森堡通过《人权宣言》,把尊重民主和人权作为欧共体和第三国签订协议的“基本组成部分”;1994年,欧盟在年度预算中增加了“欧洲民主和保护人权倡议”的新内容。如今甚嚣尘上的新帝国主义认为,在后冷战世界秩序的建立中,欧盟没有以往的帝国种族支配与专制,而是试图创建一个可接受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世界。
(二)欧洲的多边主义传统
历史上的种种机缘使得欧洲一直保持均势的状态,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这种长期保持均势的历史,对于塑造欧洲的政治文化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民族国家”、“主权”等观念都是诞生在欧洲,这与欧洲的均势局面是分不开的,在外交领域,“国际体系”的概念也是在实力均衡的欧洲出现的。列强均势的历史决定了欧洲国家外交领域“多边主义”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外交的目的是在纵横捭阖中实现自己的利益,任何国家以强权消灭异己、独占权益的图谋都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
虽然“欧洲一体化”和传统的“欧洲均势”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多边主义的观念却渗透到了共同体的各个方面。欧盟内部的各种行为体,包括成员国政府、共同体各个机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协商、协调、争吵、妥协的制度,在众多“私利”的基础上形成了欧盟的“公利”。作为欧共体第二支柱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式欧洲多边主义传统的真实体现: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外交和安全事务上,成员国在理事会内相互通报和磋商,并在必要时形成“共同立场”;理事会可根据欧洲理事会确定的方针,以全体一致决议在某个外交和安全事务上采取“联合行动”。这种“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正是欧共体成员国基于多边主义立场磋商和协调的结果。
(三)欧洲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欧洲是一个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体,欧洲国家最大的共同性就是认同“欧洲”这个文化归属。欧洲,无论它在现实中何等的不统一、何等的千差万别,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作为一种同源性的文化概念而存在的。[1]77相反,这种共同性的基础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欧洲国家不仅在利益上经常发生冲突,就是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异也很大。事实上,欧洲国家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欧洲的力量所在: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目前世界上仍然存在“英语文化圈”、“法语文化圈”、“西班牙文化圈”的概念,是欧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盟是体现欧洲共同性和差异性相统一的最新阶段。在对外关系的层面上,成员国的共同性体现在对于共同利益的确认方面,所有成员国的政府都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有自己的独立外交,体现了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差异性,例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当成员国国家利益一致时,它们可以倚欧盟自重;当它们的国家利益不一致时,各行其是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冷战后欧盟成员国的外交时间中表现得很鲜明:虽然它们在“用一个声音说话”方面有基本共识,但在实际外交决策中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欧盟更是出现了外交上的分裂。
可见价值观念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十分明显:在它的外交观念中,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主义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在它的外交模式中,还能看到欧洲传统的“均势外交”的影子。但是与此同时,欧盟对外关系的政策框架却是由成员国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共同建构的;既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欧洲外交,也不同于目前成员国外交,是一种全新模式。[1]77
三、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与对华政策
由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和欧盟在价值观上的差别是很大的,这对双方伙伴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双方在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方面存在共识,这就从价值观层面上奠定了中欧伙伴关系发展的基础。
(一)价值普世主义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欧盟作为欧洲国家和欧洲社会的代表,一直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并将这些原则作为衡量是非的道德标准。欧盟的对华政策也是不可避免的受到欧洲普世价值主义的影响。虽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欧关系的深入发展,欧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还是积极的。但是,欧盟始终表示出对中国的“担忧”,认为中国是“非民主的专制国家”。由于价值普世主义作祟,欧盟一直都想要用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来帮助中国转化。在1998年的《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宣称要支持中国向以法制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开放社会转型。2006年的《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中,欧盟也表示要支持中国转型为更加开放和多元社会,促进民主、人权和共同价值建设。
价值普世主义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最主要的就是在人权问题上。中欧分属于两大不同的文明体系,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此中欧对人权的认识存在根本的分歧。欧盟常用西方的人权制度、人权观念来批判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中国则认为自身正在改善。在人权领域,中欧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以人权为幌子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致使欧中关系几乎陷入僵局。2000年,欧洲议会公布了一份议案,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并要求与美国一起在即将召开的第5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反华决议,中国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除此之外,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也是欧盟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因素,而这两个问题又是与上述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首先,中国和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存在观念差异,欧盟主张海峡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武力问题”,暗示反对武力途径,但中国方面坚持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2002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支持台湾作业观察员“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再次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其次,在西藏问题方面,中欧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对当地人权状况的评价、达赖喇嘛的地位等方面。2001年,欧洲议会邀请达赖在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再次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由此可见,欧盟在对华的政策的制定中,总是带有欧洲价值普世主义的色彩,试图在对华政策的调整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虽然不构成欧盟对华政策的主流方面,但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二)多边主义因素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中欧伙伴关系的建立说明,中国和欧盟已经在多边主义方面达成了原则共识。这就确定了未来中欧伙伴关系的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不会针对任何第三方的“排他性”合作,而是双方建立多变主义世界秩序的努力。中欧在多边主义方面达成共识主要表现在欧盟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虽然欧盟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先决条件,但欧盟一致坚持以多边主义解决国际问题,并以建立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己任。中国在几个世界以来都处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谋求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因此,中欧在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不谋而合。从1995年以来,欧盟的对华政策一共经历了六次大调整,每一次都是中欧关系有更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这与中欧在多边主义方面达成的共识是密不可分的。
多边主义是中国与欧盟关于国际新秩序构想中最大的共同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欧盟在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方面是有差别的:中国强调的是一种按照文化多元化原则、由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的国际秩序构建过程,而欧洲则强调一种按照普世价值实施全球治理的世界新秩序。但即便如此,由于欧盟和中国在奉行多边主义原则方面有共同立场,所以双方的合作立场很大。因此,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和欧盟将以多变主义为基础,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发展双方的伙伴关系。
(三)双轨制因素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欧盟的双轨制特性表现在:欧洲国家的共同性决定了欧盟的超国家特性,欧洲国家的差异性保证了欧盟内部的政府间主义。这种双轨制的一方面是作为整体的欧盟。欧盟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经济政治实体,其政治体系架构和运作模式都与主权国家非常相似,欧盟的超国家性质使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具有不同的对外决策机制和对外行为能力。欧盟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就是欧盟整体利益的体现。双轨制的另一方面是作为欧盟成员的各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欧盟内部,各成员国还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成员国的权力让渡有限。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还在发展成型的过程中,而且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还是以“政府间主义”为决策模式的,这就决定了它在对外政策方面很难达成共识与采取共同行动。
从欧盟整体来说,其内部机制的完善和整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可能导致欧盟对华政策的倒退。从欧盟各成员国的角度来说,各成员国对华利益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华亲疏有别。首先,由于受美国影响程度的不同,欧盟各国对华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的态度并不一致。其次,老欧盟国家和中欧等新欧盟国家在经贸问题上对华更是有着明显的分歧。因此,在欧盟对华政策制定与调整中,如何协调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对欧盟对华政策的有效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欧盟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价值观因素的影响下,欧盟实现共同外交政策还有诸多障碍:首先,欧盟对外政策中过度强调欧洲的价值普世主义,时时刻刻都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来要求别国,这势必造成别国的不满,从而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实施造成不利的影响。其次,欧洲国家多边主义传统决定了欧盟共同外交建设中更多的还是遵从政府间主义的思想,很难实现真正的超国家的共同外交政策。第三,欧洲国家的共同性是的成员国大都支持欧盟建设和共同外交政策的建设,但其中的差异性又使得成员国兼顾自身的国家利益,不愿为共同外交政策付出过高的代价,更为重要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异也很难克服。可见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对外,欧盟应该抛弃价值观的偏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努力在与别国的交往中找共识;对内,欧盟始终要加强内部建设,协调成员国与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欧洲人实现其共同外交政策的理想还足有潜力的,只不过他们仍然需要时间,仍需做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周 弘.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刘胜湘.北约新战略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10-111.
[3]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B/OL]. [2014-02-15].http://www.ab.gov.tr/files/ardb/evt/1_avrupa_birligi/1_3_antlasmalar/1_3_1_kurucu_antlasmalar/1957_treaty_establishing_eec.pdf.
[4] ROY H GINSBERG. Foreign Policy Ac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M]. London: Adamantine Press Ltd,1989.
[5]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Identity (Copenhagen, 14 December 1973)[EB/OL] .[2014-02-15].http://www.cvce.eu/viewer/-/content/02798dc9-9c69-4b7d-b2c9-f03a8db7da32/en.
[6] 房乐宪.欧盟强化对外政策行动的新举措及其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7(1):70-76.
[7] 李建华,张永义.价值观外交与国际政治伦理冲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