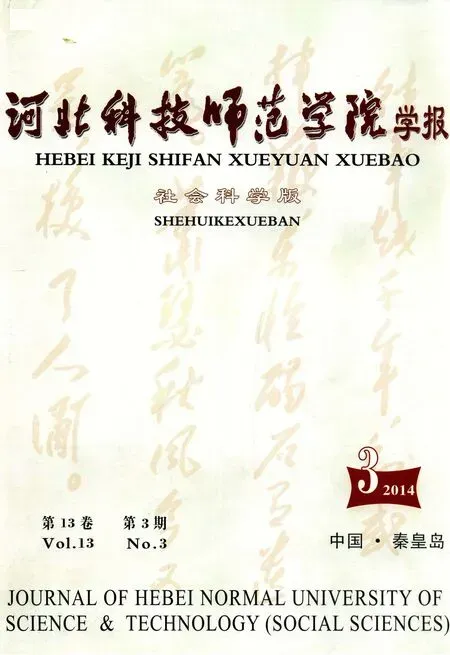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葛 炜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1]2127可见,正是孔子对伯夷的赞颂,才使得伯夷之名流芳后世。而孔子也是对伯夷形象较早进行解读的人,正是孔子对于伯夷形象的初次解读,从而奠定了后世对于伯夷形象解读的基础,这从孟子关于伯夷的有关论述即可看出。关于孔子的思想及言论,大多体现于《论语》中,因此《论语》是考察孔子对于伯夷形象解读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材料。
一、伯夷之“让”
“让”是伯夷身上最显著的一个精神符号,也是其闻名后世的一个重要内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称赞其“末世争利,唯彼争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1]3312,其中所突出的就是“让”字。而对于孔子来说,所看重的也正是伯夷之“让”。虽然在《论语》中孔子并未明确地提及伯夷之“让”,但却处处透露和闪烁着伯夷“让”的精神内涵,也正是“让”字,构筑了孔子对伯夷形象解读的重要基础。
首先,孔子对于伯夷之“让”的看重,是源于孔子本身对于“让”这种品质的看重。据《论语·八佾下》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222而其中的“韶”和“武”,据《四书章句集注》载:“韶,舜乐。武,武王乐。”[3]68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里“韶”和“武”分别指代的就是舜和武王。从中可以看出,舜与武王都达到了“尽美”的程度,但二人相比之下,只有舜进一步达到了“尽善”的程度,而武王却未能“尽善”。对于二者产生区别的原因,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3]68其中,朱熹只是隐隐约约地暗示出了舜较武王胜在“揖逊”上,也就是“让”,但最终还是没有明言,仅仅说出了二者有所不同。但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则直接点出了:“天下万物乐舜继尧,而舜从民受禅,是会合当时之心,故曰尽美也。揖让而代,于事理无恶,故曰尽善也。天下乐武王从民伐纣,是会合当时之心,故曰尽美也。而以臣伐君,于事理不善,故曰未尽善也。”[4]80可见,孔子所看重的正是舜“揖让”而有天下的行为,而伯夷是中国历史上让国的典范,孔子本身对于伯夷“让”这种行为的赞赏,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孔子通过对于“争”的藐视,进而从侧面反映出对“让”的赞赏。据《论语·述而》载:“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2]459若要理解这段话,就必须搞清楚说这段话时的背景。据《左传》载:“夏,卫灵公卒。……乃立辄。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逆者。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5]此事件为公元前492年,卫灵公去世,其孙子辄(出公)即位,而晋国赵简子却将出公之父蒯聩送回卫国,出公辄则发兵攻击蒯聩,这件事实际上就是出公辄与亲生父亲蒯聩争夺君位的过程。在清楚了事件背景之后,那么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这段对话的内涵。在冉有向子贡询问孔子是否会帮助卫国国君辄时,子贡并未直接去问孔子,而是采取一个间接的办法去问。据孔安国所云:“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耶。以让为仁,其有怨乎?”因此从中肯定的是,伯夷是因“让国”闻名,而与之相对的蒯聩与出公辄则是父子争国,正如郑玄在《论语注》中所说:“父子争国,恶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故知不助卫君明矣。”[2]462这就不难看出孔子对父子“争”的厌恶和对伯夷“让”的赞赏。
二、伯夷之“义”
伯夷之“义”是以伯夷之“让”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也是后文中将要说到的伯夷之“仁”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对于伯夷之“义”的表达较于孟子同样晦涩,其主要是通过前文中所列举的子贡与孔子的对话中表现出来的。
正如前文中郑玄在《论语注》中所说:“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2]462,看上去对话所强调的是伯夷之“仁”而非伯夷之“义”。但笔者认为,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前文提到,伯夷之“义”是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因此伯夷之“仁”也就包含了伯夷之“义”的全部内容。故而,对于蒯聩与出公辄父子争国这件事,则应当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
首先,据《中庸》第二十章载:“义者宜也”[3]28,而用“宜”来解释“义”,最早已从西周就开始了,因此在孔子那个时代,“义”作“宜”解,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对于“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3]28,从中不难看出“宜”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而进一步引申,也就是“义”就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而将“义”的含义与孔子的思想相结合之后,就可以将“义”理解为一种合乎天理的行为。但对于天理的内涵是什么,在这里似乎还很模糊。对于此,南宋朱熹在《答何叔京》之二八中说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6]可见“天理”的内涵是广泛的,但也可以肯定的是“天理”是一个包含仁、义、礼、智等一系列内容的概念。
其次,针对于子贡以伯夷、叔齐来比对出公辄、蒯聩这件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3]97在这里笔者认为,“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3]97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尊尊与亲亲的原则,简单说来就是“孝”和“悌”。而“孝”、“悌”正是孔子所宣扬的“礼”的重要表现形式,正如匡亚明所说“仁是礼的内在主导因素,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7]197。因此在这里,伯夷“逊国”不但合乎了“礼”,同时也合乎了“仁”。前文提到,“天理”是一个具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因此单纯地将“天理”理解为“仁”或“礼”都是片面的,但反过来若是合乎“仁”和“礼”的行为,那必然是合乎天理的,故而伯夷的“逊国”行为也必然是合乎天理的。结合前文所说的,“义”是一种合乎天理的行为,因此伯夷这种以“逊国”为表现形式、以“求仁”为最终目的、合乎天理的行为就是“义”。
此外,《论语·季氏》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2]1162从中也可看出孔子对伯夷之“义”的重视。首先,对于“齐景公有马千驷”,据陈祥道的《礼书》载:“齐景公之有马千驷,三千则近于天子十二闲之数,而千驷又过之,是皆僭侈而违礼者也”,正是齐景公违礼的行为,也才有了后面的“民无德而称焉”[2]1163。因此在孔子看来,“礼”是“德”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和潜在内涵,也正如前文中所说“仁是礼的内在主导因素,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7]197,因此这里的“德”与“仁”可以说有着相似的内涵,而违“礼”也就意味着违“仁”和“无德”。而“仁”作为“天理”重要内涵之一,违“仁”自然也就有悖于“天理”,那么齐景公这种行为的不“义”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与齐景公相比,伯夷却有不同的结局,即“民到于今称之”。何以如此?重点就在于其“饿于首阳之下”。而对于伯夷何以会“饿于首阳之下”?正如黄宗羲所说:“夷齐之饿,守义而不食周禄也”[2]1166,“不食周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不食周粟”,而对于不食周粟,孔子与伯夷有着共同的立场,就是认为武王这种以臣子的地位用武力取得天下的行为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武王那种以暴易暴、以臣弑君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样既违背“仁”,也违背了“礼”。因此在孔子眼中,伯夷的不食周粟的行为本身就是“义”。结合前文中齐景公的种种不“义”的行为,与伯夷“守义而不食周粟”相比,这里所突出的伯夷之“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伯夷之“忠”
伯夷之“忠”与伯夷之“义”一样,同样是伯夷之“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文中同样也未被孔子明确提及,只能通过一些侧面去捕捉伯夷之“忠”的内涵。而笔者认为,伯夷之“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伯夷之“忠”应当表现在伯夷对自身的坚守,这从孔子将伯夷列为“逸民”即可看出。据《论语·微子》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2]1279在此,孔子将伯夷列为“逸民”,但“逸民”为何,孔子却并未明言。而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将“逸民”解为“节行超逸也”[2]1283,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将其解为“民中节行超逸不拘于世者也”[4]488,二者都将“逸民”概括为“节行超逸”的人,因此“节行超逸”可以视为逸民的一个重要内涵之一。但显然,“节行超逸”并不能完全地诠释“逸民”这个概念。对于此,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称:“逸民者,无位之称。”[3]185因此不难看出,孔子口中的逸民应当具有两个标准,分别为“节行超逸”和“无位”。显然,伯夷正是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孔子才将伯夷列于“逸民”的范畴之内。何以如此?其一,“无位”,顾名思义,其含义立足于“不仕”,而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已然成为“无位”,因此“无位”应当视为逸民的一个客观条件。其二,“节行超逸”可以视为“逸民”的主观条件,其同样也是“逸民”的重要内涵,夷、齐兄弟让国,其实质是为让贤,因此其“节行超逸”也就不言而喻了。故而孔子将伯夷列为逸民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对于作为“逸民”的伯夷来说,笔者认为,这其中应当包含有孔子对伯夷自身坚守的一种赞赏。正如徐清泉先生在《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一文中所阐释的观点,隐逸应当划分为隐和逸两种境界,“隐”是一种初级境界,而“逸”则是一种高级境界[11]。结合前文就可大致清晰,“隐者”只单纯具备了“无位”这个条件,而不具备“节行超逸”这个条件,但“逸者”则全部具备了上述的两个条件,因此孔子口中所说的“逸民”也就包括“隐者”的全部内容,而伯夷也就顺理成章地具备了隐士的特质。作为隐者,伯夷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如皇侃所云:“夷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其志也;不仕乱朝,是不辱身也”[4]488(对于此,后文中将有集中论述,此处暂不赘述),而这也恰恰是伯夷坚守自身的一个最好说明,也是孔子看重和赞赏的地方。
其次,伯夷之“忠”应当表现为忠于行“义”。前文提到,孔子将伯夷列为“逸民”,而“逸民”则有“节行超逸”和“无位”两个重要内涵。对于“无位”,前文已述,此处不必多言,而对于“节行超逸”,笔者认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亦是对其的一种较好诠释。据《论语·微子》载:“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2]1284,这句话恰恰是前文中将伯夷列为“逸民”原因的一个直接回答。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伯夷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才将其列为“逸民”一类。对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皇侃在《论语义疏》云:“夷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其志也;不仕乱朝,是不辱身也。”[4]488从中可以看出,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夷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其志也。”伯夷之所以会“隐居饿死”,是不食周粟的结果。而不食周粟在孔子看来,则是伯夷对武王用以暴易暴的手段来改朝换代的不满。据《礼记·表记》载:“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8]从中不难看出孔子对“君”的敬畏。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孔子认为武王以臣子的身份、用暴力的手段推翻纣王是一种不符合天理的行为,也就是“不义”的行为。而这,《论语·八佾下》“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222从中即可看出(前文已释,此处不再赘述)对于这种不“义”的行为,伯夷采取了隐居不食周粟以致饿死的对策,从中不难看出伯夷“忠”于行“义”。其二,“不仕乱朝,是不辱身也。”笔者认为,此处的“乱朝”当指纣王统治时期的商王朝,这从《毛诗·大雅·荡篇》中所记载的“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9]即可看出,而此时的商王朝“商纣失道,其奰然恶行,延及中国之外,至于远方诸侯。是当时诸侯,皆化于纣之不善,多党纣而为暴乱大恶,所谓询尔仇方,如虞、芮未质成之先,则争田而讼,此为不义之小者。文王所伐,有犬戎、密须、阮徂、共、耆、邗、孟莒等,皆不义之国”[10],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出于对“义”的执着,最终选择隐居避世,而这也正符合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1068的观点。
综上所述,伯夷之“忠”既有对自身的坚守,也有对忠诚“行义”的执着,而“行义”则是以能够保证坚守自身为前提的。对于伯夷这种“隐居饿死”、“不仕乱朝”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本身也是一种“行义”,并且也正是前文中孔子称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2]1162的真正原因。
四、伯夷之“仁”
伯夷之“仁”是孔子对于伯夷形象内涵的一个最终概括,也是结合伯夷之“让”、“义”、“忠”三大主要内容的一个终极概括。对于伯夷之“仁”,孔子曾给予明确的肯定,这从前文中所述的“求仁得仁”就可以看出。但对于孔子何以认为伯夷已经得到了“仁”,却并未明言,而这也正是理解伯夷之“仁”内涵的重要线索。
首先,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据《论语·述而》载:“(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子贡)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2]462从这段对话中,可以肯定的是,在孔子眼中,伯夷是“古之贤人”,而伯夷能够被称为“贤人”所具备的特质的就是“仁”。对于伯夷获得“仁”的直接原因,那就是不怨,而对于伯夷为何“不怨”,孔子在此并未明言。但据《论语·公冶长》载:“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345在这段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伯夷之所以“不怨”是由于他“不念旧恶”,对于“旧恶”,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说:“此恶字即是怨字。”[2]346“旧恶”也就是“旧怨”。而为何会有“旧怨”?正如何晏在《论语注疏》中引孔安国之说:“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乎。”[2]463在孔子看来,伯夷之“怨”源于让国饿死这件事,而“求仁而得仁”则直接回答了为什么不“怨”这个问题。也正如孔安国在后面所说:“以让为仁,岂有怨乎?”因此,在这里“让”就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次,伯夷之“义”是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如前文所述,伯夷之“仁”几乎包含了伯夷之“义”全部内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义”与“仁”的内涵是重合的,但二者之间仍然略有不同,也就是伯夷之“义”是以“仁”为目的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伯夷之“义”不应当仅仅地理解为一个定义,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行为,一种用生命去践行的行为,因此伯夷之“义”也可以理解为伯夷“行义”,而这个“行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仁”(前文已分析,此处不再赘述),进一步引申,伯夷这个“行义”的过程也是一个“行仁”的过程。
再次,伯夷之“忠”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这是源于伯夷之“忠”是伯夷“行义”的内在动力。如前文所述,伯夷之“忠”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自身的坚守,一方面是“忠”于“行义”。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对于武王取天下的不义,伯夷采取了“饿于首阳之下”的举措,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不食周粟;其二对于纣王无道、殷末争利的现实状况,伯夷采取了“不仕乱朝”的举措,其最终结果依然是“饿于首阳之下”。伯夷“饿于首阳之下”的行为,不仅是对自身的一种坚守,也是一种“行义”之举。而在孔子看来,伯夷“行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仁”,因此伯夷之“忠”不仅是伯夷“行义”的内在动力,更是伯夷致力于“仁”的一个内在动力。
最后,伯夷之“仁”所包含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孔子对于“仁”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在不同的情形下,对“仁”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因此,这也就使得除了“让”、“义”、“忠”这三大主要内容之外,伯夷之“仁”还包含有其他的内涵。据《论语·卫灵公上》载:“志士仁人,无以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1073在这里孔子已将“仁”上升到了生死的高度,正如《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所言:“无求生而害仁,死而后成仁,则志士仁人不爱其身也。”[2]1074可见“仁”与“身”相比,显然“仁”更重要一些。而在孔子看来,伯夷正是这样一个“杀身以成仁”的人。
如前文所述,在孔子看来,伯夷一生都在“行义”,其目标就是致力于“仁”,这正是其“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的真正原因。从表面看,孔子只是说伯夷“饿于首阳之下”,并未言其饿死,因此对于“杀身以成仁”这个行为在伯夷身上似乎是说不通的,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孔子在称赞伯夷“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之前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2]1162为对比的,因此不难看出孔子对于伯夷“饿于首阳之下”论述的一个潜在结果就是死。其次,是前文中所载的:“(子贡)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2]462正如孔安国所言“夷齐让国远去,终于饿死,故问怨乎”[2]462,伯夷以死求“仁”因而不会“怨”。此外,笔者认为,在这里伯夷是否饿死已然不重要,无论其最终是否饿死,其以“仁”为目的的“行义”都将是贯穿伯夷生命始终的内容,而这也正是孔子所看重和赞赏的。
综上所述,从孔子对伯夷的所有评价中不难看出,“仁”是孔子对伯夷的一个全面评价,这从《论语·述而》中的“求仁得仁”[2]462就可看出。虽然孔子对于伯夷的评价仅有寥寥数语,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伯夷之“仁”的精神内涵却是广泛的,也正是这个广泛的“仁”的概念,影响了后世包括孟子在内的众多学者对伯夷形象的解读。
[1]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皇侃.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612.
[6]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885.
[7]匡亚明.孔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16.
[9]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八《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40-641.
[10]焦循.孟子正义·卷六《公孙丑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244.
[11]徐清泉.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J].北京:文学评论,2000(4):125-133.
[12]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谭燕飞,姚蓉.“遗民”三论[J].长沙: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5(1):408-413.
[14]欧阳健.伯夷精神之解读——“伯夷文化论”之二[J].厦门: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6(3):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