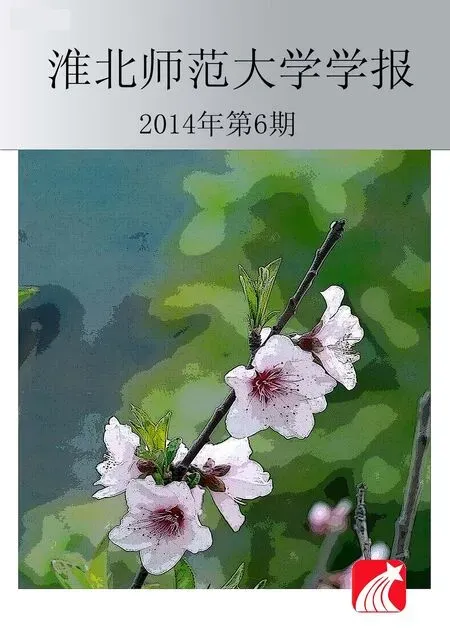由女性主义叙事建构的文本张力
——评《外婆的日用家当》
张晓平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是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结合在一起的跨学科派别。自其创始人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出版《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这一著作,很多评论家看到形式主义批评与意识形态及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相融合的可能性,并着手将叙事文本放入社会历史、性别政治的语境中去拓展内涵,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文学批评开凿了更广阔的空间。
一、女性叙事空间
将话语结构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女性主义叙事作品的特点之一,而文本中男女之间主体性的拉锯争夺是实践颠覆男性权威的第一步。作为20世纪杰出的女性作家,沃克始终极为重视对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女性遭受双重重压,囿困在狭小窒息的生存空间内,完全丧失自我;第二类女性心理上唯一强烈的渴望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第三类是获得自我意识的新黑人女性,她们认为拥有同等的“做自己,及塑造世界的权力”。
《外婆的日用家当》把上述三种形象尽揽其中:麦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就像“一个跛了腿的动物,比如说一只狗,被一个粗心莽撞的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压伤后侧着身子向一个愚昧地对它表示关切的人走去”[1]51。身体上的缺陷和歧视的环境令麦姬绝望窒息,逆来顺受,处处被动,唯一所能及的就是接受“上帝的安排”。麦姬的软弱、自卑和身上累累的疤痕正象征着美国黑人从种族奴隶制沿袭下来的伤痛文化。最后在母亲的帮助下麦姬拥有了百纳被。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的争取(虽为被动)、第一次的胜利,也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步。
然而,迪伊截然不同:“她对任何人都不畏惧。犹豫不决可不是她的本性。”[1]51迪伊在逆境中的自立能力固然值得肯定,她想要寻求自己的社会地位、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但当迪伊试图在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源和白人主流文化之间寻求定位的时候,她内心的天平严重失衡:虽并非期望被白人文化完全同化,迪伊实质却根本不懂得欣赏本民族的文化,仅仅为追赶时髦而保留祖传的手工制品,还冠以“艺术化”的美名。她浅薄的狂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迪伊轻鄙甚至敌视自己的家庭——包括家人和房舍。“她的声音凌驾于我们之上……她严肃地强迫我们听她读书,把我们两人看成傻瓜,刚有点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把我们挥之而去。”“……她对那所房屋恨得要命。”[1]52文本暗示是自私的迪伊焚毁了家人居住的房屋、导致了麦姬身体的缺陷,因为她以之为耻,她轻鄙黑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想要抹煞她的黑人家族史。
真正拥有独立意识的人物当然是叙述者母亲。在小说中,母亲不仅是具有原型意味的形象,而且被模糊了性别,成为父性与母性力量的综合体。“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大块头、大骨架的妇女,有着干男人活儿的粗糙双手。冬天睡觉时我穿着绒布睡衣,白天身穿套头工作衫。我能像男人一样狠狠地宰猪并收拾干净。”[1]50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她的自信、勇敢和能力与男人相比毫不逊色。这样的一个形象是母亲乃至作者挑战自己的性别极限、向传统男性领域突破的象征,是对主流和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颠覆。英国批评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曾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2]。这种神奇夸张的力量及对力量的性别平衡的追求是少数族裔妇女渴望获得个体解放和自我展现的写照。在对待被子的态度上,读者看到了母亲的坚毅,她维护了她谦卑的骄傲。
话语权力是两性权力的集中体现。在小说中,对于男性人物作者只是提到四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伶牙俐齿、妙语连珠”[1]51;迪伊的前男友,与迪伊分手后很快娶了一个很差劲的城市姑娘,她来自于一个愚昧低俗的家庭;迪伊的现男友Ha⁃kim-a-barber,“矮胖”、头发“像一只卷毛的骡子尾巴”[1]54,还极力想做花哨的动作;麦姬的未婚夫,有着“一张诚实的面孔和一口长满了苔藓的牙齿”[1]52。这几位男性角色的出场只起到说明陪衬的作用,建立不了自身的形象,更没有话语权力。
该小说从黑人、女性的双重视角出发,揭示了种族问题和女性生存状态,旨在重塑黑人女性的独立意识和个性以便发扬自己独特的文化。沃克极力铺陈作品中白人及男性人物的无语状态,使之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力,与现实情况中的强势形成强烈反差,增强了艺术效果。总之,在这篇以女性形象为主导的女性色彩浓郁的小说中,男性形象朦胧、地位形同虚设;而小说本身即是女性对自身和他人的自供自述,其女性叙事空间广阔纯粹。
二、表层文本与隐含文本
“相对于隐含文本而言,叙述者意在将表层叙述作为一个突出的公开型文本。隐含文本是一个私下型文本。”[3]
母亲曾说:“我上完小学二年级时,学校关门了。别问我为什么:1927年时有色人种不像现在问这么多问题。”[1]52表面上看,轻描淡写的叙述透露出作为“经验自我”的母亲乃至整个黑人种族早已形成的在强势白人文化面前自卑退让、默然接受的心理。而实际上,作为“叙述自我”的母亲此时“无声胜有声”,用一带而过、漠然处之的态度在受述者与文本之间创造对话。“表面文本”冷漠淡然;“隐含文本”却让受述者清晰看到民权运动高涨时期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
脑缺血炎症反应在缺血性脑损伤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急性期,脑组织缺血缺氧促使炎症细胞激活及小分子炎症介质如炎症细胞因子和半胱氨酰白三烯(cysteinyl leukotrienes,CysLT)上调,导致急性神经炎症和神经元损伤;在亚急性和慢性期,脑缺血炎症导致脑组织胶质细胞增生、神经元凋亡和脑组织萎缩等。这些过程均伴有神经功能的损伤。
叙事者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谦卑的黑人妇女形象。虽然没有非凡的天赋和才能,从祖辈那里学到的劳动技能足以保障她的生活并造就了她坚忍独立的性格和面对文化冲击时坦然坚定的心态。母亲总是提到自己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甚至强调自己天分的种种缺陷:“我自己从未接受过教育。”[1]52“我从来唱不好,总是走调。”[1]53“谁听说过约翰逊家的人士伶牙俐齿?”[1]51然而,整篇小说却充满了叙事者丰富生动的词汇、精妙的句法及一连串能瞬间激发读者联想的意象:
从车子的另一边走下来一个矮胖的男人,他满头的头发都有一英尺长,从下巴颏上垂下来,像一只卷毛的骡子尾巴。我听见麦姬吸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呃”音,就像你路上突然发现一条蛇尾巴在你脚尖前蠕动时发出的声音。“呃”。[1]54
看起来阿萨拉马拉吉姆是想同她握手,但又想把握手的动作做得时髦花哨一点。也许是她不晓得正当的握手规矩。不管怎么说,他很快就放弃同麦姬周旋的努力了。[1]55
从母亲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清楚地觉察到她言语中隐藏的睿智、风采和幽默,绝非普通人所能及。从这一点上讲,母亲直叙的“表面文本”与彰显事实的“隐含文本”构成的差距形成了内文本的张力。
相比之下,迪伊引以为资本的高等教育却有流于表面、矫揉造作之嫌,它并没有增加迪伊远见卓识的能力,使她获得经验和品质上的提升;相反,使其在追逐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迷失在伪风尚的泥潭中。她向母亲索要手工缝制的被子、搅乳棒等等东西并非出于对其珍视的感情,而是肤浅无知地把物质层面的东西当作文化遗产,而摈弃了精神实质。迪伊的名字是照姨妈的名字取的,因而带有家族标志的意味,正因如此遭到她首当其冲的扼杀,更名为“万杰罗·李万里卡·克曼乔”,理由是她不愿再受先辈的“压迫”。实际上,“压迫”她的根本不是家族和种族,而是她思想的狭隘和偏执,她完全遗忘忽视了她的名字所承载的历史和亲情。声称要继承“遗产”的迪伊本质上却是蔑视本体文化传统、随波逐流的代表。
与之相反,被姐姐耀眼的“光芒”完全淹没的普通甚至丑陋的麦姬毅然担负起忠实捍卫家族传统的责任——“不要那些被子我也能记得迪伊外婆。”[1]59被子寄托麦姬对外婆和姨妈的思念,但倘若失去这个寄思之物的物质存在,家族的文化遗产仍会牢牢扎根于麦姬的心里。这句话似有力的宣言,惊穿黑人女性无语的寂寥,打破唯白人文化至上的陈腐。较之以“寻根”标榜自我的迪伊,麦姬才是崇尚传统文化精髓的人,是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我。两姐妹名字的并置也是构成文本张力的一个方面。
三、能指与所指
小说的正标题是一个名词短语——“日用家当”,极其简单明了,是全篇围绕的中心、三个女主人公聚焦的物件,同时对三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意义。
“日用家当”这一说法出自大女儿迪伊之口:“麦姬可不懂这两床被子的价值!她可能愚蠢地把它们只当成日用家当来使用。”[1]59在迪伊的观念里,“日用家当”除了它的“能指”含义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然而,对于母亲和小女儿麦姬,“日用家当”的“所指”广博浩瀚——在历史进程中,被子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它不再只是用来抵御严寒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与女性的生活息息相关,联结着她们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且女性的艺术即聚积于此。“缝制百纳被是黑人妇女生活中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黑人妇女文化传统和黑人女性美学的象征”[4]——“这两床被子是迪伊外婆用一块块小布片拼起来,然后由迪伊姨妈和我两人在前厅的缝被架上缝制成的,其中一床绘的是单星图案,另一床是踏遍群山图案。”[1]58
图案各异的被子是黑人女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不仅如此,它象征着一股凝聚的力量,传承着睿智,保护温暖着一代又一代:
两床被子上都缝有从迪伊外婆五十多年前穿过的衣服上拆下来的布片,还有杰雷尔爷爷的佩兹利窝旋纹花呢衬衣上拆下来的碎布片,还有一小块退了色的蓝布片,大小只相当于一个小火柴盒,那是从依兹拉曾祖父在南北战争时穿的军服上拆下来的。[1]58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中,沃克就把百纳被确认为美国黑人妇女创造性表达的主要形式。她倡言黑人妇女要以之为荣。对于有民族意识和身份定位的人来说,看似微不足道的日用家当早已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第三代的麦姬也“学会了缝被子”。作者意图告诉读者,即便是处于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和重压之下,黑人女性仍在有意识、积极地延续和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她们的创造力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由此,沃克清晰发出沿袭黑人女性优秀传统的声音。
伊莱恩·肖瓦尔指出:“黑人经验”的语境是“个人、社会、制度、历史、宗教和神话的意义融汇在一起的复杂群体,影响到我们作为共有一个传统遗产的黑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5]文中的百纳被无疑象征黑人的文化遗产;迪伊和麦姬关于被子用途的分歧乃至矛盾的激化象征两种文化遗产价值观的冲突;结局母亲捍卫小女儿麦姬的尊严、把被子留给了她表明母亲认同后者的价值观——艺术是用心欣赏和体味的;文化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延续并不断修缮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岿然屹立。小说的深刻文化内涵与标题的简洁瘦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拉开了读者审美接受的距离,更显意味深远、结构层叠。
四、故事层与话语层
“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借助叙事学的结构分类模式探讨女作家倾向于采用的叙事技巧,有根有据地指出某一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具有哪些结构上的特征,采用了哪些具体手法来叙述故事,而不仅仅根据阅读印象来探讨女性写作,使分析更为精确和系统。”[6]
根据热奈特对叙事角度的划分,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这是女性小说惯用的叙事模式,因其在历史文化中的从属地位,女性作家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经验世界。读者透过“我”的眼睛观察世界,获得身临其境的经验和感受。同时,因视角受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角色不知的内容,故而叙事空白为读者的想象和评断留下一定的空间。
“我”对大女儿迪伊有着明显的疏离感。“迪伊”名字首次出现是在小说开始三段之后,在“我”的梦境里。之前的交代作者都是用“她”和“她(麦姬)姐姐”来代替。迪伊的形象对于读者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直至最终令人生厌的过程。然而,读者对其褒扬或贬抑的情绪并非来自叙述声音,因为文本中的叙述声音自始至终都保持平淡、没有波澜。同时作为叙述者与主要角色的母亲既置身其中、又游离其外,没有长篇累牍的评论,只是平静幽默地讲述故事。这样一来,整个故事被置于一个开放的空间去考验读者的思辨能力。处在“故事”层的母亲是主要人物、全家的核心,理智、客观。而处在“话语”层的母亲是一个叙述者。读者通过她来接触故事世界,见她之所见。叙述者制造出很多假象需要读者根据自身经验与语境甄别出事实真相,从而在听取、思考、领悟的过程中获得多层次的审美享受。
叙述者把回顾性视角与同步性视角结合在一起,叙述内容总是过去与现在相交替。故事开头,叙述者以一般将来时“I will wait for her in the yard.”为导入,毫无赘言,直接将读者带入场景,使之获得感知层的聚焦(视觉、听觉等)体验。接着,叙述者以一般现在时加入一段电视节目的画面和她自己的梦境:“Sometimes I dream a dream.”,将读者的阐释期待拉至与梦境相同的高度。然而,与之紧连的是极大的落差:“But that is a mis⁃take”。如此唐兀的急转直下或戛然而止在文中多次反复,使读者跟其穿梭于梦想与现实的悖逆中,由此文本张力自然形成。
作为回顾性视角,叙述者有权利把“我”多年前经历的事件进行总结、筛选。文中叙述者第一次有意识进行回顾的事件是“大火烧跨房屋之事”。两次提及中间仅隔两句看似漫不经心的平铺直叙。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作者选取“叙述自我”而非“经验自我”:“有时候我似乎还能听见燃烧的火焰发出的呼呼的响声,可以感觉到麦姬用手紧紧抓住我,看到她的头发冒烟,她的衣服烧成黑灰一片片脱落的情景。”[1]51读者不由惊叹,有过怎样伤痛记忆的母亲才能对那一幕不流露怨愤。这就是心理层聚焦带来的文本张力。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由于艺术创造力被视为男性的基本特征,女性作家须顺应男性主宰的文学格局,因而她们惯常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思想。文本中她们的声音往往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构成了女性叙事的基本策略。《外婆的日用家当》是一篇采用女性主义叙事的极佳的短篇小说。作品中强烈的黑人女性意识通过相衬的女性叙事策略倾泻出来。关注“故事”和“话语”层相互渗透的女性叙事技巧及其形成的艺术张力,和由此达成的独特审美效果无疑可以丰富文本分析的视角。
[1]Walker,Alice.Everyday Use[M]∥张汉熙.高级英语:第一册.北京:北京外语与教育出版社,2010.
[2]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M].Penguin Classics,2002:63.
[3]Lanser,Susan S.“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J].Style,1986(8).
[4]王雅丽.找寻黑人女性自我:《外婆的日用家当》之“妇女主义”思考[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4).
[5]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45.
[6]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