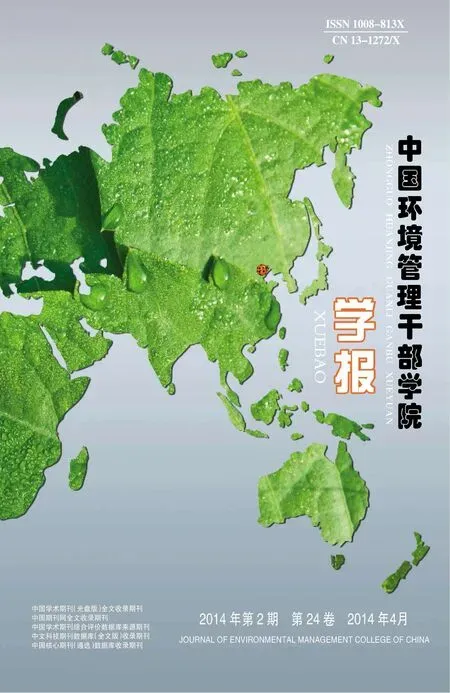危机决策的研究概述
齐 冀,林 平
(1.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01;2.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1 危机决策的界定及特点
近几年作为决策中最难以估算和评定的危机决策,因危机事故频发,已渐渐被国内外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所关注,从而成为了决策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方向与热点。危机决策可视为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等条件下作出判断和迅速行为的过程[1]。从决策的不同分类角度来看,危机决策属于不确定性决策、非例行性决策、非程序化决策。所以不能通过估算概率值得出各种可能会出现的结果,而且危机决策是一种没有固定的解决方法、没有固定的套路可以用来借鉴的决策,这就要求决策者在面对突发的紧急事件时只能随着事态的发展程度,作出与之相对应的选择。总之相较于常规决策,危机决策者可利用的资源和时间均有限,很难在短时间内觉察到危机的来源,进而使个体很难作出理性的决策[2]。
危机决策相较于风险决策的显著特点为:
1.1 时间的紧迫性
危机事件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所变化,需要个体在事发后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地作出相应的决策来避免更严重的负面结果产生。
1.2 潜在的消极性
不管是公共危机决策或是个体危机决策,其潜在的结果都存在一定的消极性,会对组织或个人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造成重大损失。
1.3 资源的有限性
由于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突然性和急剧性,决策过程所能够利用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导致了个体在时间压力下进行决策时限制了对各种资源的获得,因此所考虑到的信息往往都不完备。
1.4 高风险性
因危机事件结果的消极性,个体在对危机事件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风险水平要更高,并且这一风险水平只能预估,不能完全避免。
1.5 高不确定性
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超出人的预想且发生的时间、地点也是不可预知的,而危机决策又无法按照已有的常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判断,危机事件的发展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已有的知识经验可以指导,所以危机决策后果的不确定性极高,很难判断所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
危机决策的特点就是在危机关头决策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对危急情势作出选择,因此决策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危机事件进行逻辑推理和考证,这时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在危机决策中居主导地位[1,3,4]。由危机决策特点可知,危机事件的构成因素有三:第一,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急剧性和突然性[1,4];第二,因人们能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对危机决策有重大的意义[5];第三,危机事态的发展危及决策个体及组织的根本利益且其后果难以预知,所以决策者的决策效能将会直接影响其决策结果[6]。
2 危机决策的影响因素
2.1 情绪对危机决策的影响
基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作用,Mellers等人[7]提出了主观预期愉悦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倾向追求预期的愉悦情绪的最大化。Johnson和Tversky的情绪泛化假说证明了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当给被试呈现诱发负性情绪的信息时,增加了被试对不相关的,却有着相同情绪效价的风险事件发生的感知率;而当给被试呈现诱发积极情绪的信息时,减少了被试对风险事件发生的感知率[8]。Clore和Schwarz[9]提出“情绪信息等价说”,他们认为决策者在作风险决策时并不是根据任务特征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对风险决策明显的情绪反应来决定的。该模型认为,人们从情绪得来的信息是基于所遇到的认知问题而来的,这种从情绪得出的推断是具有易变性和情境性的,使人们更了解当下的环境以及思维加工过程的本质,进而成为决策的基础。Loewenstein等人[10]提出的风险即情绪模型认为决策过程不仅受预期情绪影响,还受即时情绪的影响。即时情绪指的是对感受到风险后立刻产生的内脏反应(如焦虑、害怕、恐惧等),也就是决策时所带有的情绪。该模型正是用于解释为何即时情绪会使得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评估有所偏离,以及情绪是如何决定决策行为的。
基于危机决策的显著特点,在决策过程中情绪不仅对认知资源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同时还对信息加工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与情绪相关的神经科学研究同时发现,情绪不但在人类思维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还能够促使人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和判断[11]。
Joanne等人[12]对个体的危机决策过程研究表明:被试主要对已有非冲突解决方案进行连续的评估来作判断,并且即时情绪对危机决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郑建君对情绪和危机决策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危机决策质量与决策任务难度、性别、情绪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由上述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情绪成为危机决策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成分已经得到大量的相关证明,且其研究正朝着更加深入的领域拓展,探究积极情绪对决策的具体作用机制。Bless等人[13]探讨了积极情绪的加工方式,认为积极情绪导致的自上而下的加工使得人们在认知一件事物的时候首先从头脑中现存的认知结构或偏见出发,进而起到干扰认知过程的作用。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人更容易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途径,会对细节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较少依赖已有的知识结构。有学者提出,积极情绪会让人们认为所处环境是安全的而不去激活大脑中太多的认知资源,也就导致了个体的低水平加工;消极情绪却因其具有强烈的唤醒度和破坏作用,使得个体认真仔细地去想如何来应付问题[14]。
Lee和Stemthal[15]发现,积极情绪不仅不会占用个体的认知处理资源,还会提供额外的资源作为认知补偿。Isen等人发现[16],大部分情况下积极情绪都能提高认知的灵活性,促进问题解决。如在研究决策的过程时发觉积极情绪状态下,决策者较少受与决策材料无关属性信息的影响,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任务上,进而倾向于对决策材料的整合,更有利于决策。
2.2 解释责任对危机决策的影响
Tetlock[17]认为解释责任作为一个情境变量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行为。解释责任是指向他人证明自己决策正当、合理的责任,即解释责任通过利用个体都希望他人认可自己所做的行为的心理来影响个体作决策[18]。Curley,Yates和Abrams[19]的研究指出,当个体发现自己决策时有旁观者会增强决策者的模糊规避。当决策者的决策还要承担他人的责任时,其决策行为会更容易偏向选择规避风险的方式[20]。当个体进行风险决策并需要在他人面前说明自己的合理选择时会选择最容易证明是正确的选项[21]。Simonson和Nye[22]的研究还发现了解释责任能够减少人们的决策偏见。
人们普遍承认,在不明确立场的人面前说明自己所作决策的合理性会诱发出更多的认知努力。Lerner等人[23]通过在不同类型、不同故事情境、不同伤害程度三种维度下对解释责任的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该实验将被试分为有解释责任组和无解释责任组,通过视频诱发出相应的愤怒情绪和中性情绪;而后请被试观看一个虚构的伤害案例,并决定伤害人要受到多严厉的惩罚。结果表明,愤怒情绪条件下无解释责任组的被试几乎全部都简化了认知加工的过程,减少了作决策所需要用到的信息数量,增加了对虚拟案例中伤害人的愤怒情绪,进而加重了对伤害人的惩罚。解释责任组被试却因为解释责任增加了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付出了更多的认知努力,反而降低了对伤害者的惩罚。Wilson等人发现,当决策者可以综合仔细地考虑决策的各个方面时,会减少情感的输入,进而严重影响危机决策的质量。
总而言之,解释责任对决策的作用己被大量研究者证明,即当个体需要向他人解释其决策时,人们的选择常常更为理性。张炜伟[24]指出,相较于无解释责任组,有解释责任组个体的决策时间更长且在愤怒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更倾向于保守。
3 结语
由于近几年灾难频发,危机决策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成为决策研究的一个新的热门方向。危机决策具有后果负面性、不可预知性,时间压力大,信息资源可利用少等主要特征。尽管近几年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但对危机决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研究范式,多集中于对理论框架的研究,实证研究并不多,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方法主要依赖于数学和运筹学。另外,对影响危机决策的因素研究还需在个体变量和心理因素上进一步进行探讨。
[1]BILLINGS R.S.,MILBURN T.W.,SCHAALMAN M.L.A Model of Crisis Perception: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2):300-316.
[2]杨继平,郑建君.情绪对危机决策质量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9,41(6):481-489.
[3]HUY,Q.N.Emotional Capability,Emotional Intelligence,and Radical Chang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2):325-345.
[4]QUINN A.,SCHLENKER B.R.Can accountability Produce independence?Goals as Determinants of the impact of accountability on conformity[J].Personality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2002,28(4):472-483.
[5]SOMMER A.,PEARSON C.M.Antecedents of cre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al crisis:A team-based simul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07,74(8):1234-1251.
[6]KATE S.Crisis Decision Theory:Decisions in the Face of Negative Event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8,134(1):61-76.
[7]MELLERS B.,SCHWARTZ A.,RITOV I.Emotion-Based Choice[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999,128(3):332-345.
[8]JOHNSON K.J.,WAUGH C.E.,FREDRICKSON B.L.Smile to see the forest:Facially expressed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cognition[J].Cognition and Emotion,2010(24):299-321.
[9]Clore G.L.,Schwarz N.,Conway M.Affectiv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J].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1994(l1):323-417.
[10]LOEWENSTEIN G.F.,WEBER E.U.,HSEE C.K.,et al.Risk as Feeling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1,127(2):267-286.
[11]BECHARA A.,DAMASIO H.,TRANEL D.,et al.Deciding Advantageously Before Knowing the Advantageous Strategy[J].Science,1997,275(5304):1293-1295.
[12]JOANNE E.H.,DAVID P.H.,RONALD E.D.Decision Processes during crisis response: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6,18(3):301-302.
[13]BLESS H.,CLORE G.L.,SCHWARZ N.,et al.Mood and the Use of Scripts:Does Happy Mood Make People Really Mindles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1):665-679.
[14]FORGAS J.P.Feeling and doing:Affective Influences on Interpersonal Behavior[J].Psychological Inquiry,2002,13(1):1-28.
[15]LEE A.,STEMTHAL B.The Effects of Positive Mood on Memory[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9(26):115-127.
[16]ISEN A.M.An Influence of Positive Affect on Decision Making in Complex Situations:Theoretical Issueswith Practical Implications[J].JournalofConsumer Psychology,2001,11(2):75-85.
[17]TETLOCK P.E.Accountability:The neglected social context of judgment and choice[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85(7):297-332.
[18]TETLOCK P.E.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ough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3(4):285-292.
[19]CURLEY S.P.,YATES J.F.,ABRAMSR.A.Psychological sourcesofambiguityavoidance[J].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86(38):230-256.
[20]GALLOWAY S.Experienceandmedicaldecision-making in outdoor leaders[J].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2007,30(2):99-116.
[21]SIMONSON I.Choice based on reasons:The case of attraction and compromise effect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9(16):158-174.
[22]SIMONSON I.,NYE P.The effect of accountability on susceptibility to decision errors[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2(51):416-446.
[23]LERNER J.S.,GOLDBERG J.H.,TETLOCK P.E.Sober second thought:The effects of accountability,anger and authoritarianism on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8,24(6):563-574.
[24]张炜伟.情绪、任务自我关联度对危机决策的影响[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