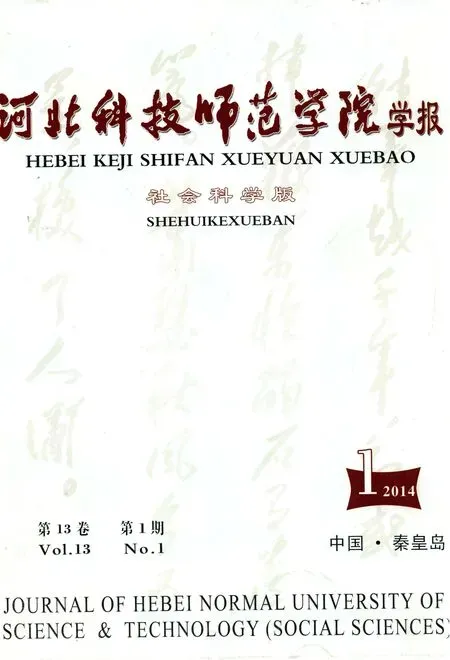论战时比例性原则的适用:要素、标准与价值评判*
崔 森,章 成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法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是国际人道法主要条约的缔约国,对于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1]。而比例性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战时保护平民,避免平民物损害,减轻战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适用中,战时比例性原则存在着不少问题。我国对于比例性原则的理论研究相对较为匮乏,因而正确认识和理解比例性原则对中国处理国际人道法的相关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一、战时比例性原则的含义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作为战争法的三部分,“诉诸战争的权利”、“战时法”和“战后法”虽相对独立,但可能发生联系,适用一个可能对另一个产生影响[2]。而比例性原则在上述三部分中都十分重要。“诉诸战争权”中的比例性原则旨在通过评估某起武装攻击中一方的军事行动是否为其防御所必要,以限制该武装攻击中使用武力的权力[3]711;“战时法”中的比例性原则是指在攻击军事物体时过失地造成平民伤亡、平民物损害等情况时合法与否的问题。“战后法”中的比例性原则旨在实现战后公正且持久的和平,这一努力对民众来讲不能得不偿失[4]。笔者所讨论的比例性原则主要限定在“战时法”,即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人道法范围内,以区别“诉诸战争权”以及“战后法”中的比例性原则。
战时比例性原则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起源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双重效果学说”,本质上是一种使“禁止攻击非战斗员”和“军事活动中合法行为”相一致的方法[3]712。该原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习惯国际法[5]。涉及到该原则的主要国际公约有《1949年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一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一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等。《第一议定书》第51条规定:“如下几类将被视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二)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针对“攻击的预防措施”,随后的第57条第2款规定:“对于攻击,应采取下列预防措施:(一)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应:……3.不决定发动任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二)如果发现目标不是军事目标或是受特殊保护的,或者发现攻击可能附带造成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为过分的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该攻击应予取消或停止。”《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规定:“为了本规约的目的,‘战争罪’是指:……2.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即下列任何一种行为:……(4)蓄意发动攻击,而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中国已于1983年加入了《第一议定书》,中国虽未签署《罗马规约》,但在其筹备与缔约谈判阶段一直积极参与。因此,笔者关于战时比例性原则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第一议定书》和《罗马规约》中的上述规定。
二、战时比例性原则的要素
要素是指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6]。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战时比例性原则主要考察了两个要素:附带损害和军事利益。
(一)附带损害
附带损害是指在打击军事目标时对非军事目标所造成的附带性的损失和伤害。由于附带损害是在打击军事目标时造成的,这便与不分皂白的攻击区别开来:不分皂白的攻击是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或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或使用其效果不能按照要求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因此,在上述每个情形下,都属于无区别地打击军事目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不分皂白的攻击并非直接等同于不符合比例性原则的攻击。不分皂白的攻击是指对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进行未加区分的打击,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将目标限定在军事目标上,而是未对目标的性质加以区分;而不符合比例性原则的攻击是完全针对军事目标所进行的打击,只是由于某些军事行为可能会造成过分的附带损害,如平民伤亡或平民物损害。这种附带损害表明不符合比例性原则的攻击不是直接攻击平民、平民物的行为,后者属于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因此,如何从各种目标中区别何为军事目标、何为非军事目标,是判断一项军事行为是否满足战时比例性原则构成要素的重要前提。
区分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有助于理解各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冲突行为的性质。《第一议定书》第48条规定:“为了保证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尊重和保护,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因此,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应仅以军事目标为对象。”就物体而言,军事目标只限于由于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或失去效用提供了明确军事利益的物体,而民用物体是指所有不是上述所规定的军事目标的物体。战斗员是指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人员,他们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平民是指不属于《日内瓦第三公约》第4条第1款第1、2、3、6项及《第一议定书》第43条所指各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人;如果在平民认定上有怀疑时,这样的人应视为平民;而平民居民包括所有作为平民的人;若在平民居民中存在有不属于“平民”定义范围内的人,并不使该平民居民失去其平民的性质。
这里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第33条的规定,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中的医务人员和随军牧师,并不属于战斗员的性质;其二,《罗马规约》中的比例性原则还具有一项无疑的进步意义,即其环境保护列入到附带损害的考查范围[7]400。
(二)军事利益
“军事利益”这一名词缺乏直接确切的概念进行解释。但根据前文所提到的《第一议定书》中军事目标的概念,“军事利益”和“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常常被联系在一起[8]。而各条约在“军事利益”前添加了诸多限定性用语。如《第一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以及《罗马规约》在此基础上所规定的“具体的和直接的整体”的军事利益。卡塞斯认为,由于添加了“具体和直接”,导致非直接的利益不能添加到与附带损害的对比中。一项利益必须能被预期为攻击的“直接后果”,而不是“随后的发展”[7]399。布斯也认为,使用“具体和直接”包含的意思是“军事利益是具体和可感知的,而不是假定和推测的”[9]。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评注认为,“具体和直接”意在表明所追求的利益应当是“实质性的”和“相对接近的”,与“难以感知的”和“只在长期中显现”的利益相对。而针对《罗马规约》为何要在《第一议定书》的基础之上添加“整体”一词,各方看法不一。卡塞斯认为“整体”一词多少扩大了军事利益的范围,使其重视在考虑时基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军事形势”,而不仅仅是战争发动的特定时刻[7]399。法国在签署《罗马规约》时也做出声明:“军事利益”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攻击中预期到的,而不是从其孤立的或特定的因素中预期[10]。但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认为,添加“整体”一词“必须理解为没有改变现存法律”,把“整体”列入条约中是多此一举[11]。
表面上看,两方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但这种对“整体”一词截然相反的态度并不代表着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存有截然相反的理解。事实上,在当初各国针对《第一议定书》的草案进行协商时,英国、比利时、加拿大、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就表示,“具体和直接”应当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攻击中预期到的,而不仅仅是攻击的孤立或特定部分[12]98。而在后来一些国家在军事手册中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确认[12]99。所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上述说法仅仅应当表示为,“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已经包含了此种意思,没有必要再添加“整体”一词却表达着相同的意思,实属多此一举。从这一角度上看,有关军事利益具体内涵的争论尽管在表面上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出发点实则是一致的。
三、适用战时比例性原则的标准以及有关理论与实践
在完成对战时比例性原则两大要素的考察后,就需要对两种要素进行权衡,考察附带损害在与军事利益相比较时是否过分。但是,这样一个高度抽象性的理论在实践应用时却面临着窘境。首先,适用战时比例性原则时所比较的两个要素在理论上还尚存一些争议,对于何者属于军事目标而可以予以打击,何者属于禁止打击的非军事目标,怎样的军事利益属于战时比例性原则的评估范围,等等。倘若无法在实践中确定战时比例性原则的最基本衡量要素,就无法将此两项要素进行相应的比较:对附带损害做广义理解而对军事利益采狭义解读的话,便很可能导致违反比例性原则的结果,反之,则可能得出符合比例性原则的结论。其次,战时比例性原则在实践中应用的困难还在于:由于比例性原则所要求的评估因素是建立在“预期”的基础之上的,“预期”是人的主观推断,而不同的人的主观看法显然是存在差异的。不仅如此,冲突的形势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而且战争中各方对信息的掌握也同样具有局限性,想要完全肯定地预料到附带损害,完全准确地估量军事利益,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即使附带损害和军事利益能够完全处于预料之中,两者的比较仍然存在无法准确估算的困难:因为所对比的两项要素,一个是具体的损失和伤害,一个是抽象化的利益和优势就像是仙人球和镜框,将两者直接对比和折算的可行性不高。为此,有关学者及国际司法机构均对战时比例性原则的实际适用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具体标准。
(一)演算法标准
弗朗西斯科·弗罗斯特·马丁使用演算的方法,将平民伤亡的具体数量和战斗员伤亡的具体数量进行比较,使得附带损害和军事利益可以进行直接对比。但一些学者并不赞成这样的标准,他们认为采用数值化的伤亡标准会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说规定一个战斗员的攻击若预期到会造成100个平民伤亡,那么该攻击就是过分的。如果预期到的平民伤亡量只有50人的时候就不可能过分吗?这难免有武断任意之嫌[13]。贝克指出,“如果摧毁一座桥梁对于特定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那么相比于摧毁不大重要的军需工厂,为摧毁桥梁而造成的更多的伤亡也是可以容忍的。”[14]34也就是说,以抽象的价值概念作为衡量标准的事物,实际上是很难量化的。不仅如此,还有学者还认为比例性原则不是不能,而是不应当予以量化。汉普森认为比例性原则的标准化会将指挥官的比例性义务将至了最低标准。只要比例性原则保持模糊,一些军事策划者便会更加努力保护平民[15]。
不过哈马杜尔·伊瑟·沙马什认为,虽然规定一座工厂在特定情况下值50或100个平民让人难以接受,但是至少它明确了这座工厂不值得更多的牺牲。比例性原则是唯一能迫使攻击者将平民损失置于最大容许限度之下的方法。所以量化损害标准是可行的,这样可以为权衡军事利益和平民伤亡提供较为客观的指导[14]43。
(二)理性指挥官标准
前南国际刑庭在加利奇案中指出:“为确定一项攻击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则,需要考察一个消息灵通的理性人在实际犯罪者的境遇中——合理使用对他或她可用的信息——是否能预期到攻击造成的过分平民伤亡。”[16]1257而在该段的注释中法院援引了一些国家军事手册中的规定作为适用比例性原则的指导。这些军事手册中也都强调了“理性人”、“合理使用信息”等要素。如上所述,战时比例性原则的考察是基于心理层面,这一标准明确了在预期“过分与否”时需要站在指挥官的角度,从而凸出了指挥官的重要性,同时也体现并加强了战时比例性原则在实际适用时的主观性和模糊性。
测绘技术还涉及到了地理信息系统,其主要是凭借着在空间数据采集、管理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在现今的测量工作中获得了很大规模的应用。而其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可以将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进行科学管理与综合分析,以此来为相关的技术系统提供管理、决策所需的信息,从而有效解决土地工程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保证整个土地测绘工作的有效性,保证城市规划等工作的水平与质量。
(三)个案分析法和累积法标准
在2002年以色列的“防卫盾牌”军事行动中,关于这两种标准的争论就曾出现过。以军在进入杰宁的难民营打击恐怖主义基地时,巴勒斯坦民兵并没有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定,相反,他们还利用以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来进行反制,包括在平民房屋中采取行动,使用人盾等等。该行动指挥官为减少难民营中民众的附带损害,使用的是步兵部队,且在行动后期战事最严重的区域才使用装甲推土机。最后这次军事行动共造成了23名以军士兵死亡。这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真的值得用本国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吗[12]80-81?换句话说,军事利益的评估是基于每一场单独攻击还是基于各攻击所累积起来的整体战略?
很显然,若是基于跨度过长的整体战略进行分析,附带损害和军事利益的考量将会变得愈加任意和不可预测,导致平民的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布朗等也认为,军事利益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于个案进行分析,持同样观点的学者还有加丹、施米特、斯通和科朗吉罗[12]97。但正如上述事例所述,“防卫盾牌”行动的策划者便是依据个案分析法指导其行动,可结果却导致了国内的广泛争议。也正是因为在此事例中,根据累积法将使得被个案分析法所合法化的行动变得不再符合比例性原则。审查北约针对南联盟的轰炸行动的委员会也采纳了“累积法”的观点。在一项有关北约轰炸南联盟电视台和电台的行为不符合比例性原则的指控中,委员会指出,该损害并未明显违反比例性原则……比例性原则并不适用特定的事件,而适用于“平民受害者总体与军事行为目标对比的整体评价”[16]1257。
(四)“针对性杀戮案”的“三条件标准”
2006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关于反酷刑公共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针对性杀戮案)的判决是国际人道法领域内有关军事行动的最引人关注的司法判决之一。巴拉克法官认为,一项军事措施必须符合三个比例性条件:一是,合理联系——所选方法应当合理的导致期望军事目标;二是,最低损害方案——所选方法应尽可能造成最少人道伤害;三是,严格意义上的比例性原则——该军事措施造成的伤害相对于预期军事利益而言应当合理比例[17]13。
巴拉克法官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比例性原则”标准与审查攻击手段的合法性之关联最为密切。但这并未因此而排除另外两项标准的适用。在针对性杀戮案中,最高法院就同时适用了“最低损害方案”和“严格意义上的比例性原则标准”[17]13。
(五)军事必要性标准
1863年美国利伯法典就曾规定:“军事必要性,正如现代文明国家所理解的那样,在于确保战争结束必不可少和根据现代战争法和惯例合法之必要措施。”[18]军事必要性原则使得所有军事行动都要符合这一双重标准:为合法军事目的之完成所必要;未被国际人道法所禁止。
在对比例性原则进行适用时,一些机构和学者以军事必要性原则作为衡量标准。如前南国际刑庭在布拉斯基奇案中就指出,布拉斯基奇将军所下的命令造成了对军事必要性而言所不比例的结果,并且知道许多平民将不可避免的被杀害,其房屋被摧毁。这里法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以军事必要性作为标准,来考察布拉斯基奇将军的行为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则。而弗朗西斯科·弗罗斯特·马丁在阐述了比例性原则应当运用国际人权法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三步标准:首先,只有当实现合法目标别无选择只能使用武力时,针对战斗员或平民的混合目标的攻击才合法;其次,如果使用武力绝对必要,所采用的武力手段或方式也只能造成最小量的可预见的身体或精神痛苦;最后,如果这一使用武力的手段或方法并没有达到其合法目标,那么武力才可逐步升级以实现其目标[13]542。阿布瑞奇也认为应当运用军事必要性原则来判断某一行为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则。他认为“禁止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害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该损害过分的攻击”[19],便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以上几种标准都各有千秋。演算法标准将比例性原则的两个要素数值化,但其在考察时只限于对比平民伤亡和战斗员伤亡,如果将两方的范畴扩大到平民物或环境,很可能变得难以衡量;而理性指挥官标准注重站在指挥官的角度来做主观推测,但这种方法任意性太强;个案分析法标准注重分析每个孤立事件中的比例性原则,却有可能导致整体行动不符合比例性原则;累积法标准注重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比例性原则,但过于宏观是否就意味着难以把握和预测呢?若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标准反而容易导致对比例性原则的违反;而以色列最高法院的三标准更像是对比例性原则的一种强调,而且“一项军事措施要符合比例性原则就……应当合理比例”的逻辑也只是在原地踏步,对理解比例性原则的适用问题未能提供很好的帮助。至于用军事必要性原则来适用比例性原则是否可取的问题,笔者持否定的态度。但由于这两者关系较为复杂,笔者拟将其在下文予以单独讨论。
四、战时比例性原则的价值评判
方案一:“蓄意发动攻击,而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不符合军事必要性原则的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这种方案禁止未被军事必要性原则合法化的攻击,支持此种方案的国家主要有科威特、韩国、泰国、俄罗斯、马其顿、古巴、以色列和智利[10]230。
方案二:“蓄意发动攻击,而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该方案指的是与预期整体军事利益相比过分的附带损害。支持此种方案的国家主要有哥斯达黎加、中国、瑞典、比利时、英国、意大利和伊朗[10]230。
方案三:“蓄意发动攻击,而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方案三或许得到的支持最多,因为它没有任何例外地禁止该类攻击。支持这一方案的国家主要有叙利亚、黎巴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腊、越南、巴林岛、丹麦、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埃及、巴西、瑞士、摩洛哥、土耳其和塞内加尔[10]230。
方案四:直接删去该条[20]。
由此可以看出,前三种方案都以略微不同的内容陈述了比例性原则,第四种方案则是直接删去该条,但在各自描述的战时比例性原则的程度上,前三种方案的文本是有所区别的。就方案三而言,它要求绝对禁止平民伤亡,这一方案被英国批评为过于宽泛而不切实际[10]230。而方案一使用军事必要性原则来判断是否违背比例性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武装冲突对平民人身及平民物损害的合法性,因此相较于方案三更为宽松,只要某一攻击符合国际人道法且对平民或平民物之损害是为实现军事利益所必不可少的话,该损害就不违反比例性原则。但是这一方案并未被采纳,最后得到采纳的是方案二,而方案二才是最终体现在《罗马规约》并源自于《第一议定书》的版本。所以,著名国际刑法学专家威廉·夏巴斯在其论著中有关“比例性原则条款中体现并适用了军事必要性原则”[10]231的提法值得商榷。体现并适用军事必要性原则的方案一并未被采纳,是由于该方案虽然比绝对禁止方案更加现实,但仍然缺乏适用性。为达到军事优势所必要,换句话说就是要将不必要的行为或损害降到最低。前文中所提到的以军“防卫盾牌”行动便是运用军事必要性原则来遵守比例性原则的极端实例。若依据军事必要性原则,便会徒然增加攻击国的负担,并可能最后看似在遵守比例性原则,实则却从另一个角度违反了比例性原则。此外,贯彻军事必要性原则会使指挥官对于遵守比例性原则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为他们须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如何避免对他国的损害——有时这种避免会导致对本国的损害,很难说清楚这种行为究竟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而“过分”方案在军事必要性方案的基础上又适当地减轻了攻击国的比例性义务。只需要其附带损害在与军事利益相比时不明显过分即可。那么,如果附带损害过分得不太明显的话似乎也是符合比例性原则的。
《第一议定书》和《罗马规约》中的“过分”标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过分”与否只是适用比例性原则的衡量标准之一。比例性原则要求的只是在实现军事利益的时候对于平民、平民物还有自然环境的保护。当然,保护的越多自然越好,但这在现实中常常不切实际。因此才会出现如何适用比例性原则的众多方案:若在某起军事行动中适用比例性原则,由于军事行动的进行肯定需要有军事利益的诉求为前提,所以军事利益在这里是一个定量,而附带损害由于是在行动中造成的,具有或然性,所以它是个变量。在变量由零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其与定量的关系也随之不同,导致了如下几类情况:一是,若这里的变量为零的话,那么附带损害便不存在,比例性原则就像上述《罗马规约》草案方案三一样,要求绝对禁止附带性损害;二是,若变量由零增加至等于定量时,那么附带损害便等于了为达到军事利益所必不可少的额度,比例性原则就像方案一那样,要求附带损害符合军事必要性原则。所以零至定量便是尽可能减少附带损害的部分;三是,若变量继续增加,越过定量后稍稍增加了一点,比例性原则就像方案二那样,要求附带损害不能“过分”。适用“过分”标准的妙处就在于它的灵活性,这种意味的口头化表达就是:“我允许你违反军事必要性原则,我允许你造成的附带损害稍稍多于你的军事利益,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你过去了,但你不能得寸进尺,若你太过分,则照样严惩不贷。”《罗马规约》最终敲定的文本扩大了“不明显过分的附带损害量”这一缓冲带。由此可知,战时比例性的价值评判基础立足于与预期整体军事利益相比军事行为所造成的附带损害是否明显过分,随着变量的不断增加,对平民伤亡、平民物损害的容忍度也在不断升高,而现在的国际条约赋予攻击国的比例性义务则呈现出不断减轻的趋势,以使比例性原则能在实际适用中更好地满足军事实践的需要。这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对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而言,战时比例性原则的现实意义即在于其将在必要时为我国处理相关国际人道法问题提供相应的法理依据,特别是在涉台军事斗争问题上(尽管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台湾问题走向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1]112,在军事利益和军事手段之间的权衡把握尤其微妙,极有可能产生在军事利益和平民物附带损害之间应如何求取平衡的战时比例性原则的适用问题。因此,惟有明晰战时比例性原则的现时发展趋势,才能在实践中做到未雨绸缪,使我国在需要运用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实现军事目的与平民权益的协调统一,这既是现代军事实践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国际人道法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即使事实上的武装冲突并未发生,战时比例性原则的完善也有助于全球化时代潜在武装冲突的公平解决。这也能更好地反映全球治理的理念特征:全球治理是民主的治理,即合理地划分国家责任,每一个国家保持与其他每一个国家平等责任的和谐关系[22]4。
结 语
综上言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可以从起因上分析,也可就行为方式探讨。国际人道法的前提之一,便是不考察开战正义,只关注战争行为本身的法律问题,以在战争发生时寻找出如何将平民的伤亡和损失降至最低的有效路径,此即“战争中的正义,而非开战正义”(justice in war,not justice of war)。国际人道法即建立于武装冲突无法避免这一无情的事实基础之上,或者说,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无法避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希望战争的手段和方式尽可能人道。而战时比例性原则的出炉,正是以“武装冲突中的无辜伤亡和损害无法避免,或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无法避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希望因战争而导致的伤亡和损害能尽可能的减少”为前提。生命虽如沧海一粟,但却重若丘山。因此,尽管战时比例性原则的逻辑演绎是令人无奈的,但增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在军事实践中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平民的伤亡和物质损失,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如今既需要在有关人道法国际规则的制定环节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需要在实践中未雨绸缪,在紧跟战时比例性原则的发展趋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该原则的解读,以满足具体应用问题上的实际需要。
[1]朱文奇.国际人道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2.
[2]黄德明,朱路.“战后法”法律建构初探[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7-124.
[3]LAURIE R.BLANK.A New Twist on An Old Story Lawfare and the Mixing of Proportionalities[J].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1(43):707-738.
[4]LARRY MAY.After War Ends: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156.
[5]JEAN-MARIE HENCKAERTS,LOUISE DOSWALD-BECK,CAROLIN ALVERMANN(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97.
[6]夏征农.辞海[M].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99.
[7]ANTONIO CASSESE,PAOLA GAETA,JOHN R.W.D.JONES.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 Commenta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400.
[8]KENNETH WATKIN.Assessing Proportionality:Moral Complexity and Legal Rules[J].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2005(8):3-53.
[9]MICHAEL BOTHE,KARL JOSEF PARTSCH,WALDEMAR A.SOLF.New Rules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Commentary on the Two 1977 Protocols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1949[M].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325-326.
[10]WILLIAM A.SCHABAS.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 Commentary on the Rome Statut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30-231.
[11]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Statement of 8 July 1998 Relating to the Bureau Discussion Paper[Z].UN Doc.A/CONF.183/INF/10:1.
[12]NOAM NEUMAN.Applying the Rule of Proportionality:Force Protection and Cumulative Assess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Morality[J].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2004(7):79-112.
[13]FRANCISCO FORREST MARTI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Humanitarian Law:Treaties,Cases&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536.
[14]HAMUTAL ESTHER SHAMASH.How Much is Too Much?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Jus in Bello Proportionality[J].Israel Defense Forces Law Review,2006(2):1-63.
[15]F.J.HAMPSON.Means and Methods ofWarfare in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in the Gulf War 1990-91 in International and English law[J].Taylor&Francis,1993(1):89、95.
[16]Final Report to the Prosecutor by the Committee Established to Review the NATO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Z].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2000(39):1257.
[17]AMICHAICOHEN,YUVAL SHANY.A Development ofModest Proportions: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Judgmenton the Lawfulness of Targeted Killing[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2007(5):1-15.
[18]NILSMELZER.Targeted Killing or Less HarmfulMeans?—Israel’s High Court Judgmenton Targeted Killing and the Restrictive Function of Military Necessity[J].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2006(9):87-113.
[19]WILLIAM ABRESCH.A Human Rights Law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Chechnya[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5.(16):741-767.
[20]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Z].UN Doc.A/CONF.183/2/Add.1,1998:15-16.
[21]章成,顾兴斌.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及其变迁研究[J].理论导刊,2013(6):106-109,112.
[22]石之瑜,黄琼致,著;李巧丽,杨志军,译.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