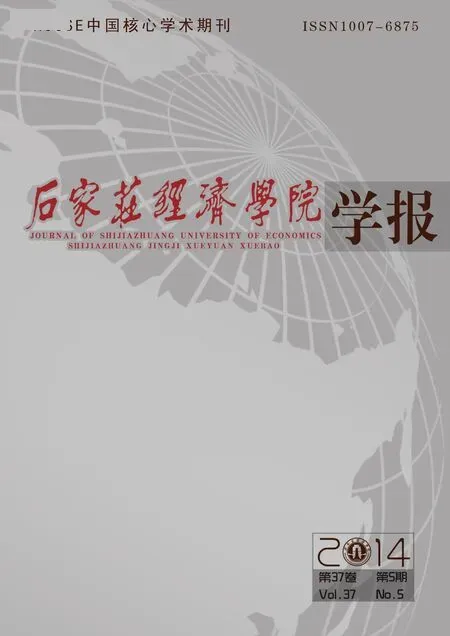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式”“艺术教育”与“灵感说”
孟庆雷,梁智博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柏拉图是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小视的哲学基础,对文艺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徒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成为西方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后又一伟大的哲学尊师,使西方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鼎盛时期。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论发展来看,对比我国魏晋时期文论的发展,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当然又有所不同,“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在我国古代这样一个文学相对自觉,人逐渐觉醒的时代,许多观点值得思考。在认真比较总结之后促进现代文论的发展,并将更多的概念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一、“理式”——构建理想国度的蓝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理式”这一哲学范畴(形而上学),并逐步建立了以“理式”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间的所有物品都是模仿“理式”而来的,“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2],所谓“理式”,是作为事物的典范和标准先验存在的,而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与真理相隔三层。柏拉图是浪漫的,他从自身精神世界出发,构想出一个超乎现实世界的“理想国”的模型,一个国家、一种政治制度,一份精神理想影响着西方哲学体系,新柏拉图学派,黑格尔正是对他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柏拉图看来这个先验的“理式”世界超越于客观世界,他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他完全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勾勒出符合等级制度发展的政治纲领、社会形态,表现出一种文艺性的虚构。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衰落时期,在多年的战争中长大,统治阶级分崩离析,党派间不断的斗争,政治制度混乱无章,善恶不分。因此,他极其强烈地希望建立有序的城邦政治体系。他指出理想的国度应有严谨的社会分工(保卫者和工艺)以满足不同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认为生产者、保卫者和统治者三个社会阶层组成国家结构,三个阶层的人应各司其职,为城邦的建设、正义、和谐作贡献。“城邦就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统治者、辅助者和农民及其他技工组成的共同体”[3]。并指出国家应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正义是最高德行,调节其它三种德行的发展,强调个人正义的重要性,能够对人的理智、激情和欲望进行有效的调节,为整个国家的正义奠定基础,个人便是国家的扩大。他还主张公有制,讨论“真、善、美”,认为“善”是一种最高的理念,这和我们今天在社会文明建设和政治纲领建设领域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证明这一丰富的精神领域设想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他指出“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4]他还十分重视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教育的实践性。
柏拉图为建立理想国,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认为文艺“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5],对于培养正义的人格以及正义的城邦有积极作用,是理想城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古代文论中,儒家学说影响深远,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战争残酷、民不聊生,使得他的思想体系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护合理的等级制度而展开,“仁”“礼”“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性,对社会、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朝不保夕,但文学进入了自觉时期,重视人的觉醒,文论家转向对文学本体论研究,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形式、辞采特点以及作家自身情感的宣泄,如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但陆机的《文赋》对文学的社会性仍具有儒家观点,其书最后写道:“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可见,陆机对文学具有“济文武,宣风声”的政治与社会作用是认同的。历代文人心中都存在着理想国度的蓝图,在战乱时期尤为强烈,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动着文化、社会、国家健康、繁荣地发展。
柏拉图的理想国度在当今世界里仍有积极意义,“理式”世界里是超乎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是由神创造的真理,人们尊重和信仰这份神赋的真理,为之不断地去追寻和实现,形成维护其社会政治制度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种巨大的政治理想一旦成为现实,将对国民的素质的提高,国家制度的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艺术教育”——政治理想
《理想国》的中心思想是塑造人、培育人,维护其社会制度,城邦的利益。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建立,离不开个人德行的培养,“一个人变好还是变坏,这关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受名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乃至于受诗的诱惑,去忽视正义和其他德行”,[6]在个人德行中最重要的是正义性的培养,他指出正义性能够调节人的理智,控制激情,克制欲望。他教育人们“遇到灾祸,最好尽量镇静,不用伤心,因为这类事变是祸是福还不可知,悲哀并无补于事,尘世的人事也值不得看得太严重,而且悲哀对于当前情境迫切需要做的事是有妨碍的”。[7]而且柏拉图更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要求文艺应对人生和国家有效用。他认为,诗人为讨好迎合群众,去摹仿相对容易摹仿的激动情感,也就是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低劣的部分,是对理性的严重摧残,因此他将诗人驱逐出一个政治修明的理想城邦。
关于文学艺术与政治这一话题,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极为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性,巩固其统治阶级地位,认为文艺作品应“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言志”的提出,也是强调从其社会、生活实用功能出发的,朱自清指出:“言志不出于讽与颂。”“讽”与“颂”即是围绕着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方面。魏晋的陆机一再强调“缘情”的同时,也表明了这一“缘情”只是文学发生的一种动机,因情感而作,并有感而发,但并不脱离政治礼义。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五点审美原则:应、和、悲、雅、艳。“雅”充分说明他对诗缘情但却“止乎礼义”的重视。“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他对情感的表达,并非放任不羁,而是处处有所节制,遵从“雅”的规范。可见文艺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应用辩证观点去看待这一话题。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设的关系,在当下则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应采取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不能过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应正视文艺自身发展的独立性、本体性特征,并看到其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影响作用。艺术创作活动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德艺双馨,注重艺术本身开拓创新的同时,也要与政治文明,社会发展相适应。近几年网络流行的梨花体、羊羔体文学盛行,开创了一种新形势的文学模式,但这个问题受到广泛地质疑,文学逐渐趋近通俗甚至低俗,大量迎合广大群众的口味,艺术性降低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有待深刻反思。
三、“灵感”——天地合一
“灵感”问题来源于《伊安篇》,所谓灵感,即诗人的灵感来源于诗神,是一种神明的启示,神力的驱遣,“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8]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诏语,由神凭附,失去理智,达到一种迷狂状态,不可名状,带有感染力,并且能够激发诗人的创造力。柏拉图受到了原始宗教的影响,将灵魂和肉体分离,结合“理式”的概念,即神赋的至高真理,一切事物的抽象典范,认为“理式”普遍的存在于万物与人的灵魂之中,神明将其唤醒,赋予肉体伟大的力量。后世的新柏拉图主义,更为极端的倾向于去贬低肉体、崇尚灵魂,奥古斯丁极为典型,他将柏拉图的心身二元论融入诸多基督教思想,他把肉体与灵魂割裂开来,又把灵魂与他人割裂开,导致了人本身的独特性丧失,对人的社会历史性,人与人之间关系性的忽视。
魏晋时期的陆机对于艺术想象与灵感问题,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创作不是主体的一种机械式过程,《文赋》指出:“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宜之乎斯文。”“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里说明主体由物生情,再用文辞加以描绘,表达意念的整个过程,充满了不可知性,从外在事物到文章内容本身,变化万千,拥有各种可能性,这种构思的过程,充满主体的“想象”,它驰骋于构思的整个阶段。所谓“收视反听”,就是一种排除外界干扰,将全部情感意念高度集中的状态,因为想象,创作主体能够“精骛八级,心游万仞”,去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自由游历于天地万物之间。关于艺术灵感是与艺术想象紧密相连的,陆机强调作文应以想象、灵感为中心。“艺术灵感”,他指出“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其中“应感”指灵感的冲动,而“通塞”即是说灵感的有无,从“应感”到“通塞”的灵感现象,不可知,无法把握,陆机重视灵感问题,认为好的创作应善于抓住某一时机灵感的涌现。最后他更进一步指出灵感的来否,主要取决于“天机”,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人自己不能去把握的。陆机对于文学构思这一阶段所强调的想象、灵感,是充分以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人的心灵为中心,与外界事物相感应,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与柏拉图相比,陆机则强调了主体的更多能动性,自身用心去不断提升,心灵的广阔与强大,最后达到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创造出源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的文艺作品,“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行内,挫万物于笔端”。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 伍彝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陆机.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