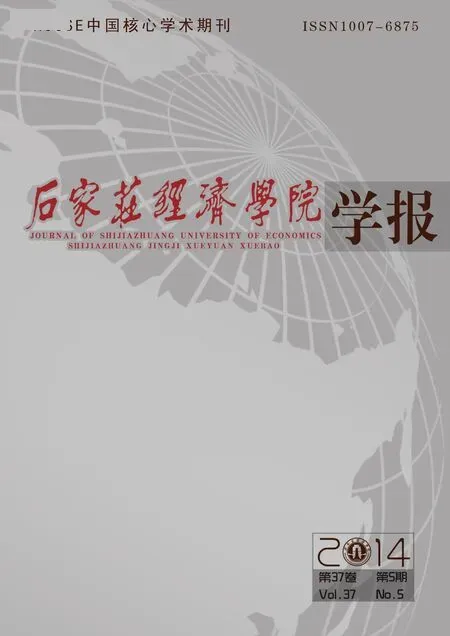中美城市郊区化差异与启示
蔡 静
(大连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新的发展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出现了郊区化,并进入了郊区化阶段。而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阳、大连、广州、天津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才刚刚开始。本文试从美国城市郊区化出发,比较中美郊区化的异同,指出其对中国城乡建设的启示。
一、城市郊区化的概念
城市郊区化(简称郊区化)是指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受到城市膨胀的影响,向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合的近郊地域变化的过程。市中心和建成区的住宅、工厂、学校、办公楼等城市设施外迁和农地转变为住宅地,构成景观上的郊区化;向中心市区通勤者的增加和购物地发生变化等,构成功能上的郊区化。这种定义可理解为广义郊区化。广义郊区化认为只要城市中心区人口(和职能)向城市郊区迁移就是郊区化,它不涉及中心市区是否停滞和衰退。而狭义郊区化概念认为:只有中心市区的人口和功能外迁引起的郊区化,并且这种郊区化导致了中心市区的停滞和衰退,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郊区化。
二、中美城市郊区化差异表现
中国和美国城市郊区化由于作用机制的特殊性,其演化的方式与结果和国外的城市郊区化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无论从宏观背景还是从微观动力方面来考察,这种差异都是巨大的:
1.发生的时间不同
中国的郊区化出现晚,发育不充分,而美国的郊区化出现较早。19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郊区化,不久这一浪潮便席卷整个美国。从此,郊区化生活便成为美国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流文化。若按日本地志研究所编写的《地理学辞典》对郊区化的定义来看,美国的郊区化不仅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及外迁上的景观郊区化,而且也表现为人口、土地利用等功能郊区化。从显形和隐性层面来说,美国都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它既有人口、基础设施等向郊区地域空间的位移和汇集,也有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趋向等观念的渐变。与美国郊区化相比,我国的郊区化充其量只能说处于萌芽期。
郊区按功能可分为主要供消费的住宅型郊区和提供就业的产业型郊区。又因为人们提供住宅而被称为卧城,产业型郊区则被称为卫星城。在美国,由于郊区化发展的程度较高,所以这两种形式的郊区化在美国均普遍存在,特别是美国有专门的纯住宅的卧城。这与美国郊区化首先从居住活动开始,之后才波及产业活动、继而产生经济活动向郊区的扩散,也就是人的居住活动先于或带动经济活动。随着卧城中各种各样的交通、通讯、生活设施等配套发展,它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它俨然扮演中心城的角色,人们的生活空间逐渐被限制在郊区范围内。郊区化中心的复合作用越来越强,它也就更加独立和完善。[1]我国学者柴彦威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郊区核”(Suburban Downtown)[2],孙一飞、马润潮甚至称之为“边缘城市”(Edge City)。[3]总之,美国的郊区化程度较大。而中国没有纯粹的卧城,只有所谓的卫星城。然而,我国卫星城不是像美国因产业外溢以减缓中心城的压力而建,它是被我国政府强行疏散的。中国的郊区化是产业经济活动带动居民的郊迁。由于卫星城生活设施不齐全,实际从市区外迁和疏散出去的人口很少。少数职工仍外来于市郊之间,形成庞大的通勤流。所以说,我国的卫星城并没有起到疏散城市人口和工业企业作用。
2.郊区化的范围不同
根据国情,中国的郊区化是高密度的近郊,而非低密度的远郊。交通技术的发展是郊区化产生的重要前提。它的发展、创新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与之呈正相关关系。交通工具越发达先进,人们的出行距离越大,城市的空间扩展范围越广。据统计,上海市迁往郊区的工业点,距市中心20千米以内的占42%,20千米~40千米的占36%,大于40千米的22%。这种现象在人口方面也有所体现。上海在1982年—1993年,近郊人口净增100多万人,而远郊变化则不大。[4]1994年上海市仓库用地面积约1 20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95%左右分布在郊区,市区不到5%。这说明,我国的郊区化过程总体上是以地理近邻性和交通可达性为前提进行的,我国的郊迁范围大多集中于近郊。与美国相比,我国还处于“准机动化”阶段。交通方式落后,结构单一,居民把地铁、公交和自行车当作通行主力军,其出行速度远远不及快速、便捷的汽车快。而尽管目前我国即将进入汽车化时代,北京、深圳、上海等11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高达464万辆。然而,美国居民在1960年就有69.5%开车上下班,1980年这一比率高达86%之多,因而被誉为“装在车轮上的国家”。从交通设施看,美国拥有极为完善、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以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为肇端,大规模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地建立起来。而我国最大的上海郊区路网密布仅为美国的1/3,这一切都限制了人口向城郊区的大规模流动。美国政府把土地纳入政治化轨道,采用政治机制使土地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对政治家和官僚来说,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可能意味着增加他的选票。因此,在美国各届政府都会政治上、行政上采取相应有力的措施,把土地问题纳入他们的政治议事日程上来。
3.产生的效果不同
(1)美国郊区人口的向下过滤趋向。美国的郊区人口分布态势是美国人富在外,穷在内,显赫与凄凉鲜明可见。居住区位的取向反映了社会集团权力的大小。中国迁往郊区的居民,大多是由于经济条件使然。由于级差地租效应,中心区位地价昂贵,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支付这笔巨款。而政府又缺乏相应的资助政策,所以他们只能到郊外购买便宜的住房。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之故,但这毕竟是小范围、极少数现象。所以说,中国郊区人口成分较为单一,生活水平间的差异也并不悬殊,只有文化和职业构成的差别,而绝没有社会阶层的地域分异和等级序列现象。
(2)美国市郊之间的离散化和中国市郊之间的一体化。中国的市郊和中心城仍然是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是由于中国郊区化发展仍很缓慢,人口外迁强度并不很大,而商业和办公场所的外迁在很长时间内仍不会太快。其次,将内城中污染重、占地大的工、企业迁出市中心,使生产要素从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流动。这样,中心城与郊区之间进行了一次存量调整,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再次,中国的各大城市市政府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它们由于其特殊的中心地位,所以必将是政府优先扶持和资助的对象。因此,政府会把大量投资用于旧城的改造和繁荣城市方面。这样,中心区的商贸、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职能不但没有减退,相反却更加繁荣。
(3)美国郊区出现特殊的“巴尔干化”现象。由于政体原因,美国的行政管理是各自独立为政的,城市间、城镇间、城乡间均没有上下行政隶属关系。随着美国郊区力量的增强,它的独立倾向就越来越大。这样,郊区逐渐摆脱了城市的管制形成了无数的小政治单元。这种“巴尔干化”式的政治单元,使得都市政府无法协调各地方政府,无法集合所有财源去建构地方政府的各种服务设施,因而不利于统一的城市规划。这也是美国中心城衰败、郊区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中国一直存在着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各级政府之间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市管县、镇带乡。一般来说,城市是由市区、郊区、农村地区组成的聚集区。每个市政府都管辖着其所属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事务。郊区当然也要受市政府的统一管理。所以,中国绝没有美国的“各扫门前雪”的现象,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中心城与郊区之间的互相协调、互为扶持。就此而言,我国的城市政策有利于城市的通盘规划、宏观调控,有利于缩短城乡差距。尽管也会造成一言堂局面的出现,但它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定、科学的政策。因而,中国的中心城与郊区仍然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5]
(4)中国的CBD结构混杂,职、住、商功能混合。尤以居住为主要功能,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商务功能。城市如同生命有机体,它需有一个中枢系统指挥和控制着整个躯体,这个躯体就是城市中心商务区CBD。中心区的确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中地和制高点,但我国的大多数城市中心区与周围住宅区没有明显的界限,并呈明显的组团式发展。1995年调查显示,扬州市、连云港市的中心区居住地所占比重分别为39.2%、37%强。美国城市中心区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次CBD。据1950年美国大中城市CBD内部结构调查,办公和商店占56%,住宅占22%,这说明美国中心区职能是以行政办公、商业、金融、教育等设施为主,居住功能只占一定的地位。
三、中美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比较
根据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组织结构发展变化的原理及美国大都市区形成的历史经验,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也将是大都市区化,它也将受到共生、竞争关系演化规律的支配。但受国情制约(包括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表现出来的特点既有与美国相同之处,更折射出其自身的特点:
1.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看,中国人从未有过反城市的传统
中国是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其主要特征。大多数人世代以农为本,他们大多生活在因袭陈规、停滞不前的村社集体,一直过着乡村生活。经过世代繁衍,便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农村生活形象:闭塞、愚昧、贫穷。然而城市则是另一种情形,它是“大小富翁们的殿堂,工商发达,文化繁荣,生活便利,对各色人都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天然即存在经济位差,而且这种位差将随着城市的勃兴越来越大。无形中,在户籍、就业、住房、上学等方面便形成了两种社会形态和两大利益集团。受利益趋高机制以及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巨大的“拉力”影响,饱尝田耕之苦、单调无味生活的“食力之民”,便趋之若鹜于城市。他们只有在城市才能获得最高的生活水准和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这对于经济尚不发达、有着浓厚农本观念的国度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所以,中国人对都市文明大多是赞誉褒扬之辞、羡慕向往之情。“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便是真实写照。中国人从未有过反城市的传统以及对乡村生活的向往。而美国人对城市化持有矛盾的态度。
2.中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美国人先天具有锲而不舍、勇于冒险的精神。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流动社会。而中国人则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宁愿固守破旧的家园,也不愿迁往富饶的地带。明清之际迫于生活压力而迁往海外的人通常被蔑为“贱民”。这种观念在现代中国人心中仍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如此。因此,在没有外在力量的驱使下,中国人还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愿意冒险去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对于美国人来说,郊区意味着是一片尚未开垦的丰富宝藏,但对中国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片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荒野。
3.政府决策行为和政策法规的差异
从政府的决策行为和政策法规看,虽然中美两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对于郊区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土地和住宅政策却实行截然相反的两种制度。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推动郊区化发展的政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土地一直归国家所有,实行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这种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土地属公有、政府可干预且无市场机制。因而,许多城市中对土地的多占少用、占而不用、优地劣用等现象大量存在。土地原本是稀有资源,但却长期得不到优化配置,所以根本无经济效益可言。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渐趋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家实施这种制度,就可以按土地的用途、数量、使用年限、建筑容积率等条件引进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原则,按协议、招标、拍卖等形式,进行土地转让导致了两个根本性变革:一是可以自由转让、出让土地。想买就买,想卖就卖。二是可以利用竞争手段出让或取得土地。谁价位高,谁区位就好。竞争的结果是,效益最高的金融业、服务业、信息业栖息于市中心有利位置,而宽广、价低的郊区则成为工厂、企业之用地。当然,对那些利润颇丰且完全能负担得起高地租成本支出但却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则给予适当的行政制裁和经济赔偿。这种政策的实行,达到了地尽其利,大大促进了郊区化的产生。
住房政策与美国也大有不同。中国住房建设由国家统一投资建设,由各单位根据各自情况以福利的原则分配给居民长期居住。有时,只收取少量的象征性租金。住房不能转租,更无权买卖。在城市里,虽然也存在着少量私房,一般也不允许进入市场流转。在这种制度下,房主根本没有自主性可言,更何谈房地产公司的大力投资。但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现,房地产事业也日益成为热点。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房地产商均很重视这一事业。从市场的双方来看,房地产公司竞相投资、纷纷承办龙头项目。而另一方面,群众福利分房的观念已发生了改变。个人购房、集资、合资购房的比重逐年上升。在北京,为鼓励现有租户搬迁至较便宜的郊区,改建公司也正在实验价格与面积上的刺激做法。想在郊区中买单元的住户将支付较低的价格,如果想继续长期租用住房,则要求通过支付更多的租金或付租金押金来支付全部的维护费用。
通过中美郊区化几个层面的比较,我们至少得出以下结论:
1.郊区化是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依照马斯洛需求等级学说,人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后,才能追求更高的目标。中国经济尚不发达,故将经济利益作为最高需求,表现在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的物质生活;美国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愈向纵深化发展,人们就愈加考虑个人取向和精神生活层面,他们更青睐于乡村生活的质朴、恬静和清新。
2.中国郊区化虽有方兴未艾之势,但现代都市文明已内化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崇尚的深层心理,这成为中国郊区化发展的深层文化障碍。
3.郊区化的实质不仅表现为人和物向郊区的简单“物理位移”,更重要的是,城市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向郊区的渗透和郊区功能的嬗变,希冀达成城市与郊区间的一体化。
4.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这里固然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差异,但也有政府政策行为这一“看的见的手”的牵制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优势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争取早日实现郊区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陈强.美国小城镇的特点和启示[J].学术界,2000(2):259-264.
〔2〕 柴彦威.郊区化及其研究[J].经济地理,1995(6):48-51.
〔3〕 孙一飞,马润潮.边缘城市:美国城市发展的新趋势[J].国外城市规划,1997 (4):25-35.
〔4〕 陆希刚.上海城市郊区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5:11-27.
〔5〕 曹邦宇,姚洋洋.美国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3(8):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