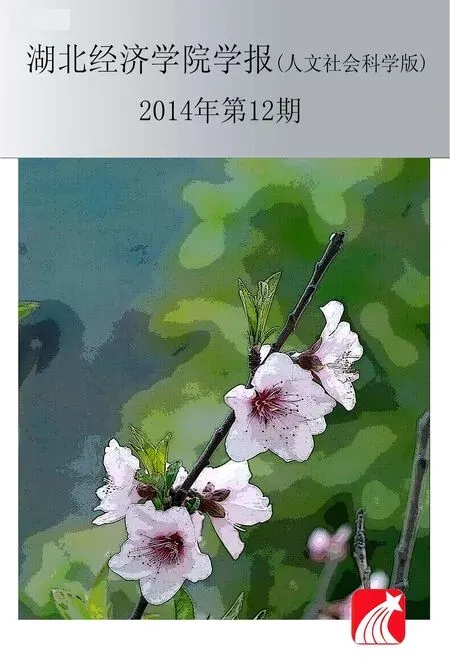景物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
——试论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
马静雯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景物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
——试论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
马静雯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樋口一叶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代表作《青梅竹马》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讲述了少年少女之间一段朦朦胧胧却注定没有结果的美丽爱情故事。一叶在小说中对季节、天气、环境、事物等细处的描写,看似只是对景、物的描写,却与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命运密切相关。现拟从《青梅竹马》中对景、物的描写出发,对景物描写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以及对小说情节发展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发掘细微之处蕴含的寓意。
樋口一叶;《青梅竹马》;景物描写;人物形象塑造
樋口一叶,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女作家,被誉为“明治紫式部”。《青梅竹马》是其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小说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讲述了少年少年之间一段朦朦胧胧却注定没有结果的美丽爱情故事,作者对细处的描写也暗示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本文拟从《青梅竹马》中对景、物的描写出发,对景物描写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以及对小说情节发展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发掘细微之处蕴含的寓意。
一、引言
一叶留在世上的作品虽不多,但是每一篇都精巧优美,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她生命最后的“奇迹的十四个月”(1894年12月~1896年2月)里,更是留下了历久弥新的《青梅竹马》、《十三夜》等杰出作品。其中,《青梅竹马》可以说是一叶最为著名、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了。《青梅竹马》以东京下町的大音寺为舞台,以妓女15岁的妹妹美登利的幼年生活为中心,以戏班头之子长吉与高利贷之孙正太郎之间的矛盾和美登利与僧人之子信如之间朦胧的爱恋为主线,描写了生活在贫民区附近的一群孩子受到混浊社会环境的残害和腐蚀而最终不得不对现实妥协的凄惨命运。作者冷静关注的目光、尖锐的笔锋、快速变化的叙事角度、以景寓情的描写,使得这部小说在淡淡的悲伤下,隐藏着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抗争。
对《青梅竹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有从作品出发研究作者思想、世界观、价值观的,有研究作品的意义、价值的,也有纯粹对作品进行研究的。
首先,看一下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桥本威(1988)对作品名字与《伊势物语》的关系以及作品名字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探讨。重村惠子(1991)通过对作品中的某些句子进行分析,得出了读者的想象力是故事发生的重要因素,而直到故事结束后仍能给读者留下思考品味的时间这种叙述方法,则形成了有余韵的 《青梅竹马》的世界这一结论。北川秋雄(1993)则通过对小说结尾出现的纸水仙花进行分析,结合小说内容和作者生平对作者的佛教观进行了探讨。荻原佳子(2007)对作品的语言、文体、叙事方法、视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爱知峰子(1997)从一叶与和歌文学的关系出发,对作品的构成以及作品中的季节、雨等事物进行了分析。另外,和田芳惠、前田爱、关良一、盐田良平等研究樋口一叶的大家们也出版了许多著作,例如和田芳惠的《一叶的日记》(筑摩书房、1956),关良一的《樋口一叶——考証与试论》(有精堂、1970),前田爱的《孩子们的时间——<青梅竹马>试论》(展望、1975),盐田良平的《评释青梅竹马·浊流》(山田书院、1958)等。
中国方面,对樋口一叶的研究虽尚不成熟,但是近几年对樋口一叶的研究则在逐渐升温。肖霞(2005)指出,《青梅竹马》是樋口一叶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成功示例。其作品有“‘形而上’的浪漫主义恋爱观”[1]和“私小说性”。[2]章毅(2005)将小说与一叶的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进行了分析论述。王蓉在(2010)分析了作品中出现的少年少女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主人公的恋爱关系以及小说中家长的为利所驱的形象,体现了一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张雅君(2011)则通过对《青梅竹马》的内容进行分析,阐述了当时日本社会女性的生活现状,并认为樋口一叶“不是强势的女权主义者,而是女性的理解者、关注者”。[3]石玉芳(2011)从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创作风格、诗化的语言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解读。杨佳嘉(2012)对小说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李慧(2012)指出了小说的四个特点。庞在玲(2012)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修辞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刘依哲(2013),对作品中的“物哀”以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论述。王漫(2013)对作品中的男主角信如的生存方式和作品中对拜金主义的批判等进行了分析论述。
本文只列举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有本文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鉴于篇幅有限,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就以上所列论文来看,日本方面的学者对《青梅竹马》的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广泛,从小说的题目、结构、语言以及社会意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对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有涉及;中国方面,多是对小说的作家、主题思想、风格等的论述,鲜有对作品本身魅力的分析,对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也较少。虽然其中也有对小说中景、物的分析,但基本上都是从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因此,对小说全文的景、物描写分析以及其与作品情节、人物关系等的分析尚有很大的可研究空间。
二、环境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
樋口一叶出生于1872年,不到25岁就因病去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家道中落、少年丧父、情感受挫等人生悲剧,一叶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尤其是一叶在迫于生活的无奈不得不搬到贫民区居住的九个月中,对那些社会底层民众的困苦有了非常深切的体会。而在搬到贫民区居住之前,一叶的小说始终无法摆脱当时女作家特有的脂粉气,词藻华丽却缺少内涵。贫民区里那些一旦长大后就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必须卖身的女孩们,那些对丈夫言听计从不能反抗的妇女们,那些每天为了解决家人温饱问题来回奔波的下层苦力,那些所谓的贵族人士身后的黑暗、丑陋,使一叶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她的文体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浓妆艳抹的冗词赘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洁有力的真情实感。可以说,贫民区的体验是一叶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一叶所居住的贫民区是离日本著名的烟花巷“吉原”不太远的街区,也是其小说《青梅竹马》中故事背景的原型。一叶在《青梅竹马》中,将一个弥漫着淡淡哀伤的美丽爱情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语言简洁明了却不失文雅。小说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品味感悟的地方,其中作者对周围环境、景物的描写,就在细微之处隐含着深刻的寓意,以景寓情,引人深思。
小说开头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舞台——“吉原”的景象。
绕过大街,便是回望柳林立、通往大门的道路。黑歯沟旁,(吉原的大茶楼上)灯火通明,三层楼上的喧嚣仿佛就在耳旁回响般清晰可闻。街道上的人力车不分昼夜来来往往,可见其生意是何等得兴隆。住在附近的人们曾说过,大音寺前这名字虽充满了佛家味道,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转过三岛神社的拐角,眼前所见尽是房檐倾斜的大杂院,有十户、二十户左右,并无像样的高楼。这里的生意惨淡,半掩着的木板套窗外,放着剪裁形状奇怪的纸张,上面胡乱地涂抹着白胡粉,犹如彩色的田乐豆腐块,纸背上粘的竹签也形状古怪。(一)(123-124)
将花柳街的景象描写作为小说的开头,喧嚣淫靡的环境使得整个小说都笼上了一层黑色的阴影。作者在描述吉原的妓院生意兴隆时,使用了褒义词“全盛(极兴盛)”,这其中饱含了作者对妓院老板、往来寻欢作乐的客人们的讽刺以及对那些为了生存不得不强颜欢笑的妓女们的深切同情。附近的住户使用“大音寺前”来指代吉原,也有一定的寓意。说到寺庙,就有佛家味道,给人一种清心寡欲的感觉,是一种圣洁的存在。但是在大音寺的前面,却是淫靡的花街柳巷,与寺庙相比,这里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低俗的地方。“圣洁”与“低俗”相依存在又相互对立,其实也是僧人之子藤本信如与名妓的妹妹美登利之间那段朦胧爱恋的象征,即使再亲近也不可能混为一体。这篇小说写作之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的初期,改革的浪潮还未波及这里,这里依旧持续着封建落后的生活方式,贫民区低矮的房屋、脏乱的环境,但是,正如爱知峰子在《樋口一叶——<青梅竹马>的季节和雨》中所说,“这种生活方式,也染上了吉原独特的风俗,散发着不健全的气息。这并不值得赞美。但是,反过来说,这里没有伪善的面具,有的却是让人感到‘朝气蓬勃’的感觉。”[4]“通过描写大音寺前住民的有趣生活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样在深入到物语世界时,也明示了一个可怜少女的命运故事的开始。 ”。[5]
小说在第六部分中,提到了高利贷之孙正太郎家里的景象。
走进幽静的折叠门,里面的庭院虽不太宽敞,却摆着许多盆栽,别有一番情趣。房檐下吊着一盆飞蛾草,那一定是正太郎在午日夜市上买来的。(六)(143)
正太郎家算是这街道上首屈一指的富户,按理说家里的庭院应该也会很大很宽敞,实则不然。但是后面说到这院子只有祖孙二人居住的时候,本不宽敞的院子就让人觉得莫名地有些冷清。正太郎的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因是入赘女婿,也在他母亲死后离开了这里,只剩下了祖孙二人。正太郎的姥姥在小说勾画的男权社会里,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虽然是靠放高利贷赚钱,被人说成守财奴,但是作者借孙儿正太郎之口,用大篇幅来解释姥姥的行为全是为了他、为了养家,第四部分三五郎也曾表示过,如果没有正太郎家借贷的款子,一家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正太郎在冬日的夜晚“在田町附近挨家收利息”(六)(144),可见这一带靠正太郎家的贷款过活的住户不在少数。与那些到花街寻欢作乐的有钱人、为了钱财不惜出卖自己女儿身体的父母们相比,正太郎的姥姥反而让人不觉得讨厌了。正太郎的姥姥虽为女人却是一家之主,虽是高利贷的施放者却在一定意义上养活了贫民街道上的很多人。然而在那个男女还不平等、男权主义仍旧占据上风的年代,一叶在创作时也多少顾忌到了当时文坛的环境,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但是从她所塑造的正太郎的姥姥身上,仍可以隐约感觉到一叶对男女平等社会的向往、对男权主义的抗争。
三、景物描写与小说主题生成
小说对季节和天气的描写对小说情节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和预言的作用。
凉风习习的夏日傍晚(五)(137)
清晨的凉爽不知不觉已经消退,太阳的热气则开始不断袭来。 (六)(146)
四月末,樱花凋谢,已是在绿叶荫下观赏紫藤花的时节(七)(146)
凄寂的夜晚,绵绵的秋雨忽然变得猛烈起来。(十)(162)
从昨天开始下起了(初冬)阵雨。(十二)(167)
一个降霜的早晨(十六)(183)
从第五部分“凉风习习的夏日傍晚”,到小说结尾“一个降霜的早晨”,作者仅仅讲述了8月20日千束神社的夏祭到11月份大岛神社的酉市之间短短三个多月间的事情,中间第七部分插叙了一些春天发生的事。春天,信如和美登利发现对彼此的在乎和朦朦胧胧的爱恋;夏夜,胡同街的长吉借信如的名义与三五郎、美登利等人发生争执,信如和美登利之间产生了隔阂;下着秋雨的夜晚,本要去笔店避雨的信如,听到店里美登利的声音掉头而去,美登利只能久久地望着信如背影。从这里开始,小说就进入了高潮。
第十二部分又有一段对雨天的描写,但是此时的雨则是“時雨”,在日本的和歌中,“時雨”指的是秋末冬初的阵雨,可见此时已经到了初冬时节。信如在去给姐姐送衣服的途中,经过美登利居住的大黑屋时,大风吹走了雨伞,大雨打湿了包裹,木屐的趾袢也脱落了,美登利恰巧看到了这些,但是两人之间仍有芥蒂,美登利只能将手中的红色友禅布条从门缝里扔了过去。
落在脚边的红色友禅布条浸湿在雨水里,红叶的图案却依然艳丽清晰。(十三)(172)
红色友禅布条被孤零零地留在格栅门外的地面上。(十三)(173)
在这里,“红绸条象征着美登利抛给信如的爱情信息”,[6]信如“惆怅地凝视着那布条,心中感到一阵酸楚”(十三)(172),却终究没有捡起来。对于美登利的主动,信如选择了逃避,他没有勇气面对众人的嘲笑,而他与美登利之间的爱恋也葬送在了这个狂风暴雨的夜里。“雨象征着大人的世界,绝不是什么明亮的东西,而是暗示着黑暗残酷的现实。很遗憾,美登利与信如之间萌生的爱恋,与分别时一起结束了。”[7]
小说结尾的时候,已经真正进入到冬天了(霜降一般发生在0摄氏度以下)。
正街上,灯火熄灭,冷冷清清。(十六)(183)
这里一反常态,与小说开头的灯火通明、茶楼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结尾蒙上了一层凄寂的色彩。小说到这里,美登利已经知道了她将要面对的可怕的未来,信如也决定了自己的道路,而在“一个降霜的早晨”,不知何人将一枝纸水仙花投入大黑屋的院落内,美登利却产生了一种怀念之情,将其插入花瓶中后,就久久地注视着纸水仙花“寂寞而又清纯的花姿”(十六)(183)。
北川秋雄在《<青梅竹马>私考——在水仙的彼方》[8]中,对小说结尾的纸水仙花所代表的含义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于“是谁投的纸水仙花”这一问题,文中列举了几位学者对此持有的不同观点。但是,不论投花者是出于同情的一叶还是选择逃避的信如,纸水仙花本身的寓意就耐人寻味。“‘一朵纸水仙花’的‘寂寞而又清纯的花姿’正好给两人之间苦闷的爱恋画上了句号。”[9]山田有策也在《关于<青梅竹马>的“专题论丛”》[10]中提到,不晓得一叶是否知道,“水仙”在佛教供花中的花语是“别离”。也许是对这段朦朦胧胧的爱恋的告别,亦或许是对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的祭奠。
小说的第十部分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景物描写:
从春天赏樱的喧嚣,到夏天悬挂玉菊灯笼的盂兰盆节,再到秋天的新仁和贺戏,在这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平均每十分钟就有75辆车子来往。季节的交替不知在何时已经完成,这时,离红蜻蜓在田间飞舞、鹌鹑在河畔鸣叫的日子就不远了。一朝一夕,秋风开始变得寒冷,上清店撤下了货架上的蚊香,换上了取暖用的怀炉。从石桥旁的田村家传出的磨面声透着一股凄寂,角海老钟楼回荡的钟声也莫名地令人感到哀愁。日暮里的火光四季不绝,当知道那是火葬死者的飞烟时,心中感到凄然。(十)(161~162)
“贯穿整部作品的却是时间之索。争闹也好,爱情也罢,无不围绕着这根隐形之索进行着。无论他们儿时生活得怎样自由自在,经历了多少欢乐与摩擦,终会被时间无情地拖进充满烦恼和悲哀的青春。”[11]没有人发觉季节的交替到底在何时完成,就像没有人发现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心理上、生理上的变化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再不是只知道玩耍的孩子了,他们也会长大,也会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不得不对命运妥协。一叶借这一段景物描写,预示了孩子们逐渐走入人生的冬季,逐渐接近黑暗残酷的现实,诉说了对那些孩子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即将面临的悲凉人生的深切哀叹。
四、结语
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创造出了一段朦朦胧胧的恋情,却最终夭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而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也会在社会的压力下对命运妥协,步上父辈的后尘。一叶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小说的环境、景物和季节的交替变换,这些看似只是对景、物的描写,却与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命运密切相关。随着季节的推移、天气的变换,小说逐渐进入高潮部分,人物的身体、心理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时,季节的推移、天气的变换也象征着美登利和信如之间的朦胧爱恋从不知不觉地产生到无可奈何地结束之间经历的种种发展变化,也预示着那些孩子们离他们将要面对的现实越来越近。另外,一叶对当地环境以及红布条、纸水仙花等的描写也于细微之处蕴含了深刻的寓意。总之,小说《青梅竹马》中的景、物描写,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小说主题的生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细微之处可见作者的匠心。
(注: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日本现代作家的历史认识与小说创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zd-096;本文中所有作品文本均引用《樋口一叶小说全集·第3卷》(万叶出版社,1946);本文中所有作品文本均为笔者自译)
[1]肖霞.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J].山东大学学报,2005,(1):111.
[2]肖霞.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J].山东大学学报,2005,(1):112.
[3]张雅君.从樋口一叶的文学表现看近代日本女性的犹疑与摇摆[J].学术论坛,2011,(3):159.
[4]爱知峰子.樋口一葉—『たけくらべ』の季節と雨[J].国際関係学部紀要,1997,(19):142.
[5]重村惠子.『たけくらべ』の哀感—語りの手法[J].日本文学研究,1991,(27):111.
[6]庞在玲.试论樋口一叶小说的叙事策略——以<大年夜><青梅竹马><十三夜>为中心[D].中国海洋大学,2012.37.
[7]爱知峰子.樋口一葉—『たけくらべ』の季節と雨[J].国際関係学部紀要,1997,(19):135.
[8]北川秋雄.『たけくらべ』私攷—水仙の彼方に[J].同志社国文学,1993,(37):12-23.
[9]王蓉.对樋口一叶<青梅竹马>的认识——以现实主义为中心[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35.
[10]山田有策.「たけくらべ」をめぐって<シンポジウム>[J].国文学:解釈と鑑賞,1988,(2):141-163.
[11]石玉芳.永恒的光芒——<青梅竹马>的艺术魅力[J].赤峰学院学报,2011,(1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