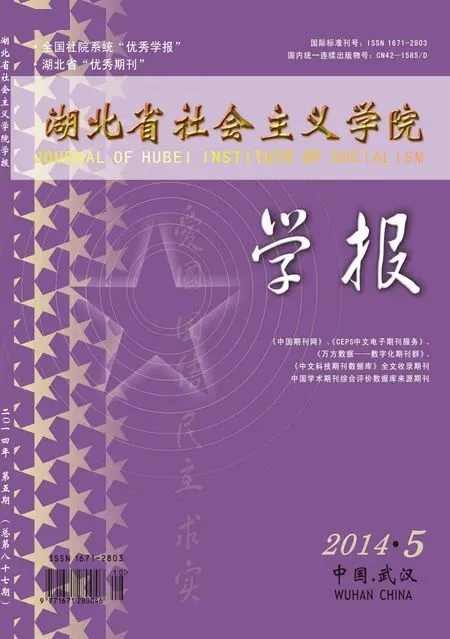西方宗教教育的历史考察
杨 兰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基督教的宗教教育在西方国家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特殊作用。对这一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西方国家宗教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也是我们分析和认识现今西方国家宗教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恩格斯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1](P550)
一、早期社团组织中的宗教教育
早期宗教社团组织是最早且最为集中的宗教教育场所。据《使徒行传》记载,早期基督徒社团是过集体生活,由使徒们亲自领导。信徒聚会是自由的,聚会的主要内容为祈祷、讲道、训诫、见证,同时采纳了一些犹太会堂的做法:诵读犹太教圣经的经文,讲解经义等;后来《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也成为诵读的经典。基督徒社团最初除犹太教的经典外并没有自己统一的经典,各社团在举行宗教活动和对外宣传时除诵读犹太教《圣经》外,往往还宣讲耶稣的生平事迹,当众宣读使徒们给各地基督徒社团的书信材料。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随着基督徒脱离犹太教而自组一个独立的宗教,他们便自认为是上帝的真正选民,是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族类,虽然服从罗马的统治,但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天国的国民。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教会。最初的基督徒组织十分简单。地方教会称为“聚会所”,与犹太会堂差不多。会务由资历较老的人管理。传教士是由主要中心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派出去的,他们在各地传讲福音或访问其他教会。
早期社团中基督徒的生活是极为严格和清苦的。每日3次诵读《主祷文》。每礼拜三和礼拜五为禁食日,表示“保持警醒的基督精兵”,主张“禁食比祈祷好,但施舍比两样都好”。只靠悔改不能取得罪过的赦免,还需要行善功来补偿,如能广行善事,就会有“分外功”,就能有“分外之赏”。 当时的人们认为,富人周济穷人,穷人则为他们祈祷,他们便有了善功,因此当时施舍周济贫苦孤寡之风盛行。有人为了救济贫困,甚至自卖为奴隶。教会也用信徒捐献的公益金来支援贫穷的教会,出钱赎买奴隶和罪犯。这样,教会不仅对富裕的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吸引力,对社会下层群众则吸引力更盛。
加入教会的基督徒需要过团契生活。主日要举行礼拜,包括读经、讲道、唱诗、祈祷、全体会餐与圣礼晚餐。后来,圣礼晚餐改为圣餐礼,作为礼拜仪式的结束。领圣餐时要捐献,作为办慈善事业的公益金。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约100-165年)是公元二世纪最早的一位希腊教父,他曾记载了礼拜日教会内部的宗教教育活动:“礼拜日的集会是诵读一段使徒的回忆录(福音书),或先知的著作;接着,主持人(主教)开始讲道,告诫他的听众,要照他们刚才听到的这些好的教导生活;然后全体会众起来,共同祷告。接着就是简洁的圣餐礼。祈祷以后,我们兄弟般的接吻,相互祝福。然后饼和掺水的酒送到主持人(主教)那里,由他以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对万有的父奉献赞美的荣耀,最后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些恩惠,接着大家齐声应和:阿门!阿门在希伯来语中是‘是这样的’意思。此时,执事们即把切成小块的饼和酒,分给出席的人,也带给缺席的信徒。我们把这种食物称作‘圣餐’,除了那些信仰基督、接受洗礼、按基督的戒命生活的人以外,没有人可以分享。我们不是把这些食物当作普通的食物,而是当作我们的救世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得救而从他那里得到的血和肉;所以我们接受的教导是,通过祈祷的话语我们得到滋养,我们的血肉也因此与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血肉相似。然后,比较富有的人和愿意捐献者自愿进行捐献,收集后由主教掌握,用以救济那些孤儿、寡妇、穷人、匮乏者、囚犯和陌生人,照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2](P10-11)这些是最初的教会组织对内部成员进行的宗教教育活动。
二、教会学校:中世纪早期的教育机构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迅速发展,并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教育被教会垄断,教师由教会委任,僧侣是法定的教育者。教学内容以神学、宗教教义为主,古代的文化被加以曲解来为宗教服务,异教学校被取缔,世俗文化教育成为神学的陪衬。教会学校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的教育机构。在这一背景下,宗教教育在中世纪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教育的垄断者和推广者。
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教会学校是教义问答学校,分为初级教义问答学校和高级教义问答学校两种。前者以儿童为主要教育对象,教授教义知识、宗教道德、音乐等等,教学场所一般设在教堂中;后者是为培养教会的神职人员而设立的,教授较为高级的教义和其他宗教课程。
中世纪教会学校数目众多,从教会办学的性质上一般可分为僧院学校、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三类。僧院学校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是专门培养未来准备担任僧职的贵族和僧侣子弟的学校,他们自幼入院并住宿在修道院内;外学是培养那些不准备充当僧侣,学成后仍还俗的人的学校。儿童一般10岁入学,学习年限为8—10年,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僧侣必备的三种品质:服从、贞洁、安贫。教师完全由教士担任,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士口头讲解,使用拉丁语;学生记录讲述内容,诵读并记忆。学习内容主要是神学经典、宗教信条、圣歌、赞美诗之类。神学是修道院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居于全部教学科目的“王冠”地位,通用的教材是《教义问答》,还包括基督教的信条、十诫、圣事、祈祷。后来“七艺”也被纳入课程范围。“七艺”即“七种自由艺术”,是西欧中世纪早期教会学校的七种学科,即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在“七艺”的教学内容中贯穿着神学思想。如学习文法和拉丁语是为了阅读《圣经》,学习修辞学是为了分析经书的文体,学习辩证法是为了替教会的宗教信条进行辩护,学习算术和天文知识是用于计算宗教节日和祭奠的日期,学习几何学是用于绘制教堂建筑,学习音乐是为了做礼拜和宗教仪式。后来“四艺”的学习还加入了更多神秘主义的解释,如把“1”解释为唯一的神,“2”解释为耶稣基督所具有的神性与人性双重人格,“3”意味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等等。
主教学校又称大教堂学校,始于英格兰。学校设立在主教所在地,其组织形式和水平与僧院学校相似,学校设备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教区学校是基督教教会对广大教民和一般世俗群众进行宗教教育的机构。教区学校通常设在村落的教堂中或牧师自己家中。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教师由牧师充任,牧师向入学者收取一定费用,以拉丁文教授识字、书写和阅读祈祷文等基本知识。
三、修道院:西欧时期的文化教育中心
中世纪最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是分散于各地的修道院。修道院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进入崩溃阶段,特权阶层穷奢极欲,民不聊生。一些基督教徒根据教义,认为肉体是灵魂的桎梏,苦修戒斋是克制肉体欲望和解放灵魂的方法。同时,为了逃避现实生活的疾苦,以图忘却尘世的纷扰,一些基督徒纷纷到远离人间的深山、荒漠之地去过隐居生活。这些修道者终日祈祷、斋戒、鞭身,有些还拥有了众多的信徒,制定了一套正规的制度,逐渐建立起了修道院。最初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只是教徒集体修行的场所。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中世纪早期其他教育形式基本不存在,这些修道院便承担起教育的基本职能。随着基督教影响的不断扩大,修道院数量增加,教徒不仅要求自身对上帝虔诚,还开始注重读经学习,收集经文并抄写、诵读。修道院还设有图书馆供教徒研修、著书立说。到9世纪,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具有了教育功能,成为宗教教育的主要场所。
1、修道院是中世纪掌管文化的场所。以修道院为中心的教会体制是由早期基督教会中的爱尔兰教会发展而成。在这种体制中不设主教管区,主教职权是授任圣职,其他方面均须服从修道院院长。修道院不仅是教牧中心,而且是学术、教育中心。中世纪初,一些罗马贵族的后裔为了挽救衰落的罗马文化,将古代文化知识编纂成书,或在自己创建或主持的修道院里建图书室,收藏古代典籍,或设抄书室,抄录原著,增加份数。这些行动虽然没有达到挽救罗马文化的目的,但却开了修道院储藏古代文化知识的先例。在以后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修道院成了濒于毁灭的古代文化的庇护所,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古典著作。如在查理大帝执政时期,经查理大帝同意,扩建在圣马丁修道院附设的学校,并从各地搜集手稿,充实修道院的图书室。同时还组织修士精心抄写拉丁文《圣经》、教父著作以及古典拉丁文书籍。后世所看到的基督教著作与非基督教古典著作,很多都是在这一时期由修道院抄写出来的。
2、修道院是西欧教师的养成所。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一直具有一种对其社会责任及其传教功能的强烈意识”[3](P136),这使它们很自然地注重教育。所有进入修道院学习的人,不管今后是做教士还是从事世俗职业,都要读书写字,这使他们在获得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化知识,一些人成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另外一些人则成了传教士。在当时无论学者还是传教士大都从事教育事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修道院又是这一时期西欧教师的养成所。修道院学校的教师完全由教士担任,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口授和学生背诵、抄写相结合。实行个别教学,学生的入学时间、学习进度和时间安排因人而异。学校的纪律十分严格,体罚盛行。修道院培养了不少学识渊博又有宗教热忱的学者,分布到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推动了基督教西方的广泛传播。此外,这些修道院还培养出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对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和提升基督教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3、修道院开办学校,培训神职人员。6世纪,罗马教廷派往英国传教的传教士,到了英国后就开始建修道院,吸收修道士,并对其进行宗教知识训练,然后再由这些人把基督教信仰传播开来。7、8世纪,爱尔兰和英格兰修道院出身的高级传教士,抱着高度的传教热忱来到德意志传教,同样是先建修道院,并以此为基地,把基督教传给德意志人。9世纪,查理大帝征服了萨克森与巴伐利亚,也在所到之处建立修道院。因此,德意志人在完成基督教化时,修道院也掌握了德意志的宗教和文化。经德意志人之手,基督教信仰传到北欧和中欧时,修道院也垄断了当地的文化教育。9世纪,基督教与日尔曼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国家把办教育的事交给了教会和修道院,从而使教会、修道院独掌文化教育的状况进一步加强。“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3](P40)“罗马帝国的教育制度受到蛮族入侵的冲击,或随着拉丁世界城市文化的衰落而衰落消逝。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the Latin classics)才得以保存下来。”[3](P41)可见,修道院在基督教文化对教育权的垄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修道院制度有着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意义。一方面,修道院制度确保了基督教文化诞生与发展所必须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教士们在一种隔绝外界喧嚣的净土中思考上帝的绝对存在和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在社会发生极大的变革与动荡不安的过程中,在西欧从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的过程中,修道院为古代文化的保存与传递提供了宝贵的场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如果没有修道院那高墙之内的修士们抄写文本的努力,没有修道院学院所实行的教育,没有修士们的积极传教,古典文化的成分也就难以延续和保存下来,基督教的文化也便难以传播和确立”[4](P33)。
四、中世纪大学:现代大学的雏形
中世纪大学在西方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西方,教育史学家通常将中世纪出现的大学视为现代大学的前身,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模式,甚至认为,大学是西方社会中仅次于基督教教堂的第二古老的机构,是欧洲中世纪三大最有价值遗产(教堂、大学和议会制度)之一,它在早期形成的精神和文化传统延绵至今。”[5](P48-49)正如恩格斯所言:“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6](P156)现代大学在科系分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位设置等方面都留有中世纪大学的痕迹。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安德森(G.L.Anderson)也指出:“现代大学的基本形式或基本结构来源于中世纪大学,从现代大学的基本结构中仍然可以看到中世纪大学的特点。”[5](P53)
1、在系科分类方面,中世纪大学起初为单科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为法学科,巴黎大学为神学科,萨来诺大学为医学科,学习以上学科,须以七艺为基础。后来,一般大学开始分设文、法、医、神四个系科或四个学院。其中法、医、神三科被认为是“高级”学院,文科则是这三科的准备阶段,隶属于其他三科。学生修完文科,才能分别进入其他三科学习。由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神学在四科中居于支配地位。
2、在课程设置方面,13世纪前,大学课程在不同的大学或在同一所大学不同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到13世纪,大学课程逐渐由大学规程或教皇赦令固定下来。从此,大学课程得以在大学间固定下来。中世纪的大学课程具有很强的神学性质。神学学习居于主导地位,中世纪大学主要是培养市政和教会管理人员、法律工作者以及医生。
3、在教学方法上,通常采用讲课、复述、讲授、辩论等方法。讲课主要是教师读教科书,学生记录讲课内容。教师的讲课包括评论、注解、推演、归纳等。复述有诵读原文和讨论,通常将学生分成小组,由成绩较好的学生带领其他同学复习学习的内容,然后进行讨论。讲授不是系统的阐述学科内容,而是教师讲解一些选定的原文和对原文进行注释和评论。其程序是先由教师向学生读古典作家的原文,接着详细解说原文,然后评论最感兴趣的段落,最后提问进行讨论。讲授分为普通讲授和特别或临时性的讲授。普通讲授是学校制度中规定的正式讲授,通常在上午进行;特别或临时性的讲授是非正式性质的讲授,一般在下午进行。辩论是讲授的必要补充,其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扫清修业中遇到的困难,也给学生提供运用辩证法的实践机会。辩论有严格的规则,要忠实地遵循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所包含的逻辑规则。在各个学院,辩论由教师组织实施。如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辩论的题目由教师每两周提出一次,用来训练学生,然后教师试图解答或“裁定”这些问题。具体做法是对学生的不同论据及其论证的正确性和优缺点作出结论。这种活动一年中有两次,一次是在圣诞节,一次是在复活节,教师也要当着许多学生的面举行大的辩论。这些辩论的主题可以是任何想辩论的内容。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在读完一年级后,就开始不断地练习这一辩论艺术。通过辩论活动中世纪大学的校园不仅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还洋溢着论证和辩论的精神。这种辩论术的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未来在法庭上、封建议会上和教会会议上进行辩论的专业人士的辩论技能。
4、在学位制度设置上,中世纪大学产生了西方最早的学位制度和相应的考试制度。学位原来的意思是任教执照,大学毕业经考试合格,可获得“硕士”、“博士”、“教授”学位。大学学位最初是为大学培养师资的需要而设立的。从13世纪开始,学位成为获得者有能力任教的依据,不必再进行其他考试。凡是具有拉丁文基础,修完“三艺”,成为熟练学习者的人,具备后补教师的资格,可获“学士”学位。修完专业课程可申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当时,硕士和博士并无等级差别。后来,“硕士”逐渐用于低级学院的成员,“博士”、“教授”则用于医、法、神三个高级学院的成员。“学士”起初并不是正式学位,只是表示学生已经取得学位候选人的资格,后来才成为一种独立的低于“硕士”水平的学位。
中世纪大学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基本上是教会的婢女和附庸。“大学虽然不是教会,但大学却继承和保留了教会的职责。”[7](P139)鲍尔生曾说,中世纪大学“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教会的教义成了它们教学的基本原则,教会的通用语言也是它们的语言。大学的成员,无论教师或学生,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在职人员或预备人员”[8](P18)。从总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宗教色彩依然很浓厚,但它的出现打破了宗教教育在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西方宗教教育的世俗化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王晓朝.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王保星.西方教育十二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5]单中惠.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7][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8][德]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滕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