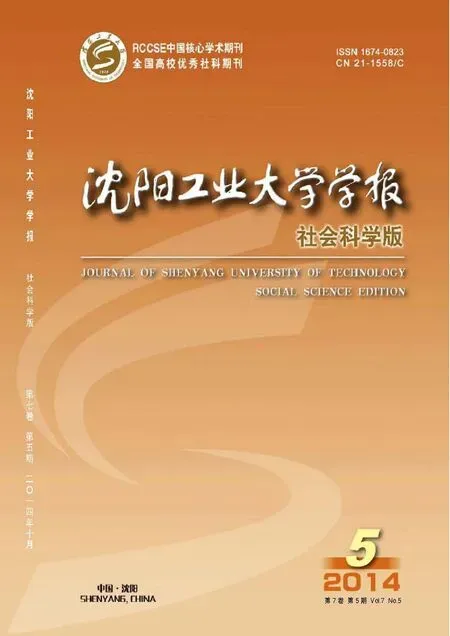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及其现代意义*
李德嘉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专题论坛:中国古代法律思维省思】
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及其现代意义*
李德嘉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内涵丰富,包涵了案件中的情感、事实与人性三个维度的意义。透过传统司法中人情与国法之间的平衡可以发现,传统司法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行为人,而是通过情理展现出的具体情感关系和人伦关系中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注重人情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
国法; 人情; 人本; 情法冲突; 司法; 法律规制
“情理”有时也称为“人情”,或简单地说就是“情”。情理对中国古代法制与司法之影响十分深远,是传统法律人本观念的特殊体现,甚至形塑了传统法制的基本性格。有学者认为:“法与情、理之间,确实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存在。”[1]但这种特殊的联系首先在司法领域体现出来,尤其在宋明清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有学者称:“宋明清以来,‘情理’一词在司法中运用渐广。确实,最初对‘情’的强调,也是从司法领域开始的。所谓情理,在其初,不过是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也有学者以“情理场”来概括分析中国古代司法的特质,认为所谓“情理场”是指中国古代司法中无处不在的由情理精神构成的法律文化特质[2]。
然而,人情在司法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对于现代司法而言有何启示?学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深入。甚至于法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古代司法重视情理而轻视法律,天理、人情往往高于现实的法律,因此造成了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也有人将中国传统的司法模式看作是一种“卡迪司法”①参见高鸿钧《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载于《政法论坛》2006年第9期。另,学者间对于中国传统司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以及传统司法性质问题的学术争论可以参见易平《日美学者关于清代民事审判制度的论争》,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透过学者们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学术纷争背后,学者们对于中国传统司法重视情理这一特征存在基本的共识,其主要的问题集中于对古代司法中情理因素的理解和评价方面。
限于学力与篇幅,本文并不打算陷入对古代司法性质的缠讼之中。本文的意义在于透过对古代司法中人情的分析,探寻其中的现代性价值。现代以人的抽象行为为规制中心的形式主义司法体系固然提供了一整套关于纠纷的法律解决方案,然而对于个案中的实质公平问题,形式主义司法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传统人情司法所能发挥其价值和意义的地方,因此值得学者的认真反思与总结。
一、人情在传统司法中的涵义与运用
人情到底是什么?法律史学界习惯将情、理、法三者并称,分别指代人情、天理和国法,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机械。其实,不仅情的涵义与理相关,所谓“天理”实质上也是人情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在于将财产关系寓于人身关系之中,因此,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合理,一般从其行为内容是否符合情来判定,凡是不符合情的也就是不合理的,凡是符合情的就是合理的。身份为情,基于此情的行为原则和要求就是理,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身份由此转变为具体的行为要求。如前面案件中所讲到的具体伦常关系为情,而这种关系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就是理。社会的根本就在情,基于人之感情而确定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即是理。戴震说:“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这正是对情与理关系的很好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之所以情与理不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理主要是一种道德理性,是基于人性、人情的,实指伦理道德的原则规范。血亲与人际之情产生了理,这种理又反过来约束指导情,使情的表达完全遵循宗法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理出于情又要节制指导情,在这里情理是贯通的、一致的,通情则达理,合情就会合理,正所谓“天理无非人情”。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语境中,情与理的关系实在密不可分,可以说,情是理的基础,是规定理之内容的本质,而理则为人正常抒发情感提供了规范。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情理”一词大概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作为裁判事实的案情,二是具有裁判依据意义的事理。案情是司法中的事实层面,而事理则是司法中的法律层面,传统司法语境中“情理”一词的两个面向其实就是事实之维与法律之维的集合体[3]。然而,对情理的理解仅限于事实与法律两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尚不能全面认识传统司法中情理因素与人情、人伦之间的关系。
1.案件中的事实
实情和情节是“情”的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个义项,比如在明清时期的“秋审”中,最后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和留养承嗣四种处理方式*《清史稿·刑法志》。。其中所谓“情实”指的是“事实认定清楚”,可见在古时官方的法律语言中,“情”往往指案情或案件事实。案情和事实层面上“情”字的用法在明清时期的判牍中经常可以发现,如《云间谳略》中就有这样的判词:“朱宗政侵盗仓粮一事,浪费有据,借贷有主,情最真,罪最确。”*[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卷四,“一件督抚地方事”。《莆阳谳牍》中也有相同的用法:“陈朝宁与翁在缙以灌水相争。朝宁之女适死,与本事无干。盖在缙何憾于幼女而击之致死耶?况乡众公呈亦无一语及死女,其情已显然矣。”*[明]祁彪佳《莆阳谳牍》卷一,“本府一起打死人命事”。这些判词中的“情”都指的是案情。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司法传统中的“情”所表达的事实或案情的涵义与现代司法语境中的“事实”在概念所指涉的内容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现代司法语境中的“事实”往往要求与所需要证明的案件争点具有相关性,与案件法律争点本身不具有相关性的事实往往在司法过程中没有意义甚至被排除。而古人所谓案情或事实,往往包括了能够被证据证明的事实和法官根据常理所推断的事实,而且,古人所谓事实不仅是指与案件的法律争点相关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当事人行为背后的隐情或缘由,这些隐情或缘由往往由司法官员推论得出。
比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记录的李茂森赁人店舍一案,其基本情况是在契约没有约定又没有主人之命的情况下,李茂森自行撤旧造新。如果本案刻板适用法律规定,则李茂森难逃专擅之罪。然而,本案的审判官没有仅仅按照所能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判,而是对事实背后的情由以及当事人行为背后的情理进行了推断。法官首先指出,蒋邦过时已久才诉之于官,不合常理,因此背后必有隐情。其次,“其告成之后,又尝有笔帖,令其以起造费用之数见谕。”可知两人之间一定事先有所约定。最后“李茂森非甚愚无知之人,岂肯冒然捐金縻粟,为他人作事哉!”基于以上这些情节的考虑,审判官作出了符合情理的推断,即“李茂森具数太多,其间必不能一一皆实”,才导致小人“欲勒其裁减钱数”。因此,李茂森真实的内心想法一定不是真的要“除毁其屋”,其不过是想通过此行为来迫使蒋邦“裁减钱数”罢了。再加上双方本是亲戚,如果严格依法判决不仅会使司法严重违背事实和公正,而且有伤亲属之间的和气,最终,审判官的裁决结果是请邻里调解,“从公劝和,务要两平,不得偏党”。
本案中,审判官所依据的事实并不仅限于法律事实,其所援引的事实多与法律无关,但是对于正确理解案件中当事人的行为和案情背后的原委却有着很大的意义。探究这些法律事实之外的客观事实在中国古代的司法中起到了两点作用:一是对于法官全面理解案件的原委和曲折有着重要意义,这些事实虽然没有直接反映案件的情形,但是往往可以作为理解案件的背景材料来运用。法官可以通过这些事实推断当事人行为背后的真实用意和真实原因,这些虽然与法律无关,但是却足以影响法官对案情的情理判断和情感倾向。此外,这些事实也能使案件中的个人血肉丰满,情感丰富。在法律的视野下,个案中的个人仅是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诉讼,精于算计,在法官眼中他们的形象模糊而抽象,其意义只剩下行为合法不合法而已。然而,传统司法中所强调的“实情”却能够使这些案件中个人的形象在法官眼中变得丰满而具体起来,他们既有行为合法不合法的一个方面,也有处于伦理关系中的情感心理和在现实生活面前的精于算计,更有在具体情景中的委曲求全。这些传统司法中所十分注重的“实情”恰恰可以对法官眼中人的形象加以丰满,而不再只是一种符号化了的“案件当事人”。
2.人之常情
明代的张肯堂曾在一则判牍中说:“人情利来未必交让,而利尽必至互推。”*[明]张肯堂《辞》卷八,“马存智”篇。这种趋利避害的描述显然是对人性所作的一种假设。而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人性假设,在法官看来也是人之常情。比如,在一宗买卖纠纷中法官就有这样的判词:“议价之始,稍有低昂,得价之后,更生变态,亦人情之常也。”*[明]张肯堂《辞》卷八,“李含芳”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之私在传统司法中的法官看来是人情之常,体现了古人对人情中趋利避害一面的认可,认为这是人们正常的利益表达,在伦理上并没有给出否定性的评价。在更多的情况下,传统司法中的法官更倾向于保护人们这种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抓住当事人趋利避害的心理特征,在调处过程中使双方的利益诉求得到大体平衡,这样就很容易做到对矛盾的真正化解。有学者根据明清之际法官们保护趋利避害之人情而产生的判决,指出传统司法中情理调处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平衡,调处的基本原则大致有迹可循,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保持双方利益的大体均衡[4]。这样的情理调处技术其核心正是对人情之常的深刻把握和运用。
一方面,传统的法官以趋利避害的人性之私作为情理调处的一项基本原则,使双方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表达和相对满足。比如,在清代一件久拖不决的私卖公田案件中,法官最后所运用的就是利益平衡的调处技艺,而非简单的依法裁判*[清]熊宾《三邑治略》卷六。。本案起因于张之才将公田私卖,得钱逃走。基于私卖的缘故,前任县官断令退田,但是张之才逃走,张之浩又贫苦,无从退价,因此各买主才“拒死相抗”,致使案件牵累七年而不能决。现任法官在查看案情后,就认为“以人情而论”此案之所以久拖不决的原因乃在于各买田之人的利益损失无法得到补偿,如果依法裁判,案件中的损失必然会由一方来完全承担,这样的利益损失是一般小民所难以承受的。因此,法官判决要求各买田之人每户按田亩数凑出一点钱另外置田充作公田,而原本应该追回的田亩则继续由各买主耕种。这样一来,各买主虽然需要另外出一笔钱,但是相比之前的判决结果而言,自己原本所买的田就得以保全,显然这样的结果更让人能够接受。
另一方面,趋利避害的“人情”也不时被用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比如,明代有这样一起案件:曾氏之夫郑中翰亡故后,其向亲家游若林讨取亡夫所寄之银,因而发生争执。判官说:“郑中翰积金四千,而不为家营寸产,以四千金寄若林,而不以数金留曾氏,此人情所必无者。”*[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九,“异冤诬银”。在判官看来,人性是自私的,决不会以数千金存寄他人之处而不为家人存留数金,由此推断此案原告一方所主张的事实不合于常理,因此不能成立。
3.人伦关系中的情感
人伦关系是我国古代法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仅影响到立法,而且贯彻于司法实践的各个方面,为指导司法审判的原则性条款。实际纠纷中,只要存在人伦的因素,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判决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一方面,法官会通过每个人所处的不同伦理关系来确定各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人伦关系中所体现出的情感实质则是裁判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传统司法强调“原情”,这种“情”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存在于人伦关系中的心理情感因素。法官裁判案件的要求就是要能够将心比心,以自己的情感经验来推测案件当事人的内心情感,从而使得判决在感情上能够被接受。正如明代州县官员张九德所说:“设以身处其地,务使彼情不隔于己情,又使己心可喻于彼心。”*[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张九德“序”。这种设身处地的情感沟通实际上就是孔子所说“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思想核心就是要求法官将案件中的当事人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情感的个人而非法律条文中符号化的行为人。
在传统司法中,案件中的个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伦关系之中、处于不同伦理关系之中的人,其应该适用的法律关系不一样,应负的责任与应承担的义务也不一样。处于不同伦理关系和不同个案中的人,其所体验的情感心理也不一样。因此,传统司法中从来没有抽象而孤立的个人,只有存在于不同伦理关系和情感关系中的个人。传统司法裁判的精髓实际上就在于使具体情感关系和伦理关系中的个人与法律之条文、天理之要义相互调适,所谓情法之争,不过是具体的情感关系和抽象的法律规定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在这种困境中,古人所采取的做法是使抽象的律文适应具体的情感关系。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在情法冲突的情形中,古人所做的是在具体的情感关系和案件事实中发现其中所隐含的法意和事理,而非削足适履地以抽象的律文来裁断具体案件中的情感关系。
二、情法冲突中对人伦情感的优先保护
如前所述,人伦情感是指导司法审判的原则性隐条款,涉及人伦情感的因素则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判决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在实际案件解决过程中,重视伦常的过程即重视案件之情的过程,该情即为伦常观念要求下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关系。“照得天地设位,圣人则之,制礼立法,妇人从之,亦犹臣之事君也。贞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信天地之宏义,人伦之大节也。”[5]217-218于古人看来,伦常又与理具有相通的含义,合于伦常即是合于理的。法官对伦常的把握与运用是重视情理解决案件一个重要方面。伦常是解决案件的依据,伦常关系的恢复是解决案件追求的目标,也是理所要求的内容。在古代法官心中,司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对被破坏的人伦秩序、情感关系的修复,而不是维护法律的秩序。法律的终极目的也在于此,传统法中的亲亲相隐、服制定罪、维护亲属间等级秩序的法律无不体现了法律对于人伦秩序和人际自然情感关系的维系。既然维护人伦秩序和情感关系是传统法的最终价值和目的,那么在司法过程中对于人伦秩序的修复,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法的价值的维护。
宋代一位基层司法官员王回审理过一个被休的妻子举报自己前夫曾经有过“指斥乘舆”言论的案子,这个案子在今人看来很有意思,其案情与德国当年的“告密者”案有些类似之处。王回的书判文书现在保存于宋代诗文汇编《宋文鉴》中,为了方便对王回审判依据的分析,现在将其书判全文摘录于下:
“指斥乘舆,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斩,而旁知不告者,犹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于海内,使虽遐逖幽陋之俗,犹无敢窃言讪侮者。然《书》称商周之盛,王闻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风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则此律所禁,盖出于秦汉之苛耳。若妻为夫服斩衰而降,其义甚重,而《礼》已来,未之有改也。且挟虐犯法,既许自诉,而七出义绝,和离之类,岂有穴怨?顾恬然籍衽席之所知,喜为路人,挤之死地,其恶憨矣。宜如有司所论已若夫减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经,窃谓非薄君臣之礼,而隆夫妇之恩也。”[6]1806
“指斥乘舆”属于古代十恶重罪之一的“大不恭”罪,如果按照《宋刑统》的规定,将可能被处以极刑。“指斥乘舆”乃是十恶重罪之一,如果明知而不告者也有连带责任,因此,本案被告之前妻就有揭发检举的法定义务。虽然一般情况下夫妻关系属于古代“容隐”的范围,但本案中被告早已休妻,恩义已绝。如果按照成文法的严格规定,对于被告之前妻显然不能适用《刑统》中关于“有罪相容隐”的法律规定。本案的主审官员王回显然没有僵硬地适用成文法的规定,而是根据人伦情感对成文法律的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依照自己所解释的法律精神对案件作出了审判。王回在书判中解释了自己的判决理由,其中有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王回并没有直接援引儒家经义对人伦情感的理解作为审判的依据,而是首先以儒家经义中所揭示的伦理原则对成文法的内在精神进行了解释,尤其是阐明了先人制定“指斥乘舆”条款时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王回引用《书经》中所揭示的政治伦理,说明王者不但不应罪小人之怨,而且应该反躬自省,如果王政能够起到美风俗、育万民的作用,百姓根本就不会去抱怨、詈骂统治者。因此,王回指出“指斥乘舆”这一罪名是源自于秦汉之苛法,其之所以存在于现在的法典中是出于历史原因,可见,这一罪名本身的正当性就得不到儒家正统经义的支持。
然而法律毕竟是法律,主审官员只能从一个儒家士大夫的角度去批评其不符合儒家的政治伦理,却不能在审判中否认其效力。主审法官如果想突破成文法的规定,就必须作出一系列的价值衡量,找出不能适用成文法的价值理由。王回敏锐地指出,本案的争点在于儒家所倡导的夫妻之恩义这一人伦情感与法律所保护的天子之尊严在个案中形成的价值冲突。一方面,天子的尊严需要保护,这乃是君臣之大礼,因此需要对“指斥乘舆”之人进行严惩;而另一方面,儒家倡导夫妻之间以恩义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尤其强调夫尊妻卑,作为妻子有义务容隐丈夫所犯的罪行。王回认为妻子应该容隐自己的丈夫的罪行,即使是在被休弃之后,也应该念及夫妻之恩义,尽到自己容隐的义务。因此王回指出,本案应该适用“当容隐者告之,同罪人自首”的法律规定,这样的判决并非是“薄君臣之义”,而是要重申儒家所倡导的夫妻之礼。
最后,王回还从人之常情的角度论证了本案判决的合理性。王回指出,本案被告之前妻被休之后难免对被告会有怨恨之情,而被休又免除了自己在法律上的容隐义务,正好可以将原先夫妻生活中所掌握的前夫的罪行进行揭发,让有司对前夫进行惩罚,恰可以公报私仇。如果判决丈夫有罪,则或许会使司法判决成为妻子报复自己丈夫的工具。这样的判决结果会起到诱人作恶的作用,当然这是主审官员所不希望看到的。
三、人情司法以现实中的人为法律规制的中心
中国传统情理司法的一大特征是以现实中的人作为法律规制的中心,在法官的眼中,案件中的人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而且是与其所处的伦理秩序、生活情景、人际情感相联系的个人。传统司法中不存在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根据其所处的人伦秩序的位置而承担着不同的法律责任,同时,法官在判决时也会考虑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情景和人际情感联系。
首先,传统司法中的人是处于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人,每个人都按照其在伦理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来承担责任。比如,传统法律中以当事人之间的服制关系作为决定案件性质和罪行的前提条件,其在刑事法律传统中的表现就是“准五服以制罪”。服制定罪的意义是在立法确定有关亲属相犯行为的罪、名、刑等时,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尊卑作出区别规定。在亲属之间的伤害案件中,法官会根据亲属间尊卑长幼关系的不同来确定每个人不同的法律责任。如果是卑幼殴击尊亲属而未折伤,则根据其所殴击对象的尊卑来确定罪行,殴缌麻尊亲属徒一年,殴小功及大功尊亲属各再加半年,殴齐衰尊亲属徒三年,殴斩衰尊亲属则斩。而反过来,若是尊长殴击卑幼而未折伤,则按照被殴者的身份秩序相应减轻处罚。可见,在亲属间伤害的情形中,尊亲属犯卑亲属,服制关系越重,罪刑越轻;卑亲属犯尊亲属,服制关系越重,则罪刑越重。这样对于不同亲属身份的人给予不同的判决,恰恰体现了儒家“爱有等差”的原则,体现了传统司法中的人往往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人伦关系之中,定罪量刑也需要根据人伦关系的远近而决定的原则。
其次,传统司法中的人是生活中的个人,每个人在案件中都有其具体的生活情景和人际情感联系,法官在裁判时必须要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理,这样才能做到“情法两尽”。比如在前文所述的“弟弟为争夺家产而殴打兄长致死”案件中,法官在裁判中就注意到案犯是家中独子这一生活事实,如果判决案犯以死罪,则难免给一个家庭造成绝祀的结局。甚至法官还假设了被害的兄长的想法,认为即便兄长泉下有知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庭因为弟弟犯罪而绝祀。因此,法官不惜违背法律的文本规定,对该案中殴死兄长的弟弟进行宽恕。
成文的律令对于犯罪或处罚的规定往往是抽象的且具有普遍性的,比如《宋刑统》对“指斥乘舆”罪的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律文小注曰:“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法律对“指斥乘舆”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模式都作出了普遍性的规定,全体臣民只要有“指斥乘舆”行为的都犯此条,除皇帝本人不可能犯此条外,无一例外。律文小注仅仅排除了因为议论国家政事有乖失而冒犯天子尊严的行为,如果是因议论政事而有过错则需要上请,由中央的司法官员和皇帝作出决断。而在上文所引述的“前妻诉丈夫指斥乘舆”案件中,被告为原告之前夫就是案件中的具体人伦情感关系,而法官在裁判时也正是基于对具体案件中人伦情感关系的考虑而作出的裁判。法官认为,夫妻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人伦秩序,夫妻之间应该存在深厚的感情和情义。在具体案件中,天子尊严所代表的国家政治秩序和夫妻间的人伦情感发生了冲突,而法官的价值取向恰恰是站在了保护夫妻之间的人伦情感关系一边。
与传统司法以现实中的人为规制中心不同,现代司法的着眼点是人的行为。现代司法以人的行为为规制中心,与整个现代法制系统的宗旨相关,体现了法律的进步和发展。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排除了传统法律中对人的思想的规制。在现代法制的体系中,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法律的规范和调整,刑法中废除思想犯是近代刑法的一大进步。而传统法律以人为规制中心,往往强调原心定罪,其规范的触角往往深入人的思想。历史上,规范和调整思想活动的法律往往打击与当时主流所不符的所谓“异端”思想,对人类思想发展造成了禁锢。同时,以行为为规制中心的法律与以权利为本位、高度抽象化、类型化的现代法律体系是相互依存的,关注行为而不是人,是法律发展史上的进步。然而,以行为作为规制中心的现代司法也有其弊端。比如,以行为作为法律规制的唯一对象,则会造成对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个人的忽视[7]。虽然现代司法理念以当事人为中心,在程序上赋予当事人各项权利,实体法律上也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基本诉讼权利,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所关注的只是当事人所为之客观行为,作为判决对象的当事人只是作为抽象的、高度类型化的形象而存在,司法所关注的只是具备或不具备行为能力或法律资格的抽象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注重人情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司法的人情化,即在司法中充分重视人情因素的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重视当事人行为背后的现实情理,成文法传统中的立法者重视对行为的抽象和类型化、体系化,而司法者就应该在普遍适用的成文法的规范下考虑具体案件中的特殊情景,在这个将普遍性规则与具体个案的特殊情景相调适的过程中,人情往往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传统法官以情理解释法律、在判决中阐释个案中的人情与法意的经验可以更好地增加普遍性法律在特殊案件中适用的合理性,不仅起到了正确适用法律的作用,而且可以同时做到使当事人口服心服,做到案结事了。
第二,司法中重视人情,使法官认识到具体生活中弱者的真正存在,看到个案中当事人因为身体缺陷或是精神缺陷等情形所具有的具体特性。比如,对于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某项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从主观方面而言,应该以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条件为标准,而不能以普遍的多数正常人的情形为标准。
第三,传统司法重视人情,看到案件中所存在的现实中的个人,往往是将人置于其所处的人伦关系中去解决案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情与人伦有互通之处。从一个方面来说,将人置于不同的人伦关系中来确定其法律适用,可以说传统社会有家族而无个人,家族伦理吞噬个人价值,是传统社会个人不具有独立性的体现。但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分析问题,传统司法重视人伦秩序和睦的法律价值,注重保护人际之间的伦理秩序和血缘亲情,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王权对家族伦理秩序的渗透,司法在王权与家族之间划上了一条人伦情感、伦理秩序不得侵犯的明确界线。
四、结 语
中国传统法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直接诉诸于生活情理而非神意这种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因而国法与天理、人情才有了沟通的基础。清代名吏汪辉祖对中国古代的法律运作有一段十分精妙的结论:“读律尚己,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佐治药言·息讼》。所谓人情,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的伦常纲纪之情。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中的人本因素正体现在这种基于人间伦常的情理之中。
西方法律中人本观念的发展,体现于人的理性的不断凸显,进而使人获得尊严、独立、自由,而在中国传统中,以个人情感体验为核心的人情和基于日常伦理实践的人伦成为法律人本观念的重要基础,从而对其人本观念的阐释也不可能是基于尊严、独立和自由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古代所谓人情往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1)性情。古人之言人情与人性相通,所谓人情,有时指的是人“智愚”、“贤、不肖”、“善恶”等品格、品性和资质,此一理解上的立法观认为,制定法律应该与人情相适应,根据人的智愚、善恶而决定礼乐和行政手段的运用。(2)情理或是情感。情理与情感难以区分,都是基于日常伦理感情的心理体验,与伦理关系密不可分。其中最为首要的感情就是父子之情,即孝的伦理。因此,人伦与人情互相为表里,相互支持,讨论人情的问题必须首先探讨人伦的思想。(3)情境。在古代司法中,“经”与“权”一直是一对相互的概念,董仲舒“春秋决狱”首先在司法中运用了权变的思想,讲究在不同的情境中以经义和情理权变僵化的法律规范,使普遍性的法律在适用时更加具体化。(4)民情。古代的情也常与民情相关,统治者往往以“为民父母”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将官员比作父母,其中蕴涵的思想就是官员应该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百姓。明代理学名臣吕坤曾经说过,第一等的官员对待百姓好比亲娘之于儿女:“忧饥念寒,怕灾愁病,日思夜虑,吊胆提心,温存体爱,百计千方,凡可以使儿女心遂身安者,无所不至。”[8]926这种由家庭伦理情感比拟而来的政治情感,我们将其称为“民情”,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情化的司法将人情与法意融为一体,通过法官在判决中对百姓的宣谕,人情、法意在判决中得到了充分的结合,成文的律令通过人情化的理解和运用,更能够为普通百姓所尊重和理解。因此,传统司法中重视人情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教育公众尊重法律、理解法意的作用。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司法人情化可能带来以道德判断取代法律判断的危险,造成法治的倒退,这一点是应该值得今天的人们警惕的。
[1] 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 [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3):1-18.
[2] 邓勇.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 [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5):63-72.
[3] 汪雄涛.明清判牍中的“情理” [J].法学评论,2010(1):148-154.
[4] 汪雄涛.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与利益平衡 [J].政法论坛,2010(3):50-57.
[5] 真德秀.名公书判清明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吕祖谦.宋文鉴 [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胡玉鸿.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之调适 [J].法学研究,2010(6):40-54.
[8] 吕坤.吕坤全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8.
Humanrelationshipintraditionaljudiciaryanditsmodernsignificance
LI De-jia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traditional judiciary is pretty rich, including significance of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emotions, facts and humanity in case.Through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 relationship and state law in traditional judiciary,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litigant in traditional judiciary is not the perpetrator in abstract sense, but the person in specific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human relations showed by the sense.In this sen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judiciary paying attention to human relationship could just make up the forgetting on specific individuals caused by the modern law by taking acting behavior as the center.
state law; human relationship; human-oriented; conflict of emotion and law; judiciary; legal regulation
2014-06-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ZD022)。
基金项目: 李德嘉(1987-),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法律思想史和法理学、中国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9-23 14∶03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926.1336.010.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5.01
DF 042
A
1674-0823(2014)05-0385-07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