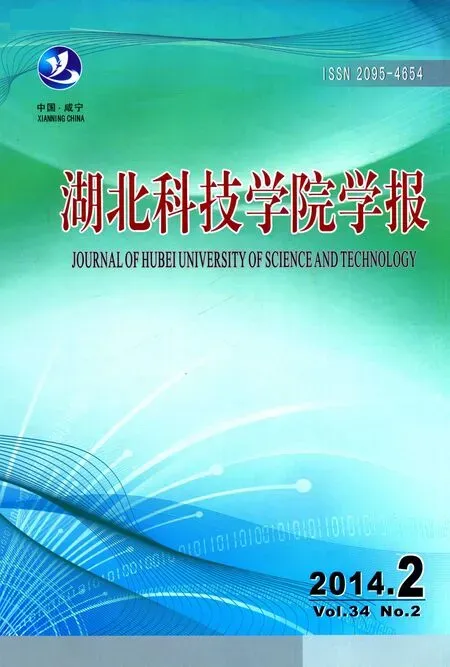艾米丽·狄金森的生死观——以《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为分析文本 *
陈明安
(湖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美国女作家原本屈指可数,而在这少数的女作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艾米丽·狄金森,她生于1830 年,此时,美国的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业已完成他的杰作《征服格拉纳达》,并又开始构思《阿尔登伯拉传奇》,但是晚起步的艾米丽·狄金森的文学成就堪比华盛顿·欧文。如果说,华盛顿·欧文用一只“蜡笔”刻画了美国的山水,平原,瀑布等风物,那么,那么狄金森却用的是一支“工笔”精致地刻画出了美国人的“灵魂”,这灵魂比大海更广阔,难怪亨利·詹姆斯称她的诗歌是“灵魂的风景画”,殊不知詹姆斯本人就是灵魂的探秘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更是称她为“圣恩主”[1](p.305),以表示对她的崇敬。艾米丽·狄金森一生写诗1775 首,这些诗“仅供自我欣赏,除了个别诗外,生前从未发表”。[2](p.30)其中五、六百首是直接关于死亡的,加上其他间接写死亡的诗歌接近上百首,加起来,死亡题材占了她所写诗歌的比例接近40%,剩下的诗歌有关爱情,自然,宗教等,但是所占的比例远远比不上死亡为主题的诗歌的比例。这种情形在美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罕见的。“死亡”无论是在东方文化语境还是西方文化语境,都是一种禁忌语(taboo)。人们一提到这个字眼,仿佛死神就会扑面而来,使人心生恐惧。而艾米丽·狄金森在“死亡”面前没有这样感觉,她一直思考“死亡”,并使其在笔端凝聚成诗,构成自己诗歌的主导题材。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它集中体现了作者独有的生死观,其文学艺术性,思想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汤姆斯·约翰逊的判断,她创作此诗的时间是在1863 年,这一年正是她生活的分水岭。之前,她性格外向,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朋友,包括伦纳德·汉弗莱,查尔斯·沃兹沃思,在这之后,她蜗居在家,真正成为了一名宅女,这种变化缘起于她的感情受挫,但却无形中却给予她一个好好了解自我,关照自我的机会。表面上她对外面的世界变得冷漠,但实际上她这是在“大隐隐于市”,她对外界封闭的同时,却开启了自我的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宁静中,她冥思着自我,而自我的局限性问题或自我的灭失死亡问题自然而然成了她心中难解的问题。正是由于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让她成为了一个哲学家般的诗人,但与哲学家不同的是,她以诗歌的形式回答人往哪儿去的终极难题。这个问题也是关于灵魂有无的问题。了解诗人对这个问题如何回答,也能使读者了解到美国非物质、非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状态特点,因为她在美国得到很高的赞誉,能代表一定历史时期美国的价值观点。因此研究她的诗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死神“伪君子”无情揭露
《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这首诗共分为五节,是一篇有关旅程的诗歌。根据内容,全诗又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歌的第一节,写的是作者上了死神的车驾,开始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到第四诗节,写旅途过程中所见所闻。第三部分为第五节,车驾到达旅程终点,并开始了另外一个谜一样的旅程。
诗人在第一部分即第一节中写了这次旅程的缘由以及参与人员。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死神是这次旅程的主角,因而他的形象被重点刻画。让读者感到意外的是,死神是以一种别具一格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下笔并没有描写死神样貌,而是写了他的动作“拦住”。这个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但是,作者明确交代,他是以一种友好的方式拦住我,请我上他的四轮马车(carriage),而且作者为了进一步强化死神温柔,为死神拦住我——尽管这一方式已经很友好,而作开脱,诗人写明死神无意拦住我,只是“因为我不能停下来等他”,诗人通过这样简单的诗行里揭示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局限性:人什么时候会“上”死神的车驾,或者更加直接地说人什么时候死亡并不是由本人决定的,而是由死神决定——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诗人曾在信件中坦露自己在人总是要死这条钢铁般硬冷的规律面前的无奈心情,她经常会想到死亡,想到它离自己究竟多远,想到自己无力阻止它夺去自己的亲人和朋友。[3](p.198)死神力量的强大隐藏他谦谦君子的外表之下,所有很多人容易被蒙骗,以致在西方谚语中说“死亡是睡眠的兄弟”,死亡似乎能让逝者安息。但是,诗人是清醒的,她认为,死神外在的友好和安详不能改变他注定限制个人之生的意志自由这一非友好,非平和的本质。在本诗第一诗节中,诗人还介绍了车上的“乘员”组成:死神,“我”,还有“永生”朋友。“永生”的出场是轻描淡写的,而不是粉墨登场的,在本第一诗节的第三行,诗人写到“车上只有我们自己”,而第四行,诗人以补充的口吻写到“还有永生”,这样行文意在表明“永生”地位的低下,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开始只是个多余的存在,这也就衬托了死亡力量的主导性地位。
诗歌的第二节与第一节在意义上来讲,可以合并为一个部分。与第一节相比,本节是进一步强化第一节的意义,突出死神形象的双重性。本诗节的第一行,诗人写到:“我们缓缓而行,(慢慢驾驶着马车)他知道无需急促——死神他不知道什么叫匆忙。”死神的“君子”形象和从容不迫延伸到他的驾车行为上来。车马是缓慢前行着,死神表现出仿佛观光旅游那很悠闲的样子,这也为诗人在第三节进一步描写沿途的“风景”埋下了伏笔。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用了施动者“我们”,好像“我”也是个驾驶者,但根据下文“他不知道什么叫匆忙”说明死神才是这个马车的主宰者,他掌握着马车行驶的节奏和方向。而我和“永生”只是一个乘客,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字里行间,死神的从容,胸有成竹的形象进一步被凸显出来。这种形象颠覆了西方文化语境中死神拿着镰刀的恐怖形象,彰显出作者的创造力。本诗节的第二、第三行,进一步丰富死神的意象,表明我坐上死神的车驾后,已经失去了我的自由,包括工作忙碌和休息的自由。第四行中的“文雅”(civility)具有反讽意味,诗中字面意思说“因为感动于死神的‘文雅’,我才上了他的车驾”,但实际上表达了死神的“伪装”与“诱惑”。死神如同诱惑天真少女的“伪君子”一般,诱惑“我”上了他的车。这样,诗人有意或无意运用衬托的手法:以弱小、无知,茫然不知所措的“我”来衬托死神的强大、“胸有成竹”和淡定。诗歌的张力也顺势体现了出来。总之,通过第一和第二诗节,一个本质上并非友好而是残酷的死神形象被塑造出来。
二、对此生无限眷恋
诗歌的第三节集中反映出了诗人对生的态度。虽然有死亡的存在,但是诗人并没认为人生是虚无的,从而给自己贴虚无主义者的标签。相反她是热爱生命的,并且享受生命的过程。诗歌的第三节内容表明了这点。
诗歌的第三节描绘了马车途经的三个地方,观察者是“我”,死神虽然没有被提及,但是他隐藏在“我”的背后,影响着“我”观察事物的心态。本诗节第一和第二行提及的是一所小学,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趁课间休息时间正在嬉闹,玩游戏。诗人寥寥数笔,却勾勒了一个无穷大的想象空间。一边是驶向人生终点的死神的车驾,一边是天真单纯的正玩耍着的孩子们,他们哪曾注意到一个生命的凋谢。而作为马车上的我,看到这一切,流露出对“生”的依依不舍,也夹杂着对健康快乐成长的孩子们的祝福。在这里,诗人再次运用比较的手法,以孩子们的幸福衬托“我”即将面临的厄运。
接下来,本诗节的第三行写明路过一片谷物地的情形。在这一诗行中,诗人十分巧妙地用到一个词“gazing”(凝视着的)来修饰谷物,从而让静默的农作物人格化了。结合下文的第四节“露珠”物象的描写,说明这是一片秋天的谷物地。成熟的谷物原本是低垂着头的,但是当有车马经过时,谷物如同有了知觉的人一样,被惊动,于是纷纷抬起头,“凝视”着那缓缓开过的马车。与上面诗行孩子们没有注意到马车在旁边经过这一情形不一样,本诗节中的“谷物”注意到这旁边行进着的马车,而且“谷物”意识到这不是一架普通的马车,而是“灵车”,所以他们“凝视”着,目光随着“灵车”移动。不难想象,这氛围是肃穆的,秋天的空气中有淡淡的忧伤。如果说本诗节的第一行和第二行说的是“我”留念孩子们的欢乐与喧嚣,那么这一行写的是安静的送行。通过写谷物对“我”的“目送”,进一步表明“我”对尘世的不舍与眷念。本诗节的第四行写到“我们路过正在沉落的夕阳”,这里的描写是写实的,有强烈的画面感,还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因为“诗人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大师约翰·济慈的影响”[4](p.59)。诗人用“路过”夕阳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搭配,意在表明在美丽的黄昏时分,太阳回到地平线,身躯变得庞大,近在咫尺,仿似“停泊”在马车附近,因此说“路过”夕阳,恰如其分,也让整个诗的意象空间变得更加宏大:这是一辆以宇宙为背景而运动着的马车,反衬出车上的乘客“我”内心的孤独和荒凉,以及无助,也揭示了“我”心底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叹息。
至此,在本诗节中,诗人连用了三次“经过”,经过的地方分别是快乐的学校,成熟的庄稼地,和黄昏下的落日。对这些意象也可作象征性的解读,即学校象征人的童年阶段,庄稼地象征成年,夕阳象征晚年[1](p.305),国外评论家也有相似的看法。但是,如果单纯地去解读本诗节,也能品出诗歌中的另外一份美丽意境,正如前段所述,诗人即通过一系列唯美意象——运动着的马车上所见之物的描写,揭示了对美丽尘世的留恋。而且不从象征的角度解读本诗节,使该诗节的内容与下诗节更加连贯。
诗歌的第四节,紧承上节,随着太阳最终落入地平线,光明与温暖(尘世的温暖)已经远去,寒冷的黑夜即将降临。诗人用了意象“露珠”这一细节来写这种外在的“寒”,再加上“我”穿着薄薄的丝衣,使读者感觉到“寒彻骨”。由此,整首诗的气氛显得很凝重。另外,从“我”穿的薄薄的织物来看,也可说明“我”还不曾为这即将到来的“死亡”旅程作好充分的准备。这也说明死神并不像一些评论者认为的那样呈现出仁慈的面孔。他逐渐呈现出冷酷的一面。最终是死神把“我”从光明引导向黑暗,从温暖引导向寒冷。
诗歌的第五节是本诗歌的结尾部分。死神的马车最终停留在一个房子前面。实际上这个房子就是坟墓,但诗人没有明确说出,这亦表明诗人写作风格上的内敛和含蓄。在意义上,本诗节对应的是“我”在世间生命的正式结束,反推前面,从死神拦住我,上他的车对应的便是“我”即将踏上死亡之旅,正是我生命弥留之际的开始。最后“我”显然是被死神赶下马车,进入狭小地下空间,而当死神达到了自己目的后就此抛下“我”,不知去向。毋庸置疑,死神的“伪君子”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形象在世界创作史上也是罕见的,它能充分显示女诗人的创作才华,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盛赞诗人在创造性方面不亚于莎士比亚[5](p.272)。
三、对来生的坚定信仰
但是这段旅程的终点并不是墓穴。本诗节的第五行写到“从那时起——几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感觉到比一天光阴还短。”这指的是从进入“坟墓”算起,几个世纪很快就过去了,而这几个世纪虽然很漫长,但是过得很快,比一天都还快,正所谓“时光如电”。诗人如此在另一个世界里创设了一种新的时间概念。在那里,时间论“世纪”来过,而不是生的世界里论年或者论天而过。在那个莎士比亚看来没有旅人归来的世界里,时间似乎是无限的,正因为手头有无限的时间,所以几个世纪这样大尺度的时间概念在那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生的世界的一天一样。所以诗人最后总结到“我开始猜测到,死亡的马车是朝向永恒的”。诗歌的最后一个词“eternity”(永恒),正是传达了对永恒的信仰。而且,更令人意外的是,全诗不是以句号结尾的而是破折号,它接在“eternity”(永恒)之后,更是形象地彰显了这种永恒的状态,破折号象一根射线,暗示这种状态永远持续着,没有终点,向远方延伸,这也更表明诗人对死神持有的否定态度。
纵观全诗,这既是一首写死亡的诗,也是一首写永生的诗。关于永生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足以成为诗人心灵的慰藉和寄托。一方面,死神以表面温情,实质是残酷的方式剥夺了我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永生与死神一样宰我的生命,只是他主宰我的灵,并且对我影响更长的时间,而这正是我的归宿。按照常理讲,死神与永生似乎有前后因果关系,是因为有了死神才有永生,但是从诗歌的第一节,诗人传递的意思却是死神与永生同时坐在马车上,并没有先后的关系,所以作者并没有能获得永生而感谢死神。在诗人看来,死神与永生是两种并列的力量,他们平起平坐,死神并不是获得永生的前提条件。诗人脑海中永生的概念是对死神的再次否定。显然,诗人内心无论怎么豁达,但是,死亡的概念常常盘桓在脑海,这恰恰反衬出诗人是热爱生命的,诗人很重视并享受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她害怕这些因死亡而失去。比如在《我死时听到了苍蝇的嗡嗡声》这首诗中就提及到诗人对亲人,以及亲人对诗人离开的不舍。而加尔文教——虽然是诗人顺手可依的宗教,但因否定尘世的美好,不能被诗人借用以便消弭内心对死亡的焦虑和不安。诗人只能信仰永生的力量,信仰灵魂不灭,这正是诗人对自由意志终极追求的体现,这也是诗人对死亡超脱的方法,即“随死神前往,一如和永生同行”[6](p.15)。于是,永生的灵魂赋予了诗人的生存全部意义。
作者世俗的生命终究结束。1886 年,艾米丽·狄金森,一位天才诗人,香消玉殒。如果真有她诗中所说的“永生的世界”,那么她宛如星辰,俯视着自己的家乡——阿默斯特镇,她的灵魂将永远不会离开那里,“几个世纪如一日”地守护着那里的人们。
四、结语
如果说欧文的作品还在“山寨”着欧洲的文学,爱默生(1803—1882)倡导着美国文学的独立,而作为美国女作家艾米丽·狄金森,似乎听见了爱默生的呼唤,有意识地以实际的写作行动展示着自己独有的思想,进而体现着独特的美国文学特色,印戳着美国的时代烙印。难怪,阿尔弗雷德·卡津称她是“新英格兰第一位现代作家”[7](p.7),而此时说她是美国的女马克·吐温一点不言过其实,象马克·吐温一样,她能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代表美国本土文学的特色。
美国人因追求灵魂的自由而漂洋过海,来到一块原始神秘的土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探索,求新,追求更大的自由。这些精神也深入到艾米丽·狄金森的骨髓中,她的诗歌因正扎根在美国文化的土壤中,而凝聚着这种民族精神。艾米丽对死神的描写充满了创新,探索意识,对永生的向往就是对自由的向往——灵魂不受约束的自由,而对永生一丝不确定性色彩,又使一个清教徒的焦虑跃然纸上。但是,在上帝与世俗之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艾米丽·狄金森最终让信仰偏向天平的永恒端。她活着的时候,人们不曾称她为是位作家,但如今,她已经进入美国杰出作家的行列,比肩欧文,爱默生,霍桑等人。对于艾米丽·狄金森而言,死亡意识正是她生命自觉的重要表现,也是她内在心灵最勇敢的裸露。她专注死亡,是因为热爱生命,她追求永生,是因为她对此生生命热爱的升华,也是她对自由的终极追求。虽然她的心灵天空总有死神的乌云笼罩,但她却是彻底的乐观主义者,她不仅享受此生的生命过程,还对来生有着憧憬。从这个角度讲,以宅女为生活状态的她,其实并没有真正把自己“宅”了起来,她的心灵没有被囿住,而是占据整个宇宙,她的名声也没有被她的居所限制,而是声名远扬。没有一艘船能像她的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她笔下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向无穷的远方……
[1]常耀信. 美国文学选读[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秦寿生. 英美文学名篇选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Thomas Johnson.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4]刘保安. 美国诗歌艺术史[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5]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M].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4.
[6]吴忠诚. 现代派诗歌精神与方法[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7]Alfred Kazin,An American Procession[M]. New York:Knopf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