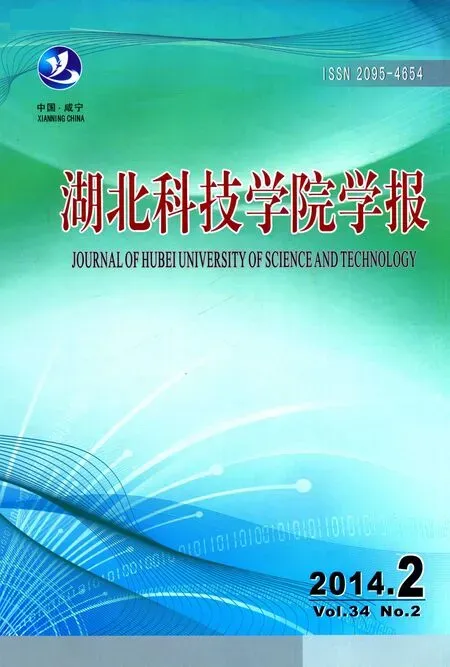基督教文化对冰心早期“问题小说”创作的影响
饶眺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中国现代作家中,其创作明显受到宗教影响的可谓举不胜举:鲁迅、许地山、老舍……相较而言,把西方基督教义理大面积渗透到文学作品之中,极力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家却鲜见。冰心无疑是当时耀眼的一位。
基督教是信奉上帝的宗教。历史上有过不同的教会形式;但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基督教,却有着许多相似的信仰和观念。就基督文化的意义而言,博爱和同情是冰心体验最深刻,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而且,这种博爱和同情都是超阶级的。基督教要求信徒去爱人,去同情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只是把“爱”作为检验对上帝虔诚度的标准。显然,这种“爱”只是一种原则而不是感情。受其影响,冰心却把这种“爱”只作为伦理、道德精神。她早期“问题小说”里充满了这种基督式的博爱和空虚的同情。这些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抒写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不满情绪,二是反映下级官兵生活和反对军阀混战,三是从人道主义立场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一
作为刚从封建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冰心对封建势力和旧礼教有所否定和揭露,对被封建势力吞食的弱小者有所同情,冰心1919年9月连载于《晨报》的处女作《谁之罪》(即《两个家庭》)中,她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小说中,陈华民娶的是官家小姐出身的太太,不会治理家政,不仅不教育孩子,不管家务,还整天打扮得珠光宝气出去打牌或应酬宴会,家里虽雇了三个老妈子,却各个护着各人的少爷,常常吵嘴打架,不得安宁。这影响丈夫的事业,摧残丈夫的身心。相比较而言,三哥与他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论职位没有他高,论薪水也没有他多,却有一个贤惠体贴、精明能干的太太,她不仅把家政管理得妥妥贴贴,孩子教育得聪明懂事,而且还能帮助丈夫翻译书籍,就连雇来的老妈子也被教会念字片和《百家姓》。毫无幸福可言的家庭生活是导致陈华民的深深惋惜和同情之情。
《去国》是写一个想贡献自己力量和才智给祖国的青年留学生,却不为当时的政府所接纳,反映了有爱国心的留学生和军阀政府之间的矛盾,揭露了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作者在揭露和谴责的同时,却同情了从旧民主主义战场上退下来的父亲朱衡。为了突现作者的这种同情之心,小说安排的结局便是儿子重蹈父亲败退的覆辙,再次去国而另觅资产阶级的“乐土”。与此相类似,《斯人独憔悴》中,汉奸父亲和略有爱国心的下一代之间冲突的结局,也是爱国心的屈服,两个曾有爱国行动的青年做封建买办家庭的顺民,变为既成事实。作者没有鄙视主人公思想的软弱,却对他们的“憔悴”寄予了同情。在《最后的安息》中,作家一方面控诉了封建社会童养媳的罪恶,另一方面却宣扬用同情心来消灭贫富之间的间隔,造成“爱”的世界。
由此可见,冰心初期的此类“问题小说”虽也确实提出过一些问题,勾起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对封建势力的某些不满。可是,冰心虽然不满封建势力的压力,却不敢正面触动它。她绝大部分“问题小说”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无力的,几场尖锐的冲突经她一处理,变得黯然失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博爱”和“同情”的召唤之下,以一种改良、逃跑或妥协的方式解决了。
冰心在“五四”高潮中所写的问题小说的另一类题材是有关下层官兵生活和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一个军官的笔记》中那位青年军官原想为国效命而从军,结果却发现自己不是为着公理正义战斗,而是为“少数主战者”卖命,这分明是“军阀的走狗”,不仅“出师无名”,而且干的是“卑贱的事”。这个作品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态度也比较鲜明。另外,在《一个兵丁》和《到青龙桥去》等作品中,冰心也寄无限同情于下级官兵。
我们不难发现,冰心的这类作品里“只有厌恶战争,只有婆婆妈妈的和平主义,只有些安居乐业的‘理想’……”当时,在冰心看来,只要反对战争,世界就光明,人们就和平。但是,在冰心笔下,如《一篇小说的结局》、《鱼儿》等作品中,她并没有具体写出战争的社会背景,背景不清则性质不明。这种将战争背景抽象化的反战小说会使人们不加区别的反对一切战争,甚至连正义的战争也加以反对。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给作者扣上一顶“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且,在这里,冰心还是以基督的“博爱”观来反对战争的。作者在作品中曾这样写道:“可怜的主战者呵!我不恨你们,只可怜你们!忠平呵!我不记念你,我只爱你!”她大概想的就是想通过“可怜”来感化军阀,停止战争。这里表现一种以超阶级的博爱观点来反对战争,“婆婆妈妈的和平主义”是冰心这类题材作品中消极的一面。
二
冰心写的反对封建势力的军阀混战题材的“问题小说”大概只坚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随即沿着作品中所呈现的博爱和同情的斜坡逐渐走向更博大的“爱”“爱的哲学”,开始从道义立场关注普通民生。母爱、童真、自然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国旗》、《超人》、《烦闷》等是这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之作。
《国旗》的主题思想便是借天真的儿童之口说出的:“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得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个国。”这并非是儿童的戏言,而是作者借童真之口,幻想用无国界的爱来乞求祖国的“安宁”。在《超人》里,冰心设置一个冷漠的心,再设置一个母亲的爱。禄儿的呻吟是两者之间的桥梁。最后完成了一个寓言:冷漠的心如何被母亲的爱感化,从而表现出主题:“世界上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在论述“自然之爱”时,冰心常常用的是“造物者”这一称呼来表达。在她的思想中,造物者是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神,是万物的“母亲”,“茫茫的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界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正如基督教义《圣经》所说:“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冰心的“爱”是神性与人性、自然与亲情的融合,她将母爱、童真、自然爱三者统一起来看,体现出了冰心的人类之爱的博爱理想。她企图从母爱的深沉、童心的纯真和自然的壮美中寻到精神危机中的“避风港”。她劝说那个时代的青年,当感到人生虚无时,当在黑暗的现实中受到心灵创伤时,可以用本能的、天性的、无条件的母爱来治疗,并主张由这种母爱而发展的博爱来解除社会上的罪恶,来拯救苦难的众生。
三位一体的“爱的哲学”建立,目的在于疗救社会,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呢?这即是冰心此类小说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之所在:儿童是通过与母亲溶为一体,而人类在童年是通过与大自然取得和谐,宗教表达的是人类与上帝建立和谐关系的精神上的追求。事实上,在冰心“爱的哲学”中,“母亲”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而被转化为宗教般的上帝。她用的是基督教神学中证明上帝存在的五大原则之一“以果求因”法。即从宇宙间一切的天地万物而推导出最初的设计者造物主(即“母亲”)。这一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并非是“盲触”的结果,而是造物主的化育(即“母亲”的孕育)而成;因宇宙万物而推导出创始成终的造物主,靠着这造物主“慧力的引导”,人在母爱、童真和自然中所受的感悟也正是对上帝“爱”意的领受。
三
茅盾曾在《冰心论》说:“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冰心和基督教文化的确有着很深的情缘。冰心的早期创作风格正是在她个人经历、文化环境的独特性和时代因素的共性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1900年,冰心出生在福州的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其幼年时代也是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里度过的。由于她出生的时代正好处在“戊戌变法”惨遭失败之后,加之其家庭相对开明,所以她的个性能够较为自由地发展,在她眼中,世间万物都是那么的单纯明朗,充满仁爱。
除此之外,冰心从小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据她回忆,她的家庭与基督教会有一定关系,二伯父在一所教会学校(福州英华书院)教书,书院里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曾来家中做客。冰心说“父母对她们的印象很好”。家迁到北京后,冰心得以进入美国卫理公会办的贝满女中读书。
冰心所在的贝满女中,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教会学校那样封闭和专制,正是在这里,冰心系统地学习了《圣经》,而且《圣经》课和英文的成绩是最好的。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由本校中美教师或卫理公会的牧师来讲道。冰心回忆道:“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
贝满女中毕业后,冰心先后又考入协和女大(后并入燕京大学)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她继续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冰心在她的老师包贵思的陪同下,在一位老牧师家里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从此,基督教文化在冰心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基督教精神已渗入冰心的情思之中。正如她自己所坦言:“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正是这种爱的哲学,构成了冰心早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纵观冰心早期的小说创作,我们能感受到“博爱”和“同情”中所浸透着的浓浓的基督教文化气息。在这种文化气息的浸染之下,作者早期的“问题小说”以自己特有的视角,针砭时弊,揭露现实,抒写人生,拯救民众。虽笔端处处略带夸张,思想也不乏稚弱无力,却也在时代的兴味征途上独具一格,这种沉积在早期伤口中浓郁的宗教情素,为冰心日后数十年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浓厚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基础,使其终生都在以自己的人格与艺术热情播种“爱”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