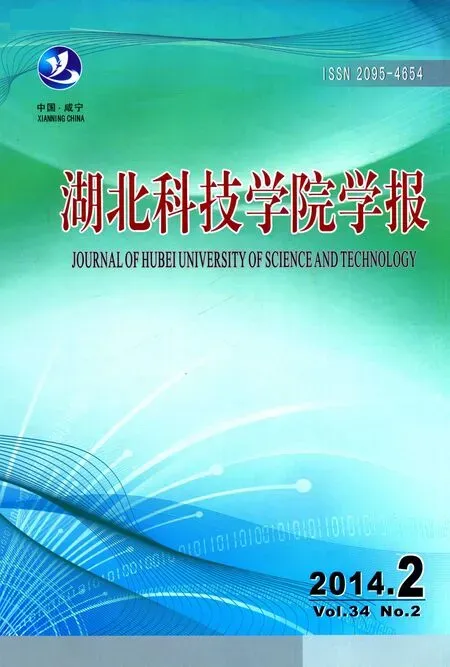试论《格萨尔》史诗婚俗事象的特殊形式——“抢婚”
王军涛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人类的婚姻史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藏地婚姻的影响,世人们从很早的时候便开始对其进行关注。早在一百多年之前,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同样都属于意外情况;关于它起源于群婚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2](P42)并且在文中对荷马的史诗也进行了分析,恩格斯将其定位为从野蛮时代步入到文明时代的重要产物,在这种引征过程中将其作为了鲜活的化石。《格萨尔》史诗中婚姻内容的反映,相比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对婚姻的反映而言,比两者反映婚姻情况的总和还要多出许多。若恩格斯仍然活着,或者《格萨尔》史诗进入到欧洲的时间能够更早,恩格斯必然会将其作为重要的例子来进行引征。
的确,《史诗》中蕴含的婚俗异彩纷呈,包罗万象。纵览《史诗》你会看到:原始群婚制的残余、一夫多妻制的痕迹、普那路亚家庭同胞姐妹共嫁一个丈夫的遗俗、对偶婚制、族外婚制、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罚婚、赠婚、赐婚、收继婚、抢婚等等不一而足。使人仿佛在了解一部别样的百科全书似的婚姻史[3](P13)。正如上述引文所及的那样如果“倘若”存在的话,恩格斯必然会将其作为重要的例子来进行引征。
但是,在婚姻缔结的万千形式中存在“抢婚”这一缔结形式,“抢婚”无疑是增添史诗艺术性,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最特殊的形式[4](P26)。
一、“抢婚”的直接原因是族外婚制的实行
摩尔根曾经提到过:“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3]。”而对这一自然法则在认识过程中,世界各民族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蒙昧期才获得的。因为诸多的自然法则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原始的兄妹通婚才逐渐被人类社会所排除,不同血缘家族和各种部落也因此而产生。在原始的氏族部落中,部落之中是严禁通婚的,部族中提倡和另一部族之间通婚,部族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也因此逐渐被淡化。但是这种血缘关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随着部落社会后期时代的到来,因为部族之间为了满足军事发展的需要,部落和部落之间逐渐形成了联盟关系。《格萨尔》史诗中对岭国六大部落的描写中就指出,这种联盟本身就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基本的联结纽带而形成的。所以在部落婚姻形式上的表现中,部落之间的通婚问题并不存在,实行更多的是部落外部落通婚的形式。其实也就是“在一个部落中的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所以,若一个氏族部落中的男子在部落中达到了娶妻的条件之后,但是必须在部落之外的女子中选择。”这时已排除了人类历史原始阶段“部落内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
《史诗》的《英雄诞生》之部中说:“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女罗刹跑到猴子菩萨的身边说:‘我俩同居到一块儿吧,应终生相伴才对’﹗猴子菩萨听后说道:‘我是猴子之身,臀部拖着尾巴,身上长着兽毛,脸上堆着皱纹,我不能做你的丈夫,供你情欲使用,最好你去找一个比我更好一些的男罗刹满足你的欲望好了……’。女罗刹说我若去找一个男罗刹做丈夫,那将生下许多罗刹小娃娃,因父母都是罗刹,将会产生不良后果,只有和你才能生下一个聪明的小孩’,……”。再如《史诗》中说,霍尔部落首领白账王丧妻,他发誓要找一个绝代佳人续弦,但在霍尔部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派兵抢劫了格萨尔的王妃森·姜珠牡,挑起了规模空前的部落战争——霍岭大战。当格萨尔为征服霍尔部落潜入其腹地时,发现一位名叫葛萨曲钟的少女,她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格萨尔为之动心,立即与她结合。霍尔王放着眼皮底下的美女不娶而兴师动众地去抢掠人家的妻子,格萨尔对他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霍尔魔地竟有如此绝代佳人,岭地珠牡虽然名声大,但真正的美人还是这葛萨曲钟姑娘。那么霍尔王为何不娶她为妻呢?莫非她是其近亲[4]?”(近亲无疑,笔者的理由见前文相关注释)这两个故事就很能说明,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藏民族已经意识到在具有血缘关系的部族中通婚会对下一代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族外婚姻是部族婚姻在发展中必然面临的趋势,是为了能够使部族吸收到更先进的血液,能够“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较为强健的人种。”
正是由于族外婚制这个直接原因的刺激,《史诗》中的部落首领“在对妻子的寻求过程中并非仅仅只局限于自身部落女子中,甚至同盟部落中的没有局限,而是通过征服或者侵略其余敌对部族,降敌对部族中的女子作为妻子[5]。”
二、“抢婚”是《史诗》诸多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格萨尔》虽然篇幅很长,但其内容主要是描写战争的,写主人公格萨尔登上王位后统率岭国将领、英雄和人民,战南征北,与一个个来犯的部落或邦国作殊死的浴血奋战,直到对方归顺称臣于岭国的整个过程。”“约略统计证明在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以战争为主体的篇章至少占总篇目的95%以上。”“全部史诗的内容主要是战争。从降服妖魔一部起,降服18 个大宗是战争,降服许多中宗是战争,降服许多小宗也是战争。”[6]根据史诗中的大量描述,诸多的著名战争都因为抢婚而引发。如《降伏妖魔》、《松岭之战》、《霍岭大战》、《门岭大战》等就是带有抢婚目的的典型战例[7]。
《降伏妖魔》是北方魔王路赞抢去了格萨尔次妃梅萨绷吉从而挑起了战火;《松岭之战》是超同抢劫了松巴公主从而引起了双方的战端;“辛尺国王有公主,梅朵拉孜最美丽。她一人智慧胜百男,一人俊秀胜百女。我们岭国众兵马,为高攀门王求亲来此地[8](P86)”则是岭军冠冕堂皇的战争借口;“我霍尔十万众兵马,今向白岭去开战,要把所有男人都杀光,要把所有城堡都毁完,要把美姑娘夺到手,了却我出兵的心愿”则一语道破了抢劫珠牡是霍尔白帐王“出兵的心愿[9]”。
“抢婚者”虽然能点燃战争的导火索,却不能凭自己的意愿乱了等级的胡强乱抢、强行婚配。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点燃战争导火索的“抢婚者”,有胜利者,有失败者。胜利的“抢婚者”欢天喜地、喜气洋洋、傲视天下;失败的“抢婚者”则要受到百般侮辱和折磨,再做极刑处理。白帐王这个引起霍岭战争的“抢婚者”,战败被俘后他被捆绑起来,押解至东门外广场,格萨尔将马鞍放在其脖子上,把金轡勒在白帐王嘴里,骑于鞍上,以剑带鞭,驱使他向东西南北各跑三趟,最后砍头暴尸。连他与珠牡所生的未断奶之子也未能幸免于难。部落战争的残酷之极可见一斑。正如恩格斯所说“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而他的部落从此还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依附于战胜部落,因而其痛苦更甚。至于抢婚中被劫掠、被俘虏的年轻妇女们,是没有权利来选择自己命运和前途的[2](P74)。“今日让我母女俩,怎么来做都可以”。门岭之战中被俘门国公主的这句回答则是对“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的最好注脚[2](P94)。抢婚更是对妇女身心的无情摧残。
三、“抢婚”的实质内涵
不难看出,《史诗》的一些篇目本身就体现了争夺财产的特点:大食牛国、卡契玉国、象雄珍珠国、祝孤兵器国、上蒙古马国、下蒙古玉国、珊瑚聚国、岗日水晶国、丹玛青稞国、白日羊国、阿色甲国、朱努绸缎国、西宁马国、阿乍玛瑙国。这些国盛产与国名相称的财货,格萨尔出兵与他们相斗,目的还在于获取财货。
那么,《史诗》中的抢婚即对美色的垂涎欲滴、暴力劫掠仅仅是敌方首领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发动战争的不理智行为吗[8](P330)?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敌人抢夺英雄的妻子,还是英雄救回自己的妻子,都只是为了一个女人的美色。敌对部落的首领因为对美色的沉迷,英雄的复仇乃“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史诗中的一种对抢婚出现原因的阐述。若从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上对其进行分析,一种非常圣神的光环笼罩着英雄之妻身上。在自身部落流传的神话中和相对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神话中,神话原型和前身都是英雄之妻必然拥有的。她作为了自身部落的女神,人口和财富都能够因她而体现[2](P58)。但是《史诗》中对部落战争情况和因素的反映,掠夺财富和人口成为了首要的原因。在《史诗》中这种战争的基本目的得到了艺术化,艺术化之后就变成了掠夺英雄之妻,为部落的发展奠定基础。对英雄之妻的掠夺不仅仅是因为她自身的美色。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她作为了整个部落的命脉,象征着部落的财产和人口,对英雄之妻的争夺也就是对该部落人口和财产的争夺,古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战争也多数是因为这一实际情况[10]。
那么史诗中的女主角珠牡的神话原型是什么呢?当然珠牡的情况复杂一些,因为这一史诗既受藏族本土古老文化的浸染,外来的佛教文化对它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珠牡的身上留下了两种文化的痕迹,对此我们应该一一予以认真的分析。按史诗中最直接的说法,珠牡的前身是白度母:“这珠牡本是白度母的化身,聪敏美丽,心地善良[10]……”我们可能对“度母”的定义没有进行仔细的了解,其实“度母”也被称之为“救度母”和“多罗母”等,是对藏传佛教中女生的称呼,传说“度母”便是观世音菩萨为了救苦救难而化身的女生,从颜色上能够划分成21 个相,其中最常见的便是白度母。在藏族地域中,人们都因为白度母的地位对其非常尊敬。当人们丰收或者得到财富之后,都要对白度母行奉献礼仪。例如格萨尔进军大食,在将大食征服之后,得到了数不清的牛羊和俘虏,而后便凯旋,和做出杰出贡献的将领们一同分享战利品,在分享之前也为白度母唱了第一首供歌,可见百度母从很早时候就在藏族地域中确立起了自身的地位。充分体现出了这位女神的地位和她拥有的财富。将珠牡看做佛教女神白度母的化身,无疑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很大影响。但我们可以推断,佛教传入藏区前,珠牡肯定有一个与白度母神性相同的神话前身。由于佛教神灵体系对藏族本土神灵的冲击,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珠牡的本土神话原型。但是事关珠牡的一些雪泥鸿爪、蛛丝马迹的存在,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佐证。寄魂观是藏民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传说珠牡的灵魂寄托在扎陵湖中。扎陵湖是个神湖,湖水清丽明澈,吉祥神秘。这个湖实实在在地位于黄河源头的玛域地方,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信仰仍不绝如缕。据著名的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考察,在扎陵湖中沐浴能够使自身的头发变得更加乌黑,更加细密,这是藏族妇女们到现在都深信不疑的。当地较为流传的《珠牡歌》中就唱到:“六为相尼恰普沟脑,七为相尼恰普沟口,八为扎陵湖岸的峭壁,九为东措嘎尔茂湖的波浪,十为颇章达泽宫的威严容华。十种光华吉祥聚集的福地上,我嘉洛森姜珠牡是主人[11]。”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一直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流传着。那儿有座草山,当地藏民称它为“珠牡山”。传说珠牡幼年时曾在这座山上放羊,与格萨尔相爱定情。这座山的青草,每年都比周围山上的草早发芽。辐辏于珠牡身上的这些传说和信仰,无疑很好地表白了她的神话前身。总之,“珠牡作为白度母,一马当先享受牛羊牺牲的馨香,足以证明她在决断财富方面无可比拟的神威。在藏族古老的信仰和传说中,珠牡也能促进青草的生长、妇女的健康和牲畜的繁衍,也与丰产和财富及人口有关[11]。”
揭开笼罩在“抢婚”表面上的一层面纱,不难发现,抢婚“原来不光是争夺她的美色。更重要的,她是部落的命脉——人口和财产的象征,争夺她也就是争夺人口和财产”。掠夺财富才是抢婚的根本目的。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中“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11]
而“抢婚”中以争夺身为王后、公主的美女则是这种掠夺战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拂去“抢婚”的深层内涵、特殊象征意义,从客观来讲,一国王妃公主的安危往往标志着一场战争谁胜谁负,劫掠她们常常伴随着该国家的彻底沦陷和王宫被洗劫一空。占有她们是对这个国家国王尊严感的莫大侮辱,男子武功的高度蔑视和氏族荣誉的极端玷污。所以把抢婚中被劫掠的美女作为战争的焦点乃是出于对掠夺战争的高度概括。
四、结束语
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赖以生存繁殖和延续的主要方式。一个民族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意识和社会状况。一部文学作品里所描写的婚姻状况,正是那种状况所处的社会的一面镜子。《史诗》中关于婚姻状况的描写是比较丰富的,它真实地反映了藏族社会的历史面貌。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提出了“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现象[11]。”接着“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2](P160)”。《史诗》里所描写的由暴力抢劫妇女的“抢婚”而引起的战争,无疑真实地再现了人类蒙昧时代的一种婚姻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研究人类婚姻史的资料。
[1]李雪琴.《格萨尔》史诗中的婚姻与家庭[J].民族文学研究,1989,(6).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
[3]霍岭大战(藏文)下部[M]. 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386.
[4]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63.
[5]王兴先.《格萨尔》论要[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189.
[6]徐英国.《格萨尔王传》军事思想研究[J]. 青海民院学报,1993,(4).
[7]王沂暖,唐景福.格萨尔学集成(第2 卷)[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806 ~807.
[8]王沂暖. 门岭大战[M]. 余希贤泽.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86.
[9]霍岭大战(上部)[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0]何天慧.《格萨尔》史诗中的藏族婚姻浅析[J]. 西北民族研究,1992,(3).
[11]罗明成. 争夺英雄妻子母体的社会文化研究——以几部有代表性的英雄史诗为例[J].民族文学研究,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