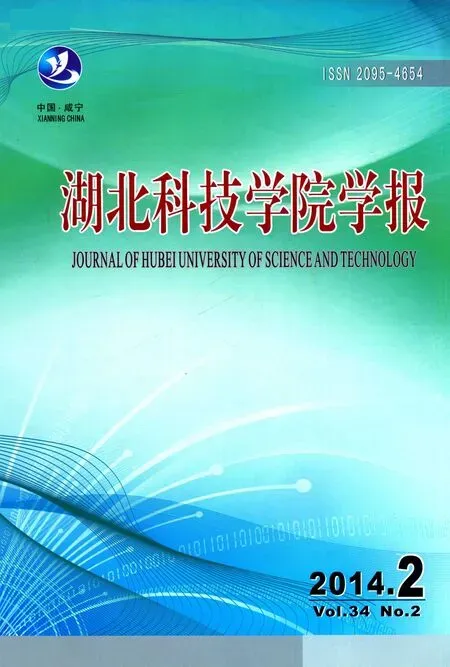论《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恐怖气氛
周莉丽
(晋中学院外国语学院,山西榆次030600)
被誉为美国恐怖小说之父的埃德加·爱伦·坡在美国浪漫主义文坛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在美国国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马克·吐温曾经评价他的文字不值一谈,惠特曼认为他的作品是“不丰富的选材和不健康可怕的质量”。(马新国,2003)然而在欧洲文学界爱伦·坡却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英国作家斯温伯娜和萧伯纳等人对他的天才成就都称赞不已。直到20世纪爱伦·坡本人及其作品才在美国本土得到认可。在我国国内,对爱伦·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在爱伦·坡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尤其是在短篇小说方面。代表作品《厄舍古屋的倒塌》讲述了在一座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环境都让人感到压抑阴森的厄舍古屋中,住着一对孪生兄妹。其中哥哥罗德里克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孤僻的环境中而造成了心理和精神上沉重的压抑,从而使自己一直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中,与此同时,妹妹玛德琳被一种说不清楚病根又无法治愈的疾病缠身。在面对自己日益加重的心理负担与妹妹无法康复的情况下,哥哥写信邀请儿时伙伴陪伴在他身边,想借此缓解自己的压力。为了摆脱心中的压力,罗德里克将妹妹玛德琳活活的钉在了棺材里。在一个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玛德琳竟然出人意料的从棺材中挣扎而出,最终与哥哥相拥而死。此时,罗德里克儿时伙伴受到极度惊吓狼狈逃出古屋,在他刚刚逃到外面,这座让人感到阴森恐怖的古屋也在暴风雨中倒塌。这篇文章将从内外环境和人物刻画两方面讨论小说中的恐怖气氛。
一、环境描写
爱伦·坡对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十分详细,为更好的营造恐怖气氛起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小说一开头就用了一个圆周句(从修辞角度说,把关键意思放在整句末尾,将次要的放在句首。读者只有读完全句才能了解该句完整含义的句子结构),直截了当的描写了厄舍古屋外部环境,为整部小说定下了阴郁的基调。在秋天一个“阴郁,晦暗,寂静的日子”(马爱农,2000),“我孤单单的骑着马,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荒野;暮色渐渐降临,满目苍凉的厄舍古屋终于望见了”。(马爱农,2000)当读者读到这句话时,心头马上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恐怖,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强烈的好奇之心,在这样荒凉僻静的地方居住的会是何许人也?接下来会发生怎样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我”乍见到厄舍古屋时,“心头顿时添上一阵愁,”(马爱农,2000)厄舍古屋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远远望去古屋的窗户就像人无神的双眼一样。古屋的围墙也没有任何的遮挡,同时被一个看上去黑黝黝的小湖包围着。湖中的芦苇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而湖周围的几根白色的树木也在逐渐腐朽,没有任何的生气。这样的场景使得“我”同时也使得读者感觉犹如走进了一片墓地,处处笼罩着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同时反应出了厄舍古屋以及“我”内心的不安并引起读者的恐惧。
其次,对厄舍古屋内部环境的描写也让读者时刻感受到小说的恐怖气氛。厄舍古屋中“昏暗的迷宫式的长廊,暗淡的壁毯,乌木船般漆黑的地板,变幻不定的盾形狩猎纹章”。(马爱农,2000)罗德里克房中的窗子又长又窄而且很尖,窗子距离地面很高。由于窗户窄小,只有微弱的光线可以从装了栏杆的玻璃上照射进来,所以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墙上还挂着黑色厚厚的帘子,家具也是陈旧破败不堪,地上到处都扔着书和乐器,即使这样“我”也无法感受到一丝生气。此外,对于妹妹玛德琳小姐棺木停放的地窖的描写也让读者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个地窖面积非常小并且很潮湿,周围密封非常严密,阳光根本透不进来。这些对地窖的详细描写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片令人窒息的墓地中一座坟墓,使小说的恐怖气氛更加强烈。故事高潮发生在一个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狂风肆无忌惮的吹打着古屋,乌云黑沉沉的笼罩着大地。而被乌云和狂风所笼罩的厄舍古屋却在此时显现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怖和美丽。在如此阴森恐怖的夜晚,读者可以想象到接下来必将会发生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二、人物刻画
首先,在“我”跨进厄舍古屋哥特式的大厅拱门的时候,遇到的无论是“蹑手蹑脚,默不作声从厅里领着我摸黑穿过不少曲折回廊到少爷画室去”的男仆,还是眉宇间夹杂着“既卑鄙狡诈又茫然无措的表情、慌慌张张跟我打了招呼便走了”(马爱农,2000)的家庭医生都给读者营造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对于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多,但读者通过简洁准确的用词深刻地感觉到他们欲言又止,行踪诡异的背后所隐含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同时也对小说中即将出现的主要人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
其次,爱伦·坡对罗德里克的妹妹玛德琳小姐的描写也不多,但却让读者对这位神出鬼没的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也加强了小说的恐怖气氛。小说中第一次提到玛德琳小姐,是在“我”与罗德里克的交谈中才得知,她长期被一种不知名的疾病所折磨,已经“眼看就要死了”。(马爱农,2000)她不曾与“我”说过一句话,也不曾和“我”在一个房间呆过,并且她只与“我”见过三次面。当“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在房间走廊的尽头一闪就不见踪影,“根本没有留心我在座。”(马爱农,2000)由此,读者脑海中情不自禁将玛德琳小姐与恐怖片中的鬼魅身影联系起来。第二次看见她时,她已经躺在棺木中,脸颊上微微泛着红晕,嘴唇还保留着一丝微笑。这里作者不但为故事高潮埋下了伏笔,而且也加强了读者心中的恐惧感,人已经死了,脸上怎么会又有红晕?并且还带着一丝让人毛骨悚然的微笑。这些疑问都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最后一次见面将小说的恐怖气氛推到高潮。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门被狂风吹开,门外站着身披寿衣的玛德琳小姐。白色衣服上有明显的斑斑血迹,骨瘦如柴的身上到处都能看到在棺材中拼命挣扎想出来的时候而留下的伤痕。她极度虚弱的站在门口,发出一声呻吟,就重重的摔倒门里,跌落在哥哥的身上,罗德里克再也无法掩藏心中的痛苦,倒在地上和妹妹相拥而死。我更“吓得没命,顿时逃出了那个房间,逃出那座古屋”。(马爱农,2000)当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必定会被死后又能够破棺而出,并且身上有斑斑血迹的妹妹所吓倒,也肯定会被爱伦·坡所营造的恐怖气氛感染到。
最后,爱伦·坡对小说的罗德里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从而为小说更好营造恐怖气氛奠定了基础。罗德里克作为“我童年时代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可有多年不见,谁知最近在国内远方,竟收到他的信一再催促我亲自去一次。”(马爱农,2000)“我”从来信中感到一种“神经不安的味道”,(马爱农,2000)但是“他诚心诚意的想见我,我是他的心腹之交,也是唯一知己,”于是“我马上应约,但心里依然认为这份邀请蹊跷透顶。”(马爱农,2000)与此同时,读者通过“我”的陈述对于这个家族也有了大致了解,另外“我”还听说一件奇事,厄舍这个家族自古以来都是一脉单传。而这些对罗德里克以及厄舍家族的描写也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好奇之心,感受到他的诡异之处,真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在“我”见到罗德里克的时候,他的外貌让人陡生寒意。毫无疑问罗德里克是一位美男子,端正的鼻子,但鼻孔却非常大,下巴不突,眼犹如铜铃般大,并且水汪汪的。但是脸如死灰,薄薄的嘴唇没一丝血色,头发也是乱七八糟的,不做任何打理。这副容貌令人难忘,并且让“我”感到惊愕,甚至是骇惧。因为这幅怪诞的神情,让人觉得罗德里克不像一个正常人。从这段外貌描写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罗德里克是一个长期受到心理折磨痛苦不堪的人。
其次,罗德里克的兴趣爱好也处处透出他的诡异之处。他总是用“如怨如泣的六弦琴弹出怪诞的即兴曲”。(马爱农,2000)而罗德里克创作的诗歌《群魔闹金殿》,单听名字就让人毛骨悚然。此外,罗德里克通过画画来展示他精巧的幻想力。其中有一张画的不知道是地窖还是隧道,看上去是个矩形,但是非常长。四面的墙壁很低,且非常光滑雪白。从画中的其他物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洞穴被深深埋在地下,面积很大,但却看不到出口,也看不到任何的光源,但是,这个洞穴却被强烈亮光照耀,让人不由的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阴森。从罗德里克的音乐和绘画作品中,读者又再一次深深体会到这个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日益扭曲变态的心理。
最后,罗德里克的行为也处处透着古怪。长期与世隔绝且腐朽的环境使他“神经过度紧张”,“手脚惯性的痉挛,不断吃力的想要控制住,结果总是白费力气”,他的态度“忽而生气勃勃,忽而郁郁寡欢,”“我看出,他完全困在异样的恐惧里了。”(马爱农,2000)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个行尸走肉,只是单纯的活着,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意识。在把妹妹玛德琳小姐安放到停尸间之后,罗德里克“在房间里徘徊,脚步散乱匆忙,漫无目的。苍白的脸色又添了层更惨白的色泽,眼睛里却暗淡无光。”在面对妹妹玛德琳千辛万苦从棺材中出来,寻找哥哥报复时,他的双唇不停颤抖,双眼睁得很大并且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他的这幅表情就像石头一样僵硬,但是全身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由此可以看出,罗德里克在小说中就是忧郁的代名词,是忧郁的化身。此外,古屋中独有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幽暗荒凉,甚至凄冷的氛围,逐步侵蚀并且扭曲他的心灵。
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里环境描写与人物刻画都体现了小说中的恐怖氛围。通过爱伦·坡所描写的环境与人物中透露出的恐怖,读者心中却能够不由自主地想象出无限的“恐怖”。爱伦·坡完全无愧于美国恐怖小说之父的称号。
[1]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埃德加·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马爱农,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3]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Russell Blankenship.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 Inc,1973.
[5]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2):91 ~102.
[6]姚乃强.西方经典文论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7]张琼.幽灵批判之洞察:重读爱伦·坡[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6):21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