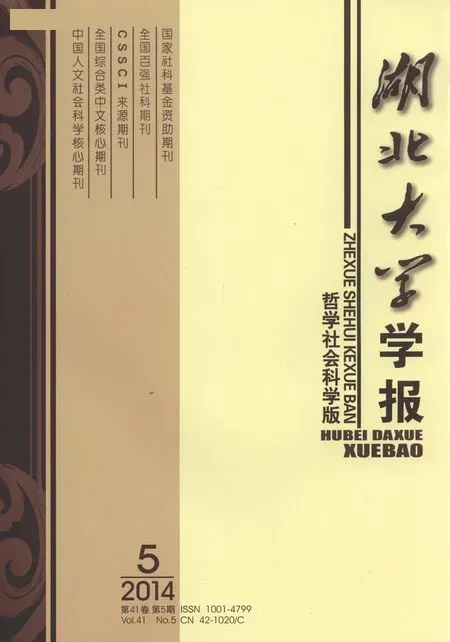儒学的生命化诠释
徐春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部,江西南昌330003)
儒学的生命化诠释
徐春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部,江西南昌330003)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生命化的诠释路径更能切中儒学的这一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动儒学走向现代社会。生命化诠释在目的上,旨在诠释某一学说的生命意涵;在使用的研究范式上,以生命学的范畴来进行;在研究态度上,强调研究者须投入炽热的情感和奉持的信念。在生命化诠释的视野中,儒学会呈现出一幅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图景。
儒学;生命化;诠释
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其学术旨趣、范畴体系、理论特色无不以生命问题为核心来展开和呈现。然而,由于解读路径与方法的失当,儒学作为生命学问的特色长期晦而不彰。本文提出儒学的生命化解读,旨在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解读方法和路径,并期待对儒学的解读方法与路径有更多的讨论,以便更好地切近儒学之本旨。
一、生命化诠释的重要性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政治化诠释(以确立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两汉经学)、哲学化诠释(以本体建构为目标的宋明理学)、学理化诠释(以概念分析为特征的现代新儒学),笔者认为现在应该进行生命化诠释。
1.从儒学的本旨来讲,生命化诠释更能切中儒学的旨趣。在表象上,儒学广大悉备,内容庞杂,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但是,剥开其庞杂的表象,不难看出,这套庞大的文化体系建立在一个基点上——对生命问题的解答。这点从原始儒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孔子的学说,是以求道(即寻求生命的终极关怀)为目标,并以仁与礼为求道的内外路径来展开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设计[1];孟子的学说,是围绕探讨人的本质的性善论来展开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入探索,其著名的仁政说是以仁人行政必得仁政的逻辑展开,显然是以其生命观为基础的。因此,从原始儒学的旨趣、特色和主题来看,牟宗三先生曾指出的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是非常确切的,儒学的确都是围绕着生命展开的。
由于生命是个整体,生命观也是个内涵丰富的多层面的思想体系,基于生命观的文化发展就有无限伸展的可能性。儒学由于历史的机缘,其生命观得以向政治、经济、教育、艺术、道德等全方面展开,贯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个枝繁叶茂、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也正因为内容庞杂、影响广阔,使得后来的解读者如盲人摸象,各执一偏,对儒学的解读陷入层层迷雾。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伦理儒学、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等等,各种分法不一而足。儒学成了万花筒里的景观,丰富多彩又变幻莫测。实际上,尽管儒学可以多维透视,但其“原点”却必须紧紧扣住,否则便双眼迷离,不得其要。儒学如果要进行定性的话,我认为只有生命儒学才能准确地揭示其性质,才能统帅其广阔的内容。因为,儒学的诸多面相,都是围绕其生命观展开的。政治儒学是儒学生命观在政治层面上的拓展,伦理儒学是儒学生命观对人的道德涵养功能的展开,其他面相无不如此。因此,对于博大精深、内容庞杂的儒学,只有回到其“生命”原点才能真正领悟儒学的精髓和要义,才能使儒学这一庞杂的思想体系得到有机的、整体性的理解。
但是,自上世纪初,尤其是建国以来,儒学的生命旨趣被遮蔽,没能得到合理的诠释。建国以来的儒学研究,我认为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建国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9年以来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
段,我们对儒学进行政治化解读,使儒学为政治服务;在第二阶段,我们对儒学进行学术化解读,使儒学学术化。如果前者的错误是歪曲了儒学,那么后者的不足则是情感投入的缺乏。如果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此缺乏情感,我实在找不出解读它的动力。曲解、冷漠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儒学。这种政治化或学术化的诠释模式不仅给人削足适履之感,更重要的是,它把儒学看成是一具待解剖的僵尸,冷漠无情。曲解、冷漠都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儒学。因此,我提出以生命化解读来体认和理解儒学,认为从政治化解读、学术化解读走向生命化解读,才能真正触及儒学的灵魂,领悟儒学的精义。而且,如果不立足于儒家的“生命”原点,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儒学必然陷入各执一偏的境地。
2.从儒学的发展来讲,生命化诠释更有助于儒学走向现代社会。儒学自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一直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依附着政权来发挥它的广泛影响。自20世纪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政府灭亡之后,儒学便失去了政治的依托而成为“游魂”(余英时语),其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的困境。许多儒者为谋求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不懈地探索。在政治层面上,儒学能否和现代民主政治兼容一直受到质疑,至今仍然是否定的声音占主流;在科学层面上,儒学也以其轻“技”而饱受诟病。儒学在现代社会的遭遇可谓极其困窘。这当然和时代的发展、西学的冲击密切相关,但诠释和解读的路径也是重要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儒学的政治功能可能有不适应之处,但儒学的生命价值观不仅在传统中国影响巨大,而且仍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是历史的产物,文化传统对人具有根本的塑造作用。在中国,作为人的本质的人文生命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塑造的。抛弃儒学必然导致中国人生命价值的失落、归属感的缺乏等诸多生命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今天中国人所遭遇的严重生命困顿,都不能不说应归咎于对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的抛弃。因此,要解决由文化传统的缺乏带来的生命问题,必须借助文化传统的复兴。现代人遭遇的生命困顿,呼唤儒学的复兴,呼唤传统儒学作为生命资源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而儒学也只有充分发挥其生命功能,才能找到重新介入现代人生活的途径,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生命化诠释的涵义
所谓生命化诠释,首先强调,在目的上,旨在诠释某一学说的生命意涵;其次,在使用的研究范式上,以生命学的范畴来进行;最后,在研究态度上,强调研究者须投入炽热的情感和奉持的信念。
1.生命化诠释旨在诠释某一学说的生命意涵。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效果历史”思想,文本的解读就是文本存在的基本方式[2]379~392,对某种学说的解读同样如此。解读者的解读就是该学说存在的基本方式。不同的解读者会基于各自的“视域”和解读对象融合而得出不同的解读结果。因此,对儒学的解读,在政治家眼里,儒学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在哲学家眼里,儒学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在经济学家、教育学家眼里,儒学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正因为解读者对解读对象存在根本性的决定性,确立解读者的视野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提出的生命化诠释,旨在解读其中的生命意涵,即其中的生命精神、生命理念、生命智慧等等,目的是揭示其在人们安身立命中所提供的思想资源。
2.生命化诠释要运用生命学的范畴来进行。不同的诠释路径得运用不同的范畴。生命化诠释运用的就是生命学的范畴。对儒学而言,其实它的范畴本身是立足于生命问题而建构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语境的变化,本来是生命学问中的范畴在大众眼里逐渐丧失了生命意涵,而渐渐成为学者们学术考察和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时代变迁带来的语境变化,要求我们建构起一套既能阐述儒学精神又能为大众接受的范畴体系。这是其一。其二,现代学术分工的细密导致传统诸多的范畴因为失去了整体的观照而变得难以理解。比如阳明后学的“归寂”、“独知”,因为现代研究者常常不将其置于“良知体证”这一宏观背景下而变得难以理喻。
生命化诠释的使命,是要建构既能解决语境变化带来的时代问题,又能体现生命学的宏观要求的范畴体系。要建构起这套体系,既必须深刻领会传统哲学的要旨,又要掌握现代人生命问题的表达。
就目前而言,生命学还没建构起来,因此其范畴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共识,就是必须和生命密切相关。笔者曾提出生命哲学的一套范畴。这套范畴包括:生存根据论、身心观、生命境界观、修养工夫观、欲望观、生死观等问题。生存根据论为人的生存确立形上学基础,为人的生命境界提供本体论依
据,并由此建立人的意义世界。它体现了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终极意义和终极存在所采取的立场,是人生命的首要问题。身心观则表达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包括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结构及其关系等问题的考察。身心观是形成人的自我观的基础,是某种人论的核心。人的生命首先是生理性存在,而生理性存在必然产生相应的生理欲求。因此欲望是任何一种生命哲学所必须思考的对象。欲望观不仅体现了一定的身心观,也制约着人们的生命修养观。所谓生命修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制欲的过程,这在理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生命境界观体现了人们的精神追求,是生存根据论在生命实践过程中的具体体现。生命修养观,则是为达到生命境界而设计的工夫论,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生死关切是生命哲学最终的归旨,是一切生命理论的终结点,在生命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生命哲学的这些基本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生存根据论是生命存在的最终根据,是人的生命的主导因素;身心观则体现了人对自身的认识,表达了人的自我观,它是确立生存根据、树立人的欲望观、境界观和修养观的基础;修养工夫是以生存根据论为理论基础,以生命境界为追求目标,以措置欲望为重要内容,以了生脱死为终极关切的过程;欲望观则是在一定的本体论和身心观基础上对人的欲望的看法,它以身心观、生存根据论、境界观等为理论基础,又直接关涉生命修养的工夫进路。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关于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有机整体。当然,这种“有机整体性”可能在形式上就具备,也可能只有在实质上具备。笔者认为,这套生命哲学的范畴大体可适用于生命化诠释。
3.生命化诠释要求诠释者对诠释对象充满热情。诠释者的情感投入会直接影响诠释的结果。生命化诠释虽然也强调诠释的客观性,但更强调诠释者的情感投入,尽管这种情感投入可能不会直接在语言上表达出来。生命化诠释不但要求要“同情地了解”,更要热情地理解,甚至奉持。没有内在的同情和认可,就很难有内在的动力去诠释。长期以来的儒学研究,把儒学看成是一具待解剖的僵尸,冷漠无情。生命化诠释的主张,认为只有从生命的角度,用生命的情感,才能真正触及儒学的灵魂,领悟儒学的精义。
三、生命化诠释中的儒学图景
以生命化诠释的思路和生命哲学的范畴,儒学会呈现出一幅与其他诠释路径不同的“生命”图景。这些图景需要我们去认识、描绘、融入。
1.生存根据论。生存根据论,亦即生命本体论,是对人的生命作出的最终说明。它告诉人们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真相,并由此建构起人们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因此,生存根据论问题是人的首要问题。
儒家对生存根据论的回答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是怎样演化的?它如何贯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天它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吸取?这些都是儒学生命化解读首先要阐述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儒家的生存根据是“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士志于道”,《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都表明“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生存根据的终极意义。正如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道”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3]503。对儒家而言,悟道、履道、体道、证道是他们获得生命意义的根本途径,与道合一是儒家的最高生命境界。但是,“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儒者中有不同的理解,儒家的生存根据论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2.身体观。身体观是解决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肉体生命或生理生命的问题。人的生命存在首先是肉体生命的存在,这是人首先必须面对的生命现实。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不满足于肉体生命的存在而去追求以价值和意义为核心的精神生命。于是,在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支配着人类的生命活动。不同的文化对这种张力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也就有对肉体生命不同的观念和态度。
儒家以修身闻名。它的修身观是建立在何种身体观的基础上的?修身的核心是什么?修身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围绕着身体观来看儒学,对理解儒学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儒家身体观,是沿着重心轻身的路线发展的。在儒家的早期著作《易传》中,我们还能看到有关重视“身体”的一些观念。但在随后的发展中,“身体”的地位每况愈下,至宋儒时地位最低。宏观地看,儒家对待身体的基本态度是“抑身扬心”,这一态度在先秦就已确立,到宋至明前期推达极至。至明中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儒家对身体的态度发生改变。这一转变在王阳明时已初露端倪,到泰州学派就很显著了。总体上对儒家身体观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对儒学宗旨的理解与把握。
3.欲望观。钱穆说:“人身上每一种器官,都代表着人类生命所具有的一种需要与欲望。”[4]27的确,人有了身体,也就意味着有了欲望。所谓“欲”,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想要”,即人的耳目口鼻等生理器官想要满足的愿望。欲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由于人的欲望常常膨胀为贪欲,欲望就往往成了人们提升道德和精神品格的障碍和社会纷乱的渊薮,因此也就成了人们反省和克制的对象。儒家亦是如此。但儒家的欲望观又有自己的特点。分析儒家欲望观的内容和特色,是我们理解儒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儒家对待欲望的基本态度是克治省察,这种抑制欲望的态度在宋儒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其本意并不意味着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否定,但其价值取向却是以欲为恶,因而事实上造成了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压制。晚明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欲望观是对宋儒欲望观在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这种修正,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及其后人诠释的放大,成为影响后世的一股文化力量。
4.生命境界观。所谓生命境界,是指人的生命所能达到的境域。由于生命境界观体现了人的生命追求和人生理想,对儒家生命境界观的考察有助于对儒学的理解。通常我们将儒家的生命境界归结为人格境界或道德境界,这是不够的。事实上,生命境界还应包括所祈望的心理境界和生活境界。儒学发展到晚明更是如此。如果大家对泰州学派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儒家境界观的丰富性。当然,儒家境界观的首要蕲向是圣人——这一儒家人格境界完美的代表。但是,儒家,尤其是民间儒家,也极为重视对心理境界和生活境界的追求。或者说,他们所理解的圣人,有着更多的面相。在心理境界上,对“孔颜之乐”的向往;在生活目标上,对“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式完满生活的追求,使晚期儒家的境界观应从人格境界、心理境界、生活境界等多个维度来理解。
5.生命修养观。生命修养观直接关涉人们当下的人生实践,因此在生命学问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不深察。儒家以“道”为生命本体,其生命修养亦因此表现为体“道”、履“道”的工夫。但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儒家的修养工夫论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色。如宋儒以“理”(或天理)释“道”,把对“道”的体认和践行转变为对“天理”的体认和践行。明中后期阳明学崛起后,又以“良知”涵“天理”,生命修养工夫又转化为对“良知”的发明和扩充,即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工夫。“致良知”工夫又由于其后学对“良知”的不同理解,分化出不同的工夫路数。要而言之,生命修养观作为儒家的工夫论,是理解儒学的重要路径,需在生命整体的观照下进行系统、深入地考察。
6.生死观。生死事大,生命的学问必对生死观有深究。理解了儒家之生死观,在一定意义上就理解了儒学。在生死问题上,儒家主要的基本态度是喜谈生、忌谈死,并采取以生克死的方式超越生死。不过,在中晚明以后,这种情形得到明显的改变,生死关切在儒家的问题意识中由“幕后”转向“台前”,从以往较为边缘的话语地位突显成为当时以阳明学者为代表的儒者们问题意识的焦点之一。死亡已不再是儒者讳言的问题,而成为关联于圣人之道的一项重要指标[5]471~472。当然,儒学是践履之学,考察儒家的生死关切问题,不仅要从理论上着力,更要从儒者的生死实践来理解。
四、小结
儒学的解读,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解读者都会根据时代的问题与需要,基于自己的学养与诉求,得出不同的解读结果。因此,这里就始终存在一个事实与价值平衡的问题。冷漠地陈述事实,难以打动人心;过度地诉说己见,又不免臆解之嫌。解决这一问题确非易事。笔者认为,充分体验儒学之旨趣,并根据时代之精神需要去解读,是一条根本思路。本文提出的生命化解读,就是基于这一思路提出的。希望这一解读路径对理解儒学、弘扬儒学有所裨益。
[1]徐春林.《论语》的生命观与生命教育思想[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5).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三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钱穆.人生十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黄文红]
B222
A
1001-4799(2014)05-0078-04
2013-10-17
徐春林(1968-),男,江西贵溪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儒家哲学、人生哲学研究。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 从“人口治理”到“关怀自身”
——资本、权力与生存美学 - 论晚清时期文官保举的基本特征①关于中国清朝保举制度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还是断代性的,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涉及或设专章进行研究。如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中国古代的文官选用、保举、考绩、监察和惩处等进行了分析。陈茂同在《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设有“荐举论”专章,认为保举是重要的选官途径,区分和确定了保举类型及标准,分析了保举的利弊。宁欣清晰勾勒“选举”制度变迁脉络,对中国的选人、任官制度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了清朝的用人制度(《中华文化通
- 德沃金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评与发展
-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诺齐克之争
-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
——休谟德性理论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