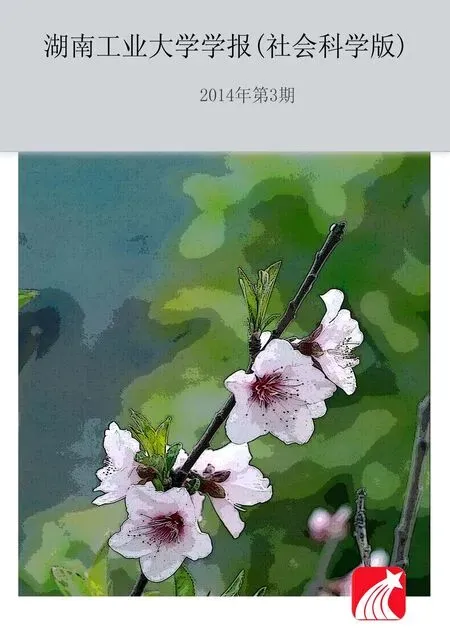植根大地 诗意栖居
——论七窍生烟的诗歌
段晓磊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七窍生烟是新湘语诗歌的重要诗人之一,有研究者认为:“读汪志鹏(七窍生烟)的诗歌,扑面而来的是新鲜感,亲切感。那么的强劲,那么的自然。诗歌可以这样写吗?来不及疑虑,就豁然开朗:诗歌真的可以这么写。这些平实的、没有任何暗指、隐喻的话语,这些朗朗上口的话语,原来都是可以入诗的”。[1]确实,七窍生烟并不是一个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故弄玄虚的人,生活中诸多常见的事物往往变成他诗里的意象,如“火车” “木马” “树” “房屋”和“鸟”等。新湘语诗歌是当代湖南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追求一种自然的呈现,新湘语诗人使用充满湘味的语言书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想,口语式的诗歌语言更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在新湘语诗人那里,诗歌已成为一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汪志鹏说,我写我看到的。他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从不奢望作中心话语、主流意思的传声筒。他居住在长沙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精神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1]他的诗散发出的是生活中泥土的气息,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2]七窍生烟的诗歌贴近生活,加深了读者对生活以及人自身的思考。诗即生活,生活即诗,简朴的文字无法掩盖七窍生烟在诗歌中所隐藏的人性话语。
梁实秋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一文中指出: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3]。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人性“有着不以任何事物为转移的属性”[4]253,并且“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5]103。七窍生烟称自己的诗歌只是记录自己“流汗的经过”,这看起来与梁实秋所说的“永久的,普遍的,固定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与区别”[6]的人性有着不小的出入,然而普通与伟大的修饰语在“人性”的话语下,各有各的阐释意味。七窍生烟的口语诗大都是由生活而来的一些只言片语,但是平凡的文字织出的却是生活中的奇观。
一 简单的文字:生活中的奇观
闻一多曾经指出诗歌要“把握生活”,使“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人生底基础上”,也就是说,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必须要由形而下的生活来主宰,“形而上学惟其离生活远,要它成为好的文学,越发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没有将现实好好把握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行剥夺了”[7]。闻一多在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下,为了抬高生活在诗中的位置,自然要贬斥所谓的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但无法否认的是,“诗人知道投入生活”,“如果他同意投入生活,那并不是命运的目的,他知道如何利用旅行。他能从丑陋和愚蠢中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奇观”[8]13。这样来看七窍生烟的诗歌,就可以找到他的视点与日常生活的契合处,这也是他的诗歌所着力表现的地方。
七窍生烟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记得20年前,在老家做了一个梦之后,我就来到了长沙,20年一眨眼过去了,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真实,我仿佛又做了一个梦。不同的是在老家时我在工厂里烧锅炉,只会流汗做卖力气的活。到了长沙后不仅会做卖力气的活,干完活后还学会了用笔记下流汗的经过,然后就觉得汗没有白白的流了。”到底梦是生活,还是生活是梦?弗洛伊德说,文学作品就是作者的白日梦。诗人书写生活,记下了这个白日梦,这大概就是七窍生烟写诗的一个理由。
“在长沙/在海口/做梦都想回到的地方/竹山还在/老屋还在/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让你的回忆/多了个句号/在白云之上/你依然望了望老屋大概的方向”(《还乡》)。很多诗人都有一个心灵上的故乡,并且时刻准备着能启程回乡。但是现实的生活却无时无刻地在提醒人们,过去的离开就已经意味着现在的无法回归,回家的愿望只是敏感诗人的一个虚假的自我安慰。时空下的疏离感,永远无法得到平息。故乡有什么值得如此牵挂?答案必然离不开一个“情”字,友情?亲情?七窍生烟在《距离》和《元旦》中分别描述了空间和时间下的亲情。“妹妹的手机/一直没有打开”,“家里的电话/她应该知道/她就是不回”,“妹妹在那叫做白溪的地方/做什么”,“我坐车回长沙的车上/还打了一次妹妹的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想象不出妹妹的生活”(《距离》)。诗人和妹妹选择了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生活,空间距离的背后是难以名状的疏离感,这是思念和担心所无法跨越的。与空间对亲情的阻隔相比,时间带来的变化是无法颠覆的。“父亲走在右边/母亲走在左边/我在中间/三个人走在资江的堤上/冬天的阳光/同时从前面照着我们/我感到/不仅仅是温暖/还很安全/父亲问我/多少年没有这样走过了/我说是的/说完递一根烟给父亲”(《元旦》)。诗人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孩子,可就在“我”递烟的这一瞬间,时间的残酷显而易见,“我”的成长换来的是父母的逐渐衰老。《梦中写的一首诗》写一个人一生中的“8岁” “18岁” “28岁” “38岁” “48岁” “58岁” “68岁”,在蒙古包里唱歌的吉玛一天天地老去,诗中每句话看起来都是在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外面格格木尔草原,一望无际的延伸”(《梦中写的一首诗》)。吴投文在诗歌《主题学》中慨叹“时间的敌人在时间之外”,“时间本身并不会凋谢”[9],对于周而复始的大自然和本身并不会凋谢的时间而言,吉玛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个陷阱,这首诗在平静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悲怆的情绪。
“中午打老表电话/老表说/你在哪里/我说在新化/老表讲/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吃/老表说/我在乡下啊。”(《无题》)金钱和利益腐蚀了人的内心,这比时空带来的疏离感更加可怕,可以想象,电话另一头的“我”该有多无奈。来自乡下的何美丽,为了见在城里上学的儿子一面,舍不得一块钱的车费,带着满满的一行囊,里面有她为儿子亲手准备的“一罐子剁辣椒”和“一大盆蒸熟的米粉肉”。经过一个上午的跋涉,当她拉住儿子的衣角唤他的名字时,“何美丽的崽/一把挣脱何美丽的手/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何美丽》)。母爱永远是伟大的,但欲望主宰的世界对母爱的回报也许是误解和伤害。何美丽的遭遇在诗人的笔下并没有被刻意强化,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位母亲所受到的心灵伤害。
即便如此,生活依然要继续,“早晨你要买些什么菜/你记得吗/大蒜,白萝葡,芹菜,豆角/镜子里剩下阳光/和风对话”(《无题》)。七窍生烟的文字简单而又平淡,似乎一阵微风就可以拂去。可愈是漫不经心,他的诗就越具有某种震撼力。他貌似无情的叙述也许隐藏着别样的感情。
二 迷醉的心灵:别样的感情,别样的诗
闻一多认为,“诗是个最主观的艺术”,感情与诗有着一条切不断的纽带,“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裂了,烈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10]。黄曼君将闻一多所划分的两类“情感”做了系统的总结,“一类是较柔和的情感”,与“思想相连属,是由观念和理智而发生的情感”,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和人生追求”;“另一类是依赖于感觉的热烈情感”,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4]244。毫无疑问,闻一多的诗倾向于后者,而七窍生烟则含蓄得多。但不论是火热的还是柔和的语言,诗本身都离不开对情感的书写。
古往今来,众多的诗人都十分钟情于“离别”的场景,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等。七窍生烟也不能免俗,他的诗《上车》便是一首离别诗,“满脸络腮髯子的人/站在车窗的外面,/火车还没有开/那个人/用手指沾着唾液/一笔一划/在车窗上/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文字/李亚伟说/那是蒙文/阳光照着我对面/女人眼睛里的泪花”(《上车》)。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七窍生烟将自己置身“离别”之外,“零度”描写成为可能,其笔下的诗如同摄像机镜头所摄下的画面,一种别样的感情就这样通过貌似无情的叙述展露无遗。
与向往回家类似,回归大自然也是许多人的梦想。自然是美的,甚至具有纯化心灵的功效。波德莱尔曾指出:“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情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是理性的材料。”[8] 206商品化的大潮加强了人们对物质的渴望,真正的诗人是孤独的,他必须为了维护诗性忍受清贫甚至是现代人不解的眼光。文学即人学,诗性即人性。文学的本体意义是“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5] 103
七窍生烟的一首诗极有意味,“那些白色的云朵/数也数不过来/它们一会儿跑到天边/不见了/你站在草原上/看看/四周无人/俯下身来/咩咩咩地/叫了几声”[1]。七窍生烟曾慨叹分不清自己与树的区别,其实何尝是树,置身于纯净的大自然又有谁能说出人与羊的区别?“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高山深谷里面,所以我们正不必像探险者一般的东求西搜。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们的心里”,人往往对近在咫尺的东西视而不见,无论它多么重要。但这并不能遮蔽人性存在于平凡生活中的事实,“纯正的人性就在理性的生活里就可以实现”[11]。你可以说诗人的想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倒退”的,不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是,这仅仅是将人放在“人类中心”的位置上,利用“工具理性”的实用精神,进行功利性定位。诗人摒弃了偏见,将“人性”置于内心,而人的心灵则是与众不同的。人性既然被放置在内心,那么,人性自然就无法具有物质本身的实在性,类似于人的意识,它空无飘渺却又时刻存在着。也许正如西方的先哲们所假想的那样,人的内心是向善向美的,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因素。
七窍生烟的诗也有某种幽微的哲思,看起来很平淡,却值得咀嚼。“我在湘江边/一个人/和一条河流/河是流动的/它不属于一个人/一个人是移动的/可以移动到河的东岸/或者河的西岸/也可以从水中飘过”(《或者河的西岸》)。河流不属于一个人,它只能潺潺向前,而人则听从内心的召唤移动,可以是“东岸”,可以是“西岸”,也可以是“从水中飘过”。七窍生烟在诗中追求的也许并非是“永久性、普遍性”的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风吹过来/风不大/树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来/我就是/那样的一片叶子/在秋天掉下来/没有任何意义”(《无题》)。人曾经编织出一个上帝,骗自己死后会有天堂,以此来消解死后的虚无带给活着的人的恐惧,但谎言毕竟是谎言。人的生命本身是有限的,可经由心灵流露出的诗却是向善向美的,这足以使人凭借诗的无限性,暂时突破自身的有限性而达至无限。
三 植根大地,诗意栖居
七窍生烟描写凡人的窘境,有非常细致的观察,流露出复杂难言的悲悯情怀。“擦鞋的女人/戴黑色的眼镜/她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先生擦鞋吧/没人答应/她就转身而去/就在她转身/那一瞬间/她右脚的皮鞋/裂开一道口/好像在喊/先生擦鞋吧”(《无题》)。“擦鞋的女人”通过擦鞋这一体力劳动来换取在城市中的艰难生存,她的身份是卑微的,给人擦鞋换取报酬如同乞讨。她自己的鞋子由于质量低劣和保养不当反而“裂开了一道口”,困顿的生存状态立即显露出来。然而,海德格尔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却听到了“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的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无法阐释的冬冥”[12]。同样是劳动者的鞋子,七窍生烟笔下鞋子的女主人陷于被异化遮蔽的生存窘境中,而海德格尔文中农鞋的主人则是诗意的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充满诗意的诗与“此在”的生存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植根于大地的人才有可能识破“洞穴”的骗局,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惟其如此,才能够在所从事的艺术创造中得出真正的、符合真理的体验和认识。“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避它和飘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从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12]七窍生烟笔下鞋子的女主人则脱离了大地,给自己编制了一个虚假的城市幻影,陷入商品经济大潮之中无法自拔。七窍生烟从擦鞋女人卑微的生活中,发现了在城市幻影的摇晃中一种令人心碎的忧郁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拒绝诗歌的贫乏时代。绝大多数人陷入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流连于充满诱惑力的情欲之中。就连诗人自己都无法完全抵挡这种引诱,“告诉你好了/我真的不可以/像一棵树/那样挺拔/然后把头发拔光”(《无题》)。但是诗人是特殊的,他必须具有自己的信仰才能称得上是诗人,无论他的终极在天堂还是在人间,“诗乃宗教,需要付出绝对的虔诚;真正的诗人少而又少,出诗集与诗人的称谓没有必然的联系”[13]。生活在一个贫乏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用诗聚集诗的本性。那所发生之处,我们可断定诗人的整体生存顺应着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这个时代隐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14]诗本身并不承担道德规训,它所蕴含的只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许七窍生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诗中表现出某种犹豫和含混的东西。
在现代社会,虚无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力量,这得益于现代人对“人类中心”的解构,如果说上帝的隐去引发了人类的信仰危机,那么“人死了”则使得世界完全地碎片化和平面化,意义和价值被前所未有地颠覆,现代人陷入空前的困惑之中。“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艺术性的活动,或是书面艺术,或是影视艺术。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15]“我被雨淋湿/这是因为/我没有带伞的习惯/你见过一只打伞的鸟没有”(《无题》),“伞”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下雨了,诗人就像天空中的鸟一样,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惠。人造的工具给人带来更多的舒适和物质满足,但是一旦沉迷其中,人的本真就被人自身的欲望遮蔽了,甚至人本身都有可能沦为人造工具的奴隶。海德格尔所推崇的“诗意栖居”并非是要将人拔离大地,恰恰相反,“诗意栖居”并非悬浮在现实的上空成为一个精神贵族,而是植根大地。七窍生烟笔下朴实的文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他在诗中想要做到的正是“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16]。
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奢谈终极关怀与灵魂救赎是一件遭现代人鄙视的无奈的事情,霓虹灯下扭动的的腰肢无限地趋近本能和欲望,诗人的精神家园早已被遗弃。诗人渴望找到精神安身立命之所,以拯救自我;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揭示本真的生存状态,以照亮他人。“你又花了一个晚上的/大好时光/你应该站到窗子边/看看大海/黑暗中的海/和白天的大海/一定有着某种关系/他们都离你/那么的近/你看着远处的火车/早已停止旋转的木马/你的沉默/是大海的延续/我有点累了/这个秋天的夜晚/我不再是天空中的那只鸟/黑暗中的海/慢慢把我淹没/我唱着戴花就要戴大红花”(《无题》)。世间“远处的火车”和“早已停止旋转的木马”勾引了“你”的目光,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却是无边的沉默。“我”也累了,这个秋天的夜晚“我”不再是那只天空中的鸟,隐没在黑暗中唱着自己喜欢的歌。世界本身是荒诞的,但诗人的存在却是要勇敢地面对绝望的处境,七窍生烟以自己“坦然的”诗歌担当着平凡的生活。潘知常直言:“在某种意义上,人活着,就是让荒诞活着”[17]。虚无驱逐了价值和意义,勇敢地面对它,便是创造价值和意义。永恒是奢侈的,但七窍生烟的诗却让人有理由相信,有了诗歌的陪伴,即使是有限的生命,也可以是快乐的。
[1] 庄宗伟.走出围城的新湘语诗歌[N].湖南日报,2003-10-22.
[2]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M]//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1.
[3] 许祖华.双重智慧——梁实秋的魅力[M]//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244.
[4] 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5] 梁实秋.文学批评辩[M]//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6] 梁实秋.书评两种[M]//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94.
[7] 闻一多.泰果尔批评[M]//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3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441-444.
[8]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9] 吴投文,朱立坤.中年生活[M].香港:银河出版社,2013:13.
[10] 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M]// 闻一多.闻一多论新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0-13.
[11]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16-112.
[12]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 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6.
[13] 吴投文.土地的家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114-115.
[14]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85.
[15]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 [M].北京:三联书店,1996:463-464.
[16]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92-93.
[17] 潘知常.荒诞的美学意义——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J].南京大学学报,1999(1):1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