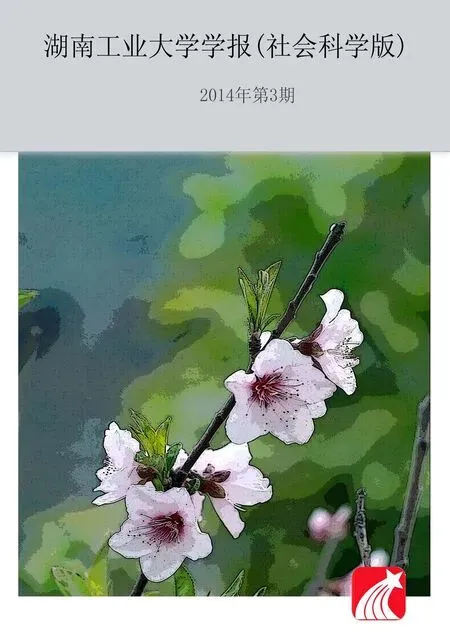日常生活里的身体诗学
——哦该诗集《地铁》身体视阈管窥
李石光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湖南 长沙 410205)
“口语诗”的源头或可追溯至《诗经》,但从真正意义上讲,它应当是现代诗范畴里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在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口语诗在汉语诗歌的语境中头一次获得了尊严感和挑战者的身份。可以说,“口语”在诗歌语境里是语言特色,也是诗体建构,亦是现实的身体诗学。在新世纪的技术信息大爆炸中,口语诗以其独特的亲和力得以在网络中蓬勃发展。在这一喷涌而发的潮流中,新湘语诗坛异军突起,以简、明、轻、快的地域口语色彩迅速崛起。其间,作为新湘语诗歌论坛的第一快枪手,株洲诗人哦该的代表作《地铁》以冷峻、俏皮、纯天然的口语述说,演绎出日常生活的身体诗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与哲学界一般,出现“转向”,“身体话语”蜂拥而起,成为后现代语境里的解构策略和“重述”手段。文学创作也纷纷挂名“身体”以示决裂来标榜新潮。这其中尤以诗歌为甚,“下半身”在欲望之海里冲锋陷阵,使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谢有顺谓之“身体的暴力美学”[1],导致了人们对“诗歌与身体”之关系的误解。其实诗歌与“身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诗歌的文本可视为语言符号化的“身体”,其次诗歌表达的是人之情感、建构的是人之“美境”——离不开人体感觉和身体“意识”。身体既是生物存在,又是文化建构。身体居于宇宙之内,“宇宙”又纳入“身体”之中。事实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学文本都存在利用身体修辞来表情达意的情况。“如果将‘身体’拆分,‘身’体现其物质性——肉身、躯体,‘体’则意味着文化建构,呈现个体性、能动性、交互性。从身出发、因身而动、由身而感,这一动态的过程见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2]
哦该诗集《地铁》的口语言说,以平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以肢体动作和切肤感受为履带,从身体出发,复归身体之痛,在生活细节的呈现过程中,影射出对生命的关怀和存在的焦虑,由生活琐碎的个体性、交互性,借助肉身的物质性功能,来见证“人之为人”的荒诞性。
一 身份意识:平民化
“身体是文学的作者:是手握着笔或者敲打键盘,是大脑在思考,是眼睛望着纸张和屏幕,总之,是身体在写作。写作中的身体不可能不将自己投射到文本中。”[3]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创造性的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4]身体投之于文学是创作主体必然具备的主体性意识,这里姑且命名为身份意识。
《地铁》一诗,诗人哦该从客观具象之呈现来反映现实生活,诗里行间似乎未着感情色彩,这是其反对主观入诗和抽象化假大空写作的策略,也是其独特的“平民化”身份意识之彰显。
这里不得不提到诗人的名字,哦该其实是长沙乡音俚语“何解”的音书,相比“何解”更贴近生活的乡土韵味,在日常的口语交流中,“哦该”一出口满腔都是长沙味,且其涵义丰富。其一,在怄气交涉中表达对对方的质问“你想怎么样?”《地铁》同名于“意象派”鼻祖庞德的代表作《地铁》且把该诗影印在诗集扉页,足可见哦该的挑衅之势儿,亦颇具乡俚家长里短之范儿;其二,在表示疑问,这是怎么回事?这该如何是好?是下里巴人面对某些令人费解之事或者在手足无措之时的顺口溜,被诗人借来正儿八经地命名之,似乎和庞德开了一个正经的玩笑。难怪诗人老庄认为诗人哦该的“哦该”是无言的“天问”,至于为什么没问是担心“上帝就发笑”[5]。
在《地铁》中,基本上每首诗都如同“哦该”一般,极富平民特色。从吊篮槟榔到妈的X,从乘地铁到散步、擦皮鞋,平民的日常生活在诗人的笔下“嗖”地一下如吊篮槟榔般被哦该从生活的窗口吊了下来,琳琅满目,五味杂陈。
再看看诗名,《妈的X》《我想跳起来》《就这样过去了》《关你卵事》《很快就会温暖起来》《真是调口味》《好大一把蒲扇》……举不胜举,当真实生活的琐碎俚语夹着油墨之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汹涌而来,给读者带来一阵疼痛的快感,初始像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进而惊喜发觉,“哦该”一声,生活不正是这档子事么?
且读读《我想跳起来》:
不晓得今天
星期几
我的手机
昨天就坏了
不然我可以
打电话问问
老七
哈,刚好
遇到一个好象
认识过的
女人
牵来的
那小孩子
望了望我
喊了声
爸爸
如果说王朔的平民化以机智、幽默的游戏化为特征,那么哦该的诗歌的平民化则以朴实、原生态的呈现为特征,虽然也带有一种冷幽默式的好玩的腔调,但是完全放弃了语言的修辞游戏,其通过诗歌所建构的文本“身体”来彰显平民现实生活中蕴藉的游戏心态。在游戏心态中,连神圣的“爸爸”都被幽默解构,诗人之为人的主体属性虚构化,其归属感被“我想跳起来”的非理性感觉所消解。
二 从身体出发
“身体总是尝试利用各种符号如眼神、表情、神态、形态、动作、感应、声音、语气、情绪以及排斥、贴近、封闭、开放等身体姿态和生命表征在表达和沟通情感与体验,书写和表达真理与价值。追根溯源,言语实际就是一种表达和交流活动。”[6]诗歌作为基本的文学体裁,亦是一种“身体”之间表达和交流活动。《地铁》的口语言说,作为文本“身体”与读者“身体”交流沟通的策略,自然会利用肢体动作、言语表达、情绪神态等身体姿态和生命表征进行叙事言情。鉴于本文篇幅和论述需要,仅仅从“说”和“看”两个向度进行分析:
(一)“说”与言外之言
哦该在《地铁》中的身体修辞首先呈现在其叙事/抒情的策略:身体的基本沟通交流方式“说”上。
“你说你想去/乘地铁/我说好;看,我的眼睛/明亮地一闪/门就开了;这个最美的/车站/为你修葺一新”(《地铁》)。这是典型私语体,在这里,读者是被动的,诗人根本没给读者表达机会,只看到诗人在述说,而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如此。《吊篮槟榔》是诗人在回忆:“以前我也嚼槟榔/所以记得七八年前”,一起句陈述式,就好像诗人在跟读者拉家常。这种私语里,诗人夹着气势,不管你或他听不听得懂,这有点像乡里的“调口味”了。
从说出发,基本上每一首诗里面,哦该都以第一叙说人出面,视角亦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就算“我”没有出现,隐含叙述者里的“我”的影子无所不在。在《年年有鱼》里,“一条木鱼/放在盘里/浇上一些佐料/从初一到十五/摆在饭桌上”,诗歌一直叙述得不露声色,读者以为这仅是诗人在絮说年年有鱼之来历,话锋一转,“儿子/那些年我们吃的鱼/就是这个样子的”,至此,读者仿然大悟,一个对儿子淳淳教导的慈父形象栩栩如生,从而使得诗歌的空间豁然扩大。由“年年有鱼”到忆苦思甜,再到亲情沟通,甚至牵涉到普通人眼中的时代变迁,留白出一片新的天地,可谓之言外之言。在《绿油油的》中,“推土机/就要来了/五爹在使劲地扯/白菜”,哦该没有评说,五爹也没有牢骚,“只剩下一片莴笋”,“在那里异常显眼/整整齐齐/绿油油的”,亦可谓言外之言。
(二) “看”与无视之视
“看”,是《地铁》中“身体”活动的基本动作元。
“看”是核心事件:“看,我的眼睛/明亮一闪”(《地铁》);“很多人看热闹”“老远看/实在像/金毛狮王”(《金毛狮王》);“没事看一看/路过的一双双/眼睛/这些窗户里面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擦皮鞋》);“搭桥下面/看一个一个英国美女走过”(《唐老鸭》)。
“看”是矛盾焦点:“朦胧的雾中/终于看清/那蒲扇”(《一把好大的蒲扇》);“隐隐约约看见鸡们/大多在睡觉”(《女士优先》);老婆发现了抽屉里的安全套(《安全套》)。
在“看”之外,还有一种无言之“看”。何谓无言之“看”,就是没有看这个动作/字眼,或者是通过说、闻、触等肢体言说方式来诠释“看”,类于通感,又与之有所不同[7]。因为通感就是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而哦该的诗歌里,基本没有描述感觉,而是通过对事物的客观呈现来让读者自行体悟。且看《它叫的什么只有鸟们知道》,“一只鸟/叫了一个上午/没有第二只鸟应答/我走近窗/学鸟叫了几声/那只鸟/停了一下/又/叫了起来”,全诗不长,合计39个字。诗写的是诗人发现鸟叫觉得有趣或甚无聊,于是学鸟鸣叫。诗分作9行,足见诗人之用心。诗题“它叫的什么只有鸟们知道”点出诗眼,表达沟通不畅的焦虑。首先是诗人在看鸟叫,以为鸟叫是在呼唤同伴,于是学叫起来,结果鸟停了一下,又叫起来了。点出鸟也在看诗人,诗人眼中的鸟“它叫的什么只有鸟们知道”,而鸟眼中的诗人在叫什么也是一片疑惑,因叫而看,由看引叫,自此深化出悲时悯世的情怀。这与鲁迅《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狂人看世道,世道误狂人),零度叙述给客观世界涂抹上荒诞的色彩,从而寄寓了存在主义哲思。
与“看”对立的有一种“无视之视”,令人感到切肤之痛、唇亡齿寒。且来读一读《左撇子晚宴》:
是的
它不能动了
它是经过怎样的历练呢
它的头伸着
四只脚做着爬行的姿势
就像它
早晨醒来的样子
现在它就趴在
一个圆圆的大大的白色的瓷瓶里面
而我们
站起身
越过它
互相望着
右手拿筷子
左手端酒杯
只有阿波相反
诗中,“它”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它肯定尊严地活过,而现在它趴在“白色的瓷瓶”里面,我们,“站起身/越过它/互相望着”,无视它的存在。这种无视之视因举杯相庆时刻左撇子阿波的异数将一片祥和撕裂。诗人依靠朴素、自然、诚实的白描,来洞见存在之痛,复归身体之痛。
三 复归身体之痛
身体之痛是一种生理状态,身体某个部位疼痛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很多疼痛无关紧要,比如轻微的外伤,因为这种疼痛没有造成内部损害,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但有些疼痛则是由内至外所引发的,这将给身体带来无尽的生存负担。文学“身体”因其虚构的无实体性,其身体之痛往往由内及外呈现在“身体意识”的解构和对生存的忧虑上。
(一)“身体意识”的解构
性原本基于人的对死亡恐惧的生存欲望,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行之路,人类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构建于其上,有学者谓之“力比多场”[8]。
“妈的X/老娘插个队算什么/他们当官的/插队招工/还插人呢/妈的X”(《妈的X》),这里身体的性欲被平面化解构,插队、招工、插人并列,还原成生活场景,成为社会关系的附庸之物。诗人将“性”祛神圣化,借泼妇之口,来表述身体“性”的迷失的痛楚。《我想跳起来》中对我与小孩、女人关系的模糊化处理,其实质也是对“性”及基于“性”原初功能性解构。
再看《关你卵事》:记得隔壁/老涂他爸/和他妈吵架/说是用两块肥皂/一条毛巾/就把哑巴女/搞定了/他爸实在老实/任由他妈/牵着耳朵在门口转圈/跟游行一样/有人前来劝架/他妈叫起来/操他哑巴妈/我们屋里的事/关你卵事。这首诗则是对“性”的商业化解构,情节采取戏剧化处理,从而让“性”以货币等价物的形式“狂欢”在饭余茶后的插科打诨中。
《白求恩新传》则是通过身体组织的肢解来解构生存与死亡。这里没有战争的正义性论述,没有英雄形象的塑造,却通过身体组织的肢解、变异,来消解英雄医生白求恩救死扶伤的意义,从而溟灭了生与死的界线。
(二)生存的忧虑
对生存的忧虑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生存的忧虑必然成为文学“身体”疼痛的归宿。相比于史铁生用生命来书写生死困境,哦该的诗歌或可归之为生活流。生活流主张“让生活本身说话”,按照“生活本身的自然流动”,对生活作一种“纯”客观的记录。这种纯客观的记录,对于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做任何思考和概括的,甚至没有情节,没有时间的串联,有的只是万象杂陈。哦该的诗歌中的叙述虽无显在的逻辑,但又呈现着某种必然性。当然他的生活流倾向不是复古现实主义,其虽然是生活片段的自然展示,但在整体中往往采用了象征、暗喻、通感等修辞手段,从而影射出现实的荒诞性,勾起读者的生存忧虑与生命玄思。
1. 视觉焦虑。《盲人体验》中,诗人关闭所有的光源,在黑夜中(由诗中的“其实,在这一过程中/我是完全可以/开灯的”可以推敲出),体验盲人的生活感觉。读者一定觉得诗人是不是疯了,所为之事很是荒诞,难道他享受这种睁眼瞎的感觉。对了,这就是诗人所感觉到的困惑/问题的所在。事实上这是对荒诞的影射——现实生活,人在生活中就是“睁眼瞎”。
2.沟通困境。诗人出国旅游,“我站在欧洲的最西边”,很是激动地“往国内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诗人没有点明,但是按照人之常情,幸福时刻肯定是与最亲密的人分享,但是“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你是谁”?诗文在“起、承”阶段笔调高昂激越,在“转”的阶段,通过冰冷的语言“你是谁”,将诗人冷水淋头,至于后事如何,诗人没有赘述,他把诗歌的“合”留白给读者自行建构。这种情绪流动的跌宕起伏犹如重锤击响我们的生命体验之钟,这是对人际沟通不可行的深层焦虑。
3.文明困惑。在《地铁》中,笔者品味出一种“文明困惑”,或许用术语化的“现代性焦虑”表达更为贴切,但笔者自始至终都在怀疑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质性,所以更愿意将之称为“文明困惑”。
我们且来读一读《关于麻雀》:
城里的麻雀
比山里的
胆子大些
小王摁了三声喇叭
路边的樟树上
一群麻雀仍然嬉闹
这可不像
前天到乡里
拐个弯
轻轻的脚步声
就给麻雀
带来了恐慌
关于城里与乡下麻雀的细节差异性,这是诗人在诗中带着的无问之“天问”?城里的麻雀肯定是见过世面的,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对现代文明“工具理性”缺乏足够警觉,沉迷在文明所带来的喧嚣的幻象中。与之相比的是乡里的麻雀,仅仅是“拐个弯/轻轻的脚步声/就给麻雀/带来了恐慌”,这种恐慌更多的是来自生命对外来者侵入的自然抵触,这是生命对生存的一类难能可贵的警醒和对自然和谐的不可得的困惑,未尝不是一种对生命的敬重。通过城里与乡下、汽鸣声与脚步声、嬉闹与恐慌的三层对比,诗人把读者带至了现代文明的“囚徒困境”,却没有点明原因,也没有指明出路,而是麻雀众生自寻出路。
王国维用“隔”与“不隔”来界定诗歌之境界,笔者更愿意用“有味”和“冒味” 品评之。哦该的诗,是有味道的。在《地铁》,无论是整本诗集还是里边的一首首诗歌,呈现出天然的整体性,犹如人类之“身体”一般。从身体修辞的视阈去品味之,其“文学身体”上富有浓郁的平民化身份意识,诗人通过对世事万象的原生态的呈现,依靠“身体”肢体动作和切肤体验,传达给读者一种身体的疼痛感,进而实现对身体意识的解构,影射出对生命的关怀和存在的焦虑,在日常琐事里建构其独特的身体诗学。
[1]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J].花城.2001(6):192-205.
[2] 李石光.身体修辞与中国当代小说研究[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1.
[3] 王晓华.主体缺位的当代身体叙事[J].文艺争鸣·理 论,2008(9 ):6-12.
[4] 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7:11.
[5] 老 庄.现代天问——读哦该的诗[M] ∥哦该.地铁.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2):1-5.
[6] 唐 涛.身体思维论[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7] 钱钟书.通感[M]∥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186.
[8] 朱崇科.身体意识形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