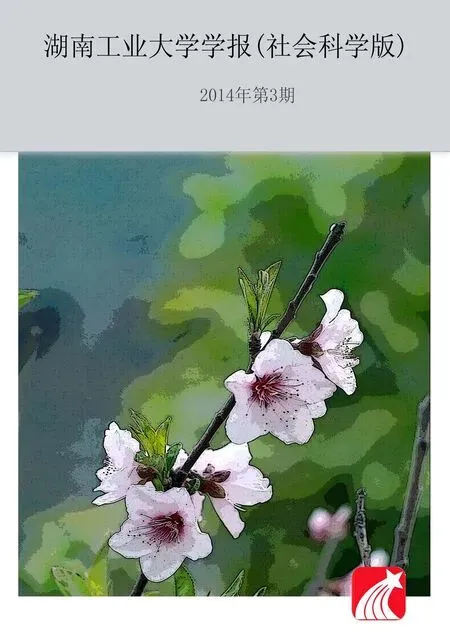打捞遗失在角落里的诗意
——论庄宗伟的诗歌创作
赵玮璐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寻根文学”的发展,全国涌现出了一批乡土诗人。1987年,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等人提出了“新乡土”这一概念,参与这一流派的诗人因此被称为“新乡土诗群”。[1]庄宗伟是其中一员,以“老庄”之名作诗。随后,湖南诗坛又出现了“新湘语”诗群,庄宗伟既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也是“新湘语”诗歌的首倡者,此时他的笔名为“金色山庄”。这一阶段“角落”叙述与地道的湖南方言成为了庄宗伟诗歌创作的特色。按照他的说法,诗歌即“小说”,小声地说。相对于那些书写宏大主题的诗歌来说,他更愿意去写渺小,挖掘那些不耀眼、不辉煌、容易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故事。陌生化的处理会使平凡的故事充满新鲜感而引人思考,进而令小诗富有超越表象的哲思,庄宗伟倾力于此。在他笔下,那些小故事无不打动人心,于浮躁喧嚣的当下社会有着治愈心灵的作用。
一 挖掘“角落”里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庄宗伟出生在湖南省西北部的桃源县,划归于常德市管辖范围。桃源县自然条件优越,物资丰富,历来被誉为“世外仙境”。少年时期的庄宗伟就生活在这样一片乐土上,远离繁华,故乡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他淳厚朴素的品格。成年之后,庄宗伟走出村庄,进入城市,生存的磨难与压力让他怀念往昔。童年的经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故乡会成为他心灵的归宿点。“当他们试图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生存感受的时候,很自然便想起乡土童年的人伦风物,总想用乡村田园的风景画、风俗画和故土亲情,来替代或冲淡眼前的生存漂泊感,并以此证明抑或是强化自己的根基意识。”[2]因此,故土赐予的力量给了庄宗伟在浮华中坚守自我本真的信仰。因此,他才会说:“诗是小说,即小声地说。反对大说。我的出生地桃源陬市,陬,角落的意思。一个人的出生地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我一生都在角落里写诗,写角落里的诗。”[3]
庄宗伟从身边的事写起,瞥见湖水里天空的倒影,便写下《两个湖》;遇到两列反向而行的火车暂时停在一处,便记录下生命中的这次偶然;一只被宰杀的芦花公鸡引发他的联想,他便一口气写下了5首关于那只鸡的小诗。对于身边的朋友,他也愿意将他们写进诗里,《凝视/献给已在另一个世界的学友杜平》《李文革》《以前的欧阳》《我们大家的李婷》《阿红你在哪里》等,每首诗也就十几句,这些朋友的形象立刻就跃然纸上。有哪些不能成为诗歌呢?在庄宗伟眼中,生活中任何平凡的小事都可能成为一个聚焦点,这是他对诗歌写作所持的一种观点。写角落里的诗,是一个诗人甘于日常的诗心之体现。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的,能在平淡中发现惊喜需要一定眼力,也必须拥有对生活始终怀抱希望的热情。“从岳麓山下来/躲雨的人/靠墙壁站着/闪电将夜晚/照得雪亮/飘飘洒洒的雨丝/不紧不慢地下/几个躲雨的人/一点也不急/与其说是在躲雨/不如说是在看雨”(《躲雨》),如躲雨这般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在庄宗伟笔下也能获得一种新生,让人忍不住遐想:走进飘雨的那一天,那个地方,居然发现躲雨也可以躲出一种美妙的感觉。诸如此类的感触在庄宗伟的诗中无处不在,他有一种功力,能使读者平心静气地慢慢体会、感悟生活。“起初的夜晚/阳台上/还有隐隐的哭泣声/后来,在风中/越来越干/越来越冷/再也不可能/回到水里/便不再哭泣/这样的夜晚/安静得有些可怕”(《风干鱼》),在冷清落寞的氛围中,诗人为一条风干的鱼唱一首挽歌,庄宗伟的情感就是如此细腻。生活处处都充满哲思,只要你愿意用心去观察。在《知觉》这首诗中,庄宗伟如是写到:“那些树/已经长了一千年/使劲地敲打/一点都不痛的/可是,那像枯藤一样/裸露在地上的根/我只略为踩了一下/它们就尖叫起来。”前半部分,树还是树,于常人看来,就如同一件摆设,无关痛痒;可后半部分的描述让我们不禁心头一颤,树是有痛感的,你若在它的根部踩上一脚,即便已成枯藤,它也会尖叫。
角落,是庄宗伟诗歌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的细腻感悟,反过来又成全了角落里的故事,让它们呈现自我的意义。当然,这些意义有时是诗人附加上去的,但至少能让我们也关注这些稀松平常的小事,发现与远大理想、目标不同的微小现实的另一面,它们不再是抱怨、烦恼的借口,只要你肯换一种视角看待,它们就如夜空中的繁星,闪闪发亮,玲珑可爱。
《土壁虎》这本诗集里有许多作品是叙述性的,短到几行,长到一百多行去交代一件事。“鸟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爱鸟的人/和不爱鸟的人/背起行囊/纷纷赶往鸟村//有的被水淹/有的遭蛇咬/有的干脆打道回府/最终进入鸟村的人/少之又少”(《赶往鸟村》),这首诗读起来像一则新闻报道,简单叙述了人们赶往鸟村的情况,客观而又简约是庄宗伟的风格,但这看似客观的叙述背后,其实隐含着诗人的价值观。去往鸟村的人因遭遇困境而不得进入,这是诗人亮出的态度:鸟村不欢迎人类的到来,因为他们将会破坏这片自然生态区的安宁。又如小诗《地域之差》《关于我的称呼》《鸡腿鸟》《宋老太太》等,就如同与读者聊天般自然流畅。如《宋老太太》:“假如你想知道明天是晴还是雨/就去问一栋八楼的宋老太太/她的天气预报/比中央电视台的还要准……是呀,对于天气预报有谁留意过/——除了宋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做到”。长诗《卡通小唐》《冻死鬼》等讲述又类似于小说,所以,叙述性风格是庄宗伟诗歌的又一特点。在小诗中,叙述显得质朴而亲切,长诗中的叙述则使诗歌类似故事,生动鲜活,引人入胜。《冻死鬼》略显厚重,《卡通小唐》的叙述则轻松活泼,仿佛是从孩子眼中看到的世界,从孩子口中说出的天真无邪的语言。
二 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处理
“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于现实的感受和反应变得陈腐、滞钝了,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了。”[4]同日常语言的这种现象相似,生活中的小事也被“自动化”了,如何能使它们引起读者足够的关注,是庄宗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生活离我们太近、太熟悉就容易熟视无睹。这时,陌生化在生活书写的转化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日常琐事被写进诗中,原本就是一种对“非文学”的文学化处理,能提升生活中过度自动化的寻常事、惯常作为的被感知度,进而使之陌生化。而后,诗人的思维方式也得跟着变换,要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讲得新鲜,描绘得出彩,设置疑问与悬念,既让他们获得阅读的快意,又能引起思考。
先来谈谈庄宗伟为一只被吃掉的芦花公鸡写下的一组小诗。关于一只被宰杀后吃了的鸡,人们已经漠然了。一个怀有诗心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为一只鸡的代表写下5首悼念之作——《那只芦花公鸡》《上帝的旨意》《对芦花公鸡的哀悼》《一只真正的芦花公鸡》《少了一只漂亮的芦花公鸡》。人们已成习惯的宰杀行为,造成了漂亮的芦花公鸡的死亡,在诗人看来,这不是一件可漠然对待的事情。“它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商议着/杀一只活鸡/款待贵客”(《那只芦花公鸡》),鸡的不知情和人残忍的预谋形成反差,“那只芦花公鸡就这样/在一个炊烟袅袅的黄昏/走到了我们的餐桌上”,一只无辜的鸡死于人手。看似平淡的叙述,却令读者心中戚戚然。“鸡吃虫子/我们吃鸡/真的是很平常”(《上帝的旨意》),确实是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大自然的生物链本就如此,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吃什么都有可能,越吃越离谱,而鸡是人类最平常不过的食物了。“鸡吃虫子时/虫子时活的/我们吃鸡时/鸡已炖熟”,诗人在怀疑:“只是/我不知道/哪一种方式/更符合上帝的旨意”。习以为常的事情就一定是合理的吗?这不见得。诗人有着反向性的思考,他在怀疑在反思。随后两首是对芦花公鸡平日里活动的一种怀念,类似于葬礼上的追悼。最后一首诗中,诗人写道:“我略为有些不安的是/对不起那些刚刚学会了撅屁股的母鸡们/——明天,它们会发现/少了一只漂亮的芦花公鸡/一定会若有所失”,诗人用戏谑的口吻,站在母鸡的立场上,表达了自己对于死去的公鸡难过与不安。
通过这5首诗的连续提醒,我们能隐约感受到内心的拷问,这是在平日里大口吃鸡肉时所不曾想到过的。通过写一只鸡,诗人带给我们更大的思考空间:关于世俗陈规,关于道德,关于自然界的公平。这些深入灵魂的反思都是诗人在陌生化处理过程中所收获的精神财富。
我们每日行走在马路上,经过的房屋可曾引起自己的注意呢?每座房屋在庄宗伟这里都被赋予了生命,他写那些将要被拆除的旧房子,就像在同情一个将要离开的朋友。“街上有很多旧房子/都划着一个红色的圈/里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这些房子这些人》),画面定格在这些有圈有字的房子上,“布告栏里/要枪毙的人/打着一把大大的/红色的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些房子就像被审判的人一样,等待着命运最后的裁决,没有了反抗的余力。他们“很不好意思地望着/对面的银行/和街上来往的事/这些房子/这些人/不久要/彻底消失”,由即将被拆掉的房子,联想到还在使用的建筑和正在行走的人们,其结局都是一样的——不久就要彻底消失。一座旧房子照见了万物的命运,谁说行将消失的事物就毫无价值呢?这其中蕴含的哲理同样能留给我们无穷的回味。令人震撼的历史事件,我们能引以为鉴,在庄宗伟这里,不动声响的旧房屋同样可以。
另外,庄宗伟诗歌创作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陌生化处理的效果。他坦率的、叙述性、聊天式的语言风格与那些内敛、节制的诗歌语言风格形成差异,让人读来感觉耳目一新。
三 湘方言书写的魅力
湖南方言在诗歌中的运用是“新湘语”派诗人的“专利”。他们用地道的湖南话来组织诗歌语言,形式灵活多变、轻松随意,用调侃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语言表述上近乎口语,但相较于当下的“口语诗”而言,它又具有鲜明的湖湘地域特色。同样,他们书写的也是日常生活中平淡的小事,庄宗伟的诗作在其中又颇具特色。
读庄宗伟的“新湘语”诗,不懂湖南方言的人肯定会有点不习惯,只能大概猜出些意思。比如《讲点别的啰》里面有句话:“我还价:‘5块钱一斤,要得唦?’”“晚上,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发呆/讲点麽子别的啰?/我偏不讲/要讲就讲一句:碰哒鬼”,《鸟儿问答》中的“你哦该啰?”“那我还冇哦该些”“个砸妹子蛮灵范的”,《阿红你在哪里》中的“我在哪里关你卵事”,《童谣》中的“看哒看哒长/看哒看哒结”,《冷水浴》中的“身上冒哒好多的热气”,《戴妹子》中的“咩黑的”,《八月的西藏》中:“天哦该/是透蓝的/云哦该/是嫩白的/刚下飞机/你又哦该/歪着个脑壳”,《行走高原》中 “不晓得/是哪么上了天的”等等。语气词“唦、啰”都不妨碍理解大意,“哒”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助词,如要得、麽子、灵范、关你卵事、咩黑等等,我们大都还能猜出意思来,毕竟和普通话中的用法有相同或相似的用字、结构。至于“哦该、个砸”如此太过于地方个性的词语,就不太好猜了。方言里没那么多礼数,讲起来比较有快感,这更增添了庄宗伟诗歌的坦率气质。
“新湘语”似乎有意将“乡土化”写作进行到底。语言本就是一个地域文化标志性的元素,作为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方言,将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无疑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方言出现在诗歌中,这当然是极少数的情况。与普通话相比较,方言有其局限性,对于不懂某地方言的人来说,也许很难读出诗的味道。贾平凹的《秦腔》借用近乎完全口语化的方言系统,展现了中国西部农村近20年来社会传统风习的衰变。作家在用方言对“清风街”民众“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铺排陈述的同时,也为秦地的民俗风情保留了一份历史记录。我一直相信,只有本地区的语言才能准确完整地记载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
庄宗伟以方言写诗,又何尝不是在记录与保存桃源乃至整个湖南的地域文化呢?诗歌由从前的象牙塔尖落户到现在的平常百姓家,语言不再拘泥于阳春白雪的书面语,而追求多元化、个性化。不熟悉的语言制造了理解障碍,却增添了不少地方的生活情趣,也因为这种暂时的障碍,延长了诗歌审美的难度与感知时间,对于诗歌来说,这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读诗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新湘语在庄宗伟诗歌中的运用,是一种形式上的“角落化”,这与他诗歌内容方面的“角落化”互为依托,也算是彻底地实现了“角落”的创作。作为庄宗伟的“母语”,湖南方言的写作使其作品具有了乡土民谣的特点,增添了诗歌的现场感与生活气息。既然是方言,就要说出来,这些主要体现在对话中,所以庄宗伟的“新湘语”诗多数都有人物的对话。比如《讲点别的啰》中有三组对话。第一组出现在菜场,“我还价:‘5块钱一斤,要得唦?’/那汉子将刀往案板上一撂:/‘讲点别的啰!’”活生生就是市井生活的再现。第二组诗在烈士公园,“我对其中的一位女士说:/‘你蛮漂亮咧!’/那女士笑着对我说:/‘讲点别的啰!’”第三组在办公室,“我对他谈起新湘语诗歌/他打断我的话:/‘讲点别的啰!’”方言决定了诗歌主题只能是小地方人物琐碎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手法,方言入诗,无可非议。但是,口语化因过于随意,引发了很多争议,似乎这种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很多否定者认为方言口语诗已弱化了诗歌的美感。这的确是“新湘语”诗歌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将方言运用得恰到好处,既体现地方个性,又不影响诗歌该有的审美,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挑战。
四 寻找精神的“安所”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庄宗伟对此也表示赞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伴随经济开放的还有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如何在外来文化大潮冲击中守住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在此背景之下,“新乡土”诗派诞生了。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火热的诗歌浪潮中,湖南诗人也不甘示弱,全国七八个省的“新乡土”诗派中当属他们最引人注目。“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并且,由江堤、陈慧芳合著的《两栖人》被当时的评论界认定是‘新乡土诗派’的标志性作品。此诗准确地描绘了两栖人的生存状态:‘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我很可能腹背受敌/其要害正是/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5]这是那个年代诗人的心声,这样的情怀突出地体现在城市中的某一类人身上,他们称自己为“两栖人”。“所谓‘两栖人’,就是侨居在城市的农民子孙,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仍生存在城市之外的村庄。”[5]这些人认定自己是农民的后代,他们的根依旧紧紧牵系故土,对于本地的城市人来说,他们只是“侨居者”。即便物资富足,精神却常常游离在都市之外。他们书写着“两栖人”的迷惘和困惑,致力于建设一个“精神家园”,试图找寻到精神上的安稳与满足感。庄宗伟也是其中之一,他的诗大多涉及湖南地区的山水、人文,这也是他成为“新乡土”派诗人的原因。
与日益物质化的都市相对应的,是人们越来越空虚的精神世界,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不仅仅是“两栖人”需要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和谐的大自然与温馨的日常生活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渴望与追求,这也造就了庄宗伟诗歌存在的意义——为身心疲惫的人煲一碗家常的菜汤,清淡舒爽,暖人心口。小碗菜汤比不上鲍鱼燕窝的滋补功效,但我们偏偏离不开它,就如平淡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生命只有依赖它们才能持续下去。庄宗伟不书写宏大主题,只钻研他的小事情,慢慢研磨,就是要清淡这个味道。我们读到他的诗,能够暂时卸下繁重的包袱,偷偷乐一乐,再想一想,竟然真能在其诗中获得一点安慰与片刻安宁。这也是小诗的伟大之处,虽然小,却能慢慢修复心灵的创伤。
除了日常生活的细腻,庄宗伟还关注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身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他的良知唤醒了责任感;作为一个诗人,他义不容辞地写下了组诗——《鸟村纪事》,一共16首,写到了鸟村的每个角落。他写鸟村的概貌,鸟村的历史,前往鸟村的游客,鸟村的村长、村民,鸟屎,鸟村行恶者的报应,鸟村的风景,鸟村的灾难和最后鸟村的结局。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庄宗伟热爱大自然,关注环境保护,所以才会用心写下这么长的一组诗。这与之前关于芦花公鸡的5首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鸟和鸡都是自然界的生灵,诗人用诗歌呼吁人类与这些小动物和谐共处,珍惜它们的生命,保护大自然这个共同的大家庭。
虽然单纯的、叙述性的小诗占据了庄宗伟创作的主要部分,但他也写走向内心世界的诗歌。《霞为谁而燃烧》《小美人》都是发自肺腑之作,读来让人震撼,可见庄宗伟是个性情中人。“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呼吸/有时候,你呼吸春天/有时候,你呼吸女人的温馨的气息”,“长久以来,他对自身意义的思考/如同走进一个幽暗的回廊/没有希望,没有结果,因而也没有意义/直到——/她来了/像一束猛烈的阳光/在一阵眩晕里他扶摇直上”,在《霞为谁而烧》中,诗人的感情起伏跌宕——懊恼与绝望,希望与渴求,都表现得那么热烈。《小美人》中,诗人也坦白自己为那位美人所倾倒,不断赞美,一次次地奔向他心中的女神。然而,“三次死亡是一部史诗/三次死亡构成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三次死亡是一部天书,无人解读/三次死亡像一道神奇的光波,在宇宙中飞旋”,这是诗人强烈的感触,自内心发出。也只有这样的性情,他才能在心头喷涌出热烈的情感流,也才能写出这样的诗。
庄宗伟的诗歌有其鲜明的个性。“庄宗伟保有的坦率是诗人最可贵的品格,诗人坦率才能真诚,单纯、坦率,就更诗味的,更灵性的,更大气的,最素质的了,最本性的了。”[6]他诗歌的乡土味道、方言特色,他的“角落”叙述,他的真情抒发,都是这个时代看似与之相悖但又极其缺少的东西,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慰藉,所以它们不会消失。
[1] 刘向朝.湖湘文化与1980年以来的湖南诗歌[D].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2007.
[2] 欧阳友权.论新乡土诗派的诗品与文心[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7):55-59.
[3] 桃花源诗歌网.诗与影像:庄宗伟[EB/OL].(2011-03-27).http://ad.cdyee.com/taohuayuan/info/newsview.asp?id=540.
[4]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5] 陈慧芳.长途跋涉的诗歌之旅——新乡土诗派概论[J].创作与评论,2012(7):74-78.
[6] 彭燕郊.土壁虎[M].台北:黑眼睛文化,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