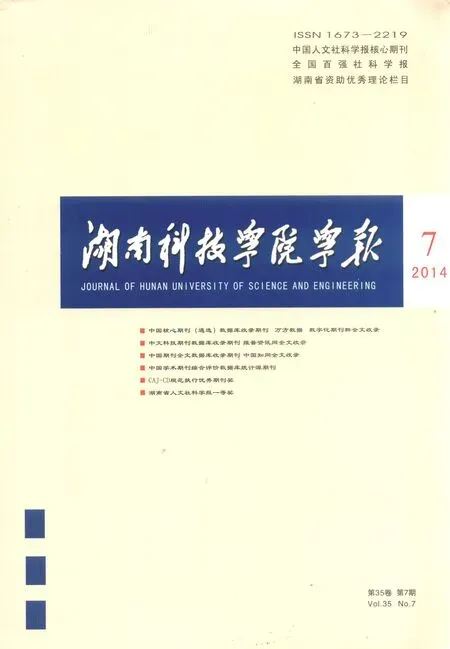女性摆脱“他者”的地位——从《她乡》看吉氏母职观的进步性
龙 沁
(广东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她乡》中从女性的角度重新定义母职,赋权于母亲,号召她们摆脱他者的地位,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在第一波女权运动风潮的影响下,吉尔曼为女性发声,将女权主义思想写入颠乌托邦小说之中,其思想具有前瞻性。这不仅是对当时乃至今天社会的改革和女权主义运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20世纪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性要勇于走出他者地位,正确的认识自己,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就波伏娃的观点,在父权社会,男性是绝对的自我,女性则处于他者地位。女性是往往是按照男性的要求来塑造自我而不是根据本身的需求来发展。
一 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回顾
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意指“没有的地方”或是“好地方”。柏拉图最先在《理想国》中表达乌托邦思想,它源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但内心仍向往美好,在精神上建立理想国度。而乌托邦文学则源于托马斯•莫尔1516年创作的《乌托邦》。乌托邦文学是驰骋的思维来谱写理想的精神家园,在作品中将理想变为现实。早在18世纪,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就已诞生。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是在乌托邦精神的指导下,在虚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运用女性主义思想批判当下社会、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其终极目标是改变女性在父权社会的他者地位,表达女性作为平等的社会人想要谋求独立自主的呼声。初期的该类文学的代表作是英国作家萨拉•鲁滨孙•司各特于1762年出版的《千年圣殿》。19世纪,在女性主义发展的浪潮中,许多女作家积极创作乌托邦小说。1890-1920年是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创作的繁荣期,吉尔曼的《她乡》便在此时孕育而生。20世纪后半期,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的创作出现二度繁荣,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1980年以后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不再遐想构建美好的理想家园,它们根据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端预测明日世界的种种问题。如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
二 吉氏母职观的内涵
《她乡》通过描述三名美国男性科学家范、泰利和杰夫在她乡的奇遇,开始关注故国女性的生存境遇,对当下美国社会的男性主体地位观产生了动摇。三位探险家在她乡先后经历了囚禁,企图逃脱不成,再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结识她乡少女,进而结婚,最后驱逐出境。在这一次探险中,他们体会到男性在她乡的境遇竟如同于当下美国的女性,她们得抑制自我的需求来迎合男性,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塑造自我。
在见识了她乡女性的社会成就之后,范·泰利和杰夫感到他们自以为傲的男性尊贵被完全颠覆,传统中轻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是错误的。在没有男性涉足的土地上,女性运用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建设了令男性叹羡并为之向往的乐园。他们在叹服于女性社会的文明与和谐,摒弃当下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来反思社会现实中的父权价值观。在父亲们眼里,所谓的母职就是帮他们料理好“后花园”,相夫教子,在育儿和家务中终其一生。然而在《她乡》,“母职是个人对国家生命伟大的贡献,其他的个体一同分享共有的活动。”如此一来,《她乡》正面驳斥女性只能待在家中终日繁忙于家务中的宿命与历史使命,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以颂扬之名行限制之为的罪行,颠覆了女性没有话语权,无法参与政治的谬论。
(一)母职代表一种独特的身份
艾德里安·里奇认为“母职体验”是女性“与自己的生育能力和孩子之间的一种潜在关系”。虽然吉尔曼反对父权社会的“女性生来就是母亲”论,也并不认同所谓的“母性直觉”观,但从未否定女性的生育潜能,甚至认为母职体验能让女性在精神上更加的丰腴,这一思想在《她乡》中而有所体现。在她乡人看来,不生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她们的生命因此而缺乏重要的亲职体验。生育女性在她乡有着至高的荣誉。但经验性母职并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母亲不应被家务和育儿而困于家中。父权社会企图通过“家中的天使”这类假说来将母亲麻痹,要求他们本能的无私奉献,遏制其发展自我的潜能。吉尔曼并不赞同范在她乡时的言论:母爱不是母亲对孩子强烈的情感、纯粹的直觉,对女性来说,它就是一种宗教、信仰。
吉尔曼认为,破除制度性母职的第一步是女性必须得清楚的认知自己的身份。已婚生育女性不仅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更是有着思想的独立的社会个体。生物性母职和社会性母职两者间并不相矛盾,母亲有权选择,有能力兼顾,能在两者间找到平衡。家务和育儿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能将母亲从家庭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在她乡,母职不仅是直觉,更是理性选择。母亲身份不仅是一种本能,而且是一门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女性都能成为生理上的母亲,是个人和社会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不像我们的受孕是无助的,不是出于自愿”,她乡女子有权自由选择是否生育,倘若被认为不适宜履行母亲职责则被劝服不要生育。在当今社会,这一论断仍有进步性与指导性。培育、教养孩童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人人都得投入到爱护、抚养、教育孩子的大军中来。
(二)母职包含一份神圣的职责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母职和家庭领域的必然联系有着一定的历史语境。以美国为例,在工业化之前,家庭构成社会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参加生产,例如作为织工,厨师或手工业者。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分工加剧了性别角色学说,至少是在话语上,把男女两性分成不同的类别。在如此重新定义的新世界的阶层里,母亲被贴上了“家庭道德卫士”的标签。一旦男人们外出工作,他们就想要有个私人领地,能让他们享受家的温馨已得到身体上的休整和精神上的支持。顺理成章,妻子-母亲的职责就是经营温馨家庭给外出务工的男性提供避风港。制度性母职赋予母亲的专属职能是家务和育儿,将母亲约束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之中。她们因母职而生,为母职而活,对母亲而言,生命就是漫长的母职周期。
吉尔曼在其乌托邦作品中强烈的批判父权制对女性天职的定义。吉氏察觉到女性不仅是生命的孕育者,更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体。母亲需要挣脱家庭的桎梏,进入公共领域,在社会中寻求发展,履行平等社会人的职责。因为其在性别阶层社会里的特殊位置以及母性经验的独特体验,根据平等的原则,她们比男性能够更好地建造社会。她乡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母性社会,国民们爱好和平、遵纪守法团结仁爱,这里秩序井然、公正富足,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她乡的母亲们自尊自重,享有良好的教育,她们不仅是和美家庭的维系者,同时担负着社会责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当范·泰利和杰夫三人初到她乡时,他们叹服于女性们所建构的她乡世界的美好与井然: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秩序井然,平整而光洁,洋溢着温暖的家的感觉。我们越走近镇中央,房子也越密集,好像随时可以转换成结群的宫殿,一起逃跑,漫游于公园和敞开的广场之间,又好像大学的建筑矗立在安静的绿野之上。更令三位科学家折服的是她乡女子们匠心独运的道路设计丝毫不亚于发达的欧美地区。
(三)母职赋予母亲不可剥夺的权利
女性身体的功用不仅限于性交或是生育,它还是女性成事的载体,包括受教育和进入公共空间实现自我的权利。女性在荣升为母亲之前,应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清晰的认知力与辨别力来为自己的人生特别是身体作出独立的选择,这也是她们摆脱“他者”地位的有效途径。吉尔曼并不认为母亲是家庭工作的不二人选,相反地,她主张女性要敢于获得本身应有的权利,从而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在吉尔曼展现给读者的理想婚姻的范例中,她倡导的是一种与她所处时代截然不同的婚姻关系,这种积极的伙伴关系能让男女双方自由平等的发展,婚姻中的两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相互依靠的整体。吉尔曼所塑造的她乡人,是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与压迫的环境中,她们有着全面的发展以及鲜明的个性。故事中的男人没有丝毫的社会优势,带着既定的社会成见,他们不相信她乡和美社会的建设源自于女性,更无法接受自己逊色于女人国的国民。依吉尔曼的观点,男性需要经历进化,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转变,他们的充分认知到母亲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以及权力。
吉尔曼极力宣扬打破制度性母职观的必要性,她站在女性的角度重新定义母职,其核心就是赋权于母亲。在完成经验性母职之后,母亲应该享有履行社会性母职的权利。作为独立的社会人,她们可以选择在家料理“后花园”,更能进入社会领域,提升实现自我。泰利带着故国传统的男性价值观审视着她乡女子,他认为他们不会谦让,无法忍让,不懂顺从,从未流露丝毫柔弱令人怜悯的神情,毫无女人的魅惑。社会学家范后来反省:我们所谓的女性魅力是长久以来男性们所期望的女子特征,为了取悦男性而持有的。她乡女子无须男性的雕琢,她们美得自信,美得自然。
三 结 论
吉尔曼通过虚构她乡设想了一个与眼前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女性自主的乌托邦世界。作品借由三位外来之客之口来重新审视现实社会盛行的男权价值观,强烈的批判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表达了女性迫切需要打破制度性母职的呼声。作品通过揭示母亲独特的身份,明确母亲的神圣职责,赋予母亲不可侵犯的权利,建立了女权主义的新型母职观,同时也为建立新型平等的社会做出了积极的展望。
[1]波伏娃,西蒙·德.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陈榕.女性主义乌托邦之旅——吉尔曼的《她乡》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之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3):96-101.
[3]吉尔曼,夏洛特·帕金斯著.她乡[M].林淑琴,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4]刘英,李莉.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历史使命[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55-59.
[5]刘英,张建萍.从“他乡”到“她乡”——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J].妇女研究论丛,2006,(4):67-72.
[6]曾桂娥.理想与现实的对话——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范式[J].国外文学,2012,(3):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