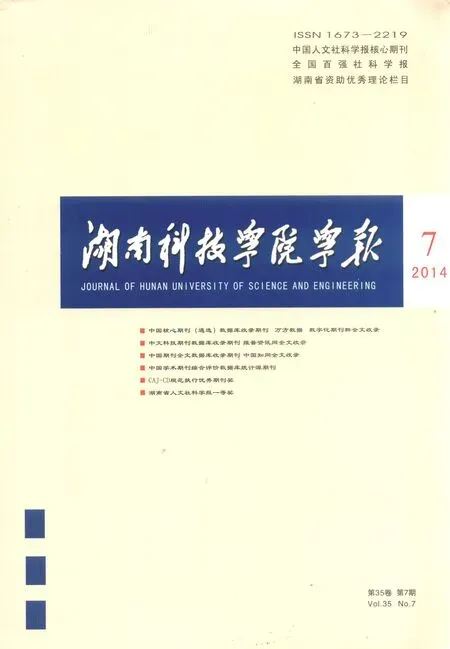从“虎中美女”与“梦幻泡影”论《金瓶梅》两大系统的主题差异
陈利娟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明代小说《金瓶梅》存在两大系统(严格地说,《金瓶梅》有三大系统,即“词话本”、“绣像本”以及“张评本”系统,但因“张竹坡评本系统”是在“崇祯绣像本”基础上进行的评注和修改,与“绣像本”区别不大,故归入“绣像本”系统),即词话本系统与绣像本系统。然而,后世的研究者或读者往往将这两大系统统称为“金瓶梅”,如百度百科解释:“《金瓶梅》,也称《金瓶梅词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1]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这部小说时,也大多使用“金瓶梅”这三个字来涵盖自己的研究对象,未对论述的小说系统进行特别的标识,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金瓶梅》与人情小说”(上)、朱星的《金瓶梅考证》、王汝梅的《金瓶梅探索》、周钧韬的《金瓶梅研究论集》等,他们往往仅以词话本或绣像本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却涵盖所有系统、所有本子,这种研究视域产生的结论与小说本身实际是有偏差的。因此,本文拟从两大系统第一回中的重要意象“虎中美女”与“梦幻泡影”为视角,论述两大系统在主题意旨上的不同,从而为研究者限定研究对象提供基础。
《金瓶梅词话》与绣像本在叙述上的共同点之一是,它们总是通过词或诗和解词或解词来导入故事,由此对故事的内涵形成重要的暗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引词或引诗、解词文或解诗文来推究作者的创作旨归。
词话本的第一回明确体现了作者的主题意旨。作者在引入酒、色、财、气四首词后,开始解说上文。“虎中美女”就出现在这段起承转合的解词文中: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去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2]
“虎中美女”这一意象是词话本一书的关键,它既作为章回小说的引子牵惹出下文,又以暴烈妩媚的意味比对作品人物的形象,还暗示了小说人物的最终命运。这一意象最早来自隋朝萧吉尊的《五行记》开始。《五行记》中的《袁双》即讲述了一个虎变美女与人类男性婚配的故事:“晋孝武太元五年,谯郡谯县袁双家贫客作。暮还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与双为妇。五六年后,家资甚丰。又生二男。至十岁,家乃巨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后,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脱钏挂树,便变形作虎。发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饱后,还变作人。有见之者,窃语其婿:‘卿妇非人,恐将相害。’双闻之不信。经时,复有死者,辄复如此。后将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实。后乃越县趋墟,还食死人。”[3]文中美女“姿容端正”,深得男主人公袁双喜爱,并与其结婚生子、经营家道;但美女实乃猛虎所变,尽管在人类世界中饱受文明教化,但嗜吃人肉的本性丝毫不改,当死人的肉体刺激她时,她便变形作虎,食吃死人。这个故事尽管只是简单地叙述了虎变美女终不改虎之本性的现象,没有对女子刻意隐瞒身份、以色相赢得爱情的情节做明显的描摹,但文本当中的男主人公至终才相信自己的妻子乃猛虎所化的事实,隐约地告诉我们:美女在真身显露前,一直欺瞒着丈夫。至唐朝,虎化美女的象征意味更为明显,其姿色更为出众,人性也更为鲜明,以美色惑人的性质也更为突出,如薛用弱的《集异记》卷二中的《崔韬》:“崔韬……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馀。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着之。’妻乃下阶,将兽皮衣着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3]小说中的“虎女”不仅颜色美丽、修饰严整、美艳动人,且主动投入男子怀抱,自荐枕席,其炫色诱人的色彩非常突出;男子也曾怀疑过美女的身份,以为其可能是猛虎所化,可是耽于美色,依然与之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期望其人性永存。但最后的事实表明:若得遇其时,遇到刺激其兽性大发的媒介,美人会即刻幻化为虎,恢复兽性,吃人嗜杀,不再遵守人类伦理规范。到了晚唐,虽然虎妻吃人的色彩渐渐褪去,但虎妻化虎时狂躁暴烈的形象依然震撼人心,这在皇甫氏的《原化记·天宝选人》有所反映:“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数年秩满,生子数人。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明日,未发间,因笑语妻曰:‘君岂不记余与君初相见处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此人方谢以过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转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此人惊惧,收子而行。”[3]虎妻身为人类时,与正常妇人无异,遵守人类伦理规范,生儿育女,但是一旦触犯其心怀,激发其内心的怒气,其兽性就会突显,倘得到助长其威力的虎皮,最后会成为真正的猛虎。薛渔思《河东记·申屠澄》中的“美女”更为美艳动人、风情万种:“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其女见客,更修容靓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不仅如此,还能够吟诗作赋:“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申屠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后加官进爵,其妻相夫教子、持家有道,与人间贤德妇人无二。但有日偶归山林,复遇虎皮,“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攫。突门而去。”[3]即便在人类社会中浸淫多年,拥有世俗的幸福,但其本性始终不改,得遇其时,终化猛虎而去。
这些故事中的“美女”皆从虎皮中脱化而出或是披虎皮而化虎,是“虎皮”当中的美女,可称之为“虎中美女”。这些美女虽然在其为人时并无恶德恶行,与正常的女性无异——养儿育女、辅助丈夫经营家道、富裕生活,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一般女性:拥有出众的外貌与气质、聪明贤良的性格、出类拔萃的诗才,丰富饱满的情感,但是其一旦触及虎皮,就会即刻泯灭人性、回归到兽类。其形象充满了恐怖无常、妩媚暴烈的意味。若再联系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脱衣、裸睡、偷窥、盗衣、求欢等一系列颇可驰骋想象的视觉盛宴场景,以及小说中男子惑于美色无法自拔、最后为其所害或所惊的情节,我们可以说这种“虎中美女”是隐隐带有“红颜祸水”意味的女性。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虎中美女”喻书中所写情色欢娱、酒肉流连不过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而已,可惜当事人沉溺于此浑然不觉,直至身首异处。
而下文的解释,从男子之丧志,写到妇人之丧身,最终又从丧身的妇人,回到断送了性命家业的男子,隐括了全书情节,照应了作者的暗示,体现了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词话》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贪淫与贪财的恶果。无怪乎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里面明确小说意图道:“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愚,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2]
另外,“词话本”第一百回的回前诗亦照应了小说秉承的这种思想:
人生切莫持英雄,术业粗精自不同。猛虎尚然遭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
七擒孟获奇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珍重李安真奇士,高飞逃出是非门。[2]
此回再次重申唯有“持盈慎满”,持之有度,方能逃出是非,颐养天年。既照应首回儒家“文以载道”的意旨,结构上也首尾照应,有一种对称和谐之美。
“梦幻泡影”是绣像本第一回“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一诗解诗文中的重要意象,它是作者关于此书主旨意图的在综述人生几样大的诱惑尤其是财与色本为虚空的过程中出现的:
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两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乘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污粪土。高堂广厦,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纷袄,孤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姗;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只有《金刚经》上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环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肩落眼,人皆掩弃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倒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装装,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案,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4]
“梦幻泡影”是佛教用语。出自《金刚经·应化非真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5]宋代王铚《四六话》中引丁晋公之话可为之注解:“梦幻泡影,知既往之本无,地水风火,悟本来之不肖。”[6]其含义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像梦境、幻术、水泡和影子一样空虚,喻世上事物无常,如梦境、幻术、水泡和影子,即梦幻泡影,一切皆空。它是《金刚经》佛学思想的最形象的体现。
《金刚经》乃后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是他所译大乘佛教空宗经典《大乘盘若波罗密多经》的浓缩本,包含了般若学的主要论点。《金刚经》的宇宙生成论、宇宙本体论和认识方法论是源起性空论,主要阐释此岸世界一切现象皆“假有性空”的奥义,宣讲宇宙万物是因缘而生成,生来变化,所有现象皆为幻想,此岸世界实为虚空的佛理。这种世界观深深影响了“绣像本”作者。
具体看绣像本第一回解诗文。此文的前半段,表面看来不过是“粪土富贵”的劝诫老套,但作者很快便把议论转到人生短暂、死亡无奈的悲伤方面。面对无法把握的世界,作者以《金刚经》是思想安慰读者,人生在世无非“如梦幻泡影”,只有“削去六根清净、参透空色世界”,才能彻底解脱苦海。这种思想相比词话本显得极端惊人许多,因为这样的出路,远非常人可以遵从。词话本的“持盈慎满”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针对社会中人发出的劝告;而剃度修行却已是超越了社会与社会关系的方外之言,是向读者进行的当头棒喝,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紧接着上面引述的那一段话,作者感叹:
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这既承接了上文“梦幻泡影”的虚空,又进一步突出了佛教“人生无常”。通过这段解诗文,我们可以看出绣像本所强调的,是红尘万物之无常与空虚,并在这种富有佛教精神的思想背景之下,唤醒读者对生命——生与死本身的反省,从而对自身、对同类,产生同情与慈悲。绣像本的开头,就这样为全书定了一种十分不同于词话本的基调。在这一基调下,绣像本《金瓶梅》中本应堕入阿鼻地狱、十恶不赦的恶男坏女竟有了人性的光辉,有了让人原谅的作恶动机,也因此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能让我们从生命尽头的虚无反省世俗的沉迷不悟、愚昧无知。
另一方面,小说第一百回的回前诗亦传递了这种意旨:
旧日豪华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黄芦晚日空残垒,碧草寒烟锁故宫。
隧道鱼灯油欲尽,妆台鸾镜匣长封。凭谁话尽兴亡事,一衲闲云两袖风。[4]
此诗与这段解诗文互相照应,明确传达“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的虚幻之意,也进一步突出了佛教提携幻化俗世之人最终看破红尘、皈依宗教的旨意,体现了作者刻意营造的佛教慈悲精神的主旨,结构上也首尾照应,亦有一种对称和谐之美。就这样,小说开始处作者重笔点出的“空色世界”,在小说的结构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换句话说,绣像本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本身,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的完美实现。
这两大系统主题明显的分歧几乎使得两书的主题思想与艺术价值判别有二,以至于哈佛学者田晓菲说:“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体现了一个事实,也即它们不同的写定者具有极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美学原则,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7]因此我们在论述这部作品时应该对研究对象予以明确地区分。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2]兰陵笑笑生.全本金瓶梅词话[M].香港:香港太平书局,1982.参见: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绣像[M].香港:文化书局,1983.
[5]陈秋平,尚荣译注.金刚经 心经 坛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