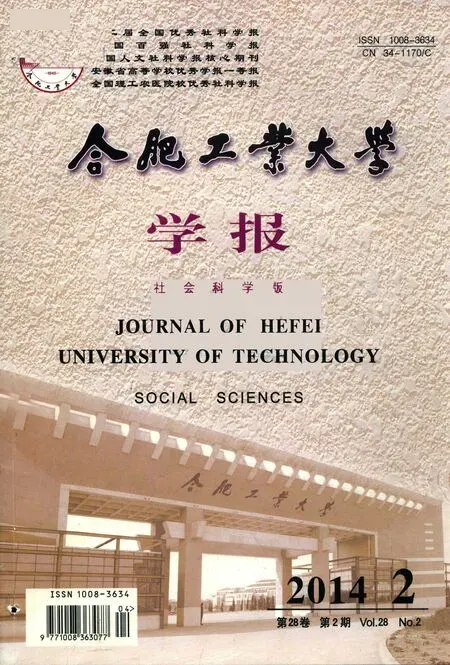精神世界的构建与解构——《沉沦》中的灯火意象解读
吕 蒙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一、引 言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佐证作者的病态心理或者其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以往《沉沦》研究的重点。其实小说对精神世界的构筑是更加复杂的,如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和主人公的“率真”自白,一副白热的心肠[1]24;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作者对意象的组织隐含着丰富的精神矛盾与冲突,读者通过这些重复的意象,可以解析小说中更深层次的寓意。
“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写而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2]51自然意象的塑造常常被认为是其“心像的外化”,在《沉沦》中有很多对于景物环境的描写,有分析认为,“他沉浸于自然景物中,把主体融入自然客体之中,消除主客体界限,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从而缓解和消除焦虑感”[3]113。自然意象在郁达夫早期小说中有独特的艺术指向,在《沉沦》中这些意象就是抒情的意境。本文所选取的灯火意象是富有内涵的,值得仔细推敲。
灯火是《沉沦》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其描写主要集中在文本中的三个地方:第一次是“我”坐夜行车离开东京去往N市时,火车奔驰在暗黑的夜色中,“我”开始数那星星灯火;第二次是“我”搬到N市的乡下之后,夜幕中看到的“望眼连天,四面并无遮障之处,远远里有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1]31;第三次是“我”“临死前”看到的“西面堤外的灯台的黑影 ”[1]31“一层茫茫的薄雾,把海天融混作了一处”[1]48。虽然灯火出现的场所不同,展现为“灯火”“渔灯”“灯台”等不同形态,但同样能渲染作者感伤的意境。
灯火在《沉沦》中多次重复出现有其奇妙的隐喻作用,能将纷繁复杂的文化环境和人物内心糅合在一起,表明主人公因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对峙而产生的多疑与敏感。文本中对灯火进行了三个视角的描写,首先,灯火的出现都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夜晚,第一次是在离城的车上,第二次是在乡下独居,第三次虽离开梅园,还在港口的“大庄子”;其次,灯火的出现都有黑暗的背景作衬托,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苍茫的夜色里,第二次是在“四面都是沉沉的黑影 ”的包围中,第三次是在“有着几点疏星”的“淡青的圆形天盖”[1]50下;再次,灯火的出现都有开窗远眺,是“我”在百无聊赖之中下意识的动作。第一次是“一个人靠着三等车厢”[1]28开始“数窗外人家的灯火”,第二次是因为“开窗一望”“远远的”[1]31,第三次是坐在酒家“打开了窗门”[1]48遥望海景。三种灯火意象的描写切入到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活动,可以看出其在构筑的精神世界中具有构建与解构的双重作用,同时能够引领读者对文本进行人物心理、环境隐喻以及文化隐喻三个层次的解读。
二、主人公心理的直接体现与自嘲式解构
意象是主人公心境的直接凝聚物,是自我心灵的外化。将主观描述与作者的情绪互为表里是郁达夫小说的特点,通常研究者认为这种写照是“描绘自我”,亦是李欧梵所认为的“自我的幻想”。有人将郁达夫小说的意象特征归结为“女性化倾向、死亡化倾向、病患化倾向、古典化倾向”[4]81,这些倾向展现出郁达夫小说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内心情感复杂的特点。
《沉沦》中,灯火直接透露出主人公忧伤、孤独、彷徨的情绪。因为远眺灯火,感觉离别的哀伤,对过去的留恋,被死神引召:“远远里有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1]31这样的灯火让“我”“几乎要哭出来了”[1]31。灯火本身并不会真的如灵异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会夺走人的性命,但是“我”仍会觉得恐惧,此刻“我”由于离开东京变得颓废沉闷,触景生情,感觉灯火像“鬼火”。灯火最终还是召唤“我”走向死亡:“他在海边上走了一回,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这种招引使得“我”想要跳下海去。“我”完成了招引中的动作,最终“我”并没死掉,此时灯火却给了“我”少许的安全感,这里完全是景替人愁,是“我”自己产生了被灯火招引死亡的幻觉。
与“灯火”相对应的另一个意象即“太阳”,在文本中太阳的出现更能说明主人公被复杂的情绪所困扰。“我”搬入梅园之后,见到雨后的旭日,生起的是“比平日更添了几分欢喜”的情绪。对梅园的这一段描写,因难得未受干扰而显得异常平静,灯火意象在此决然消失,一直到这种生活再次受到外来情欲的影响。“我”逃离到海边,看见太阳已经变为“夕阳”,夕阳半落,“灯台”与“夕阳”同在。这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灯火意象进行的烘托,其实是对人物心理进行了一次浓彩重描。作者笔下的意象群是以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轴展开的,不同的意象表现其不同的精神层面,“灯火”意象与“太阳”意象相比,前者显然有负面效应。
《沉沦》中的灯火,一方面可以作为景物描写的表现手法,是对象和内容的记叙;另一方面,是将主人公的心境承载于所看见的灯火之上,让读者能解读到文人公无聊、孤寂、渴望死亡等心理层面。灯火可以视为主人公灵魂的写实,是主人公情感的映照。
意象的“人格化”在郁达夫小说中的出现已经被前人所关注,“对于自小浸染于明山秀水中的郁达夫来说,把自然人格化来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情感需要恐怕是绝佳的途径了。”[5]109景物的“人格化”对于郁达夫而言,是自然的景色与心境的变化浑然一致,灯火意象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我”会数次因为凝视灯火而生出新的情绪,显然灯火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承载情绪的客体,还可以和主体交揉再生为一个新的主体。在拉康的“想象的凝视”之中,他诠释了“凝视”这一动作是如何诞生新主体的:“应这样来理解新主体的出现,即不是在已然有一个主体即驱力主体的意义而是在新的东西就是有一个主体出现的意义上。这个主体——它其实是他者——得现,是因为驱力能够显示它的循环路线。只有随着主体在他者的层面出现,才有驱力的实现。”[6]172用这种逻辑来解释灯火与“我”之间的关系,则不难看出为什么“我”在第一次远眺灯火骤然生出了“万千哀感”后又“自家笑起自家来”[1]28,第三次又是“只觉得好笑”[1]48。两次情绪最终都化为自嘲,虽然行文上顺理成章,但是必须要有能够引起变化的媒介,即为灯火,脱离了这一媒介,连“我”也“忽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1]48了。
第一次凝视灯火,其实为数灯火。“一个人”的车厢,静静地凝视着窗外,思绪在“我”与灯火之间轮换。此时此刻,点点灯火是“我”能看到的唯一景物,也是能让“我”产生共鸣的物体,是“我”认可的另一个“主体”。“我”无人相伴感到孤独,想到了“黄鹂”“十字架”等典故中被拟人化的东西。在这里,“我”也一样完成了灯火的人格化,灯火无法象征着东京的朋友和亲人,因为这里本就没有“我”的朋友和亲人,一切都是陌生的。“远随车”仿佛挽留远去的“我”,“万千哀感”[1]28油然而生,“我”会因只有灯火的相送而感到离别的伤悲。显然这种情绪是短暂的,一旦发现被灯火怜悯完全是“我”的自作多情,“我”和灯火之间的和谐很快就会断裂开来,“我”与“它”并无关系,其实“我”是因为无人相伴而感到迷惘,之前因凝视灯火黯然伤神只不过是一种好笑的行为。第三次凝视灯台,“我”也一样将灯台的影子和夕阳视为一种“惜别”,同样情绪很快被平抚,为自己的想法感到了“好笑”。终于觉察到“我”的情感不能完全寄托于灯火,将自己的情绪加载于某种物体之上都是徒劳。可以说这是作者自己进行的解构。所以说,一方面灯火成为情绪的外化,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断自嘲加以否认,使得小说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
三、灯火之中的城市隐喻与逃离
在《沉沦》中提到了在学校没有开课时,“我”独自一人居住在N市的乡下,有前所未有强烈的“都市的怀乡病”,这是“我”在异国他乡的郊外,对都市、对人潮的怀念和渴望。灯火是“都市”的典型特征之一,将文化生命意识灌注于自然景物中,可以把作者对灯火的憧憬看作他内心向往都市生活的一种隐喻。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郁达夫在《沉沦》的前半部分虽然也描写“我”在东京的都市生活,但却很少有对“都市”的直接描述。同期的新感觉派作家在描绘繁华的街道和灯红酒绿的景致时,是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来展现灯火的:“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7]247“霓虹灯色调变化之中报童绿了红了蓝了的脸”。与之对相对照郁达夫对都市的描述更多的是暗喻,除了灯火“黑影子”之外着墨不多,很少有多姿多彩喧嚣繁华的热闹场景。其实这种暗喻,更能反映出他怀着一种对都市既逃离又忍不住向往的心情——“我”是一个对都市既有厌倦又有渴望的人。
“我”刚搬来城市时很想与人交往,但在学校里又会“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1]21,自己想要逃避却无法逃避。“你的眼泪究竟是为谁洒的呀!或者是对于你过去的生活的伤感,或者是对你二年间的生活的余情,然而你平时不是说不爱东京的么?”[1]28由此可见,“我”对城市是渴望和恐惧并存,自己陷入到离开城市流泪和“不爱东京”的矛盾之中。
“我”在离开东京之后,对城市的依恋之情更加浓厚。作者多次运用数量词来形容灯火,在离开都市时想到了“六街灯火”[1]29,而在乡下则是“一点灯火”[1]31。二者之间既存在着数量上的对比,也存在光亮程度的差别,在这种比较中,灯火成为“我”离开都市后思念都市的一个理由。“我”生活的地方只有一点灯火,有些鬼气,引起“我”的恐惧。“我”开始思念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都市,这种怀念被名之为“对于都市的怀乡病(Nostalgia)”[1]31。但是这种怀乡病只有在那天晚上最盛,是那个推窗后只见“一星灯火”[1]31的夜晚。对比这里的冷清,城市在“我”心目中有了光鲜感。坐车时是“灯火随车”,看着窗外的灯火,知道城市不再属于“我”,城市已经离“我”越来越遥远,那晚的“怀乡病”会随时随地引发自己对已逃离的城市的留恋。
“不爱东京”[1]28在“我”身上集中表现为对都市的逃离,可以断定“我”不是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闲荡者”,而是都市的“逃离者”。同样是对离开都市的心理描写,新感觉派施蛰存的《魔道》和《沉沦》却截然不同,如李欧梵所说:“对施蛰存的那些城市人来说,乡村成了一个魔鬼般的‘他者’,随时准备折磨或瓦解他们业已纷乱不安的神经。”[8]195《魔道》的结尾,主人公还是返回了城市,一直困扰他的黑衣老妇的影子也走入了小巷中。在《沉沦》中,“我”虽然也患了“都市的怀乡病”,但是却没有停止对都市的逃避。“我”是因为贫穷困厄,在都市没有立锥之地,人际关系又失败而被挤出了都市。“我”移居乡村,一直到死,“我”也只能在荒芜的海边酒家寻找一点个人的慰藉,最终并没有重新返回到东京。
《沉沦》之中的灯火意象,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是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一方面“我”因乡下寥寥灯火而勾起对都市生活的回忆;另一方面“我”并不热衷于都市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且自己的思想与当时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相脱离,所以想起都市时,并没有新感觉派笔下身临其境的“光潮”。施蛰存回忆城市的景象,写到了“咖啡馆门前的咖啡女……”,而郁达夫只通过灯火来寄托自己对都市的思念,对城市里的其他优越之处,则一概不提,这正符合他有一点忧伤却又十分倔强的性格。郁达夫和施蛰存的城市观念显然不同,施蛰存即使居住在至交的西式住宅中,却还是羡慕城市的物质生活和区位的优势;郁达夫心目中的城市和田园的唯一区别是人际交往密集和稀疏,没有丰富的物质内涵。当他远离都市感到失落时,只需要远眺密集的灯火,他的灵魂就能得到满足。郁达夫通过灯火意象隐约地展现出了城市的轮廓,显然它还不足以代表一个完整的城市,它只是城市的一个侧影,是一个既留恋城市又不愿回归的、城市逃离者的记忆。
四、灯火对于全文古典意味的解构
灯火是比较现代的意象,是审美现代化的产物。被包裹在自然意象中的灯火,却因为有意境寄托的特点,不仅是现代与古典的和谐统一,藉此也可对陈规陋习进行颠覆,对所构筑的古典意味进行解构。
《沉沦》中的自然意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它们和“我”所读到的自然景物密切关联,“我”漫步在稻田的官道上,欣赏着道路两旁草木,朗诵起爱美生的《自然论》、沙罗的《逍遥游》和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我”喜爱诗,因为诗词里有着形态各异的自然美景,“我”眼中的英国诗、中国诗,中外典故都是相通相容的,这些自然意象就是“我”想象中的田园世界,这是一个风光旖旎、充满诗情画意,既典雅又能消解忧愁的古典意味的精神乐园,人们消遣时聚在一起吟诗作画,大声朗诵诗歌,闲暇之余写些旧体诗。李欧梵认为,在郁达夫自我的幻象中,存在着道森和黄仲则两位中外诗人的影子,二者之所以能中西合璧,是因为郁达夫和他们有相同的悲剧命运,都是“一个脆弱和孤独的天才,时常生病和忧郁,只能在与他疏远的社会里,耗尽自己的生命及才华。”[9]116
如果小说中的自然田园是净化灵魂的地方,那么灯火意象则映射着“我”疏远社会,在百无聊赖中消磨着生命力,这样,作者极力营造的古典意味被化为了虚无。在众多自然景物中,灯火意象的出现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三次灯火都是以夜幕为背景,黑夜的掩盖使得白日熟悉的草木田园都不复存在,如第二次描写的如鬼火般的“一星灯火”,窗外的“平原”上有“沉沉的黑影”,此时除了灯火就是黑暗,这样的情景之下即使古典意象再现,也不会让人感到惬意。文本中出现了古典的梧桐意象,借着灯火遥望梧桐,“梧桐的叶战声,近在他的耳边”。叶子被风吹动的声音如同打战,灯火的鬼气使得周围的景物都笼罩在诡异阴森的氛围中,使人心惊肉跳,给“我”带来了恐惧。此时完全没有了温庭筠笔下的“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的恬静与美感,其象征高洁美好的“梧桐”也一并沉寂,小说的意味也由恬静忧郁的古典美变为灵怪故事里的荒诞诡异。
每当灯火出现后,“我”的情绪便会无法捉摸,其中的负面影响不能简单地被一首诗消除,古典意味的裂缝随势出现了。如果这是由于古典诗词本身表达得过于哀伤,“我”会效仿古代诗人在空旷的田野上吟诗作赋,将自己的无聊释放到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去。
在小说中,因为灯火的不断出现,“我”越发多愁善感起来,如在列车上,看见灯火之后生出万千哀感来。“我”在稍微平静之后写出了一首旧体诗,诗歌中也提到了灯火,并且灯火与旗亭对仗,它被完美地融合在诗歌的古典意境之中。然而,忧伤的情绪并未完全排解,只因疲惫袭来,便进入了梦境中梦幻的世界,残存的寂寥也不断壮大起来。
“诗歌”与“灯火”,到了全篇结束的时候又双双浮出了水面。面对窗外的灯台,“我”又一次做诗,但这首诗歌比前面一首更为悲伤,意象的灯火也随即“熄灭”,前文的“六街灯火”现在只剩下“茫茫烟水”,灯火不再和诗歌中的自然美景融合在一起,在“我”离开酒家之后,情绪引导“我”走向崩溃和死亡,萦绕在全文的古典意味也随着这一死亡走向终结。
五、结束语
灯火意象作为《沉沦》众多意象群中的一个独特个体,正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强烈的矛盾性,因而既在文本中构建其精神世界又成为其精神世界被解构的一个重要要素。通过对灯火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了《沉沦》这个文本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强烈矛盾性,并由之可以对作者本人的精神人格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灯火是作者塑造的自我幻想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也是逃离都市文化与古典意味解构的一个曲折影射。
[1]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美)韦勒克.意象· 隐喻·象征·原型[C]//汪耀进.意象批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3]杨 泉.心像与自然——论郁达夫小说中自然的艺术功能[J].理论导刊,2007,(7):103-112.
[4]方仁英.物化感伤——郁达夫意象特征初探[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5):81-86.
[5]李跃力.论郁达夫小说中的自然意象[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08-112.
[6](法)拉康.论凝视作为小对形(对象a)[C]//吴 琼.视觉文化的奇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C]//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美)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M].王宏志,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9](美)李欧梵.上海摩登[M].毛 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