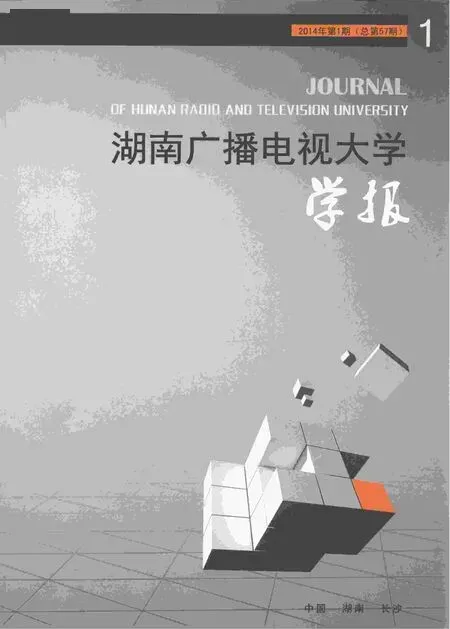近十年宫体诗界定研究评述
李冰心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对诗体的界定,从古至今都是诗评家们乐于探寻的一个方面。因为通过对各种诗体的分类和界定,我们能从中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创作的规律及其时代特征。在各诗体中,宫体诗的界定算是争议较大的一种,它自产生之后不久就获得了各种界定,有些是客观的叙述,有些是高度的赞扬,还有些是严厉的批评。正是因为如此复杂,有必要对各观点进行梳理,特别是对近十年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简单评述,以期管中窥豹,能对宫体诗的界定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一、宫体诗界定的流变
关于宫体诗的界定,大致是一个从狭义说到广义说再到近几年综合说的一个过程。狭义说以闻一多为代表,由于闻一多在“五四”时期的地位高,影响大,他的观点也成为了学术界较典型的观点。他在《宫体诗的自赎》中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①,刘永济、刘大杰等人都基本认同。如刘永济就说:“迨宫体既兴,情思逾荡。绮罗香泽之好,形于篇章;帏闼床笫之私,流为吟咏。”②这一说法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文学史,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直称为“色情文学”,袁行霈也说“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③这种界定对宫体诗略显草率,而且带很强的道德评判意识在里面,轻视了它的文学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沿袭了隋唐以来对宫体诗的评价——“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④同时也和当时的思想观念不可分割,“五四”以来虽然西方思想已大量进入中国,但仍保留着传统文学观念,加上建国后“文革”的影响,敢于发表其他意见的人就更少了。胡念贻正是在1964年发表《论宫体诗的问题》为宫体诗做辩护而遭到批判。
广义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起,以周振甫为代表。他在《什么是宫体诗》中认为宫体诗既有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也有其他题材的新变体诗⑤。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了,对宫体诗的研究也采取了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但若按周振甫的说法则无疑过于宽泛,很难区别宫体诗与其他诗体的特征。与其相比,曹道衡、沈玉成的界定则稍显准确:“宫体诗的特点是: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绮丽,下者则流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⑥
正是在曹、沈的基础上,近几年曹旭和归青将他们的三个标准进行结合,提出了综合说。综合说其实是对曹、沈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创新性,影响也较大,近年硕士论文就有采用其观点的,如河北大学金艳的《南朝乐府与宫体诗关系研究》。下面具体论述综合说的内容与得失。
二、综合说
归青在他于2003年所作的博士论文《南朝宫体诗》研究中,用一章的内容对宫体诗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确定。他从题材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和现存作品,得出了他的论断:“从题材上看,宫体诗只能是一种艳情诗。”⑦此结论的依据是“新变”不能作为宫体诗的特征,因为《梁书·庾肩吾传》记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可见“新变”的内容是指“四声”的使用,而宫体诗并不是唯一具有这一特征的诗体,只是继承发展了永明诗。既然形式走不通,自然就只好从内容上分析,于是归青认为艳情才是宫体诗区别于其他诗体的唯一特点,因为“齐梁之际,特别是从徐扌离、萧纲开始,艳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增加,乃至到大同年间终于盛极一时成为诗坛之主导。”⑧
然而翻阅《玉台新咏》和《梁简文帝集》等收录宫体诗的著作,里面许多诗都与艳情无关,所以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如2005年李慧芳在《宫体诗“艳情诗”商兑》中辨析了“艳”与“艳情”的区别,认为宫体诗更偏重的是写“艳”,“艳”的解释则应该是对女子的赞美、欣赏和尊重,而非男女之欢。李慧芳认为这又回到了“艳”在《说文》中是“好而长”的本义,后人不知,误将艳诗读成色情诗歌。这里她举了宫体诗的代表作《咏内人昼眠》,认为就是表达夫妻之常情而已。又如东北师范大学孙勇前就于2006年所作的硕士论文《轻艳的秘密》中指出:“萧纲的不少诗作所表现的诗歌风貌、生活情感与一般文人诗并无二致,与女性、闺情根本无关的亦不鲜见。”2009年上海古籍研究所的徐艳也认为所谓的“艳诗”,其实追求的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多维度拓展,代表着属于诗歌凝练空间的文学语言的成熟。”⑨
于是对“艳”本身的界定又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对“艳”的界定也是狭义说与广义说的一种反映,归青依据对史料的解读(见下文),赞同狭义说,认为“艳诗”是对女性的描写,是淫乱的诗歌,这与传统文学史的观点是一致的。孙勇前、李慧芳等人为广义说,认为“艳诗”是表达真情实感,是健康的,这是他们对作品的解读后得出的观点。
笔者认为:“艳”的理解如果从现存的诗歌中去分析,《咏舞》、《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和《率而成咏》等诗确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不同,但最多是用华丽的辞藻描写女性和女性使用的器物,缺乏深情,失之轻薄,依袁行霈文学史的观点认为是“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⑩则未免太过。
尽管归青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将当时诗歌题材一一分析,排除了田园山水、咏物公宴等,最后得出只有艳诗才能将宫体诗的含义明确下来,但是归青从史料出发对于艳诗本身的界定也值得商榷。
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资治通鉴·梁纪十八》)
(萧纲)文章妖艳,堕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全陈文》卷五)
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大唐新语》卷三)
以上为归青举的史料上的依据。然而第一条《桑中》真是淫奔之诗吗?《诗经》时代此类诗歌难道更多的不是可理解为描写男女幽会表达爱意吗?第二条史料说萧纲的文章“诵于妇人之口”,诵于妇人之口并不见得就是描写妇人之作,而且如果都是艳情诗甚至色情诗,也未必会诵于妇人之口,可能更多的是像徐扌离的“春坊尽学之”一样,其作品受到宫女喜爱而乐于唱诵。至于第三条史料,作者也提出了是否将所有艳诗划入宫体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归青借《梁书·徐扌离传》:“扌离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认为只有将艳诗加上“新变”方可准确定义宫体诗。关于这一条史料,2009年复旦大学古籍所的徐艳研究员撰文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她认为“属文”的“文”指文章而非诗,笔者在文体说一节中将具体评述。
因为有了“新变”的限定,所以外延的界定其实就是从此入手,有“新变”则为宫体,无“新变”则为普通艳诗。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曹旭,他于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宫体诗的定义与裴子野的审美》一文,也抓住“新变”不放,认为是“新变”将狭义“衽席之间”的界定和广义的界定结合了起来。当然,在曹旭这里,“新变”的内涵更广,除声律对偶的运用外,审美观也有所转变,是“典”和“丽”的交汇,是儒家传统与时代审美转变的折中,而集中的体现就是《玉台新咏》。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是“新变”,“新变”则要有“旧体”,然各种史料中并未给出“旧体”是什么。徐扌离“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旧体是指《诗经》、乐府,还是民歌?新变是指审美上从“温柔敦厚”的诗教转为“伤于轻艳”,还是形式上从古体诗转为讲究声律和对偶的新体诗?归青强调后者,曹旭兼而有之。笔者以为二者都很难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旧体到新体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三、文体说
由于狭义说、广义说和综合说都各有缺陷,于是有学者试图避开这两种说法,避开题材和形式的纠葛,从宫体诗的源头上寻找答案。徐艳2009年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文章对宫体诗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论证“:徐扌离所创‘宫体’实为‘宫体文’……都在于文体的创新,而无关乎特点题材(包括女性题材)。”⑪这是近十年宫体诗界定研究上的一次创新的尝试。为了证明宫体的首先出现在文而非诗中,徐艳列举了两条《梁书·徐扌离传》的文献资料:
一是“扌离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此条史料曹旭也看到了,但他认为宫体文是宫体诗的雏形,二者并没有严格界限)。
二是“大通初,王(萧纲)总戎北伐,以扌离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扌离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扌离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徐艳认为首先“属文”的解释应指文而不是诗;其次从“教令军书”和“管记”可看出徐扌离从事的工作和写诗无关;最后《玉台新咏》未收录徐扌离的诗也说明他不善写诗。笔者按:首先,广义来说“属文”应包括诗和文,《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中“文咏”就是指宋初的诗歌,而下文的“春坊尽学之”则从逻辑上推断,春坊宫女学诗的可能性更大。其次,为说明未收录的原因是不善写,徐艳一一反驳了刘跃进、章培恒和日本学者兴膳宏对此现象的解释,最终将不收和不善写形成因果联系,简单的解释为不收现象的原因是不善写。笔者以为此因果结论也值得存疑,一是徐扌离现存诗歌只有五首,不能仅凭他现存诗质量较差认定他不善写诗;二是《梁书·徐扌离传》记载:“梁武帝萧衍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容貌’。”可见高祖需要的是“文学俱长”和“仲宣之才”,“文”前文已说当包括诗,而且诗的娱乐作用大于文,结合“晋安游处”更能断定高祖看重徐扌离要会作诗的。后面“仲宣”指王粲,王粲的诗才更不言而喻,所以周舍才敢推荐徐扌离。因此徐扌离善不善写诗还有待商兑。但总的来说,从这两史料中可见徐扌离在“宫体”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文体特点是“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最终影响了萧纲等人的创作。
尽管文体说存在这些疑问,但仍有人支持宫体文的观点。江苏大学的赵咏源,他认为从史料和现存诗歌看:“徐陵是以文章著称的,闻名一时的‘徐庾体’,也就是就文(狭义)而言的,它包括书序碑志骈赋等体式。”⑫虽然他的论文是为了论证徐陵不是一个典型的宫体诗人,但其实从侧面支持了徐艳的观点。
然而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徐州师范大学的戴志军认为“徐庾体是个错误的称谓,不能划入宫体的范畴”⑬,他依据《北史·庾信传》: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扌离为右卫率,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认为“绮艳”文风的人很多,独二人并称不是因“绮艳”而是政治产物,是因为“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的政治原因。如果由戴志军的看法推断下去,那么即便“文并绮艳”的“文”指文章,徐陵和庾氏父子追随学习徐扌离文体形成徐庾体这一现象,“徐庾体的这种特点,应该同时也是宫体文的特点”⑭这一结论,便都不能成立。
四、非政治说
以上都是依据史书和现存诗歌作为界定的依据,对代表诗人的文集书信较少注意,北大中文系教授傅刚则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在查阅宫体诗代表诗人萧纲的《与湘东王书》、《临安公主集序》、《答新渝侯和诗书》和《闲愁赋》等文章后发现,他追求的是“吟咏性情”、“摇荡情性”、“性情卓绝”、“寓目写心”、“情无所治,志无所求”和“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这些史料是近年其他研究者所忽略的,傅刚将《玉台新咏》选诗特点和萧纲的这些言论相结合,认为“就是追求题材的非政治性,情感的通俗性。即使那些感怀节候、咏写风物的诗歌,也都偏重在‘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的闲愁上。以上这些才是宫体诗的主要特征。”⑮
六朝的宫廷斗争残酷而激烈,或许正是因为厌倦了政治和战争,文人们才会沉浸在宫体诗的闲情雅致中,求得一时的逃避,所以傅刚教授才得出了他对宫体诗界定的看法。不过,从本质上来说,这还是一种广义说的界定,题材的非政治性,《诗经》中早就有了,“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的闲愁,永明体诗中也已出现,如沈约的《夜夜曲》便是如此:“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孤灯暖不明,寒机晓犹织。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傅刚看到了宫体诗人的追求,却没看到他们的追求其实和前人是共通的。
五、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广义的界定难以切入宫体诗的核心,狭义的界定又容易忽略掉其他题材,综合说和文体说成立的前提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近十年出版的专著如石观海的《宫体诗派研究》和胡大雷的《宫体诗》研究,也大多借用前人的观点。他们从题材、形式和文体进行界定,如此便都只是关注了宫体诗的一个方面,又或多或少要受到历史上对宫体诗各种评价的影响,重新界定宫体诗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们需要的是正确评判古人的界定,站在当时的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如今视为艳情的诗歌在当时并非如此,如今是人之常情的诗歌,在当时人眼中是为艳情,审美的标准是在变化的。
笔者认为,如果把宫体诗的命名和宫体诗作为一种诗体分开来看,也许对宫体诗的界定能看得更为清晰。关于宫体诗的得名较早的记载一是《梁书·简文帝纪》:“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二是《梁书·徐扌离传》说:“扌离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可见起于东宫,因地得名,正是宫体诗得名的原因,其得名之初也许和前文提到的‘徐庾体’一样,和文学并无太大关系,只是因为政治地点敏感,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相投,身份特殊而得名。为什么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应制诗、悲愤诗和送别诗等都容易界定,独宫体诗存在如此多的争议?可能宫体诗自成一格的原因不是它本身有多少特殊性(毕竟它也是一种对前人的继承),而是界定的过程使得它自成一格,使得它具有了争议。所以我们才要将宫体诗得名与诗体分开辨析。道德、审美和朝代都在转变,隋唐以来“衽席之间”、“亡国之音”的界定,甚至闻一多的狭义说,周振甫的广义界定,他们很多时候是出于思想文化的需要。即如八十年代对宫体诗的重新评价,学者们也正是借宫体诗界定之尸还思想开放之魂。若胡念贻的论文发表在八十年代,他的悲剧便不会上演了。
注释:
①闻一多.唐诗杂论[M].开明书店,1948:11.
②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M].中华书局,2007:185.
③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4.
④魏征.隋书(卷三十五)[M].中华书局,1972.
⑤周振甫.什么是宫体诗[J].文史知识,1984.(7).
⑥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41.
⑦归青.南朝文学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
⑧归青.南朝文学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
⑨徐艳.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J].复旦大学报,2009,(1):23.
⑩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5.
⑪徐艳.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J].复旦大学报,2009,(1):12.
⑫赵永源.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J].扬州大学学报.2004,(4):49.
⑬戴智军,李燕.徐庾体与宫体关系探讨[J].沈阳大学学报,2010,(2):75.
⑭徐艳.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J].复旦大学报,2009,(1):17.
⑮傅刚.宫体诗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1):16.
[1]徐陵.玉台新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归青.南朝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