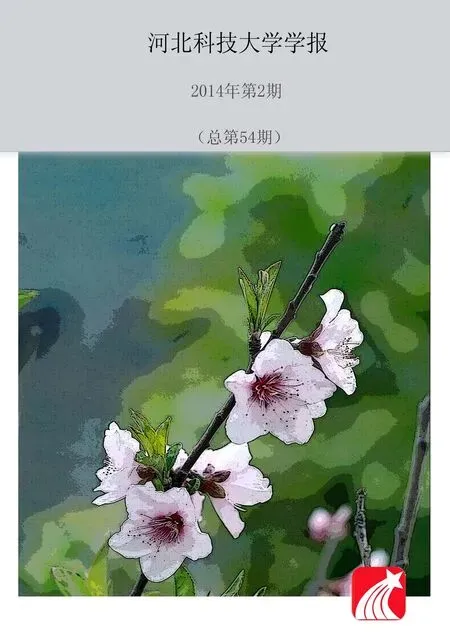叛逆与超越: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先锋性
张 赟
(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先锋”一词源自法语,原指军队中的先头部队,后成为文学艺术术语。“先锋”艺术家通常表现为: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方,注重创新,大胆突破僵化的常规和传统;积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并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极端的前卫姿态常被同时代的人看作异类。
新时期伊始,“先锋”这一术语开始应用于我国文学批评界。“文革”中以食指、北岛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诗歌、小说领域的探索被看作是当代先锋精神的源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文学中的先锋精神形成强大声势,出现“先锋文学”、“先锋派”和“先锋小说家”。然而至此问题也出现了,由于指称的固定化,“先锋”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显然,先锋精神并不仅仅存在于所谓的“先锋文学”中,许多“先锋文学”以外的文本同样闪现出叛逆的光芒,尤其是常被忽视的女性作家作品。
在对女性小说先锋性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批评界存在将女性文学研究等同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倾向。因女性主义理论属于政治批评范畴,与形式主义各行其道,本文借用形式分析方法,将解决女性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叙述学方面薄弱的问题。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由于多种时代因素的限定,存在对女性小说的先锋性内涵的“遮蔽”,而在思想解放条件下,更有及时出现的具有前瞻性、导向性的批评,即批评的“敞开”。批评的“遮蔽”与“敞开”是研究新时期女性小说先锋性不可忽视的现象。女性小说中既有对传统的叛逆与超越,也有对传统的理解与熔铸,考察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先锋性,更不能忽视其与传统的关系。
一、新时期女性小说先锋性的历史嬗变
(一)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恢复与重建中先锋性的初现
“文革”结束初期,文学表述着抚平伤痕、反思历史的时代共鸣。在“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占主导的七八年里,女性作家也肩负着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但与当时常见的宏大叙事相比,女性文本中泄露的却总是一种私密性的、情感性的,甚至自传性的,关乎两性关系而无关“集体”的情感,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读者读完她们的作品,也会谴责极“左”政策对人的摧残,但更能体会到对女主人公伤害最深的是婚恋情感上的伤痛,这种伤痛或源于“菲勒斯”中心的传统,或因为某个具体男性的自私或猥琐。然而与当时盛行的战争、历史或农村题材相比,这些作品难免显得格调“暗淡”,题材“狭小”,以致遭到主流文学规范的巨大压力,但这里却蕴涵着女作家对小说中千篇一律的个性化特征消融的不满,这是叛逆的先声,是另辟蹊径的探索与尝试。
(二)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酝酿与突变中先锋性的凸显
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女性创作的自由度提高,相应的,女性小说中的先锋性表达也以更强烈的冲击力瓦解着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一些女作家汲取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和哲学精神,以荒诞、夸张、变形、象征等表现手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关系、生存方式以及个体命运进行思索与追问,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方方的《风景》、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和《岗上的世纪》则从两性性爱入手探究原欲的力量,彻底撕开延续千年的人性伪装,显露出叛逆和先锋的特质。她们的作品动摇了束缚文坛多年的审美惯性,丰富了当代小说多元化创作的格局。
(三)20世纪90年代:喧哗与躁动中先锋性的张扬
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正是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所说的“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女性小说创作超乎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锐利耸起于中国文坛。”[1]以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徐坤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开始以群体的姿态显示出先锋者的热力与激情。对于她们来说,写作是性别反抗与表现自我的载体。在文本中,背对历史、社会以及人群,去直接描绘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和躯体感受等生命体验,从而构成对传统规范的彻底颠覆,如《私人生活》、《双鱼星座》、《一个人的战争》和《我的情人们》等。体现在题材内容上,对同性之爱或“姐妹之邦”的描写、对传统的牺牲型女性形象的颠覆以及自我身心欲望的袒露等等,犹如打开了一扇扇尘封已久的人性之门。
(四)新世纪十年:迷失与超越中先锋性的消解
21世纪女性小说整体格局呈现新的变化,“男权的藩篱”已削弱了以往的威力,女性小说的先锋性随之呈现出转型。曾经激进的女作家最终“从我挣脱,走向他人”(埃莱娜·西苏语)。以《枕黄记》为开端,林白尝试与镜像中的孤独自我分离,走向广阔大地;以《知在》为标志,张洁消解了对男权社会的怨恨激愤,王安忆、铁凝、徐小斌等人也相继以写实主义手法走进历史,将女性的成长和时代社会的变迁结合;陈染在搁置小说创作之后,终在散文写作中显示出与自己与现实和解的平和。先锋的女作家从对自我的专注转向对自然万物的体察,由此获得充盈的生命和飞翔的心灵。而这正预示了女性小说从狭隘走向开阔、从肆无忌惮的破坏走向轻灵隽逸的细致的发展路径。她们以自身诠释了先锋之本质——这就是尤奈斯库所说的:先锋就是自由。
二、女性小说先锋话语与文体建构
(一)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
作为个体的人,我们都被语言所诱导和塑造。表面看来我们在随心所欲地表达意图情感,而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深层文化结构所控制。今天女性使用的每一个文字都形成于男性中心的文化语境中,这些文字所蕴含的历史、习俗、传统都积存着男性中心的思维定式,甚至在无意识、潜意识领域也无法逃脱。
新时期女作家开始对此发起挑战,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拯救自我的唯一途径。“如果妇女一直是在男人的话语‘之内’活动,是一个总要回头求助其对立面的象征者的象征者,其对立象征者则消灭其特有的精神并且减弱或者窒息其不同凡响的声音,那她就该打乱这种‘内在’秩序,该炸毁它、扭转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她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造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2]因为现存的一切关于女性的想象、期望或规定都是男权价值观念下产生的,都与实际有一定偏差,因此先锋女作家们必须对几乎一切关于她们的东西进行挖掘和改写,以破坏或澄清。
身体、婚姻、爱情、历史等主题是构建女性话语空间的突破口,它们意蕴丰富,融汇着女性的成长、欲求、困惑、叛逆、抗争与希望。女性身体是被男性话语霸权遮蔽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也是男性经验无法到达的领域。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某一微小又巨大的躁动,都是对一个曾经畏怯的但即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支撑下,陈染、海男、徐坤等女作家以女性为欲望主体进行以“身体”为核心的女性欲望化叙事,形成了强大而凌厉的对于传统性别秩序、性文化观念,尤其是性禁忌的解构之势,她们“在男性划定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把原来不可说、不该说的东西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和认识体系”。[3]在婚姻、爱情、历史等主题的背后,酝酿着对现存的伦理道德的颠覆和重构,也体现出女作家建构女性话语空间的努力,如《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在同一地平线上》等。至于历史,人类的“历史”恐怕应置换为男性的历史,而女性自己的历史已经被遗忘在岁月中。先锋女作家以“历史”为切入点,拆解已有历史的庄严与伟大,让其显现出内在的破损和虚伪,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她们要找回一部女性自己的历史、一部母系的历史,如徐坤的《女娲》。
女性话语空间建立的过程其实是对男性话语霸权解构的过程,但并不等同于男性话语霸权瓦解的过程。形成几千年的传统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惰性,女性话语空间的不断完善和维护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二)女性文体模式的诗学建构
文体的演变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单纯演化,它潜存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美学观念的变化或新的审美机制的生成。新时期以后,先锋女作家挑战既有美学秩序,打破小说创作中陈腐的形式规范的限制,从语言文字到结构框架,再到叙事视点及文体风格,都表现出独创性、超前性和叛逆性。
在语言上,女作家打破传统女性诗文建立的潜规则,不再以温柔婉转的文字表达贤淑良善的妇德,竭力将陌生化、诗化、碎片化的语言推向极致,如陈染的《潜性轶事》、《与往事干杯》,残雪的《黄泥街》、《我在那个世界的事情》等。所谓“内在生命”的东西,就像森林中的灼火变化不定,而传统语言常常捉襟见肘。铁凝、方方、张洁等作家的笔下则出现了审丑的文字,那些丑陋的、变态的人格,肮脏的、令人作呕的事物,那些暴躁的、变态的、绝望的情绪,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小说结构的非逻辑化。非逻辑化是指女作家改变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述顺序和逻辑要求,以自我情绪和意识的流动为线索,在回忆或梦境的框架下书写呓语式的身心体验。在表层非逻辑的掩盖下,往往潜存着一种对话式结构。在陈染的《凡墙都是门》、《沙漏街卜语》等小说中,十分巧妙地隐含着两套语言,将女性独白放在开放性的现实与历史交织的复杂情境中;也运行着两种时间,即男性的历史时间与女性的心理时间。“凡墙都是门”的生命哲学使两套话语之间实现对话汇通。所谓的非逻辑符合先锋女作家对抗传统叙事规则的初衷。
叙述视角的内置。以个人内在视点放射性联系外在世界,往往使女性小说具有“自叙传”特征。通过回忆、梦境等框架结构,也通过前卫、叛逆的叙事姿态对现实进行重组,从而构成生命体验无比真切也无比诡异的“世纪末想象”。当然小说叙述视角的内置并不简单等同于“自叙传”。叙述人、主人公和作者三种角色之间往往发生改变,例如,当第一人物和叙述人讲述故事时,“我”是个人经验的讲述者,而当“我”转换成作者时,第一人物同叙述者的个人经验就成为作者审视的对象。对同一对象的反复审视具有怀疑论色彩,意味着女作家对世界对自我的重审意识。
当然,对于女作家来说,文体模式的意义固然是重要的,但不是自足的。建构文体模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条进入女性独特精神空间的通道,惟有通过它的独特性,女性精神空间才能被开拓出来。
三、批评的“遮蔽”与“敞开”
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20世纪80年代,女性小说研究中出现了批评的“遮蔽”与“敞开”的碰撞;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一枝独秀,又使女性小说先锋性研究走向过度阐释的另一个极端。这种批评与创作的不平衡关系说明,女性小说创作已走到了理论批评的前面。
(一)批评的“遮蔽”与有限的“敞开”
张洁于1979年发表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光明日报》、《文艺报》、《北京文艺》等几家报刊相继开辟专栏讨论。以李希凡和肖林为代表的批评者从小说的格调和人物的道德情操方面进行否定。肖林断言,“这篇小说的格调不高,”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渺小可鄙的,自私虚伪的。”[4]李希凡说:“‘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5]讨论中,李希凡和肖林式的批评并不是少数,因为仍然没有走出“文革”思维,仍然在传统道德感、贞洁观念,以及自我崇高化的想象中陶醉。但正是这些遮蔽了小说真正内涵的批评几乎对作家造成毁灭性打击,以致作家做出艰难的辩解:“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6],可贵的是还有王蒙的保护性意见:“小说写的是人,人的心灵。难道人的精神不应该比常见的和人人都有的更坚强、更热烈、更崇高、更理想吗?”[7]
1982年,《光明日报》、《读书》、《文艺报》等报刊就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展开论争。否定者认为“男主人公的个人苦斗与我们所提倡的个人努力、事业心、拼搏、奋斗精神并不是一回事。”“赞美他们,不就是赞美极端个人主义,不就是赞美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吗?”[8]肯定者认为,小说“描绘了一个自私、冷酷、像孟加拉虎一样只有兽性、不通人性的个人奋斗狂——‘他’”。①上述批评都忽略了小说最本质的内涵:即女主人公两性平等意识的觉醒。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对两性平等的呼唤也没有引起注意。今天我们将这篇小说看作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声,感动于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然而当年这篇作品争议的焦点却不是这些。
被批评“遮蔽”的还有王安忆。批评家们习惯将她的《小鲍庄》划入“寻根文学”。而正是这样的“理所当然”,遮蔽了《小鲍庄》中带有弗洛伊德色彩的“性”与“情”的表达。对“二婶”与“拾来”(老妻少夫)、“小翠子”与“文化子”(叔嫂之恋)两段“不伦”之恋的描写,显然不是“寻根”能涵盖和阐释的。文本中对从小与“大姑”一个被窝儿睡觉的“拾来”性意识的萌动有着精彩细致的刻画,是对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的演绎。遗憾的是这篇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恰当的解读。当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和《岗上的世纪》发表后,批评界一片嘘声,人们普遍不能接受王安忆赤裸的性爱描写,谴责其描写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少男少女之间某种性本能冲动、发泄并从中获取快感的全过程”,“有妇之夫、有夫之妇之间不正当的通奸行为”[9]。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有批评者断言:“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一时间成为了某些作家追求的时尚。《岗上》便是这股浊流涌掠过程中沉淀下来的艺术泥沙。”[10]
(二)批评的“敞开”引发的“遮蔽”
20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文艺批评理论种类繁多,但对于女性文学来说,女性主义批评仍是重镇,但当其由主导发展到泛滥,即引发新的问题。
新的“二元对立”局面的出现。当批评者面对女性作家,总要先明确其性别立场,因此在各种作家访谈中,“您是否是女性主义者?”也成为访问者的必出题。不经意间已形成“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那些游离在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之间的女作家,批评者们该如何着手呢?显然,这一局面必将限制女性小说的意义阐释。
女性主义批评存在过度阐释。女性主义理论从被拒斥到被文学界认可并大行其道,几经曲折。然而它一旦被接受,便成为一些批评者手中的万能法宝和灵丹妙药,几乎无所不用,无往不胜。几乎所有女性小说都被以女性主义理论阐释,更被过度阐释,如针对张洁、王安忆、陈染、林白等人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女性主义理论下的过度阐释使小说中出现的任意意象、细节、语言都被看作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象征;将所有女性生理欲望的描写都看作是性别意识的流露,是对抗男性文化压制的手段。
女性小说前后矛盾的评价。西方女性主义在传入初期,是以一种叛逆、激进的姿态出现的。1982年张洁发表《方舟》,多种权威报刊发表批评文章,其中出现了最早以女性主义为理论依据的研究成果,开始把激愤的张洁视为“女性主义者”。而20世纪末的陈染说:“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11];铁凝说:“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12],“超性别意识”也得到了理论界的回应。刘思谦、盛英、孙绍先、刘慧英等人表达了相似的观点。[13]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使女性主义批评自身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早期被视为女性主义者的张洁,在今天批评者们看来几乎成了“反面典型”。新一代先锋女作家仍然与女性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同性之爱、姐妹情谊、自恋等固然大胆、叛逆,但却少了力量和尖锐感,削弱了先锋者的锋芒。
四、先锋与传统:界域的对立与融合
社会文明正是在先锋与传统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先锋是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具有新鲜的生命力,每一代先锋都以“反叛传统”起家,最终超越并取代旧的传统,成为新的传统;而传统虽是保守的,却并不会乖乖地等待先锋取而代之,而是进行顽强抵抗,在不经意间打得先锋措手不及。
(一)先锋女作家对传统的叛逆与超越
在新时期文学历程中,女作家对传统的叛逆与超越成为女性文学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人们或为之激奋,钦佩其无止境的探索,或认为其离经叛道而避之唯恐不及,女作家们却依然故我,大有震塌传统“大厦”之势。
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旧的传统不可能总是适应当下。先锋者不断在古老的传统中注入现代精神。在新时期文坛,女作家们通过对女性历史场景的想象与缀连,实现对传统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先锋女作家以弘扬女性自觉意识为主旨反驳了传统之于女性的压制,破解了传统习俗、文化价值观念对女性的歪曲。显然,女作家在当代语境下对传统的阐释过程是不断叛逆传统、超越传统的过程。
女性写作行为本身也是对传统的叛逆。弗吉尼亚·伍尔芙曾不无激愤地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极富天资的妹妹,“她与他一样富有冒险精神和想象力”,但她因无休止的家务、不幸的婚约以及无处不在的欺辱和偏见搏斗而遍体鳞伤,直到穷途末路。[14]作为世界妇女共通的体验,它曾经在历史场景中反复出现,也许直到今天也仍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延续着。虽然中国的女性从“五四”后就开始走出深闺,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男女平等,但直到新时期,她们生活的疆域才得以自由打开。文学女性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半边天”,更谈不上文学主流,女作家们的创作依然带有强烈的“夺权”色彩。
在对传统的叛逆与超越中品味孤独。在文本中她们以“渎神”的方式对传统进行全方位解构,但她们又是孤独的。如果我们翻检一下她们的作品,会发现极少有畅销书,这也说明了先锋思想精髓对传统思维定势的叛逆和超越。而先锋之受冷落正是先锋者的使命和宿命。
(二)先锋女作家对传统的理解与熔铸
先锋女作家总是以叛逆和超越传统为目标,但是已将某种传统融入血液的她们又常常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传统的因素。在她们的先锋精神最张扬的时期恰恰是暴露传统的马脚最明显的时期。那些先锋性文本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相通,甚至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返回传统”。以陈染、王安忆、张洁为例,从她们身上先锋者的激情之下寻觅隐藏其中的传统心结,如对爱情的渴望、对男性的依恋、对做母亲及生育权利的坚守等等。
陈染在无数次对男权文化进行反抗、颠覆和谋杀之后,更在渐次清晰有力地表达女性立场之后仍然宣称:“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②在不断地勾勒又不断地拆解一个个“父权场景”之后,陈染却掩藏不住潜藏着的潜意识与欲望——她并未脱离普通女性渴望一个“领导”自己的男性伴侣的情结。而被称为“女性主义者”的王安忆事实上却恰恰给那些冠名者们泼了冷水,《弟兄们》可以说是并不“女权”的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的领悟和参透。小说先是铺排了强大、独立自主的三个女性的形象,然而却在家庭亲情和母爱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功亏一篑,形成巨大的落差和反讽。“她们想着,男人、究竟是什么?她们说,男人是女人最天然的终生伴侣”——又回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古老爱情主题。曾不乏偏激地向男性社会发出愤激言辞的张洁,也脱离不了传统的束缚。“性羞耻”、“贞洁观”、古典爱情神话的炮制等等,都暴露出她并没有走出传统的阴影。而无论是《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祖母绿》似乎都重复了古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古典爱情神话。
从陈染、王安忆、张洁等先锋者的呐喊声中,我们捕捉到了传统的余音。虽然男女平等的目标已经部分实现,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每个人的肌体中。你要叛逆传统吗?你自己就是传统。当然尽管表现出对传统的理解与熔铸,但毕竟这传统中已经渗入新的内容。带有传统因子的先锋终将“走过”传统。
总之,先锋的女作家身上体现着这样的文化悖论:那些最激烈的叛逆者正是将现有传统深刻内在化的人们,她们常比传统继承者更为痛楚地联系着传统的观念和秩序;她们在叛逆传统的同时,也是在与自我厮杀。如果将激进的叛逆者看做是至纯至善的理想主义者,是独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那么,他们的反抗之舞同时也是镣铐之舞。
注 释:
①刘俊民.《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得与失[N].光明日报,1982-03-15,薛炎文的《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也持相同观点。
②陈 染.陈染小说精粹·另一扇开启的门——陈染访谈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50。此外,在小说《私人生活》中,倪坳坳对于自我心态的陈述文字亦与此雷同。
[1]李洁非.“她们”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7,(5):68.
[2][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2.
[3]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J].天津社会科学,1996,(6):69.
[4]肖 林.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N].光明日报,1980-05-14.
[5]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EB/OL].http://house.focus.cn/msgview/20/74558426.html,2014-01-16.
[6]季红真.爱情、婚姻及其他[A].文明与愚昧的冲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3.
[7]王 蒙.当你拿起笔(评论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161.
[8]朱 晶.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N].光明日报,1982-07-15.
[9]钱 红.优美失落之后[N].光明日报,1987-08-21.
[10]董崇理.凡性皆美吗?[N].中国文化报,1990-06-03.
[11]陈 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J].钟山,1994,(6):105.
[12]铁 凝.铁凝文集·玫瑰门·写在卷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2.
[13]降红燕.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J].文艺争鸣,1997,(5):26.
[14][英]玛丽·伊格尔顿.胡 敏,陈彩霞,林树明,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