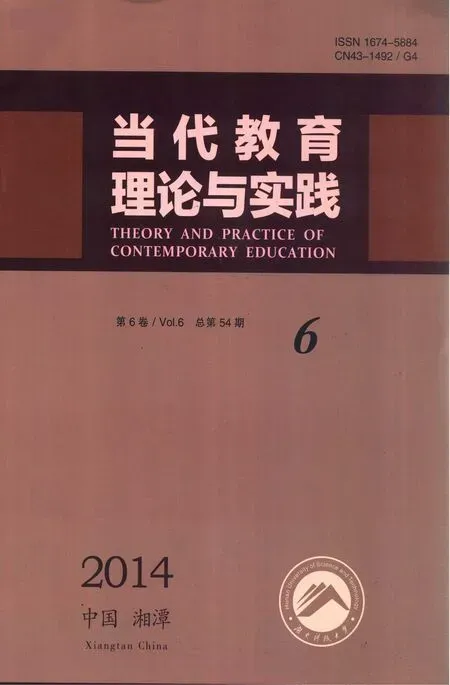现实的面具——《十八岁出门远行》人物分析
黄智诚,李 学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最初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上。这篇“怪异”的小说当时得到了《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和副主编李陀的一致肯定,李陀在看过小说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认为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1]。20 多年之后,这篇小说以“突兀”的姿态出现在了文学教育领域,入选人教版高中新课标教材第三册和语文版高中新课标教材第一册,这是中学课本中第一次收录先锋派小说家的文章。遗憾的是,阅读这篇小说并没有“远行”般轻松愉悦,反而是一次苦涩的阅读大冲击。作为先锋文学,作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更热衷于在“怎么写”上获得叙述快感,注重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陌生化和象征化,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戴着面具的人,他们各有象征,面具之下隐藏着现实的世界。该文意蕴丰富,解读视角多样,下面笔者主要从小说中出现的四类人物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1 童真的“自然人”
童真,可释义为幼稚天真。“我”已经十八岁了,为什么还说是童真呢?细看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文中多处表现了“我”作为少年的天真单纯。“我”对世界充满了热爱,“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我”叛逆轻狂,做事没有分寸,想拿石头砸汽车,甚至想躺到路中央去拦车;“我”天真无邪,学着像成人一样给司机递烟,认为他接受了烟就代表接受了“我”;……这些地方都显示了“我”只是一个在年龄上刚迈入成年而在心理上却还是一个充满童真的少年。
如果单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童真的原因,应可归于“我”的社会化程度低,缺乏处世经验,显得不够成熟。社会化过程是人类学会共同生活和有效互动的过程,也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体由一个“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我”作为“自然人”所持有的价值观还是很童真的,还是一种主观世界的价值观。当“我”奋不顾身为司机阻止抢劫苹果的山民时,司机却看笑话似的袖手旁观;当“我”遍体鳞伤倒地不起时,司机却偷了“我”的背包与抢劫者一起离开……这些荒诞的事情就像一颗炸弹,将“我”原本的价值观摧毁殆尽。“我”在十八岁时怀着热情和梦想第一次出门远行,现实世界却给“我”当头一棒。
童真的“我”代表着一类涉世未深,懵懂迷茫的少年,他们在与现实社会的碰撞中,一直持有的理想的主观世界价值观瞬间土崩瓦解。简单社会显露了复杂,现实世界揭开了虚伪,常规逻辑暴露了荒诞,单纯人性表露了险恶,童真的“我”,也会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与成人社会的格格不入,在社会的磨砺下,终将会“脱去”童真,逐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
2 复杂的看客
文中的司机,是一个复杂的角色,我们除了了解他的司机身份以外,其它一无所知,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怪异荒诞行为也让人迷惑不解。在司机的身上,生动的体现了作者的一个创作观点:对常理的破坏。常理单纯认为司机只是驾驶员,而在文中他却一点也不简单,他是个不按逻辑出牌的怪人,让人有诸多疑惑。
疑惑之一,司机和抢苹果的农民是否为同伙关系?很多人在读了文章后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理由也很充分。一,“我”友好的递烟示好表示想搭车,他却动手推我并怒声呵斥叫我滚开。粗暴的举止表明司机不是一个友好的人,甚至是一个坏人。二,“我”想去拿车后面的苹果,他却把车开得飞快,图谋不轨。三,“我”奋不顾身的为司机阻止抢劫苹果的农民,司机却袖手旁观,“我”受伤倒地,他乘机拿了“我”的背包和抢劫者一起离开。虽然这些理由看起来很充分,却经不起推敲。假设司机与农民是同伙关系,他获得的好处就是“我”那没多大价值的红背包,但是他损失的却是一辆汽车。就正常分析来说,司机这样做明显是得不偿失的,司机和抢苹果的农民并非同伙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疑惑二,既然司机和抢苹果的农民并非同伙关系,如何理解“我”奋不顾身为司机捍卫利益,司机却在一旁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呢?笔者认为这与司机的处事原则有关。司机面对气势汹汹的抢劫者,没有丝毫抗争的意思,因为他明白,在这样一个暴力群体下,他弱小的抗争是徒劳无力的,“我”奋不顾身的相助,也只是以卵击石,在他看来极为可笑。虽然他损失了苹果,汽车,但是他保全了自己,当“我”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已经摇身变成了看客,一个能在“我”身上获得补偿性满足感的看客。最后,司机拿了“我”的包与抢掠者一起离开,因为他发现在“我”面前他是一个强者,在“我”身上,他可以肆无忌惮获得强者的满足感。所以与其说这个司机是一个复杂的人,还不如说他是一类拥有看客心理,世俗化,愚昧麻木,欺善怕恶,圆滑世故的病态群体。
3 暴力的穿越者
余华是一位擅长写暴力、血腥、死亡的作家。很多人评价他“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是“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他自己认为“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2]
文中山民是暴力的代表。山民看见抛锚的汽车,然后就像参加日常生产劳动一样,有条不紊地搬运起苹果来。“我”上去阻挡,结果被狠狠打了一顿,就连原本天真可爱的小孩也很暴力,“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拿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这些人就像野蛮人一样暴力无情。在一批抢掠者之后,又来了更大一批抢掠者,抢了苹果然后开始卸汽车,最后汽车“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
余华对山民暴力抢劫行为的描述,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解剖世界的揭示。我们来想象这幅抢掠画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那时人们就像这群山民一样,暴力无情,无知无畏。中国古代文论有“知人论世”的观点,联系余华的生活背景,这个画面就更加清晰了。余华自己也肯定了这一观点,“那个时候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比较阴暗,我觉得‘文革’的经历跟我的经历有关。”[3]念中学时,正值文革时期,余华迷恋上了大字报,大字报大多是粗言谩骂和造谣攻击,余华在这里面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阴暗。这些山民,就像是文革历史中穿越而出来到“我”的面前,然后抄家一样抢掠了苹果,破坏了汽车,气势汹汹,扬言打倒了一切牛鬼蛇神。
4 温暖的“阴谋家”
作者在文中对“我”父亲的描写非常少,可以说完全没有正面的描述,仅有的描写是“我”与父亲的几句对话。
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在这几句对话中,很容易发现一个词,温和。再看下他们对话的时间,是“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安静闲适,阳光明媚的中午,说话温和的父亲温和地看着“我”,递给“我”一个背包,让“我”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他应该有些不舍,又有一些决绝。“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家门。
在这里父亲是一个善的代表,跟复杂的司机和暴力的山民相比,他就像阳光,给人温暖。有学者就认为“除了‘我’和‘我’的父亲外,《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把众多人物写得为恶不善,这不能不说是这篇文章的一大缺陷。”[4]笔者认为这不是缺陷,反而是点睛之笔。
人们往往说人生要经历三个阶段。当你还没有能力独立做事时,有你的长辈来为你指导;当你闯进社会,经受磨炼的时候,有你的朋友为你助力;当你明白人生,了解世间诸多世事,要为你的下辈做好服务。此时“我”正经历着人生第一与第二阶段的交界,“我”的父亲作为长辈,作为朋友同时也作为一个“阴谋家”出现了。这个“阴谋家”可能策划了很久,然而绝非不怀好意。他终于在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下定决心将“我”推出家庭的庇护,推入社会独自去感受社会的阴暗,人生的陷阱和生活的欺骗。
作者将父亲刻画为温暖的善者,而不是一个荒谬丑恶的人物,这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真实,现实世界的温情。他说:“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忍受现实的狭窄,人们需要一个虚构的世界来扩展自己的现实,文学一直承受着来自现实世界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情感和想象。”[5]文中父亲没有与恶为伍,而是一个用心良苦,温暖的“阴谋家”,他就像阴天里的一缕阳光,给人温暖,照亮黑暗。同时他还承载着现实世界里所有父亲对儿子深厚的爱。
[1]余 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斌的谈话[J].当代作家评论,1999(1):4 -13.
[2]余 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68-69.
[3]余 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4]孙长芳.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先锋性及其缺陷[J].语文学刊,2007(20):79 -80.
[5]陈晓明.中国先锋小说精选·序[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