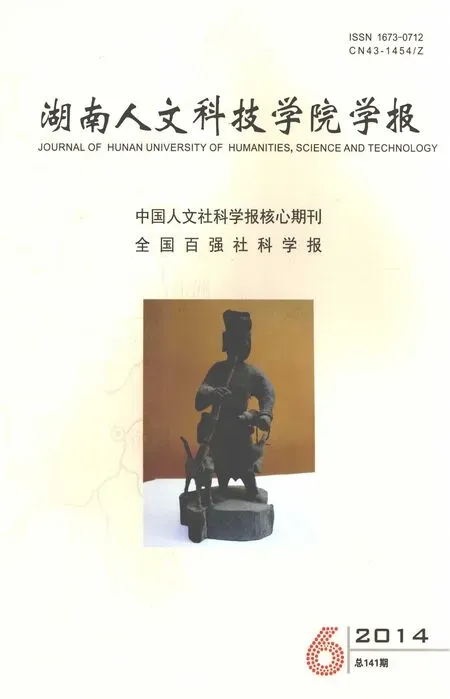“自然状态”范式:现代西方国家形成的理论基石
张小妹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 娄底417000)
在分析西方近现代国家的形成时,我们发现,从阿尔色修斯、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康德,无不对“自然状态”进行深入探究与描绘,尤以霍布斯、洛克等为甚。以霍布斯开创的独具特色的“自然状态”范式何以有如此之魅力而为近代重要思想家所青睐,并成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共同“理论基石”[1],进而设计出近现代国家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它实际上蕴含了两个议题:其一,霍布斯开创的自然状态范式为什么能够有效地解释现代国家的形成?其二,自然状态范式为什么会形成自然状态理论家所描绘的这样或那样的国家模式,而不是其它类型?究其原因,可归之为二:一是“自然状态”范式在方法论方面的解释。首先,自然状态假设者以数学似论证方式,根据自然法将事实的真理建立在几何论证的基础上,以致整个假设理论不可驳倒;其次,在没有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范式的前提下,后继者针对方法论假设提出批评,不断转换方法论前提预设而发展出丰富多彩的自然状态各样式,进而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国家。二是“自然状态”理论家受基督教国家理论的影响,接受基督教“人性恶”等这样的理念,从而设计出“有限政府”等现代国家模式。这种国家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关于人性的设置、对统治者的理解、国家权力的分配、确立何种程度的国家以及国家的意义等几个方面。
一 “自然状态”范式与现代西方国家
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作为一种数学(几何公理)似的论证方法却始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近代以前,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主要有三种传统,即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哲学传统、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哲学传统、伊壁鸠鲁主义传统。此时,自然状态学说的理论中心并不明确,他们关于国家的解释模式在相互竞争中没有一个占据任何重要地位,只有到了近代的霍布斯这里,情况才发生重大的转变。
自然状态理论之所以能为各位思想家所广泛接受,并成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主要理论资源,我们认为,社会契约论研究者高夫说的很有道理:“霍布斯既被嫌弃又遭羡慕,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契约论学说史上的重要性。随后的作者或受他影响,或得尽力对他做出回应。”[2]纵观历史,在黑格尔“绝对理念”国家解释理论以及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学说出现之前,除了霍布斯开创的强有力的自然状态解释范式之外,理性的思想家们确实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然而,“法律或政治互相攻杵且自相矛盾,使多少君主的人头因此落地”[3]1。至此,理性的思想家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找到政治的真理,使得政治学象几何学公理一样成为真理,从而避免这一人间惨剧。霍布斯认为:“要使学说服从理性规则并绝对无误,除了首先将这些原理置于一个激情不会猜疑也无从撼动的基础之上,别无他法;随后根据自然法将事实的真理建立在这些基础上,最后整个理论就不可驳倒了。”[3]1为此霍布斯从自然状态出发,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最后推导出结论:首先,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论证得出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然后,以国家本质为依据,论证了主权学说和专制理论,最后,以主权学说为起点,论证了民众的权利与主权者的义务。
(一)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首先,他假设了自然状态。他认为,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都是平等、自由的。其次,他假定人们必然遵循自然法。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的第一共同欲望就是对权力不断、无休止的欲求。为了保存自己,维护和平,人们必须有一个大于一切人的公共权力,使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由此,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彼此间共同约定:放弃自己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这样公共权力或国家就建立起来了。其次,他认为国家的本质就在国家本身,也就是主权。他在《利维坦》第17 章中指出:“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叫做国家,“主权者”,“人格”不过是公共权力的抽象体现。
(二)关于主权学说和专制主张
霍布斯将“主权”视为国家的本质,并指出了主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性质。他认为,主权者的权力不受任何个人、团体的权力限制,也不受法律的限制。他否认任何对主权者的约束。构成主权的各项权力都是统一不可分的。他批评了民主制的种种弊端,认为君主制是所有国家类型中最佳的。
(三)关于民众的权利与主权者的义务
首先,他认为,作为一个臣民,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即使有主权者的命令,人们仍然可以拒绝不做的自由。另一种是在主权者未以条令规定的地方,臣民有自由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或不采取行动。其次,根据人们在国家中的权利,霍布斯又规定了主权者的义务。他认为主权者的根本义务是保卫人民的安全。他将服从自然法作为君主的主要义务。除此之外,他还为主权者规定了一些具体的义务,如主权者必须保护好主权、教育人民,根据良好的法律和平等的原则进行统治,确定和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等。
二 “自然状态”范式的发展与现代西方国家
数学公理似的论证方法一旦在逻辑推理上无可争议,那么,其结论也应该是不可驳倒的。但是,我们知道,数学方法也有着本身的弱点。怀特海认为,“一切的麻烦就在于第一章上,甚至于就在第一页上。因为正是在这个刚一开始的地方,作者很可能在假设上有失误”[4]。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后续的自然状态理论家,如洛克、卢梭、康德等,为了完成各自的国家学说,都把前者赖以推理的前提或理论预设当作批判的中心,把它作为攻击的最佳切入点,主动对其修改、加强或改造。
洛克认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在理论论证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这种“自然状态”范式的理论预设却存在着重大的问题。第一,关于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与和谐、完备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5]第二,关于主权者权力的问题。洛克指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契约的关键是人们的同意,由此,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因此,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是无限的、专断的,而是有限的。
在这里,洛克在为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他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调整契约各方关系,把主权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转变为契约当事人的地位,从而达到其理论及政治目的,并进一步推动发展了“自然状态”范式。与洛克对霍布斯不满一样,处于追求民主、法治治国时代的卢梭同样不满意洛克的“自然状态”范式前提预设。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的“理性”仅仅是潜在的。“真实的自然状态”首先应该是一种彼此孤立的状态,彼此之间无所谓平等与不平等、善与恶的概念存在。其次,在自然状态中,一切都是公共的,相互之间对土地及其它财物所有权的承认便不可能存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人人生而自由,按自己的意志占有财产,按自己的意志享受生命。但是,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并不能享受绝对的自由,自然法构成了对自由的约束。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固然是一种自由状态,但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状态。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要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由于人性使然,即“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6]。他认为,人们要寻找出一种结合方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在服从他自己本人而已,并且他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他认为,人们在同意建立国家之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所以,所有人都是同等的,权利的转让是毫无保留的。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侵害的一部分”[7]。这个由全体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就称为国家。由此,个人进入政治社会后,自然的平等被摧毁了,代之以道德的平等和法律的平等。国家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成全好人,最好的政府就是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和最好的人民的政府。在权力的运用上,卢梭根据公意的要求,坚决反对分权。他认为,分权之后公意就成了众意,它只代表私人利益。公意一经分割就成了众意,不能代表公共利益。
自然状态理论假设发展到卢梭这里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还是无法脱离经验的樊篱,而且,各种假设本身也还存在逻辑矛盾,遭遇了种种理论困境,并由此导致各种批评,尤其是经验哲学家休谟通过对理性概念的批判,摧毁了作为自然状态模式的理性根据的自然法理论体系[8],那么,复兴自然法传统,重建自然权利概念,挽救自然状态理论,就需要一种批判的理性为之探讨更深的根据。由此,康德分三步利用“自然状态”范式创立了自己的国家学说。
第一,康德以形式的或先验的方法论证了自然权利。他通过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与自由,强调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自由高于自然等,把自然权利归之于基于人的本质的自由,从法理哲学角度提高了自然状态理论的论证水平。
第二,他在批判卢梭自由的基础上确立了人性论。康德认为,恰恰是在内在自由领域,卢梭放弃了自由的自主性质。“良心”作为道德原则具有缺乏规定性、非先天普遍性和没有客观标准几大缺陷。所以,卢梭虽然认识到了自由是对内在原则的服从,但还没有达到自由即自律的高度。
第三,康德用“概念世界”创立了独特的国家学说。康德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的自由是一种野蛮的自由,于是,人的道德命令要求人类必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使人们的自由和国家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普遍法治的社会”[9]。
康德指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外在自由,目的是又立刻可以获得作为一个共和国成员的自由。“国家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个人追求合法利益提供保障,国家唯一的职能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国家不得也不必干涉公民的活动,不得也不必以家长式的方式关注他们的利益和个人幸福。”[10]203国家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只能是经人民同意的限制,也就是说,是人民自我的限制。
为了防止专制统治,康德主张三权分立,实行共和主义的君主制。他认为:“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反映的应该是人民联合的意志,否则就会导致暴政。”[10]313行政权属于国家的统治者或摄政者。他们代表“公意”,即主权者及其机构行使职能。不论立法权还是行政权都不应该行使司法职务,只有任命的法官才能行使该职务。同时,他主张必须建立世界的共和国联邦,发展出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种国际性的联合应该是“自由国家联邦”。
三 “自然状态”理念与现代西方国家模式
施特劳斯、奥克肖特等指出,在人性基础、国家的必要性、国家权力的范围以及个人自由的依据等内容上来说,近代自然状态学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其学说旨趣可以归结为自由主义。在近现代,基督教对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极其深远,“人性恶”等观念深入人心。基督教对自由主义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消极的国家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根源于人性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祸害,它只有消极的工具性价值和职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国家学说是对基督教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与世俗化和现代性的转换。
(一) 关于人性的设置
基督教神学的国家解释学说是自由主义的样板,并从此处找到了国家存在的理由。基督教从伊甸园开始,而自由主义则从自然状态出发。基督教认为,国家之所以需要,乃是由于人类本性堕落之缘由。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产生乃是自然状态的缺陷所致。自由主义认为,人类之罪与亚当夏娃的过失无关,它深植于人性,而国家植根于人性之恶。自由主义不关注人的纯洁无邪,他们面对的是人的堕落。他们的政治模式设计与上帝救世的计划毫无关系,与彼岸世界也没有任何的联系,要的就是政治现实,而自然状态正是基督教的堕落状态的翻版。从霍布斯开始,人性邪恶与人性缺陷就是国家产生的根源这一强大信念,已扎根于自由主义者思想家心中,从此也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基本预设。他们根据这一信念,确定对国家的态度、国家的权力结构图式、国家活动的范围等等。正如汉密尔顿指出:“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1]也就是说,人类并非如天使般纯洁无邪,所以就需要政府的管辖,统治者也并非如天使般纯洁无私,所以必须设置复杂的监督制约机制来控制他们。所以,政府绝非人类的荣耀,这是人性低劣卑污的表现。
(二)关于统治者的理解
众所周知,基督教强调的是精神生活和彼岸命运,贬低世俗权力,因此,他们以不信任、甚而敌意的态度来对待国家。相反,自由主义者关注的是人的现世处境和命运,即人的自由、权利、安全和福利等等。由于人性的邪恶和自私,自由主义者由此也并不信任统治者。他们从消极角度出发,把国家权力看作是个人权利的威胁。正如休谟指出:“许多政论家已经确立这样一项原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该制度中的若干制约和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统治成员都假定为是一无赖,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的。”[12]117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就要对他们保持怀疑和警惕,不能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13]。
(三)关于国家权力的分配
自由主义从人性之恶中为国家找到存在的有限理由,那么,他们又如何能避免产生更大的恶呢?基督教以独立的教会掌控国家权力,而且成为道德权威。受基督教的影响,自由主义对国家做了如下的限制:首先,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权力有限定的范围;其次,对权力进行内部分权制衡,使国家权力控制者在追求自我利益时,也要他们必须增进公共利益。正如休谟指出,“议会中所有成员都追逐自我利益,但明智的政府组织通过巧妙的分权,使其中各个集团在谋求自己利益时,必然和公共利益相一致”。[12]28然而,我们也知道,对权力的防范不能仅从权力结构内部找到出路。正如基督教思想家提供的思路,我们必须从外部找到约束力量,即上帝、末日审判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卢梭仰仗人民的道德素质、人民的监督甚至反抗行动等。
(四)关于何种类型国家的确立
“自然状态”国家学说发展到现代,有三种著名的国家类型: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有限的国家”。国家主义的典型代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只在英国刚刚取得革命胜利,急需稳定国家秩序和恢复经济之时才有意义。在现代西方,他的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只具有理论意义。
无政府主义和“有限的国家”在本质上都对国家抱有相同的认定——国家是恶和祸害,只是无政府主义更是将政府或国家视为纯粹的恶。无政府主义对社会自身的力量充满信心,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表达的政治意愿是自由个体的自愿结合,互助和自治,这样,注定它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无法形成对应的历史形态。只有“有限的国家”理论深受基督教国家学说影响,且在现代处于主流形态,具有现实价值。
基督教认为,教会作为道德权威,即使在世俗生活领域,也承担着监督国家的功能。由于人类的堕落,我们首先需要国家来扼制其犯罪倾向;如果人类犯罪,我们则需要国家来予以惩罚,以防止更大的罪。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基督了解人性的弱点所做的安排[14]。“有限的国家”理论家一方面认定政府或国家为恶,但同时又承认它还具有有限的善,或者可以说至少是善的有力工具。所以,他们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这两个祸害中选择了国家或政府,但他们也绝没有从此就对它产生崇拜。他们认为,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也就是说,它追求的是法治,而法治的最重要的政治职能就是确立和维持一个在权力、作用和规模上都受到严格法律限制的“有限的政府”,而法治的最高阶段就是宪政。宪政的目的也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以达到充分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公权力侵犯的目标。
[1]刘小枫.《创世记》与现代政治哲学[M]//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秋季号(15):9-11.
[2]GOUGH J W.The Social Contract: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2-3.
[3]GASKIN J C A.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
[5]洛克.政府论:下册[M].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
[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长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
[7]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5.
[8]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M].刘训练,李丽红,张红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0-122.
[9]康德.普遍历史理念[M]//康德.康德全集:第8 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
[10]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康德.康德全集:第6 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4.
[12]HUME D.Politicai essay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17.
[13]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86.
[14]BRIAN T.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with selected documents[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