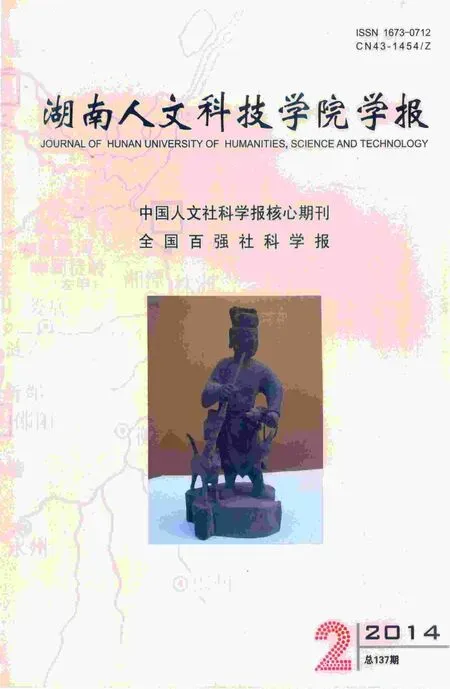论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
周兴杰,唐赛男
(1.湖南科技大学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湖南湘潭411201;2.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就起源而言,中国流行歌曲自欧美舶来。至今,这种影响仍未断绝,如本世纪大行其道的R&B、Hip-Hop等诸多曲风,就是如此。但与此同时,将之本土化的追求和相应的本土化的音乐生产实践,从未停止过。早如1920-1930年代黎锦晖的《毛毛雨》、《桃花江》,1980年代又有“西北风”、“高原风”,都是引民歌曲调入流行音乐,借中国民间音乐丰厚的养分以丰富流行歌曲的音乐表现形式。而近年来流行的“中国风”,曲调上虽仍效法欧美,填词却极力追摹中国古典诗词,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中国特性,提升自己的审美品格。所有这些,都印证了中国流行音乐本土化进程中多种多样的探索方式的存在。
近年来,另一种中国流行音乐本土化的方式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注意,那就是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它构成了流行音乐本土化的又一重要表现。本文拟围绕这一现象进行探讨,以揭示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具体的文本形态,阐明其内含的文化意义。
一 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发展历程
戏曲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其与流行歌曲的融合,赋予了这种音乐生产方式鲜明的中国特性。学界一般认为,这种融合始于1980年代。下面这种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上,将戏曲音乐元素融入流行歌曲的现象早在1980年代就已有作曲家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如姚明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故乡是北京》,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流行歌曲中运用戏曲音乐元素进行创作的手法、形式更加多样,更具有时代感。”[1]的确,1980 -1990 年代涌现了一批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经典作品,但如果将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起点勘定于当代的话,则忽略了此前几代中国音乐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殊为可惜。
我们认为,戏曲中的特定音乐元素在流行歌曲中的融入,其实早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发轫期就已经出现了。说到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就不得不提起上海滩的时代曲,提起周璇。周璇自幼受戏曲熏陶,其后人回忆道:周璇的外婆很喜欢戏曲,“常常带小苏璞(周璇本名,论者注)去观赏在当地搭台演出的地方小戏”,所以三岁的周璇就开始学唱[2]。在后来的演绎生涯中,她虽然博采众长,但戏曲的影响一直存在,细心的听者不难觉察出这种特点。对此,有论者做出高度评价:“她的唱法延续了中国戏剧的唱腔唱法,音调很高,例如歌曲《爱神的箭》,在问‘爱神的箭射向何方’时,一腔一调,举止动作,都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戏剧的痕迹。这时的流行音乐还处于发展期,她能将自己多年来从戏班、歌舞团里面学到的东西糅和起来,借鉴中国的传统艺术,和西洋流行音乐渗透在一起,活学活用,成为当时一种独特的唱法,具有丰富的内涵。这样的音乐才是真正的中国流行音乐,符合了‘中国’二字,中国深沉的文化底蕴和灿烂的传统文明沉淀于其中,又不失流行与时尚的色彩,让人们在欣赏这首曲子的同时,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戏剧的魅力,同时满足了人们对于流行的追求。”[3]据此,我们可以说,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在第一代流行音乐人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周璇借鉴传统戏曲的这种方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流行音乐的跨文化移植特性,最早的流行音乐家几乎都是在首先拥有本民族音乐素养的基础上再来接受和再创作这一新的音乐类型的,戏曲等民族音乐形式作为前提性的音乐素养,对他们产生影响或者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自身艺术机能的惯性反应。就像后来一些美声歌唱家、戏曲名家演唱流行歌曲,其发声运气仍留有自己原来的美声或戏曲演唱方式的痕迹一样。这也表明,最早的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是一种基于艺术家音乐素养的个体性自发行为,这一阶段也可视为一个自发性的探索阶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现象是1950-1960年代的在内地和香港涌现的大量的戏曲电影。仅1950年代,香港就拍摄出了500多部粤剧电影,20余部黄梅片和10多部越剧片。内地也涌现出《天仙配》、《女驸马》、《花木兰》、《红楼梦》等一批深受欢迎的戏曲电影。戏曲电影中含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本议题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方面是戏曲在大众媒介传播中的普及化问题。戏曲的接受,本来很大程度上受方言的制约。进入电影这样的大众媒体之后,戏曲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为自己赢来更多观众,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故而,像一些香港的黄梅片、越剧片就在唱腔、咬字方面有意识地做出了改变,使之更适应其他方言区的听众,扩大了自己的受众范围。如果说这一改变只是戏曲为了适应影视传媒的一个细小变动的话,那么它实际产生的传播效应却是巨大的。这些影片中涌现出了像《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样脍炙人口的选段,这些选段作为一首首歌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于今不绝。这些选段后来还被一些流行歌星反串演唱。不妨说,这是使戏曲演唱歌曲化了。这也为后来戏曲与歌曲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一定的受众基础。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戏曲电影对流行歌曲产生的直接影响。像香港粤剧电影《帝女花》就对香港粤语流行歌曲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冠杰、汪明荃、罗文等较早一批的香港歌星在访谈、回忆中都多有提及。更有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就是将这些戏曲电影名段稍加变化,竟成了流行金曲[4]。综合这两方面看,1950-1960年代的戏曲电影时期也是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它从媒介、受众基础和演唱等方面为这种融合做了必要的准备。
应该说,有了发轫期的摸索和戏曲电影期的准备,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才有了1980年代后期至今的成熟与繁荣。虽然围绕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涌现了大量成果,但有一点却为许多人忽略了,那就是不仅存在引戏曲元素入流行歌曲的探索实践,也存在引流行音乐元素入戏曲的尝试。甚至,后者的发生还要略早于前者。按著名乐评人金兆均的记载,新时期第一首戏曲流行歌曲化的作品应该是著名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此曲为19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当年红遍大江南北。1985年,国际音像艺术公司又让著名配器师温中甲着手用迪斯科舞曲来改编京剧。而且,“录音完成,小样儿正好被当时参加振兴京昆研讨会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听到,他当即提出:能否搞一台演出。结果,两星期后,一台《南腔北调大汇唱》就与北京观众见了面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轰动”[5]。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姚明创作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等引戏曲入流行歌曲的成功。而从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角度看,引流行音乐元素入戏曲的意义尤为特殊。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文化气候的影响,流行歌曲存在的合法性还备受质疑。将流行音乐元素引入戏曲,并获得北京市副市长这样的领导干部支持,无疑是流行歌曲争取其存在合法性的重要策略,甚至是获得合法性的一种证明。此后作为当代流行歌曲第一人的李谷一再唱《前门情思大碗茶》,无疑是寻此而对流行音乐合法化做出的进一步推动。而戏曲与流行歌曲的相互交融,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探索与尝试,终于在近20年迎来了自身的繁荣。
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特殊性,从发轫到今天的繁荣,尽管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发展历程是跳跃式的发展的,但其谱系上的承接关系却不容忽视,我们必须将其联系起来。由此,我们认为,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发轫期的探索、戏曲电影时期的准备和新时期以来的成熟与繁荣三个阶段。明乎此,我们才能知道这种音乐生产方式成熟的来之不易。
二 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音乐文本形态
通过梳理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交互的。在此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诸多优秀作品,许多学者称为“戏歌”。但对于何为“戏歌”,人们一般未作严格界定。像有的学者就说:“什么是戏歌?戏歌是一种新兴的音乐体裁,是戏曲这种传统而古老的艺术形式与当代流行因素结合的产物。戏中有歌,歌中有戏,但它还是应该属于歌的范畴。”[6]这种描述虽然抓住了此类音乐文本的一般特征,即非戏非歌,亦戏亦歌,但却失之笼统,因而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形态差异作出进一步细分。根据上文梳理的这种融合的不同趋向,我们大体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音乐文本形态:加入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和加入流行歌曲元素的戏曲。
首先,我们来看加入了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此类音乐文本说到底还是流行歌曲,因为其基本的音乐结构是流行歌曲的,而且演唱方法主要也是流行歌曲的,只是在歌曲的一些部分借鉴了戏曲的音乐元素,所以听觉上给人的感受仍然是流行音乐。而从容纳、吸收戏曲音乐元素的程度来看,这些歌曲又可以分出两小类:一类是有个别乐句在曲调和唱法上借鉴戏曲。如陈升的《北京一夜》,此歌在新加坡获得金曲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副歌乐句“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加入了京剧花旦唱腔,显得新颖别致。但其整体音乐结构仍然是流行歌曲的,甚至连伴奏乐器都是采用的吉他、架子鼓和萨克斯等流行音乐的常用伴奏乐器。据陈升回忆,当时他来北京为电影配乐,却迟迟找不到灵感,当时陈升已经想好要打包回台湾了,一边懊恼的用闽南话哼出“为何在北京”,此句像极了英语“one night in Beijing”,他由此获得灵感,创作出了这首知名的歌曲。据此,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融合探索,不如说是一次不同地域、乃至民族文化成分在音乐人意识中杂糅后的巧合。后来,王力宏的《花田错》在类型上也与此相似。只是在副歌的编曲和演唱中借鉴、模仿了京剧唱腔,文本的主体仍然是R&B这样的流行音乐结构。不过,这首歌与《北京一夜》的不同在于,它在题材上是取材于京剧剧目的。
另一类情况则是不是单句的借鉴,而是存在乐段上的歌与戏并置。例如,由闫肃、姚明的作品《唱脸谱》发展而成的作品《说唱脸谱》就是如此。这首歌是将流行音乐化了的京剧唱段与流行音乐的说唱唱段并置一处。这样的歌曲中,戏曲的比重比较大,配器上也以京胡等传统戏曲乐器为主导,但行腔走板比起京剧等戏曲来已经自由得多了,伴奏中除流行音乐乐器外,甚至加入了交响乐。这样,在给人京味儿十足的感觉同时,也突破了戏曲的程式化束缚,显得时尚了许多。必须指出,这种歌曲与戏曲的并置,不仅有京剧元素的加入,也有其它地方戏曲元素的加入。像慕容晓晓的《黄梅戏》,音乐结构上就是在主歌与副歌之间加入了黄梅戏《女驸马》的经典唱段。其他,像近来流行的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亦属此类。他们与一般流行歌星的演唱区别在于,他们都有一定的戏曲演唱功底,也很好地掌握了流行歌曲的发声方法,所以戏曲部分字正腔圆,整首歌曲的演绎也自然到位。就演唱而言,此类作品的演唱比上述个别乐句的借鉴的演唱难度更大。
其次,我们再来看加入流行歌曲元素的戏曲。此类音乐文本相比较而言更贴近戏曲。因为其主要的音乐基调和演唱方法都是戏曲的,而演唱者也主要是专业、或准专业的戏曲演员,所以在听觉上给人的戏曲感更强,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戏歌”,是以戏曲的方式来唱歌,但已有流行音乐元素加入其中。
如前所述,新时期第一首戏歌当属骆玉笙老人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就演唱而言,这首歌是原汁原味的京韵大鼓,八十高龄的骆玉笙老人根本就没有去吸收运用所谓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她甚至都不适应流行音乐伴奏的录音方式。后来,是采用了分轨录音,才艰难完成了演唱与伴奏的混成,因此,这首歌可以算作是“戏曲”+“流行音乐”。其后涌现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等作品的融合情况就要顺畅得多了。演唱者李谷一虽不是京剧演员出身,但在京生活多年,既掌握流行歌曲演唱技巧(她是新时期内地第一首流行歌曲《乡恋》的演唱者),又有戏曲(花鼓戏)演唱底子,故而她在这些歌曲的演绎上给人水乳交融之感。这一系列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并作为一种特定的音乐体裁和音乐生产方式被稳定下来。
随着这种音乐生产方式影响的扩大,出现了一种新的演绎方式,那就是用戏曲的方式来重新演绎流行歌曲。例如,一些越剧演员就用越剧唱腔来全盘翻唱经典流行歌曲《涛声依旧》(演唱者有王君安、孙静,还有被称为“越剧王子”的赵志刚)。他们在演唱这首歌时,基本上只保留了原作的歌词(当然,适应越剧演唱需要,也在个别地方有改动),其它从曲调到演唱,全部按越剧来处理,别开生面,韵味十足。而孙静这样的戏曲演员更是尝试把流行歌曲的演唱技巧融入到戏曲演唱当中去,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7]。
通过上述两大类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音乐文本类型的区分,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二者在不同作品中的融合程度,以及这种融合的不同趋向。这就使我们在认识这一融合现象时不会失之偏颇,不会只看到一种趋向、一种类型,而忽略其它,进而在这种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思考这种融合的意义。
三 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文化意义
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无论对于戏曲而言,还是对于流行歌曲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它为当代社会条件下戏曲与流行歌曲的发展探明了新的路向。在当代艺术生产条件下,不管是戏曲,还是流行音乐,其生存和发展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中国的戏曲艺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已经具备成熟的表演体系和丰富的艺术内涵,但是受当代新兴媒介文化的冲击,它的受众群日趋萎缩,特别是很难为青少年群体喜爱和接受,生存和发展正面临着严峻考验。走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之路,为它们更好地适应当代媒介技术条件以及吸引青少年群体创造了条件。流行歌曲,随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应运而生,作为新兴的文艺生产类型,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喜爱。但由于其商业化的价值定位,和对娱乐功能的过度追逐,其整体性的艺术品位还有待提高,人文内涵还有待丰富,因而无论中外,自诞生之日起,流行音乐就饱受批判。这方面无需展开,西方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中国1980年代初对《乡恋》的抨击与封杀,都是著名的例子。而走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之路,无论对拓展流行音乐的表现力,还是提升其人文、艺术内涵,都有着显著作用。从《唱脸谱》到《新贵妃醉酒》,越来越多的作品的涌现,并受到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群的喜爱,都从事实上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创造的音乐类型,虽然亦戏亦歌,非戏非歌,成为一种难以准确定位的亚音乐文本类型,却正是二者相互取长补短的成功范例。
进而视之,由于这种取长补短的融合,它也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性的音乐生产方式。如前所述,由于流行音乐的舶来特性,它长期受到欧美流行音乐生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促进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本土流行音乐发展的限制。故而,非止一代的音乐人为促进流行音乐的本土化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前文所述的“民歌风”、“中国风”,即是这种努力的结晶。而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同属如此。而且,由于戏曲这一中国独有的音乐艺术种类具有独立完整的表演体系和艺术理念,因而它的引入,更有利于中国流行音乐吸收优秀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创新观念,增强底蕴,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生产模式,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创性与竞争力。
而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层面,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则是民间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有机融合的突出表征。“民间的”与“市民的”二者本都源自“civil”一词,二者的基本意义中都有“非官方的”的意思。就此而言,民间文化就是市民文化,戏曲与流行歌曲因而本属同一文化系统,二者无需强分彼此,二者的融合由此视之也是一种必然了。但实际上,二词在现代汉语语境的实际应用中还是存在细微差异的。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民间”一词有如下几重内涵:“(1)平民自愿组织的;(2)来源于老百姓或在老百姓中间广泛使用的;(3)非官方的;(4)百姓中。”在实际应用中,“民间”更倾向于“来源于老百姓或在老百姓中间广泛使用”的意思。例如,中文语境中的“民间音乐”更对应英文语境中的“乡村音乐(folk music)”。而“市民的”所指更强调“城市的”、“商业的”,如流行音乐即是在此层面上被称为市民文化。因而,二者在社会空间形态上实际包含着乡野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分野,在历史形态上包含着威廉斯所言“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的差异。明确了这种内涵上的差异,我们才能明了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难度,也才能明了戏曲与流行歌曲融合的可贵。
[1]黄晴葵.戏曲音乐元素在流行歌曲中的运用[J].才智,2010(1):168-169.
[2]周伟,常晶.我的妈妈周璇[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9.
[3]伍春明,伍音菲.民国时期上海流行歌曲的歌星演唱风格初探[J].齐鲁艺苑,2009(6):60-66.
[4]宋哲文.古曲·粤曲·流行曲:略谈粤剧音乐编排之灵活性[J].南国红豆,2010(2):8-10.
[5]金兆均.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80.
[6]赵虹炫.戏歌,架起流行歌曲与戏曲音乐的桥梁[J].中小学音乐教育,2008(3):12-13.
[7]孙静.“戏”与“歌”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浅谈戏曲演唱与流行歌曲的共性与个性[J].剧影月报,200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