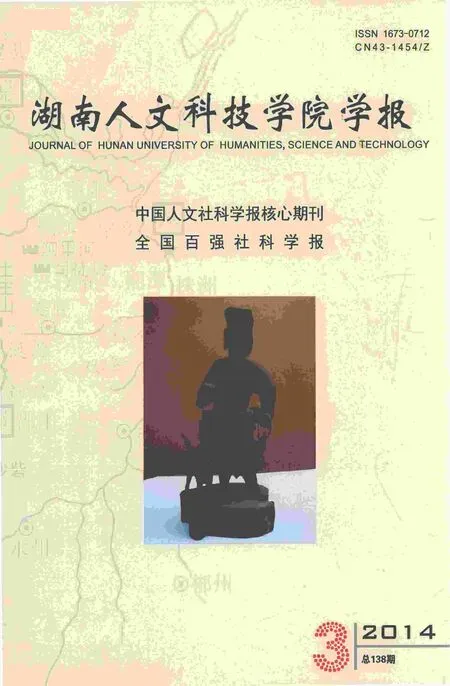论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叙述者”
王影杰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叙述者”是指小说中讲述故事的人,是“表达出构成本文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1]。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将其分为“戏剧化的叙述者”和“非戏剧化的叙述者”[2]170,叙述者在小说里的不同表现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技巧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数百篇小说里叙述者的声音极富变化,既有《假面丑八怪》《偷盗》里面的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又有《地狱变》《河童》里面的戏剧化的叙述者,更有《妖婆》《开化的丈夫》中交错相合的双重叙述者。芥川在叙述者方面的创新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审美感受。形形色色的叙述者也让他的小说变化多端,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目前国内对芥川小说中叙述者的研究多是从一个视角着手的微观探索,本文拟从宏观的角度对芥川小说中的叙述者进行总体概括和分析。
一 戏剧化的叙述者
戏剧化的叙述者明显带有个人特色,在文本中既有叙事功能又有角色功能,并且往往以“我”的身份出现。戏剧化的叙述者又分为自觉的叙事者、叙事代言人和旁观者。在芥川的小说中,这3类叙事者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觉的叙述者会故意让读者知道自己就是作家本人,为此他甚至会直接在作品中谈论自己的创作或思考。自觉的叙述模式和西方后现代时期出现的“元叙述”有相似之处,都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创作过程,小说的叙述往往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芥川在20世纪初的文学创新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觉的叙述者在芥川的小说里并不少见。《罗生门》开头作者以全知视角写仆人在罗生门下避雨,而此处在近两三年来变得异常萧条,狐狸做窝、盗匪落脚、死尸堆弃,到处都是腐烂的恶臭气,仆人只能木然地盯着下雨的景象,接着文本中就出现了“作者写到‘仆人在等雨停’”[3]30这样一句话。作者把自己的写作也搬到小说的舞台上,让读者猛然从已营造好的阴森可怖的气氛中醒悟过来:原来这都是作者编织的故事!接着他分析了仆人的处境,显然“在等雨停”并不是对仆人现状的最好概括,因为他已经被主人扫地出门,而眼下经济凋敝,要找到能糊口的事情做是不可能的。于是作者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与其说‘仆人在等雨停’,不如说‘困顿雨中的仆人无处投身,穷途末路’。”[3]30作者把自己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写入小说,这样就有两幅画面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副是罗生门下仆人避雨,一副是作者伏案写作。此时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是清晰明确的:作者在现实中而仆人在虚构的小说中;读者由身临其境变为隔岸旁观,与人物的距离由近变远。芥川在此处打破了读者入戏的幻觉,使之产生了出戏的清醒。正当读者暗自庆幸自己已经出戏不再被虚构的文学作品左右之时,芥川又开始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作者深入人物内心时读者会不自觉地被带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感情上与人物融为一体,近而达到入戏的效果。叙述者深入仆人的内心与他一起经历思想的挣扎:到底是为摆脱困境而不择手段还是宁愿饿死也不沦为盗匪?叙述者在揭示人物内心时,也把这个问题摆在读者面前。读者仿佛又掉入了作者的叙述陷阱,与人物一起思考生存与道德的悖论,一起经受罗生门上恐怖环境的压迫,一起发现城楼上的尸骸中蹲着的老妪。正当这时,小说写道:“仆人揣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一时间忘却了呼吸。借用一位旧事记者的形容,那感觉真是‘毛骨悚然’。”[3]32显然,借用旧事记者话语的是作者芥川,而不是仆人——作者又一次把自己搬到舞台上来了!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即自觉的叙述者,两次跳出来将他的思考和感受告知读者,使读者在入戏与出戏之间不听转换,形成心理上的跌宕起伏。
叙述代言人是指“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某些可以估量的影响”[2]172的叙述者,与自觉的叙述者相比,代言人对情节的介入较少。芥川的小说多运用非戏剧化叙述,以旁观超然的态度静观事件的发展,这与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并且他旨在表现的多是对人性的反思、对人生的不安、对宗教的思索等沉重的主题,这样的主题直到现代派才大胆地用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而这之前则多是常规的非戏剧化叙述。但是芥川是新技巧派的服膺者,他除了塑造常规的代言人外,还大胆地尝试了戏剧化的代言人。《暗中问答》是芥川自我剖析的文章,其中的“一个声音”和“我”是作者人性的两个方面,“一个声音”代表本我,“我”代表超我。“一个声音”对“我”发起的责问是潜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担忧和疑惑,“我”机智巧妙的回答是作者对自己的积极暗示。因为“一个声音”是作者的叙述代言人,他秉承了作者本人的睿智和犀利,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软肋:内心软弱、害怕失去读者、思想矛盾,并且指出“你的悲剧在于你有比别人更了不起的智慧”[4]771,这些可以说是对芥川最恰当的描述。作者“分裂”成两个对立的叙述者,他们相互诘难,显示出晚年时期芥川内心的挣扎、迷茫和恍惚不安。叙述代言人在小说中很容易被识别,作者操纵代言人为自己发言,能自由地表达情感和态度,同时也可以与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至于使介入太过明显。
旁观者是指站到故事之外,对情节发展不产生任何影响的叙述者。他负责提供为促进故事顺利展开读者必须知道的信息,并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如《地狱变》中的“我”。故事由“我”之口讲述,“我”的性格特征则可以通过“我”对待事件的态度达出来。文中涉及到“我”的价值判断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对堀川大公的判断:第一,当有传闻说大公偏爱良秀的女儿是因为好色的时候“我”不相信,并坚持认为“大公老爷偏爱良秀之女,完全是出于赞赏。赞赏姑娘对于小猴的怜爱,赞赏姑娘孝顺父母的恩爱”[3]325;第二,良秀想把在大公身边做侍女的独生女儿要回来,但大公却不肯放人,这件事情在“我”眼里是“大公不肯辞退良秀之女,完全是出于怜悯。与其将姑娘送回那冥顽不灵的父亲身边,不如将她留在邸中自由生活”[3]328;第三,大公将良秀的女儿缚在车中烧死,并让良秀以此为实物绘画地狱变屏风,“我”对这件事的评价是“大公的真正意图绝非要烧车杀人,而是要惩治屏风画师良秀的邪恶根性”[3]347。对良秀的判断:第一,良秀瘦骨嶙峋,并且嘴唇由于舔画笔变得异常红润,令人嫌恶;第二,良秀对世间的一切惯例嗤之以鼻是傲慢专横的表现,他多描画丑陋惊悚、怪异恐怖的事物,并且为了绘画地狱变不顾他人死活,表明他已经沦落画道邪途;第三,良秀眼睁睁看着女儿烧死,是铁石心肠的恶汉。
对于戏剧化的叙述者,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他的“可信度”。聆听叙述者的声音时我们一定要对他的价值评判保持清醒的认识。《地狱变》中的“我”是侍奉堀川大公的仆役,“我”的判断也带有个人偏见。如果起初读者不明白大公把良秀的女儿留在身边到底是出于好色还是赞赏,那当知道他宁愿让良秀父女忍受着思念和担忧之苦也不放人时,我们可以确定这绝不是出于“怜悯”。随着情节的发展,“我”偶然间撞见泪流满面、衣衫不整的良秀之女,此后大公残忍地在良秀面前将其烧死,由此可见“我”对大公的判断并不是始终可信的。而对良秀的评价,“我”难以摆脱世俗的眼光。对于这类不可信的叙述者,读者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通过客观分析事件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美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把不可靠叙述分为两种形式:疏远型不可靠性和契约型不可靠性。疏远型不可靠叙述拉大了叙述者和“理想的读者”(在伦理、情感、知识等方面完全符合作者要求的读者)之间的距离,造成作者和读者之间关系的疏离或缺失;而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则缩短了叙述者和“理想的读者”之间的距离,我们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还是会在情感上走近他,这形成一种悖论[5]。在《地狱变》中,事发之初仆役由于自身的局限向读者发出错误的判断,他的叙述引导着我们一步步偏离隐含作者的旨意,疏远了我们和隐含作者的距离。而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火烧良秀女儿”事件让仆役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他看到了大公的谲诈、残暴、狰狞,也看到了良秀的可怜、恐惧和无助。他的情感和伦理逐渐向隐含作者靠近,但他的叙述话语仍然是不可靠的,他不具备引领理想读者走向隐含作者的能力,他认为“大公的真正意图绝非要烧车杀人,而是要惩治屏风画师良秀的邪恶根性。这是大公亲口对我说过的”[3]347。此时仆役的不可靠叙述由疏远型转化为契约型,读者能意识到他不可靠,但还是在情感上与他产生共鸣,在对待良秀的态度上他与隐含作者和理想读者之间达成共识。“地狱变”的故事靠一个不可信的仆役来叙述,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而为之。“正是由于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叙述与交代,也正是由于他在作品中所言非所指、富有意味的展露与评价,才使得这部作品极具神秘感和讽刺力量。”[6]
二 非戏剧化的叙述者
非戏剧化的叙述者“没有被赋予任何个人特征”[2]169,他往往出现在以不带个性特色的“我”、“他”为讲述中心的叙述中,或者是严格的无人称叙述中。
有人称的非戏剧化叙述多以“我”或“他”的意识为中心来展开。“意识中心”说由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7]。亨利致力于小说叙事的客观化,他主张有选择的全知叙事,即叙述者只呈现小说中一两个人物的有限的视域,并且对人物意识的挖掘也只限于浅层的,叙述者不能做出评价和议论。这一类的叙述方式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里居于主导地位,他大多数的作品都是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如《假面丑八怪》《偷盗》《戏作三昧》《素盏鸣尊》《玄鹤山房》等等;也有第一人称叙事,如《野吕松木偶》《文友旧事》《湖南的扇子》《点鬼簿》等。这种有人称的叙述方式与严格的无人称叙述相比,叙述者的存在更为明显,因为叙述者可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主观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叙述者的客观性,好在芥川从来不在小说中发表“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这样明显的议论,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对人物和事件作出评判。《假面丑八怪》讲述的是一个人带假面跳舞而猝死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叙述者首先采用的是限制叙事,他细致地描绘了吾妻桥的自然环境和桥下观花船的盛况,并且告诉我们“船上,一个尖嘴猴腮的矮个男人,伴着音乐入迷地舞动”[3]16。男子的舞姿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片刻之后,只见一个看客惊慌失措地对船老大说着什么,船突然调头驶去,大约过了十分钟观客们才听到舞者骤逝的消息,而且是在翌日的新闻中才知道舞者名叫山村平吉,骤亡的病因是脑溢血。在这里叙述者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与看客站在同一平台上,除了眼睛看到的外在的表象和听到的传闻消息,其余我们一无所知。叙述者把我们与主人公的距离拉得很远。告知山村平吉逝世之后,叙事者开始追述他的生平。叙事者深入人物内心,将他的意识、潜意识剖析给我们看,这在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心理距离。文章中说平吉在醉酒后“瞎跳乱舞算不得什么,他还糟践鲜花,挑逗女人”[3]19,如果叙述者直接描述平吉的这些行径,我们厌恶甚至会憎恨平吉,可是叙述者在此之前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方式先给我们分析了平吉的心理。他平时为人谦恭有礼甚至有点唯唯诺诺,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而且醉后总要癫狂般地跳舞。他因嗜酒几度中风,可是始终戒不掉,因为饮酒之后他觉得自己平添了几分豪气,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再畏畏缩缩,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平吉爱撒谎,他自己也不明白好端端地为什么要说谎,可是谎言总是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他最后一次醉酒跳舞时引发脑溢血致死,临死时他只说了句“假面……把假面……拿下来”[3]21。由此可见醉酒前的平吉活得非常压抑,他一直在伪装,在带着面具生活,这不由得让人同情,然后不自觉地与平吉的立场保持一致。在此案例中,叙述者成功地控制了我们的同情心理。文章结尾当叙述者再一次回顾平吉逝世时的情形时,我们甚至会为他的死而悲伤。在整篇文章中叙述者没有直接呼吁读者的同情,而是巧妙地运用限制叙事和全知叙事,让读者由旁观转入置身其中,一点一点将情感酝酿起来,在结尾达到高潮。
一般来说非戏剧化的叙述者可以看作是隐含的作者,如采用第一人称则更给人以真实感。芥川的许多小说都取材于自己的经历,以至于他在《文友旧事》中说:“本文或许不可称之为小说。但此类体裁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我自己却不得要领。我只是尽量不拘一格,原原本本地将四五年前自己和周围的事情描述下来。”[3]447这样的小说故事性不强、通俗流畅,明显带有散文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隐含的作者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自身,如《阿吟》中的叙述者就明显不是芥川本人。《阿吟》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种非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叙述者就是作者,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叙述者的“意识形态眼光”[8]是完全维护天主教而反对佛教的,这与芥川龙之介的信仰体系差别显著。可见非戏剧化的叙述者有可能无限接近于作者,但他与作者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如果把叙述者与作者混为一谈,我们就难以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理想、想象力与作者的实际道德、人生态度区分开来”[9],就会混淆文学与人生之间的界限。
无人称叙述,会给读者造成一种没有叙述者的错觉,让人以为故事无中介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不然,叙述者不动声色地拉开画轴把一幅幅画面展示出来,我们才得以产生如亲眼所见的真实感。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可以等同于隐含的作者,学者申丹从编码和解码两个方面分析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出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特定立场来写作的作者(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断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真实作者’则需要根据传记、信件等史料来推知)。”[10]隐含作者又被称为作者的“第二自我”,以区别于真实的作者,即“第一自我”。无人称叙述要求作者完全隐退,不能直接说话,所以人物的对话就成了小说的中心。芥川的戏剧体小说《青年与死》《往生画卷》《两个小町》以及对话体小说《一篇恋爱小说》等采用的都是严格的无人称叙述。故事只呈现人物的言语、行动、神态等外部特征,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则需要读者自己去推断。因为作者完全隐藏在文本之后,所以这种叙事方式最具客观性。《往生画卷》讲述的是一个杀生成性的恶人决计要遁入佛门的故事。他听说只要信奉阿弥陀佛,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能进入西方净土,于是便抛弃妻子削发出家。他从讲法者的口中得知阿弥陀佛在西方,便大声喊着“喂,喂,阿弥陀佛”[4]86一路西行去寻找。路途中他遇到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恶魔、混蛋,甚至连年迈的法师也认为他是个疯子,不过这个“疯子”坚持认为只要自己一直呼唤阿弥陀佛的名字佛陀就能感应到。最后这个“疯子”饿死在一棵树上,他的嘴里绽放着一朵雪白的莲花。这个人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我们无法定夺,只能说他在皈依佛法之前是恶的,他的皈依功利性极强,并且他信奉佛法的方式不是潜心念经打坐,而是大喊阿弥陀佛的名字。但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死的时候口中绽放着白莲。《往生画卷》属于戏剧体小说,具有很强的舞台呈现性,文本中的人物或对话、或各说各话,我们很难从中看出作者的价值判断,也正是这种不透露任何感情色彩的写作方式赋予了文本多层阐释空间。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可能是想通过主人公口中的白莲告诉人们心中有佛就能得享极乐,但我们也只能说是“可能”,毕竟谁也没有从作者口中得到答案。恰如罗兰·巴特所言:“因为(叙事作品)说话的人不是(生活中)写作的人,而写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11],“作家不再是写什么东西的人,而是绝对写作的人”[12]。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说出芥川到底持什么态度。
三 双重叙述模式
芥川的部分小说并不是单纯的戏剧化叙事或者非戏剧化叙事,而是将二者融合起来形成双重叙事,小说《妖婆》《开化的丈夫》《秋山图》等是双重叙事的典型代表。《妖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我”为营造气氛而讲述的幽冥事件,另外一个是与小说题目“妖婆”有关的中心情节。总的来说这两部分的叙述者都是“我”,但细致分析之后便会发现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叙述者经过了巧妙的转换。第一部分开头便说“您也许不相信我讲的这个故事”[3]569,这种一、二人称面对面交谈的形式一下子就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接着“我”便有凭有据地讲述发生在日常生活里的超自然事件:冬日午后银座大街上飞舞的纸片,深夜在无人的站台停靠的末班车,炮兵工厂里逆风而飘的黑烟,空荡的国技馆里莫名的喝彩声……这些事件经“我”之口讲出颇具可信性。讲了这些奇异事件之后“我”说道“我要讲的故事并非与您熟知的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并非子虚乌有”[3]571,于是引出了《妖婆》的中心情节。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是直接讲述关于“妖婆”的故事,而是“一两年前,故事的主人公在某个夏夜与我相对而坐,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他的遭遇”[3]571,至此我们才发现虽然“我”费尽心思地证明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可故事的主角不是“我”!这一巨大转变在读者的心理造成了一个不小的波澜。“我”并没有借主人公之口向读者直接传达信息,而是间接转述了故事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文章的中心故事是靠第三人称叙述的。文中有一句话精炼地概括了叙述者的微妙变化,“他讲的,自然是我要讲给您听的妖婆的故事”[3]571。在以主人公新藏为聚焦者的有选择的第三人称叙述中,作者还时不时地让“我”介入,这样就形成了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错的双重叙述方式。双重叙事的优点是视角的转换可以增加情节的曲折感,也使叙述方式多样化。但是,双重叙事要求两个叙述者的转换之间要有自然的过渡,否则会有突兀之感,破坏文章的整体美。在《妖婆》一文中,“我”作为第二叙述人对第一叙述人叙事的介入很值得关注。在故事刚开始进行时,作者就说新藏在与同学阿泰立饮酒时不打自招地透露了心事,然后阿泰立就建议去找能掐会算的阿岛婆。为了证明阿岛婆的确神乎其神,阿泰立又详细讲了她怎样用咒符帮忙找出投水自尽的女老板的尸体。于是两人约定去拜见阿岛婆。这时“我”跳了出来,说:“我该说说新藏的心事。”[3]572“我”的出现恰好照应了前文“新藏不打自招透露出心事”这件事,这种介入就显得自然而然且浑然天成。当然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我”的介入频率在整个文本的前后不成比例。如果说把“妖婆”的故事分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四个部分,“我”只是在“开端”频繁地跳出来说话,在后三部分中却完全不见踪影,导致双重叙事有始无终。“我”在中心故事开始之前大费口舌营造气氛,却在中途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到结尾都没再出现,这难免显得有些头重脚轻。不过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作者叙述故事太入迷,以至于把叙述技巧都给遗忘了。连作者都陷入自己讲述的故事中去了,又何况读者呢?
《开化的丈夫》一文可以与《妖婆》作为比较,二者的叙事模式相同,都是分两个部分,前奏和主体。同样都是双重叙事,《开化的丈夫》中两个叙事者都是“我”,当然这两个“我”代表不同的人:隐含的作者和本多子爵。前奏部分由“我”叙述“我”和本地多子爵的相遇和交谈,在插入简洁的衔接“如果你不反对,我就讲讲那位朋友的往事吧”[3]464之后,子爵就亲自讲述了关于“开化的丈夫”的故事。在子爵讲故事的过程中,“我”有两次适时地介入。之所以说“适时”是因为子爵所讲的故事比较长,长篇大段的单人叙述会让读者劳累疲倦,而“我”的介入恰好把故事分为三部分,这既使故事层次清晰又让读者轻松愉悦,可以称为是“完美的介入”。与《妖婆》相比这篇小说的双重叙事可谓是有始有终,作者让本多子爵讲完话后不忘给全文加个结尾,这样双重叙事的“故事套故事”结构就完整无缺了,外围故事是:“我”在博物馆遇到子爵——子爵给“我”讲个故事——闭馆时间到,“我们”走出展室;中心故事是:文明开化的理想主义者三浦直记宣告结婚——三浦的妻子闹出意外传闻——三浦理想的破灭。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使文章层次清晰、张弛有度、美感十足。
芥川的很多小说都会交代故事的来历如《龙》《疑惑》等,所以文中会出现两个叙述者。如果从简洁精练的角度评价一个短篇小说的话,上述的几篇恐怕不能算为上等,作者完全可以直接叙述与中心情节紧密相关的事情,至于这个故事是从哪儿得到的也许读者并不感兴趣,作者把这些不相干的周边材料都写入小说,难免会给人以详略不分的冗杂之感,正如芥川自己所说的,他有“解说癖”[13],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小说写作技巧的创新之处。
通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会发现,一方面他注重技巧的创新,打破了小说叙事的常规,他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按照传统理论来讲不应该在文章中出现的部分,这会给读者新奇之感;另一方面,他有“破”而无“立”,芥川打破常规却没有建立自己的规则,他的小说创作几乎无章可循,日常交谈可以作为小说,幻想梦境可以作为小说,游记见闻也可以作为小说,小说的外延不断扩大,使得小说与散文、戏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过也正是这些改变和创新启迪着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思考小说与创作。芥川龙之介本人和他的作品值得我们不断探索。
[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
[2]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M].高慧勤,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4]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2[M].高慧勤,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5]尚必武.西方文论关键词:不可靠叙述[J].外国文学,2011(6):103-112.
[6]王芳.富有意味的叙述者: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解读[J].名作欣赏,2007(22):102-105.
[7]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M]//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90.
[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9.
[9]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52.
[10]申丹.自我禁锢与突围:美国修辞性叙事研究的传承与发展[J].外国文学,2011(6):84-94.
[11]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张寅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0.
[12]BARTHES R.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M].New York:Hill and Wang,1986:49.
[13]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5[M].高慧勤,等,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