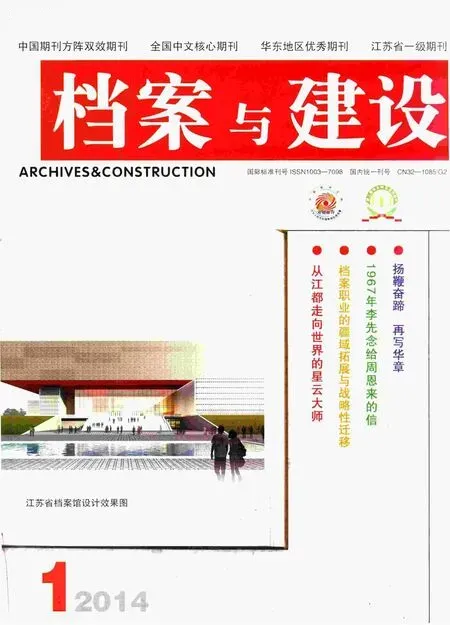风物长宜放眼量:档案职业的疆域拓展与战略性迁移
张照余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长期以来,档案职业被看成是小众化的边缘行业,默默奉献、因循守“旧”成为档案人留给公众的职业形象。国外曾用“佝偻着背、躲在小阁楼里摆弄着一堆发霉的文件”来形容旧时的档案专家。这种“静默”、“坚守”甚至颇显“保守”的品格与社会赋予档案职业“守望历史”的使命比较吻合,因而社会对档案人的奉献和低调投射的是赞许的目光。
然而,这一切却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下迅速改变。最先让档案界忐忑不安的是其职业对象的数字化。数字化无非是信息记录方式的改变,这种技术变化对于图书、情报等职业意味着更高的采集、管理和利用效率。但作为历史记录的档案文件,数字化带来的是对其证据属性和长久保管可能性的怀疑:电子文件可靠吗?数字档案能够长久保存吗?这种质疑的现实反应是司法领域对电子文件作为直接证据的排斥和档案馆在接收电子文件进馆上的犹豫不决。而在业务活动中,电子文件取代传统文件已成不可逆转的大势,面对几何级增长的电子文件,我国档案界在迟疑彷徨之后拘谨地选择了“双套制”。事实上,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十分明显,由数字资源回退纸质资源是一种极不环保的资源浪费,遑论音视频、数据库等数据信息根本无法形成纸质版本。因此,笔者以为:“双套制”充其量只是权宜之计,面对数字化冲击,档案界应该寻求更为正面、积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回避退守。
一、坚守职业使命,拓展档案概念
可喜的是,有识之士作出了行动。十多年前,档案学界首先自电子文件的特点出发反思档案概念,对构成档案证据价值的“原始性”做出新的诠释,强调:凡“内容原始”并严格执行“过程控制”和提供“背景信息”的电子文件即为“原件”。这一“大档案”概念,与基于内容而不是载体来判断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电子签名法”相呼应,为电子文件的归档保存扫除了理论障碍。
此后,学者进一步认同:记录社会活动的信息资源是多样化的,以往我们之所以选择文件而不是图书抑或文献资料归档收藏,是因为它相比其它记录材料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和代表性。随着业务环境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发展,非纸质的电子文件和非文件的各类记录信息,诸如今天大量存在的网站资源和社交媒体信息等,都可能成为我们选择进馆赖以记录社会活动来龙去脉的档案。评判我们的选择是否合理,唯一标准只能是在现有条件之下这种选择是否更有利于记录历史,而不是是否符合既定的档案定义!作为历史证据,选择电子文件等记录材料并不理想,但在无可替代或权衡利弊之后,或许就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促使其档案属性的最大化,而不是为坚持所谓的档案质量而造成证据缺失或记忆空白。
这种“大档案”观念颠覆了对我国档案职业的传统认识,意味着我国档案界开始将“保存社会记忆”作为整个职业的逻辑起点,以此来界定档案外延和档案业务范围。这种基于存史职能而拓展档案馆藏的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国外档案馆热衷于收集“口述史资料”(oral history),在缺乏直接书证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程式采集当事人的口述信息,并将这种可靠程度值得推敲的“资料“作为珍贵馆藏,为未来的史学家提供考辨史实的基础材料,避免记忆空白。这是一种基于职业使命的、积极的档案态度。同样道理,今天的档案人为避免“数字失忆”完全可以敞开怀抱欢迎电子文件的到来,而不是对之心生芥蒂。
在“大档案“观念的指引下,电子文件采集、数字资源存储均成为档案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档案职业的疆域被迅速拓展,档案信息化风生水起,电子文件真实性维护、数字档案的长期保存等难题开始成为国内外档案界协力攻关的课题,文件格式、元数据、电子签名等大量技术术语渗透档案著述,以人文见长的档案职业华丽转身,投向了IT的怀抱。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引发诸如“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之类的争议。但笔者以为,这些貌似“跨界”的探索是档案机构勇敢应对数字危机的顺势之举,是整个档案职业战略性迁移的前奏。
二、转变管理模式,突破职业疆域
在数字环境中,档案的真实有效性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件阶段的管理状态。因此,为确保数字档案的质量,档案界必须超前控制电子文件的形成、流转乃至业务系统的开发,规定文件数据的格式、标准、处理方式,并记录其处理过程和技术环境信息。文件与档案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为此,国外档案学界提出了“文件连续体理论”和“后保管模式”等理论模型,积极寻求对文件的超前控制,“档案管理与文件管理”之间的关系被再一次聚焦。这一争论了百年的命题曾经让“二战”后美英等国的档案机构合法拥有了监管文件工作的权力,美国联邦档案管理机构定名为NARA(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即见其一斑。
我国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在行政体系上分割已久,睿智的学者从电子文件管理的困境中看到了我国档案职业突破的方向和机会,积极推动行政层面上的文档管理一体化,并提出了电子文件管理的国家战略。这种探索是一种顶层设计,对档案职业而言是革命性的,如果成功,有望破解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的困局,并为国际档案界树立典范。然而,这种改革必然艰难,因为它是对整个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的变动和权力结构的调整,涉及到最终责任的交付,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循序渐进。这场由学者倡导的机构改革并没能得到档案行政机构的积极呼应,缺乏自信或许是一个主要原因。欣喜的是,档案学人的不懈努力还是赢得了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的设立、《国家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规划(2011~2015年)》的颁布和由档案专家牵头的“中国电子文件研究会”的成立,意味着我国档案职业正在逐步迈向掌控电子文件的新时代。
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大档案”观念和文档一体化思路的引领下,一些务实的档案机构已经尝试将管控的触角伸向电子文件。例如,自2004年起,江苏、安徽等地的档案局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建立起区域性的电子文件中心,基于政务网络平台采集、管理和提供利用仍处于现行期的电子文件。2009年,浙江省全面启动数字档案登记备份工作,明确规定各级档案局应当依据一定程序对本地区形成的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登记、验证,并由同级综合档案馆对经过认证的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进行数据备份。这些实践超越了传统档案工作的范围,在组织实施、资源配置、技术支持和法律依据上都会面临挑战,在操作过程中会产生各
三、调整战略方向,融入开放社会
在数字化背景下,档案人不再是相对被动的“证据守护者”,而上升为积极的“记忆构建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承载社会记忆的数字档案在技术上变得难以把握,需要档案界与文件形成者、管理者、IT技术人员紧密合作,通过设计出可靠的技术系统、业务流程和管理手段来共同维护档案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与长期可读性。这些系统与手段设计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档案证据价值的大小乃至有无。因此,当今的档案职业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社会记忆的维护成为档案职业内外共同劳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博客、微信等新型社交媒体的爆发式增长,人类进入了大众书写的时代,民众参与意识和档案意识的提升使得构筑社会记忆的信息来源空前广泛,档案职业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来得复杂和紧密。档案机构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将关注的重点局限于政府机构和官方文件,因为这种职业取向根本无法构建起完整的社会记忆。而必须积极转向社会大众,以人为本,构建“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在此过程中,档案界需要重新定位档案职业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梳理各种档案来源渠道,调整档案馆藏策略,转换档案职业方向,充分发挥档案人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与社会各方合作,全面融入现代社会,获取档案职业发展的长久动力。
古老档案职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期而遇,使许多档案从业者措手不及。由于对技术的生疏,全国年投资近百亿的档案信息化项目似乎成了“局外人”的盛宴。受到知识结构和学术惯性的影响,学界对IT技术也普遍存在排斥心理,更乐于在抽象“概念”、“模式”的搭建中自娱自乐,固步自封。这种集体性的“技术失语”严重危及到档案职业的活力和前景。为此,档案界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实施职业队伍改造,积极引入新生技术力量,吸纳融合社会人才资源,以壮士断臂之勇气调整群体知识结构,实施职业队伍的历史性迁移。
总之,眼花缭乱的信息化变局在给档案职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职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今天的社会档案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来得更为强烈、复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实施结构转型和战略迁移后的档案职业一定会涅槃重生,笑对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