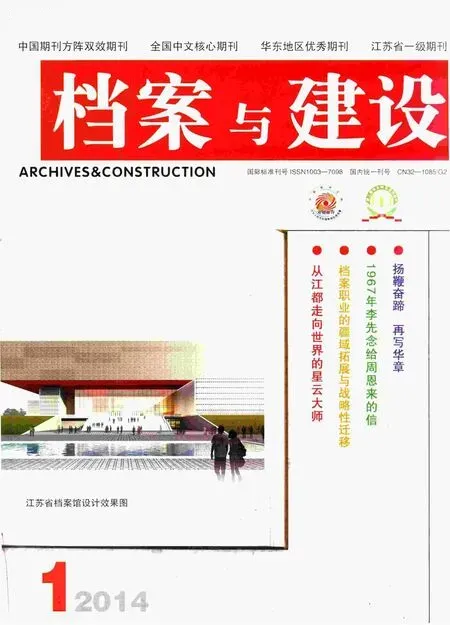1967年李先念给周恩来的信
留勤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南京,210008)
江苏省档案馆珍藏有“文革”期间李先念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笔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在信的抬头“孙岳同志并报总理”处,文件拟办人员用红笔划去了“孙岳同志并”,直接呈报周恩来。信的第一页下方空白处盖有一小方蓝色的总理值班室呈办文件章。在信的第一、二页,文件拟办人员用红笔在内容重要处划了红线,标出重点,便于周恩来审阅。信的内容如下:
孙岳同志并报总理:
最近接到苏州财贸部门好几个单位来电反映,苏州地区两派斗争激烈,市内外分别由两派控制,各自设立了业务机构。并且相互拦截、扣留车辆,运输问题无法解决。一些仓库物资调拨不动,据说,出口港澳、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商品不能履约;内销商品需要调往外地的调拨不出,或者要用其他货物交换。十月十日止,市区粮店中断供应的有44%,饮食糕点中断供应的有50%。
此事,经向南京军区了解,并请其协助解决,据说省军区、省管会给双方多次做工作,都不起作用。听说省里派五人小组在苏州,也难解决这些问题。省军区建议国务院直接找两派在京谈判的代表谈一谈,请他们分别打电话回去,也许能起作用。
为此,请总理批请江苏在京谈判代表,要求两派本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对出口物资、外调商品按国家计划,进行调拨,对粮、油、棉、煤等生活必需品,要保证运输和供应。
此致
敬礼
先念
十月十九日
根据总理值班室呈办文件章上的时间和信的落款确定,此信为李先念1967年10月19日所写。两天后的10月21日,周恩来在信上空白处用毛笔作了批示:
呈请康生、春桥两同志阅后,建议转杜平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在京同志约苏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当地驻军在京同志一谈,解决此事,如能达成协议更好。妥否,请酌。
周恩来十月廿一日
在周恩来批示“呈请康生、春桥两同志阅后”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其名字上画圈并在空白处批:“春桥同志决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在其名字上画圈。
从这两页信及批示内容来看,“文革”期间全国陷于内乱,苏州也不例外,难逃厄运。造反派派系斗争激烈,导致苏州对外出口失约,影响国家形象,粮、油、棉、煤等生活必需品断供,危及百姓生活,事态十分严重。当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近于失控,省里无法解决造反派派系之间矛盾,希望国务院出面解决。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在周恩来对这封信的批示中就有呈请文革小组的康生、张春桥一阅的批示,反映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实际控制全国局势的权力。
当时,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突起,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冲击党政机关,并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乱的一年,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中央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不顾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财政大权不能夺的指示,开始酝酿夺取财政部的权。1967年初,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李先念严厉批评财政部造反派,明确指出:“中央财权不能夺。”
在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李先念也被冠以“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可以想象,当时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是在一边头顶着黑干将的罪名接受批判,一边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忍辱负重地工作,保证财贸口正常的工作秩序。
李先念(1909~1992)出身贫寒,念过三年私塾,非常好学,历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李先念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在1976年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基本条件。他197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一批造反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各级领导权。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军队和各行各业,掀起了全面夺权风暴(即“一月革命”),全国处于空前混乱之中。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苏州的两派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发生的。这个阶段是“文革”开始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时期,整个社会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苏州的一部分造反派也夺取了苏州的党政大权,2月,建立了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苏革会)。但他们的行动很快被另一部分没有取得权利的造反派所反对,于是就形成了“支派”(支持苏革会)和“踢派”(主张踢开苏革会)。支、踢两派从摩擦到对立,都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打着革命的旗帜夺权、斗争,最后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双方动用枪械开始了武斗。1967年8月2日清晨,两派展开枪战。整个8月里,苏州城两派之间就发生了三起火并枪战,武斗分子烧毁大楼、洗劫财物、冲击监狱,造成几百户民房被烧、400多人无家可归。支、踢两派以大运河为界分守城内、城外,形成割据局面,拦截扣留对方车辆。李先念在数次接到苏州财贸部门的电话反映后,感到事态非常严重,认为此事必须国务院出面才能得到解决,于是在10月19日就苏州两派斗争严重影响物资调拨、希望国务院出面调停一事,给周恩来写了亲笔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多。“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遇到的困难常人无法想象。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巧妙地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性灾难,尽一切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减少经济损失。我们从周恩来对李先念来信的批示就可看出端倪。周恩来身为国务院总理,呈请当时权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和张春桥一阅,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一方面说明周恩来为了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得以保障,采取隐忍和巧妙的做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苏州市大事记》中对“文革”期间苏州派性斗争的记载,与此信内容相印证。该信保存良好,对研究“文革”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中央的办文程序都有价值。此信被完好地保存在江苏省档案馆,2012年入选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