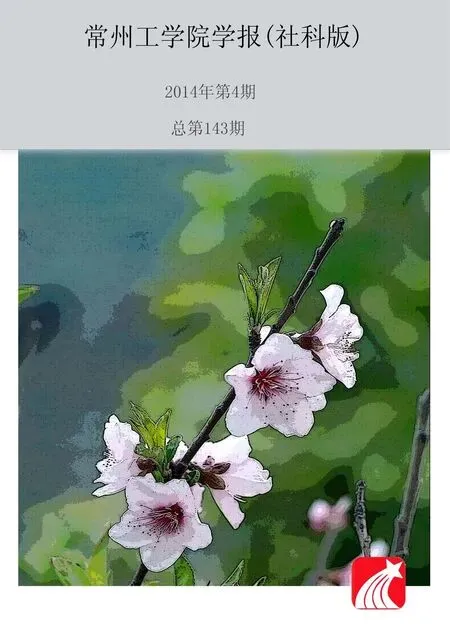浅析《男孩子与女孩子》中的女性性别意识
林亚丹
浅析《男孩子与女孩子》中的女性性别意识
林亚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男孩子与女孩子》被认为是最能代表爱丽丝·门罗写作关注点的一篇文章。文中,门罗着眼于普通女性的生命体验,细腻地描写了小女孩从性别意识萌芽到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文章拟从女性主义角度尤其是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对小女孩的性别意识的形成进行解读,并对促使女性性别意识萌芽与觉醒的自身以及社会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爱丽丝·门罗;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性别麻烦
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在英语文学界享有盛誉,被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master of the contemporary short story)。门罗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加拿大本土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门罗出生在安大略省西南的温厄姆小镇,1951年开始其创作生涯,迄今已发表百余篇短篇小说,大部分收录在其13部短篇小说集中。1968年,门罗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一经发表,便好评如潮,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随后她又两次获得同一奖项,并于2009年将英国布克国际奖收入囊中,最终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使其走上文学生涯的巅峰。
门罗的小说常带有自传性,以她自己居住的小镇作为背景,以她身边普通女性生活经历作为素材。她擅长描写少男少女的迷惘、困惑、矛盾和好奇心理,作品常以聪颖、敏感、精神生活中充满烦恼的女性为主角,以女作家特有的洞察力、女性独特的感受和视角描写生活中的冲突。“她的文字简约、不事雕琢,刻画出平淡而真实的生活面貌,给人带来真挚而深厚的情感。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甚至将芒罗称为‘当代契科夫’。”[1]109
《男孩子与女孩子》是收录于《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一篇文章,故事以“我”——一个普通小女孩——作为主角,描述了“我”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我”的爸爸是一个狐农,靠卖银狐皮为生。爸爸是一个典型的硬汉,粗犷少言,从事带有血腥与杀戮的工作,给银狐剥皮、剁马肉喂银狐是家常便饭。而妈妈则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絮絮叨叨,终日操心各种家务事,生活的范围以厨房为中心。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我”的性别意识形成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在性别萌芽初期,“我”向往独立、自主,想要从事农场工作,而后“我”意识到性别差异的存在,逐渐明白“我”作为一个女孩,和妈妈一样要干琐碎的家务事。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我”性别意识的形成进行解读,重点从性别意识的自我萌芽与觉醒和性别意识觉醒的社会因素两方面来探讨门罗想要展示的女性性别构建过程。
一、性别意识的自我萌芽与觉醒
(一)性别意识的自我萌芽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南茜·乔多罗认为“在俄狄浦斯阶段,随着小女孩的成长,她开始渴望父亲所象征的一切:作为独立、自主主体所具有的特征”[2]192。“我”在性别意识萌芽阶段的行为和心理正是对乔多罗观点的印证:“我”渴望成为英雄式的人物,“我”热衷于与父亲一起干活,“我”在感情上也更偏向于父亲。
门罗在一次访谈中称自己从小就喜欢随时编故事,《男孩子与女孩子》中的“我”也热衷于在睡觉时编故事。故事的主要思想也总是离不开“有勇气、有胆量、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366这一男性意识。其中情节往往围绕“我”救了一群人,“我”是英雄来展开,内容上充满了“我”骑马、打枪这些画面。然而,“我”连马鞍都没有,更别提打枪了。人们常常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男性与强壮、主动、积极划上等号,而把女性与柔弱、被动、消极联系在一起。“我”的这些幻想说明“我”渴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英雄式的人物,而“我”作为女性注定不可能成为幻想中的那类人。
“我”非常乐意帮爸爸干农场上的活儿,而排斥帮妈妈做家务事。“我”觉得帮妈妈削桃子、切洋葱是十分乏味的事情,一有机会“我”就从妈妈眼皮底下逃走了。农场的活儿对“我”来说却是别有洞天,“我”喜欢跟爸爸一起在农场干活。“在我看来,屋里的活儿没完没了,枯燥无味,而且使人感到一种特殊的压抑,但是到外面给爸爸干活却像是参加一个盛典,我觉得十分重要。”[3]368此时“我”的意识里尚未有社会分工这一概念,“我”不知道帮爸爸干农活只是暂时的,最终“我”将和妈妈一样,为家庭琐事忙忙碌碌穷尽一生。
“我”觉得农场是属于爸爸和自己的,进而在感情上排挤妈妈。“我觉得这里的活儿不干妈妈的事,而且我想要爸爸也这么想”[3]398,“……但是她(妈妈)也是我的敌人,她总是在打我的主意……在我看来她这样简直不可理喻……我倒没想过她可能是感到孤单或者有点嫉妒”[3]369。在“我”眼里,不经常涉足于农场的妈妈成了“我”的敌人,因为她总是伺机让“我”回归到“我”所厌恶的家务事里去,“我”在感情上是偏向于爸爸的,同时“我”也想得到爸爸情感上的认同。
处于性别萌芽初期的“我”,向往成为爸爸那样独立自主的人,渴望同爸爸一起在农场上干活,希望得到爸爸的认同。“我”萌发的是对父亲所象征的一切的一种向往,并未意识到“我”出生的性别已决定“我”不会被纳入男人的战线。
(二)性别意识的自我觉醒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露丝·伊瑞格瑞指出:“以女孩回到一个由‘阉割的母亲’代表的性别位置,作为她性别认同与获得的完成。”[2]200尽管“我”在性别萌芽初期产生了对父亲所代表性别的向往,但“我”也逐渐意识到社会存在对性别的具体界定,这进一步促使了“我”性别意识的自我觉醒。
“我原来认为女孩子就是我这样的人,女孩子就是我。而实际上是我必须成为一个‘女孩子’才行。”[3]370“我”在思想上认识到社会对女性的形体和行为有众多规范,作为“女孩子”的“我”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按着社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正如巴特克所说:“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4]66此外“我”的心理反应——“‘女孩子’是一种定义,人们提到时总要带着强调、责备和失望的口气”[3]370——表明“我”意识到社会存在对女性的偏见。
“我”行为上的改变也暗示了“我”性别意识的觉醒。“我”一直保留睡前编故事的习惯,故事的情节依然惊心动魄,内容悄然发生变化。“我”不再是从前故事里那个救人的英雄,而成了被救的对象,且每次都是被男性所救。此时“我”已然明白,英雄这个角色只可能由男性来充当,女性只能处于被救的弱势地位。故事还会具体描述“我”头发的长度,衣服的样式此类典型女性关注话题,“我”开始转向母亲所代表的女性性别认同。对于农场上的活儿,“我”已不如先前那般热爱,甚至有了厌恶之情,“然而我还是感到有点羞愧,对我爸爸和他的工作产生了一种新的警惕和疏远的感觉”[3]373。
性别意识的觉醒在“我”的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有所表现,“我”逐渐意识到“我”必须牢记自己是个女孩子,并按照已有的对女性的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我”也开始遵从母亲所代表的女性性别认同,认可亲切、细心、服从和富有奉献精神等所谓“女性特质”的存在。在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我”性别意识的自我萌芽与觉醒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一些社会因素也进一步促使了性别意识的觉醒。
二、性别意识觉醒的社会因素
《男孩子与女孩子》中,门罗用明晰而亲切的笔调描写了“我”性别意识萌芽与觉醒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仅自我意识到性别界定的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也促使了“我”性别意识的最终形成。社会的准则规范、社会关于男女的明确分工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这些因素,在“我”性别意识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认为文化礼仪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对于女性的形体和行为的规范远比对男性严格。”[2]70姥姥在“我”家住的几个星期里,时常告诫“我”“女孩子不能那样使劲关门”,“女孩子坐下时腿要并上”[3]370,甚至在“我”问些问题的时候,她会立马说,“那不是女孩子的事”[3]370。姥姥的这一行为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有具体的规范。事实上,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近乎苛刻,如对女性的面部表情都有具体规定:面部需要被驯服出顺从的表情,眼神总要往下看,目光要柔和,要时常微笑。
社会不仅约束女性的言行举止,对男女社会分工也有明确的标准。女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被限定在与育儿、养儿有关的事务上,她们适情适所的地方被规定只能是在家庭内;相对地,男性的创造力则与语言、文明、文化、意义的创生相连属。也就是说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属于家庭,男性属于社会。在文中,尽管“我”认为弟弟莱尔德不会做农场上的事情,“我”帮爸爸给狐狸喂水、耙草都做得得心应手,妈妈却对爸爸说:“等莱尔德再大一点,你就有真正的帮手了。”[3]368并且从妈妈对爸爸的抱怨——“我一转身,她就跑了。就像家里根本没有这么个女孩似的”[3]369——可以看出在妈妈的观念里,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这样的观点并不是妈妈所特有的,当爸爸向“我”介绍他新雇的卖饲料的人时,“我”因为害羞满脸通红,转过身去耙草,卖饲料的人立即说道:“我差点弄错了,我还以为是个姑娘呢。”[3]368因为“我”的羞涩让卖饲料的伙计认为“我”是个女孩,而转念一想,女孩不可能在农场上干活,才会有此番对话。长久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世世因袭。
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更是根深蒂固。“我”故意违背爸爸的意志,放走本该被宰杀的一匹母马,在爸爸和弟弟去寻找母马的过程中,“我”忐忑不安,“我”知道弟弟会告诉爸爸真相,“我”反复猜测爸爸知晓后的反应,害怕失去他的信任。当爸爸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没有严厉地责备“我”,仅仅用“她只是个女孩子”[3]283一笔带过。爸爸宽恕了“我”,“我”清楚地明白“我”和爸爸之间有一条显眼的、无法逾越的界限。法国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指出:“女人的存在只有两种情况:作为男人的‘他者’或者根本不存在。就算男人愿意对女人进行一些思考,但往往草草了事,女人最终仍是不可想和不必想的。”[2]118在男性眼里,女性似乎是愚笨的代名词,不管女性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是不足为奇且可以原谅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性与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朱迪斯·巴特勒是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她在《性别麻烦》[5]里面提出的“性别述行理论”(gender performative)影响颇深。我们可将“性别述行理论”视为一种权力话语的产物,并用其来解读《男孩子与女孩子》中“我”性别建构的过程。当“我”出生被宣布为是一个女孩子时,它就包含了以下含义:首先“我”的生理性别是女;其次,社会上有一系列关于女孩子的行为准则和标准,即“我”应如何行事、着装等,而这些理念伴随着长期的实践早已深入人心;再次,它要求“我”执行这些准则,即“我”在成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都要符合社会对性别的要求。《男孩子与女孩子》中“我”从一开始的性别意识模糊,到最后按照社会规范来完成性别建构,恰好可用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来解读[6-7]。
三、结语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大多从女性的视角,以现实主义的风格,书写了女性独特的心理历程和生命体验。她的作品中一直保持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细腻地描写了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如她们的爱情经历、性体验、成熟和衰老的经历,她们的欢欣、愉悦和痛苦、困境。正是由于门罗始终将目光投注于普通女性的生活,不断从自己身上寻找灵感,才能把女性心理的波折与隐情刻画得如此精妙准确、几近完美[8-10]。
《男孩子与女孩子》是门罗的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她用简单的措辞、简短的句式、规范的语法向我们展示了小女孩性别意识形成所经历的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在文中,门罗不仅细腻地描写了小女孩性别意识的自我萌芽与觉醒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性别意识觉醒中的社会因素,她想要颠覆对女性的传统定义,揭示社会对女性性别构建产生的深远影响。在相关领域中,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持续了半世纪之久足以看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与研究的课题。
[1]于艳平.《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3):109-112.
[2]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Jerome Beaty,JPaul Hunter,Carl E Bain.The Norto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M].London:W W Norton&Co Inc,1998.
[4]Sandra Lee Bartky.Foucault,Fem ininity,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M].Fem inism&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
[5][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6]孙婷婷.性别跨越的狂欢与困境:朱迪斯·巴特勒的述行理论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0(6):11.
[7]艾士薇.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J].南方文坛,2011(6):79-84.
[8]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9]宫萍.身份问题对艾丽丝·门罗文学创作的影响[D].长春:吉林大学,2009.
[10]尹玲夏.平淡是真:评爱丽丝·芒罗短篇小说《平坦之路》[J].外国文学,2005(2):33-36.
责任编辑:庄亚华
I106.1
A
1673-0887(2014)04-0032-03
10.3969/j.issn.1673-0887.2014.04.008
2014-02-28
林亚丹(1990—),女,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