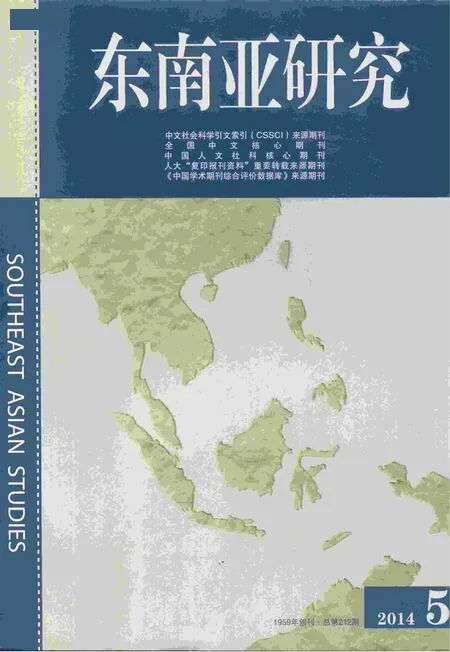依照国际法院判例论证中国南海岛屿主权:方式与问题
王子昌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510630)
本文将主要研究国外学者依照国际法院判例分析和评价南海岛屿主权争端各方证据的方式。之所以要研究这一课题,从大的方面看,是因为笔者对方法论抱持的一种信仰:即如何说一件事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大于事件内容本身的影响;从小的方面看,是尝试为论证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面对众多关于中国南海岛屿主权论证的相关文献,特别是中越双方关于南海岛屿主权的相关文献,笔者一度很困惑。在既有关于南海权益争端的研究中,各方的学者都尝试对自己和对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分析,意图做出一个公断。这些研究多是从自己的立场或自己的专业出发,各说各话,很少以国际法院对于关键证据的判定为标准,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和归类,并做出判断。由于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中国的读者虽然看到中国学者和政府列举了中国权益主张的各种各样的证据,但依然感到在法理上站不稳,特别是在看到他国的学者所列出的对中国不利的证据和分析判断之后,这一点就会更明显。面对这一困惑,笔者试想,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论说方式,可以为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提供一种坚实的法理依据,而又能避开或化解对中国不利的证据。
这一研究更大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中国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尽一份力量。笔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应仅仅体现在物质力量的提升,更应该体现在解决问题时提出更让人信服的理由,即体现在软实力的提升。从这一角度理解,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论证方式的研究,就是对更让人信服的理由的探寻。
依据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国南海岛屿主权的论证方式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传统式的,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按照年代顺序,列举中国对南海岛屿实施有效占领和管辖的各种行为,以此证明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这是当下中国政府的主要论证方式,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权威文本就是198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第1 版刊登的中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1]。二是以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丁(Greg Austin)为代表的论证方式。奥斯丁在分析南海岛屿主权争端时,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割开来,采用国际法院选择关键日期关键证据的做法,确定有关岛屿主权争端的几个关键日期,根据关键日期断定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某一时期的主权归属之后,再对所谓的各国证据的效力进行归纳和评价,得出了中国拥有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主权的最终结论①需要指出的是,格雷格·奥斯丁并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论证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依据国际法院审判国家间领土争端的案例和逻辑,对相关各方的主权依据进行分析和评价,得出中国拥有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主权的最终结论。。奥斯丁1998年就在自己的专著《中国海疆:国际法、军事力量、国家发展》中对这一论证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②Greg Austin,China's Ocean Frontier:International Law,Military For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llen Unwin Australia Pty Ltd.,1998. 本文所引述奥斯丁的观点和论述皆出自此书,除直接引用的,其他不再一一作注。。可惜的是,到现在其分析和论述也没有得到详细的介绍和足够的重视。笔者在这里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奥斯丁的研究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是因为其研究提出了某一时间段中国不具有南沙群岛主权的看法吗?为什么奥斯丁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分开?这样的论证方式对论证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更为可取吗?如果不可取,是否有其借鉴意义呢?本文的分析和叙述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本文的分析和叙述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尝试对奥斯丁的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第二部分将对比前述两种论证方式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一 仿照国际法院判例,选取关键日期,判定主权归属和证据效力
在审理国家间领土争端案件中,国际法院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即通过选择一个关键日期,来确定在某一时间段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所谓关键日期,就是这样一种日期:在此日期之前,争端各方对某一领土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通过这样一种做法,就可以简单明了地判定关键日期之前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在确定主权归属之后,国际法院再对关键日期之后各方的所谓的主权依据进行判定。根据现代国际法,如果没有主权国家的同意(这种同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许的),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合法地取得另一个国家的领土的,那么其他国家在关键日期之后的所谓的对争议领土的占领和管辖依据也就没有任何的国际法依据,在国际法上也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国际法院实行的是判例法,前面的审判对以后同样的案例具有约束力,因此依照国际法院的审判案例,分析和研究各国对南海岛屿主权的依据,对于南沙岛屿主权争端的可能的司法解决,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奥斯丁在分析南沙岛屿主权争端各方证据的过程中,仿照国际法院的判例,通过确定关键日期方式,对各方的主权主张进行分析。在西沙问题上,奥斯丁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日期:
一是1816年。依据越南提供的文献记载,直到1816年越南阮朝时,嘉隆皇帝才首次在越南所谓的西沙群岛树立了国旗,安置了主权石碑。如果以此作为关键日期,那么中国此前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是不可置疑的,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其他国家对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根据越南提供的所谓主权事件,奥斯丁认为这恰好可以证明越南所谓西沙群岛在此之前就是越南领土的其他证据是荒谬的。奥斯丁认为,虽然以1816年为关键日期,可以确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但依据越南提供的官方记载的行政管辖行为,此时期中国没有抗议越南的主权行为以及中国没有官方记载的有效的行政管辖行为,使得此后越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逐渐占了上风。
第二个关键日期是1931年。1931年12月4日,作为越南宗主国的法国第一次对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提出了抗议,即法国就当时的广东当局有意招标开发黄沙群岛鸟粪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抗议的理由是,根据1816年越南嘉隆皇帝的主权行为和1835年明命皇帝在黄沙岛建筑寺庙和石碑的行为,作为越南的宗主国,法国享有西沙群岛的主权。
奥斯丁认为,1816年之后越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逐渐占据了上风,但1909年之后中国政府的主权和管辖行为以及法国的反应使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逐渐占了上风。中国政府在1909年派军队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巡视,并派出专家对西沙群岛进行了调研。而作为越南保护国的法国不仅未对中国的主权行为提出抗议和进行阻止,而且在1921年和1929年两次对中国主权进行了承认①1929年法国驻印度支那署理总督承认:“根据多方报告,西沙群岛应认为中国之所有。”参见《外交评论》1934年4月号,第97页。。这一点对确定中国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国的承认反证了此后法国政府企图吞并西沙群岛的非法性,依据当代国际法,禁止反言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越南虽然也提出了在这一时期政府一系列的所谓的管辖行为作为自己拥有西沙群岛的依据,但依照准确的事实和国际法院对证据效力的判定规则,这些所谓的管辖行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法律效力(国际法院通过自己的审判案例表明:作为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证据,必须是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实施的明确的主权或管辖行为)。下面是越南列举的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依据及奥斯丁的判定和分析。
(1)189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向巴黎建议在黄沙群岛中的黄沙岛(Pattle)上设置一座灯塔,为过往该区域的海船导航,但因缺乏资金,此计划未能实现。在奥斯丁看来,严格说来,这根本算不上一种证据,一是建议的行为没有实施,二是即使实施,也可能不是一种主权行为,而可能仅仅是一种便于航行的管理措施。
(2)1925年,芽庄(Nha Trang)海洋学院派出德拉内桑号(DE LA·NESSAN)船在黄沙群岛进行海洋学考察。奥斯丁认为这也不能构成一种主权的依据,而可能仅仅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需要。
(3)1926年一艘法国军舰对永兴岛进行了访问。奥斯丁认为,依据国际法院审判案例,这也不能作为一种证据,因为不清楚其目的。
奥斯丁认为,相反法国这一时期的一些做法反证了法国不具有西沙群岛的主权。如20 世纪20年代初,日本一家公司向法国申请在永兴岛及其周围开发渔业和鸟粪,法军指挥官对这一申请的回应是没有证据证明印度支那海军部提交过该申请②经笔者查证,当时的法国海军司令答复说:“西沙群岛并不属于法国。”参见《外交评论》1934年4月号,第95 页。。
奥斯丁认为,根据国际法院的审判案例,如果把1931年作为一个关键日期,那么就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具有西沙群岛的主权。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那么此后法国和越南一系列的所谓主权行为和管辖行为将构成对中国西沙群岛的侵略,而中国此后的一系列行为将构成中国主权行为的延续,从而形成一系列的中国具有西沙群岛主权的完整的证据链。
在南沙问题上,奥斯丁提出的关键日期有如下几个:
第一个是1939年。奥斯丁认为,依据这一日期,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法国对南沙群岛中的主要岛礁具有主权,其中一些岛屿的主权是法国从英国手中取得的。1877年英国吞并了南威岛(Spratly Island)和安波沙洲(Amboyna Cay),并将其出租给一家北婆罗洲的公司开采鸟粪。1899年当合约租期到期以后,英国又向该公司颁发了新一期的租约证,这构成了英国拥有南沙岛屿的主权依据。1930年4月,三艘法国军舰登陆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并正式声明占领。1933年7月26日,法国在官方公报上宣布吞并南沙群岛中的6 个岛屿。1933年12月21日,印度支那总督在一个法令中重申了这一吞并,不同的是,总督令中列出的是7 个岛屿而不是6 个。这7 个岛屿是南威岛、安波沙洲、太平岛(Itu Aba)、南岛(Loaita/South Island)、中业岛(Thitu)、北子岛(Northeast Cay)、南子岛(Southwest Cay)。在宣布吞并之后,法国在主要岛屿上驻扎了一些军事人员。由于英国没有抗议法国的行为,奥斯丁认为,英国通过自己的不作为,已经放弃了对所占南沙岛屿的主权,承认了法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1939年,日本占领了南威岛,并将其置于台湾总督的管辖之下,法国对此进行了抗议,显示其企图继续占有南沙岛屿主权。奥斯丁认为,根据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确认法国对南沙岛屿的主权。
奥斯丁认为,从中国提供的大量有关航路、岛屿名称及其位置的文字记载和地图,虽然可以初步确定中国对南沙岛屿的主权,但依据中国政府对英国和法国的吞并行为的消极反应,对他国一些私人机构开发岛屿资源的不作为(根据他掌握的资料,从1917年开始,日本就开始在一些南沙岛屿上开发鸟粪,而中国似乎没有抗议)以及一些当时专家提交的有关中国南部边界的调研报告和当时出版的有关中国南部边界的地图,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已经放弃对南沙岛屿的主权。
奥斯丁认为,虽然中国对1933年法国的吞并行为作出了抗议,一是8月4日中国外交部对法国政府的知照“中国保留对所说被占领土的权利”,二是1935年官方出版了包含南沙岛屿详细名称的地图,但相对于法国的占领行为而言,其法律效力是比较弱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从效力上看,法国对南沙部分岛屿的主权证据更有力些。按此推理,在日本投降之后,南沙群岛应该属法国所有,但法国并没有依此提出主权要求,这成为以后法国放弃南沙岛屿主权的一个有力证据。
第二个关键日期是1971年。奥斯丁认为,从1946 至1971年,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可以说是绝对的(exclusive),因为在这一时间段,对南沙岛屿提出主权的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对中国的南沙群岛主权提出挑战。直到1971年,菲律宾占领了南沙群岛中的三个岛屿,才对中国的南沙群岛主权开始提出挑战。奥斯丁认为,在从1946年到1971年的时间内中国对南沙群岛实施了有效占领,而其他国家对此予以了默认,这构成了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有力证据。
首先看中国有效占领的相关证据,这种证据包括中国自己的驻军和占领以及对他方觊觎的抗议。
1946年中华民国宣称对整个南沙群岛具有主权,并在主要岛屿太平岛驻军直到1950年。
1956年7月,“中华民国 ”外交部 对菲律宾人托马斯·克洛玛(Thomas Cloma)侵占南沙部分岛屿提出抗议。
1956年6月至9月后,“中华民国”三次派海军对南沙岛屿进行巡逻,重申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同时作为对克洛玛侵占的抗议。
1956年“中华民国”军队拦截了一艘闯入该海域的菲律宾船只,对该船船长进行了质询,没收了该船只携带的武器。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领海声明,特别指出南沙群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自此以后,中国对南越的每一次主权声称行为都予以抗议。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沙、中沙和南沙行政管理机构,对南沙、西沙和中沙群岛进行行政管辖。
1963年10月, “中华民国”派侦查和补给部队到太平岛,并在其他几个岛屿树立界标。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占领和管辖行为构成了中国占有南沙岛屿主权的有力证据。
其次,相反南越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对西沙群岛提出了主权要求,但其不仅在时间上落后于中国,而且也没有实际的占领。
南越第一次正式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是在1951年。1956年的某一天,南越在其中的一个岛屿树旗以示主权,并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在南沙群岛中的6 个岛屿建立主权标志,1973年修订了其国内岛屿管辖的条例,但直到1973年,南越都没有实际占领其中任何一个岛屿。因此奥斯丁认为,无论从时间上看(南越晚于中国),还是从其他具体的管辖行为看,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依据都要强于南越。
再次,对于上述这些有限的证据,当今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能引用。因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官方在20 世纪50年代就对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予以了公开的承认,这种承认一直持续到1975年。根据国际法禁止反言的原则,越南不能引用南越这一时期的证据证明自己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总之,奥斯丁认为,从1946年到1971年这一时间段的相关证据表明,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依据以上的分析和结论,奥斯丁认为,1971年以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对南沙岛礁的占领就是恶意侵占(adverse possession),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也许一些人可能担心,这种恶意侵占以后是否会构成国际法所认可的有效占领和管辖?奥斯丁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会削弱中国的主权。
以上是把南沙群岛当做一个整体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把南沙群岛分割开来,结论又会如何呢?奥斯丁认为这要取决于这些岛屿被占领时的具体情况,即这些岛屿是否是无主地(terra nullius)。
如果将南沙群岛分割开来,奥斯丁认为,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但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依据1946年以后中国政府的占领和管辖行为,中国对太平岛及一些主要岛礁(包括鸿庥岛、安波沙洲、中业岛、双子礁)的主权依据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依据都要强。其次,即使可以确定中国对一些岛屿的主权,但一些礁石可能距离这些岛屿太远,不在岛屿的领海范围之内,且又没有人居住,那么一些国家确实可以以此为借口主张其为无主地①依据现行的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岛和礁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岛可以有领海,礁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其归属往要取决于其所在水域的位置。依据国际法院的判例,如果一个礁是在一个国家的12 领海之内,那么该礁将属于该主权国,否则它不属于任何国家。而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中,特别是南沙群岛中,一些岛和礁的距离比较远,按照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即使可以确定一个国家对岛屿拥有主权,也无法判定礁的主权归属问题。而菲律宾侵占部分南沙岛礁的一个法理就是,这些岛礁由于距离较远,根本就不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即使可以确定中国对南沙岛屿的主权,也不会影响其吞并一些礁的合理性。与此相关,因为一些礁石或暗沙只有在低潮时才露出水面,而高潮时被水淹没,没人能在此生活和居住,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效行政管辖的问题。依据当代国际法院的判例,依据海洋法公约,在礁石和暗沙的主权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对礁石的实际有效的管辖将构成主权的主要依据。由于礁石和暗沙没有人类居住,实际有效管辖也往往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判定一个国家对不在岛屿领海主权范围内的礁石归属问题就没有了法律依据。。如果是这样,奥斯丁认为,那将迫使国际法院根据实际的占领和管辖情况对每一个岛礁的主权进行判定。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笔者认为,这对中国的主权主张可能是非常不利的。
从以上对奥斯丁分析方式的介绍可以看出,与既有的中国政府的论证方式相比,从法律的角度看,其论证方式体现出更强的法律专业思维。笔者认为,两种论证方式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对待证据材料的方式不同。奥斯丁的分析论证方式,不是平等地看待争端各方按照日期列举的所谓各种证据,也不是逐一批驳对方提出的所谓的主权行为,而是通过选取关键日期,如南沙群岛争端中的1971年,来分别对待关键日期后争端各方所列举的证据。在南沙群岛争端中,因为按照证据已经可以确定1971年之前中国对南沙岛屿的主权,那么此日期之后,中国对南沙岛屿的管辖行为就可以看作是中国主权行为的延续,而其他国家对南沙岛屿的占领和管辖行为就被看作是恶意侵占,不被赋予法律效力,因此也就不值一驳。
二 两种论证方式的对比及各自的优缺点
为什么要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论证分开来?奥斯丁并没有对此明确说明。按照笔者的理解,这是依据国际法院判例进行分析的逻辑要求使然。
也许在奥斯丁看来,在判定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如果将二者混在一起,依照国际法院选择关键日期的做法,将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关键日期,明确某国对整个南海岛屿的主权,因此必须将二者分开。笔者认为,按照国际法院的判例,奥斯丁的分析是思路最为清晰、说理最为透彻和公允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10 多年来其分析没有得到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中国学者依然按照过去的思路进行论证?
是因为奥斯丁的分析得出了对中国不利的结论吗?笔者认为显然不是,奥斯丁的结论明显是有利于中国的。奥斯丁认为,在西沙问题上,“证据效力对比表明: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依据强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2]
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奥斯丁认为,“从最不利的角度讲,中国在整个南沙群岛方面的立法和行政行为,如1958年的领海声明,以及随后的对其他国家入侵的抗议,绘制清楚表明中国主权范围的各种地图,都不得不让人得出一个相对容易接受的解释:中国对整个南沙群岛的主权至少和其他国家打个平手。”[3]
从以上的引证来看,中国的学者不愿意接受奥斯丁的分析方式,显然不在于他最后的结论。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愿意触及奥斯丁的分析和论证,是因为他在分析中提出两个中国学者不能接受的分结论:从1816年至1909年,基本可以确认越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1939年之前,基本可以确认法国对南沙群岛具有主权。虽然这不会危及到中国对西沙和南沙岛屿具有主权的最终结论,但这是中国政府和学者不能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主张,中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进行了不间断的管辖,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一直拥有主权,中国从未放弃过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如果中国要坚持这一主张,中国学者坚持自己的分析和论证方式,就需要在某些问题上进一步论证,就需要对某些不利证据进行反驳。
依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中国要坚持自己传统的论证方式,依然要面临以下几个对自己非常不利的证据:(1)中国对英国1877年吞并中国部分南沙岛屿和对南沙岛屿行政管辖的不作为; (2)20 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的一些文件和一些专家学者的报告对南沙群岛主权表达的含糊。
需要指出的是,奥斯丁的分析结论是在假定中越双方提供的依据真实和准确的条件下作出的,他并没有对越南对所谓的黄沙就是中国的西沙进行分析和判别。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南海问题研究专家韩振华先生对越南官方记载中的黄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越南的黄沙根本就不是中国的西沙[4]。傅崐成教授也对清朝政府对南海的一系列管辖行为作了系统的梳理[5]。笔者认为,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推翻奥斯丁的分析框架和论证方式,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论证方式中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主权论证的效果。
笔者认为,奥斯丁的分析方式,可以作为我们继续论证中国西沙和南沙岛屿主权的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式。一是它可以化解对我们自己不利的一些证据。依据这种论证方式,虽然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论证面临一些不利的证据,但依然可以得出中国具有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强有力的结论。二是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即使今后我们有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其某些阶段性的分析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一框架和论证方式。三是它符合国际法院审判国家间领土争端的惯例,其话语方式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可以为我们的主权论证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支持: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不再是一种自说自话,而是按照国际法院的判例分析和推理得出的一种强有力的结论。四是它指出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根据这种论证方式,如果1931年就已经明确了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那么此后越南所谓的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就不值一驳,根本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相应的,中国关于西沙群岛的论证研究重点就应该放在1931年以前对西沙的有效管辖方面的相关资料的梳理上。按照这种论证方式,如果1971年之前就已经明确了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那么1971年之后其他国家对南沙岛礁的占领就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相应的中国关于南沙群岛主权的论证重点就应该放在1971年之前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水域进行有效管辖的相关资料的梳理上。
虽然有以上种种的长处,但笔者依然预言:依照国际法院判例的分析论证方式,虽然看上去简洁明了,给中国拥有南海岛屿主权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支撑,但传统的论证方式还会占据主导。为何?除了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和历史情感的原因之外,笔者在这里愿意以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类比给出一个心理学的理由,并结束本文的分析:两种论证方式就如同中国学校考试时学生的答卷与老师的参考答案。老师判卷只看要点,没有要点,答再多也不会给高分。学生不知道标准答案,因此在答卷时把自己知道的相关的所有知识都列举上去,自认为即使答不对,也不会得负分,甚至可能赚取一些同情分;而答多点,老师判卷时给点同情分也有依据。在标准答案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答案是标准的,完全正确的,因此答多点总是一种占优的策略。
【注 释】
[1]参见斯雄:《南沙探秘》,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52 -61 页。
[2] Greg Austin,China's Ocean Frontier:International Law,Military For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llen Unwin Australia Pty Ltd.,1998,p.130.
[3] Greg Austin,China's Ocean Frontier:International Law,Military For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llen Unwin Australia Pty Ltd.,1998,p.161.
[4]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4 -180 页。
[5]傅崐成:《我国南海历史性水域法律地位之研究》,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3年,第57-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