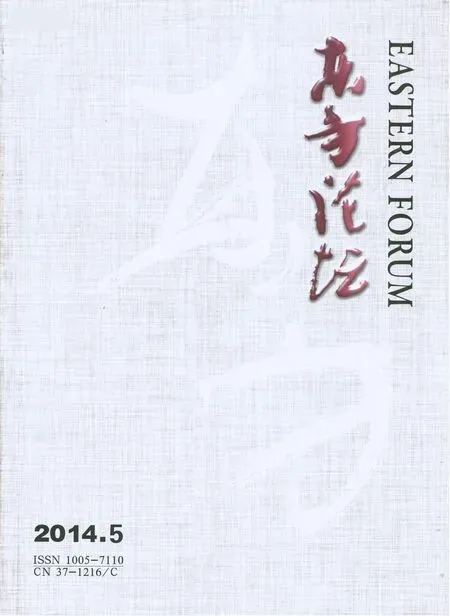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林榕杰
(太原理工大学 政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魏晋之际是曹魏向西晋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司马氏专权的时期,又是曹魏统治的最后时期。在此政治大变动的时期,当时的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这里所说的士人,包括在当时政治界或思想界有影响的人物,比如正始名士中的钟会、裴秀,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等等。我还会把当时的隐士作为一种特殊的士人来介绍其特殊的政治抉择。
魏晋之际的士人,固然有以权术而著称的,比如起兵反司马氏的钟会;也有些则是看不出有何权术的,比如被杀的嵇康。然而,象嵇康这种人是有风骨的。
一
魏晋之际名士裴秀的出仕,是在曹魏正始年间,当时毌丘俭(他后来起兵反司马氏)把他推荐给秉政的大将军曹爽。曹爽属于曹魏宗室,才能平庸但却在幼帝曹芳即位后执掌朝政——先是与司马懿一起秉政,而后又排除司马懿独揽大权。
曹爽起初任用裴秀为掾,又让他继承其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后来裴秀迁官黄门侍郎。在曹魏时期黄门侍郎一职较为重要,并有较光明的政治前途。当时就连王弼这样的人在吏部尚书何晏的力荐下还是不能充任黄门侍郎。裴秀能任黄门侍郎肯定是得到曹爽同意的,而这说明曹爽对他较为赏识。这年他35 岁,可以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有远大前程的。
曹爽、何晏等人在正始十年(249)的洛阳政变中被司马懿杀害,而裴秀作为曹爽的故吏则被免职。这可以说是他仕途上的一次挫折。但到后来,相继掌握朝中大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改变了用人策略,重新启用曹爽、何晏曾经任用过的那些青年才俊,裴秀也在其中。从此以后他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作过司马昭的属官(安东将军及卫将军司马)、卫国相、散骑常侍等等。[1](卷三五,《裴秀传》)
司马氏专权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淮南三叛”,王凌、毌丘俭与诸葛诞先后在淮南起兵或谋划起兵反司马氏。诸葛诞举事淮南是在甘露二年(也就是257年,距离魏国灭亡只有8年),那时裴秀与钟会等人都跟随司马昭前往镇压。魏师凯旋后,裴秀到尚书台任尚书。以后他又任尚书仆射,这是尚书台的副职,仅次于尚书令。后来他又任尚书令,而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魏前后的事了。[1](卷三五,《裴秀传》)
在魏晋禅代之际,裴秀是以追随权臣而得以步步高升的。他在显达后是否还曾回忆起在他走上仕途之初提拔过他的曹爽、何晏呢?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做任何事阻止司马氏篡权,没有在其父亲裴潜(他在魏国曾任荆州刺史、河南尹、大司农、尚书令等要职)效忠的、他自己也曾效忠的曹魏灭亡前出力拯救。
在当时还有大臣不但没有出力拯救曹魏,而且指使他人杀了魏帝,这就是贾充。在曹爽秉政的正始年间,他与裴秀等人一样,曾任黄门侍郎。曹爽被杀后,他很快转投司马氏阵营,先是任司马师的属官,后来又追随司马昭。魏帝曹髦说过这样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2](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后来这位年轻的皇帝对擅权的司马昭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亲率僮仆数百人向这位权臣进攻。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虽率众多兵将而不敢迎战,但当时任中护军的贾充则指使太子舍人成济杀了曹髦,做了司马伷所不敢做或不忍做的事。
据史书记载,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贾充与成济二人有这样的对话:
成济问:“事急矣。若之何?”
贾充答:“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
成济说:“然。”[2](卷四《三少帝纪》注引干宝《晋纪》)
由此可见,对魏帝之死来说,成济固然是直接凶手,但贾充应承担的罪责不比成济小。此后贾充就更死心塌地为司马氏效劳,因为他知道忠于曹魏的那些人不会原谅他。后来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后,他作为元老重臣,历任车骑将军、司空、太尉等显职,死后还被追赠太宰。[1](卷四〇《贾充传》)
贾充跟现在的官员们不一样,史书记载他在“年衰疾剧”之时“恒忧己谥传”[1](卷四〇《贾充传附贾模传》),也就是他还担心自己的身后名。他最担心的应该就是魏帝遇害与他有关,在古代这属于“大逆不道”,必为后世著史者所贬斥。
贾充的所作所为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人们为当权者服务的时候,能否作恶以及作恶是否应有底线?亲手杀死皇帝的成济后来被司马昭除掉以推卸责任,而贾充却被司马昭保护下来。最后贾充虽得到善终,但《晋书》中称他“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可谓无德而禄,殃将及矣”。他生前曾先后任尚书仆射与尚书令等要职,死后“配飨庙庭”,可谓以禄、寿而终,但灾祸会降临到其后代的身上。他的两个儿子年幼就夭折了,两个女儿以后也被杀,包括历史上有名的以淫乱著称的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她与太医令等多人有染。[1](卷三一《惠贾皇后传》)
《论语·先进》中季子然与孔子有这样的对话: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
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孔子认为他的这两位弟子仲由(字子路)与冉求算不上“大臣”,只能称为“具臣”,因为他们不能做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过,就是象他们这样的“具臣”,也不是绝对唯令是从的,让他们做弑父、弑君这样的大恶事,他们还是会拒绝的。而贾充这样的人,连“具臣”都算不上,应当归为“奸臣”或者“逆臣”,后来正史《晋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
裴秀是以“儒学洽闻”而著称的,但他实际上没有完全遵守儒家的道德准则,包括“臣事君以忠”“见利思义”等。然而,他也未象贾充那样做出弑君之类的大恶事来。裴秀在当时可说是跟随司马氏而不断加官进爵者,在这点上他与贾充相近。
二
那一时期在司马氏手下为官的人中,阮籍属于与裴秀、贾充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所谓竹林七贤,包括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还有他共七位在竹林中集会的人。他们相互交好,共为“竹林之游”。
史载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他好读书,也好出游。有时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有时又登临山水,多日忘归。他博览群籍,尤其好读《庄子》《老子》。他嗜好饮酒能长啸,又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也能终日不说话。《晋书》记述他曾随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由此还可见他属于个性很强的人,且不会巴结当权者。
曹爽在正始年间辅政的时候,曾召阮籍为参军。阮籍与贾充、裴秀等人不同,借口生病推辞了,隐于乡间。一年多后曹爽被杀,当时的人服阮籍有远见。司马懿发动政变后以太傅掌重权,他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去世后,阮籍又为其子司马师的大司马从事中郎。曹髦即帝位后,以他为散骑常侍,可见他也是这位年轻皇帝拉拢的对象。
《晋书·阮籍传》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对我们理解阮籍的一生有重要启示意义:“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可见他原来有大志,但是处在魏晋之际政治变动的年代,名士还是面临不少危险的,除非象裴秀那样“与时俱进”。阮籍也就不再积极参与世事,而是将其志向淹没于酒中了。
司马昭曾为其子司马炎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连醉六十日,司马昭始终找不到提亲的机会,于是放弃了。后来钟会多次“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1](卷四九《阮籍传》),但阮籍都以酣醉而免难。他听说步兵校尉营中厨人善酿酒,且贮酒三百斛,于是他求为步兵校尉。这与他好酒是一致的,他也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因为好酒而想做步兵校尉这样的官。他或以为任此职可能使其嗜酒稍会为其他官员理解些。
阮籍不可能持续沉醉,他也必然会有酒醒(或近乎酒醒)的时候。这时,谨慎的他在重大事情上会表现出与现实妥协的态度。《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魏帝封司马昭为公爵,备礼九锡,司马昭装作极力推辞而不接受。公卿将校们当然会知道“司马昭之心”,于是要到其府中敦促劝说他接受。司空郑冲自己不写,却派人到阮籍处求“劝进”之文。阮籍当时在袁准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
尽管有这样的举动,总括其一生来看,阮籍是不失风骨的。这种风骨尤其表现在他对礼俗之士的态度上,此类礼俗之士多是当时的官员,因此他这样做会得罪不少人,包括有权势者。据史书记载,阮籍母亲去世后,他对来吊丧的客人能为“青白眼”——见到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比如在官员嵇喜来吊丧时,他就作白眼,嵇喜不高兴地离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后,带着酒与琴来拜访他。阮籍大悦,于是露出青眼。[1](卷四九《阮籍传》)正因为他的这类行为,礼法之士对他疾之若仇,然而他本人对此并不会在意。
对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而言,究竟该如何对待阮籍这种不遵循礼教的人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司马昭还是决定对没有站到敌对阵营的阮籍予以容忍,而未对后者加以惩罚,包括将其免职等。对阮籍来说,尽管他没有也无法选择公开退出司马氏政治集团,但是他实际上对司马氏抱着不合作的态度。这应该是因为他对司马氏的专权并不认同。
上文已经谈及三种在禅代之际仍出仕的人物。其中的阮籍属于隐于朝中或醉于朝中者,裴秀属于“与时俱进”、步步高升者,贾充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为虎傅翼”的一面。由此可见,同样在朝中当官,三人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政治表现差别较大。无论是裴秀还是贾充,对魏国来说都不能称为忠臣。他们实际效忠的是有“不臣之心”的权臣。贾充指使成济杀害魏帝,表明他不仅无忠君之心,反而将君主视为敌人。至于阮籍,既难以说他忠于曹魏,又无法说他忠于司马氏,或可说他忠于自己的信念与原则。
三
阮籍属于似仕实隐或隐于朝中者,而当时也有人隐于山间——后者更符合通常意义上的“隐士”概念。下面我们看看当时不愿与司马氏合作而避居山野的士人。这里我们主要提到有明显差别的两人:嵇康与孙登。
嵇康是谯国人,与曹操可说是同乡。他的兄长嵇喜,历官江夏太守、徐州刺史、太仆、宗正等,在地方、在朝中都曾任职。嵇喜、嵇康兄弟二人在性格、待人处事上都是有很大差别的,两人的结局也不一样。
嵇康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关于他年少时的材料很少,不过在他写给旧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这样的话:“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3](卷四三)嵇康小时丧父,而他的母亲、兄长对其不大管教,这就养成了他放纵、任性的一面。嵇康也清楚自己性格中有傲散与懒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与走上仕途是不相适应的。但嵇康的性格中还有其他方面。据王戎说,他与嵇康在山阳交往二十年,未曾看见其“喜愠之色”。[1](卷四九《嵇康传》)可见嵇康的自制力是很强的。
他与曹魏公主结婚,并曾先后官拜郎中、中散大夫[1](卷四九《嵇康传》),这些都不算高官显职。这种婚姻表明他其实难以完全脱离政治。他的妻子是长乐公主。关于长乐公主,目前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她是沛王曹林的孙女,一说她是曹林的女儿。曹林为曹操杜夫人所生,曹魏末年他还在世。[2](卷二〇《沛穆王林传》)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司马懿父子在洛阳发动政变后,竹林七贤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各奔前程。司马懿在政变后不久就辟阮籍为僚属,而山涛在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主动拜见司马师以求仕。但是,嵇康却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不过,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政治,毕竟他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这样,嵇康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在求隐,另一方面他又未能象真正的隐士那样完全摆脱政治。
嵇康在求隐期间曾从事“采药”“服食”等活动。他的《游仙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这反映了他在山中有采药等活动。他还曾与向秀一起锻铁。《文士传》中提到嵇康“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可见他锻铁并不是为了钱,而这可以说是他隐居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司马氏控制魏国朝政的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毌丘俭在淮南举事,这次举事后来被司马师率军镇压。有史料记载嵇康与此次毌丘俭起兵反司马氏有“牵连”:“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2](卷二一《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这则史料未必很可信,不过嵇康与反司马氏势力应有一定的联系,而这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嵇康之死,《晋书·嵇康传》记载钟会对司马昭说了这样的话:“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他又称嵇康曾经想帮助毌丘俭,但因山涛劝阻而未实现。他还说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于是,司马昭在钟会的劝说下就杀了嵇康。
正史中的记载把嵇康被杀的主要责任归到钟会身上,这是片面的。嵇康固然得罪了钟会,但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司马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他提倡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家知道,儒家是肯定商汤、周武王革命的,而当时的司马昭也有改朝换代之心。嵇康的“非汤武”则有反对改朝换代之意,这肯定为司马昭所不喜。他与毌丘俭起事有关,也明显犯司马昭的忌讳——不过按理说司马昭不会仅从钟会那得知此事,因为山涛本人就是他的亲戚。嵇康被杀还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在山涛向司马昭举荐他到吏部任职的时候他明确去信拒绝了。吏部在当时负责官员的选拔等工作,权力相当大。嵇康的拒绝,清楚地表明他不愿与司马氏建立任何政治关系。
嵇康看似做出了疏离政治尤其是洛阳朝中政治的选择,但他其实并未彻底远离政治。作为娶了曹魏公主的人,他也很难真正地摆脱政治。最终,他仍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在司马昭看来,他并不是真正的隐士,而是扮作隐士的政治反对派。
嵇康难以被视为真正的隐士,魏晋之际真正的隐士应以孙登为代表。据《晋书·隐逸传》记载:孙登是司州汲郡人,住在郡北山上的土窟中,生活非常简单,“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他好读《周易》,也好抚琴弹奏。他不会发怒,曾经有人故意将他扔到水中,想看其发怒的样子,但他出来后却大笑。别人给他衣食,他都不接受。真正的隐士必须要能耐清贫,并且与世无争。
司马昭后来也听说了他,于是派阮籍见他。可见孙登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名气的,对这种人司马昭未必完全放心。阮籍见到他后,与他说话,他却不回答。嵇康曾经跟随孙登游历三年。临别时,孙登对他说:“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1](卷九四《隐逸传》)孙登明确地警告嵇康他不会为世所容,其原因在于他“才多识寡”。看来人要想自我保全,“识”比“才”更重要,宁可“识多才寡”,也不要“才多识寡”。这位隐士孙登之“识”应是优于嵇康的,他能“识其真”并“保其真”。后来他不知所终,不过可以肯定他免于为司马氏所杀。
上面我们提到了两类隐士:孙登是真正的隐士,因此他在魏晋禅代之际使自己免于遭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杀戮。而嵇康则不能算是纯粹的隐士,他与政治还暗中保留着一些联系,最后未能躲过司马氏的屠刀。
四
在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期,也有士人采取了“走为上”也就是投奔他国的做法,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夏侯霸。夏侯霸算是曹魏宗室,他的父亲是在与刘备部将黄忠交战中被杀的夏侯渊。他得知父亲被刘备部下杀害后,很想复仇。为此他曾参与魏国伐蜀之役,并与蜀汉军队交战过。后来他任右将军、征蜀护军[2](卷九《夏侯渊传》注引《魏略》),驻在曹魏西线的雍、凉,统属于曹爽的姑表兄弟征西将军夏侯玄。司马懿杀曹爽后,将手握重兵的夏侯玄召回洛阳,又将雍州刺史郭淮升为征西将军。夏侯霸对曹爽被杀、夏侯玄被召回洛阳感到不安,尤其对他要成为郭淮这个过去政治对手的属下感到难以忍受,因此最终下定决心投奔蜀汉,也就是投奔这个他原来视为仇敌的政权。
然而投奔蜀汉之路并不平坦,他选择的是从阴平南下,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他行进于无人的山谷间,后来粮食吃尽,不得已杀掉所骑的马。这样他只能步行了,但是后来脚又破了。他躺在岩石下,让人向蜀汉方面求救。后来蜀汉方面派人来接他,又将他送到成都。
后主刘禅亲自接见了他,并特地向他解释说:他的父亲夏侯渊不是被刘备亲手杀死的,而是在两军交战时于阵中遇害的。[2](卷九《夏侯渊传》注引《魏略》)张飞的妻子与夏侯渊有亲戚关系,而她的女儿则嫁给了刘禅。这样,夏侯霸也就与蜀汉皇室有亲戚关系了。刘禅的解释或使得夏侯霸能更安心地在蜀汉任职。
夏侯霸这种人算是曹魏宗室,在魏国期间就官居要职。对于蜀汉来说,他显然具有重要的“统战”价值。刘禅对夏侯霸是“厚加爵宠”。[2](卷九《夏侯渊传》注引《魏略》)夏侯霸在蜀汉就任车骑将军这一显职,还曾与姜维等率军向魏国进攻,并在洮西一役中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2](卷四四《姜维传》)这次夏侯霸参与北伐,是在魏正元二年(255),而被召回洛阳的夏侯玄在此前一年就因为牵连进中书令李丰反司马师的政变图谋中被杀。[2](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还要指出的是,夏侯霸参与发动的此役距离司马氏篡魏不过只有十年时间。
在当时的曹魏士人中,夏侯霸的选择是比较特殊的,多数人都不愿或难以找到机会走这条路。比如夏侯玄就宁愿回洛阳去而不愿投奔蜀汉,他的理由是他不想在敌国苟且偷生。然而,他在洛阳过的日子可说是如履薄冰,远远不如夏侯霸在成都日子过得好。夏侯霸奔蜀后,他留在魏国的亲族并未被司马氏诛杀。而夏侯玄回到洛阳后,最终为司马师所害,并被株连三族。看来夏侯霸奔蜀既保住了自己,又保住了亲族。
就“走”来说,有“走而仕”“走而隐”两种情况。夏侯霸属于“走而仕”者。
五
在魏晋之际的士人中,还有人最终选择以实际行动反对司马氏——或是计划在首都发动政变,或是决意在其它地方起事:前者以李丰为代表,后者以钟会为代表。
李丰为曹魏太仆李恢之子。他年轻时就好结交英俊,并以才智显于天下。[2](卷一六《杜畿传》注引《傅子》)在正始之初,曹爽、司马懿一同秉政,但后来司马懿因被排挤而告病。这时的李丰并未看风使舵,完全倒向曹爽一边,史载他“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2](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当时他任尚书仆射这一要职,但却常常称疾。尚书台那时有规定,生病达到百日就要解职,而他就称病数十日然后回去上班,其后再称疾。他的经常称疾说明他在政治上处于观望之中。
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懿去世后,李丰担任中书令这一要职。按魏国官制,中书令掌机密,并参与朝政决策。虽然李丰过去为大将军司马师所亲待,但因为他儿子娶了曹魏公主,加上他内心又支持时任太常的夏侯玄,于是就与皇后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合谋欲让夏侯玄辅政——夏侯玄是当时曹魏宗室中较为突出的人物。嘉平六年(254)二月,魏国皇帝要拜贵人,李丰等计划趁司马师入宫的时候用伏兵杀掉他。但是,司马师事先已听到一些风声,于是派人劫持李丰到其府中,并将其杀害。[2](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世语》《魏氏春秋》)政变图谋也由此失败。
李丰受到曹魏与司马氏两方面的重视,本可以左右逢源、保其禄位而已。但他却选择走上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那就是反对当时大权独揽的司马师,支持已被打入“政治角落”的夏侯玄。他为他的政治选择付出了代价,但他的这种政治选择说明他不是唯利是图者,也不是明哲保身者,而是有政治立场、政治抱负者。
另一位走上反司马氏道路的人是钟会,这是大家较为熟悉但也有较多误解的人物。他不是从首都洛阳发动政变,而是从新占据的益州起兵。
钟会走上仕途与裴秀等人一样是在正始年间,并且最初也受到曹爽、何晏的提拔。在司马懿发动政变并杀曹爽等人后,钟会也被免职。到司马师执政时,钟会又得到任用。司马师率兵平定毌丘俭举事以及后来司马昭统军镇压诸葛诞起事时,钟会都曾随军出征,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尤其在平定诸葛诞一役中,钟会的计谋受到了司马昭的赏识,史载“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2](卷二八《钟会传》)可见他在当时被称为汉高祖谋士张良一类的人物。
但是,后来他又走上了反司马氏的道路,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司马昭身边不乏不信任钟会者,这些人的看法对司马昭不可能毫无影响。例如司马昭夫人王元姬就多次对他说:“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1](卷三一《文明王皇后传》)后来贾充也曾以特定方式对司马昭表示过对钟会的怀疑。还有其他一些史实也说明当时司马昭周围对钟会的猜疑、戒惧不会很少。而对这些猜疑、戒惧,钟会本人未必毫无觉察,如有觉察也会考虑对策。我们在分析钟会走上反司马氏道路的原因时,不能忽视下面这一点——他明白自己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这也与钟会所认识到的司马昭的为人有关。
钟会在姜维(字伯约)投降后,曾对他有如下赞誉:“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他以诸葛诞(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为中土名士,在他们被司马氏杀害数年后仍未忘却。当年在司马昭下令把诸葛诞从扬州调到洛阳任司空一职时,钟会虽居丧在家,但因估计到诸葛诞不会服从命令,于是特地赶去劝阻司马昭,但后者并未改令。这件事可能使钟会更清楚地认识司马昭的手段。钟会此行说明以前他对司马昭的为人尚了解不足,而他此后在讨伐诸葛诞期间尽力出谋划策或出于他力求消除司马昭对他可能产生的猜疑心。这些连同魏帝曹髦的被害,应该使他对司马昭的为人有更清醒的认识。
司马师废魏帝曹芳迎立曹髦之初,钟会曾对司马师称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可见他非常看好这位年轻的皇帝。而曹髦后来常与他以及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等讲宴。甘露五年(260)这位皇帝被司马昭手下贾充、成济等杀害对钟会内心究竟有何影响,缺乏史料尚难断定,不过他应会对司马昭、贾充的为人有更深入的认识。此后,当“哭王经于东市”的向雄被太守下狱后(王经受曹髦遇弑一事牵连而被杀),是钟会从狱中提拔向雄为都官从事即其属官的。[1](卷四八《向雄传》)这件事为后人了解钟会的内心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可见他已表露出对司马昭、贾充等人所作所为不满。曹髦去世后过两年钟会抓住了众人反对伐蜀因此司马昭无他人可派之机,出任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这次他不再象以前那样力辞官爵,或可见他想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
钟会率大军伐蜀后,尽管占据了汉中主要地方,但蜀汉政权最终是亡于曹魏将领邓艾之手。不久他与胡烈等人上书称邓艾欲反,于是司马昭令其进军成都收捕邓艾。钟会派监军卫瓘先行,捕获邓艾父子。[2](卷二八《钟会传》)其后钟会赶到成都。
在此前后他接到了司马昭的书信,称由于担心邓艾难以控制,于是这位当权者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部入汉中,而他自己则亲率十万大军往长安,“相见在近”。钟会接获该书信后,已经知道司马昭对他起猜疑之心。这时他面临重大政治抉择——是否立即起兵反司马昭。此时的他能否不起事仍回魏国辅佐司马氏呢?钟会多年辅佐司马氏并号称“子房”,或许他料到即使回魏国也未必能保全自己,他在当时所说的话“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中应有此意。而他又非隐退避难之人,并拒绝了姜维在降魏后给他的建议——效法范蠡“泛舟绝迹,全功保身”。[2](卷四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在此还要提到的是,钟会当时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在蜀灭、邓艾被擒后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宁愿起兵放手一搏。
他是从司马昭的亲信走上反司马昭道路的。这时的他既不愿归隐逃避,又感到难以再回去走象裴秀等人那样的步步高升之路(钟会在灭蜀后已经是司徒了),再加上他就在刚被征服的益州,不必象夏侯霸那样赶往他国。他选择了起兵,但很快失败了。
结语
魏晋之际士人大体有四种基本的政治选择,可以分别简称为仕、隐、走、反。其中阮籍的选择是较为特殊的,可说是似仕实隐或隐于朝中。由这四种基本的政治选择,可以得出若干派生的政治选择,比如先隐后仕(向秀)、先走后隐(诸葛靓)等等。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其中或成或败,或存或亡,都给人们留下了足以思考、借鉴之处。
[1]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