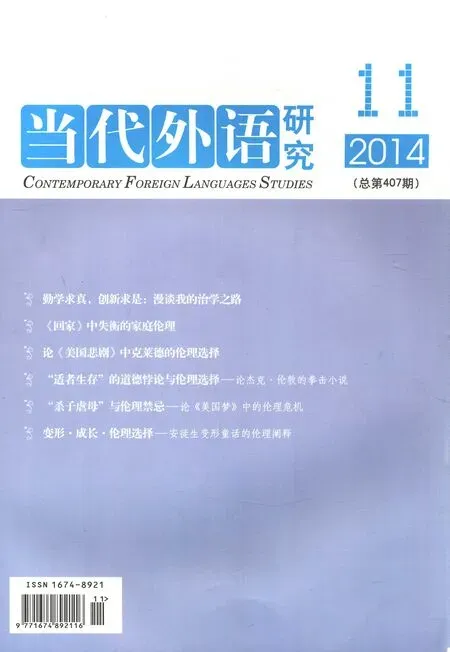论《美国悲剧》中克莱德的伦理选择
陈 晞 张 玉
(湖南大学,长沙,410082)
论《美国悲剧》中克莱德的伦理选择
陈 晞 张 玉
(湖南大学,长沙,410082)
《美国悲剧》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德莱塞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克莱德短暂一生的细致描写,深刻地揭露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风气、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和摧残。本文认为导致克莱德悲剧的外因是他生活的伦理环境,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人们对“美国梦”的曲解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扭曲了克莱德的个人价值观;内因是他本身伦理意识薄弱,易被欲望所支配,为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享乐违背伦理道德,破坏伦理禁忌,迷失自我导致悲剧。因此,《美国悲剧》不仅是一部关于家庭、爱情、法律、政治、宗教的悲剧,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部伦理悲剧。鉴于小说丰富的伦理内涵,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解读当时的伦理环境对克莱德伦理选择的影响,着重解构小说三部分分别对应克莱德兽性因子的蠢蠢欲动、自由意志的失控、理性意志的回归的三个阶段,分析斯芬克斯因子在克莱德的伦理选择过程中的不同组合和变化所导致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目的在于阐释克莱德悲剧的伦理本质,向世人昭示传统道德规范在伦理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性。
《美国悲剧》,伦理选择,斯芬克斯因子,自由意志,理性意志
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1871~1945)是20世纪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创作了《嘉莉妹妹》、《珍妮姑娘》、《美国悲剧》和《欲望三部曲》等多部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颇具影响的小说,其中《美国悲剧》公认为“是德莱赛最精彩的一部作品,是一部描写美国生活方面的史诗”(Lord 1941:235),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同上:236)。从这部巨作问世以来,批评家们多就美国梦的破灭、克莱德毁灭的原因、作者的道德观、欲望与消费等主题对其进行研究,就克莱德毁灭的原因而言,评论家詹姆斯·法瑞尔认为:“克莱德没有特别的天赋和社会优势,他的无知、贫穷、缺少机会导致了他的悲剧”(Farrell 1946:136);而特里格·萨莉则认为,“克莱德贪得无厌的欲望加上他意志薄弱的天性和无知导致他不可避免的堕落”(Sally 1990:435)。除了主题研究以外,还有不少学者探讨德莱赛的写作技巧、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和自然主
义特色等等,但是从总体来看,鲜有人从伦理的角度对德莱赛的作品进行深入地探讨。笔者认为《美国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伦理悲剧,而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正是他身上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
“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聂珍钊2014:38)。人的行为是斯芬克斯因子的外在表现,而文学作品描写的就是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斯芬克斯因子必然成为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用它来分析作品能够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作品,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同上:276)。在《美国悲剧》中,主人公克莱德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伦理选择,每个阶段的伦理选择都对他的身心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他走上了迷失、沉沦、疯狂和毁灭的不归道路。
1. 兽性因子的蠢蠢欲动
《美国悲剧》这本长篇巨著共分三部。第一部讲述了克莱德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在某豪华旅馆工作的经历。克莱德少年时期,敏感早熟,富于幻想,自命不凡。由于克莱德的父母忙于传教,孩子们的教育全都不幸地被耽误了。克莱德没有一技之长,却好高骛远,鄙视体力劳动者,认为“做些平凡的事情,那岂不是太下贱了吗”(德莱赛2001:10)①?尽管家人生活很拮据,克莱德却渴望有“一条较好的硬领衬衫,一双好看的皮鞋,一套好衣服,一件讲究的大衣”(11)。他厌恶自己贫穷的家庭,不甘于现状,向往奢华的生活。他极其反感跟随父母沿大街小巷布道卖唱的生活,在他的潜意识中希望脱离传教士的家庭,改变自己的伦理身份进入上层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莱德成人以后,离家应聘于堪萨斯市最大的一家旅馆——格林-戴维逊宾馆。在那里,美国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展现在他面前。每天目睹有钱人花天酒地,滋润潇洒的生活,克莱德禁不住诱惑,从最初的羡慕,到后来想方设法追求享乐。他向父母隐瞒工资收入,极力打扮自己,而这些行为“导致克莱德在道德上模棱两可,之后困扰他的肇事逃逸、谋杀等事可以说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McAleer 1968:130)。
克莱德的同事都处于社会底层,上层社会高雅、奢侈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他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极力模仿那些有钱人寻欢作乐:跳舞、下馆子、去赌场、逛妓院,道德自律意识十分薄弱。与这些同事相比,克莱德起初是有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听到同事们低俗下流的谈话,他会感到反感。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逐渐地他的道德自律意识开始下滑。当同事们邀他一起通宵聚会和喝酒时,他起初还犹豫不决,因为父母反对这些放纵的行为。他的犹豫和迟疑说明父母传授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在其内心根深蒂固,他仍有比较清醒的伦理意识,人性因子和理性意志处于上风。尽管与正统的家教相悖,最终,克莱德还是与同事们同流合污而且感觉到“行动自由的快乐”(44)。克莱德的自由意志从先前的萌芽状态,逐渐脱离理性意志的束缚,不仅晚归、喝酒,还在同事的怂恿下逛妓院,“非但不觉得厌恶,反倒着了迷”(52)。克莱德错误地认为性爱是“花钱就能买得到。跟这里随便哪个姑娘打交道,都不用去克服心理上的不安或道德上的拘束”(52)。逛妓院是克莱德自由意志和兽性因子蠢蠢欲动的表现。当自由意志挣脱理性意志的束缚,人的原始欲望就占据上风,表现出非理性的倾向,从而抛却传统的道德规范,沉迷于感官享受。纵欲行为彻底激发了克莱德身上的兽性因子,是小说第一部的一个重要伦理结。
妓院的经历让克莱德得出一个结论:金钱可以满足自己的肉欲。他被自己身上的兽性因子所控制,和女性交往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与爱情无关,他对霍旦斯展开疯狂的追求就是属于这种性质。霍旦斯长得虽然漂亮,但轻浮淫荡,追求享乐。克莱德的同事曾拉特勒劝诫他不要与霍旦斯深交,“她对谁都没诚意……她也许不过逗你一下,你可能什么都捞不到手”(62)。可克莱德执迷不悟,企图用钱买霍旦斯的人与心。在他与霍旦斯的关系上,他企图用物质来换取性享受,因而他对霍旦斯的追求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是受兽性因子的控制,属于“动物性本能的范畴,并无善恶的区别”(聂珍钊2014:282)。克莱德为了博得霍旦斯的好感,满足霍旦斯的物欲,四处借贷,“追求霍旦斯使他陷入一种难以置信的困境中”(McAleer 1968:130)。当他的姐姐难产,向他借五十美元请医生时,他身上正好有为霍旦斯买皮草的五十美元,但是,他没有借钱给处在生死攸关的至亲,亲情在肉欲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一边是霍旦斯,代表着原始肉欲;另一边是姐姐,代表着血缘亲情,把钱给霍旦斯意味着满足个人的情欲,把钱给姐姐意味着拯救生命,有人性的人在这个伦理选择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而克莱德却为了前者抛弃了后者。在这个伦理结中,克莱德被兽性因子控制,自由意志压倒理性意志,导致他漠视亲情,做出为了满足肉欲抛弃亲情的伦理选择。
在小说第一部,导致克莱德命运转折的另一个重要伦理结是车祸事件。克莱德乘坐同事斯巴赛未经主人允许偷开出来的车郊游,心里惴惴不安,认为这样做“不太合适”(101),担心出事,弄丢工作,但一想到同行的霍旦斯,克莱德就把顾虑抛到脑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他的犹豫和最后的决定可以看到克莱德意志不坚定,易被自由意志所支配,最终遭致灾祸——归途中撞死了一个小女孩。车祸发生后,克莱德不去自首反而告诫自己:“一定得脱身,绝不能被抓”(116),否则,“一场美妙的设想就会落空,甚至被关进牢房”(117)。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为了逃脱法律的惩罚,他从堪萨斯城逃到了芝加哥。“在文学作品中,伦理犯罪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同数个伦理犯罪连接在一起”(聂珍钊2014:223),他的这种畏罪潜逃实则又是一种犯罪行为。压死小女孩,再加上肇事逃逸,克莱德触犯了法律,破坏了伦理秩序,却都侥幸地逃脱,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为他后面更严重的蓄意犯罪打下了伏笔,“克莱德现在所展现的逃跑本能,预示着他之后所作出的选择,当他和罗伯塔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时,不能勇敢地承担”(McAleer 2014:131)。车祸逃逸这个伦理结是克莱德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他的价值观,助长了他犯罪的侥幸心理。
小说第一部中,逛妓院、追求霍旦斯、肇事逃逸这三个重要伦理结串联成一条伦理线,清晰地呈现了克莱德逐渐的堕落过程及其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较量。随着兽性因子的比例逐渐增大,克莱德的伦理意识经历了从清晰到迷失的转变过程,作出的伦理选择也经历了由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变。
2. 自由意志的失控
故事的第二部讲述了克莱德在伯父的衣领公司担任部门主管以及恋爱的经历。这个阶段他的意志力仍很薄弱,易被欲望所控制,比如:克莱德在伯父家第一次遇到桑德拉时,立刻对桑德拉“有一种冲动”(177)。“冲动”是他体内的荷尔蒙在躁动,“属于生理活动的范畴,在本能的驱动下产生,是人在本能上对生存和享受的一种渴求。这种渴求在特定的环境中自然产生,并受人的本能或动机所驱动”(聂珍钊2011:12)。担任部门主管必须遵守公司章法,公司规定职员“禁止跟他手下的女工或本厂其他部门的女工有来往,不管在厂内还是在厂外”(536),除此之外,在公司担任秘书的堂兄也警告他,“我们决不允许你干一些不正当的事来破坏家族形象。”(188)公司规定和警告可以说是在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一种伦理规范,这种规范在克莱德初到公司任职时对他的自由意志起到了一些束缚作用。
当漂亮的女工罗伯塔·奥尔登出现在克莱德的部门后,克莱德压抑的兽性因子瞬间被唤醒了。罗伯塔“迷人的嘴巴”,“可爱的大眼睛”让克莱德着迷,他不由自主地像当初迷恋霍旦斯一样,想尽办法接近罗伯塔。在克伦湖游玩不期而遇后,本应该和女工保持距离的他却提出与罗伯塔交往:“我们打破这些规矩好吗?”(210)“打破这些规矩”就是要违反公司的规定,是有意识地违反伦理规范,究其原因是非理性意志占上风的结果。克莱德很清醒地认识到,“走的这条路很危险”(208),却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他们偷偷幽会,不被别人发现就没有问题。被强大的肉欲所支配的克莱德向罗伯塔告白:“我觉得我快要疯了,……你太美了,我太爱你了!”(213)克莱德对罗伯塔的爱其实只有欲的成分,“真正的爱是生产性的表现,它包含着关心、尊重、责任和认识,它并不是一种为他人所影响之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努力使被爱者得以成长和幸福的行动”(弗洛姆1988:129),而克莱德只想与罗伯塔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占有对方,他的爱属于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情感,“是人的兽性因子的外化”(聂珍钊2014:280)。但是,和克莱德一样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罗伯塔坚守教规,因为“基督教反对任何非婚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认为它们与抢劫、谋杀同罪”(侯建新1993:54),对克莱德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罗伯塔认为“太不符合规矩,太不道德”(225),认为性“只有当它和婚姻联系起来才符合道德伦理”(转引自蒋道超2007:15)。克莱德却完全漠视传统的两性伦理规范,如果小说第一部中克莱德的兽性因子还只是蠢蠢欲动,还在理性意志的约束范围内,那么这时候他的兽性因子已经挣脱人性因子的束缚,急剧膨胀。当罗伯塔始终拒绝同居的要求,克莱德以分手来威胁,“要是你不愿意,那你就不必勉强,我还可以到别处去”(224-225)。克莱德对罗伯塔的爱是受到自然情感驱动的结果,因而做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违背伦理规范的伦理选择。这个伦理结的决定性因素是克莱德的非理性意志,“是一种不道德的意志,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渗透在人的伦理意识中”(聂珍钊2011:13)。克莱德对罗伯塔的自然情感越强烈,自由意志越强大,理性意志就越弱小。在占有罗伯塔后,克莱德也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可赦免的致命罪恶,是诱奸是私通,是在神圣婚姻关系以外的胡作非为”(233)。这一认识说明在克莱德的潜意识中,人性因子还是在发挥作用,提醒他这种的行为是违反伦理道德的。
“欲望激发下的情感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刘红卫2013:31),就在和罗伯塔私下密切交往时,克莱德邂逅了上层社会的桑德拉。桑德拉集美貌、高雅、财富于一身,对于克莱德说,她就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存在,既有动物性的原初欲望,如食欲,性欲也有人性得以确立之后产生的世俗的理性的欲望”(毛凌滢2008:60),克莱德的原始欲望在罗伯塔那里得到了满足后,就滋生出更高级的欲望,试图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彻底改变伦理身份,成为上层社会的一份子,为此,他想方设法博取桑德拉的好感。开始时,克莱德还顾忌罗伯塔的情感,但是在与桑德拉的关系亲密后,克莱德认为自己已经逐渐进入上层社会的社交圈,于是他对罗伯塔逐渐刻意冷淡,准备弃之如破履。可就在此时罗伯塔怀孕了。怀孕的罗伯塔对克莱德来说无疑是爬进上层社会的绊脚石,于是克莱德私下里去买药,企图让罗伯塔堕胎,根本没有考虑罗伯塔的安危。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堕胎不仅是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而且“介绍堕胎、提供堕胎……为他人施行堕胎者则触犯刑法”(赵梅1997:57)。克莱德强迫罗伯塔堕胎不仅是违法的,同时也是一种潜意识的伦理犯罪,因为罗伯塔腹中的孩子就是克莱德的孩子,他想方设法要罗伯塔堕胎其实触犯了“弑子”的伦理禁忌。由于当时法律规定“任何医生要是帮了人家做手术,不论结果是好是坏都得判刑”(325),没有人愿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罗伯塔堕胎,堕胎的计划终究落空。面对法律的明文规定和当时的伦理规范,克莱德还执意胁迫罗伯塔堕胎,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违法犯罪和触犯伦理禁忌。做出弑子的伦理选择,是克莱德自由意志发挥到极端的表现,构成了小说第二部的一个重要伦理结。
罗伯塔的逼婚让克莱德感到危机重重,“如果他不能马上摆脱她,那向他即将到来的一切,一定都会被收回去,而他自己也会被从前的穷困给围起来”(348)。恰在此时,帕斯湖谋杀案的新闻报道给了他启发,他立刻将溺水而亡的女游客与罗伯塔联系了起来。“当一个人刻意以如此强烈的程度将注意力集中于谋杀时,他的行为就自动变得极其邪恶,而这些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当然,他也必须承担这种无意识行为的后果。他的这种痴迷状态是自行诱发的,其无意识的反应却又与一桩邪恶的事紧密联系在一起”(Gerber 1991:231)。克莱德这种无意识其实是他的潜意识,但是人性因子仍然提醒克莱德摆脱这种邪恶的潜意识:“绝对不能,这太怕人了!可怕啊!竟然想到杀人,简直是嘛!杀人!!!”(356),因而,“克莱德在无情算计与良心不安之间备受煎熬”(Rhodes 1996:399)。但是一想到他渴望的自由、成功、爱情,克莱德的非理性意志就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兽性因子又一次压倒了人性因子。马斯洛(Maslow 1987)曾指出,人的需要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是最基础的,是人类保持自我生存的基本条件,对于克莱德而言,罗伯塔仅仅能满足他的生理需要,而桑德拉代表的是社会地位,可以满足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克莱德权衡“拥有一切的桑德拉,愿意为他奉献一切,却一无所求;而罗伯塔一无所有,却要他为她奉献一切”(385),摆脱罗伯塔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他开始策划谋杀,为了避免落下证据,他以“会惹麻烦”(370)为由,不让罗伯塔在与自己通电话时称呼他的名字。当克莱德收到罗伯塔的威胁信,决定实施谋杀罗伯塔的计划时,他的自由意志如脱缰的野马,完全脱离了理性意志的束缚。此时的克莱德已不是一个有清醒伦理意识的人,有人性的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他模仿帕斯湖的惨剧,筹划罗伯塔的死亡之旅。在人迹罕至的大卑顿湖中,克莱德让船“意外”侧翻,抛下溺水挣扎的罗伯塔,独自游上岸逃生。策划和谋杀罗伯塔是小说第二部中至关重要的伦理结,克莱德做出这样的伦理选择说明了他的自由意志彻底脱离了理性意志的束缚,在他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组合中兽性因子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导致他的人性泯灭。
在小说这一部中,克莱德的兽性因子完全脱离了人性因子的控制和束缚,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克莱德毫无顾忌地挑衅道德底线,破坏伦理秩序,与罗伯塔未婚发生性关系,逼迫罗伯塔堕胎,试图弑子,最后计划并实施对她的谋杀。克莱德在这一阶段做出违反伦理道德、违反法律规范的伦理选择标志着他的自由意志彻底失控。
3. 理性意志的回归
小说第三部分讲述了案发后,克莱德从被逮捕、审讯、判罪到处死的过程。在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的较量中,克莱德的自由意志占了上风,谋杀了罗伯塔。“伦理犯罪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犯罪者没有认识到其行为是一种犯罪之前,他是不会产生罪恶感的”(聂珍钊2014:183),而克莱德在实施犯罪后首先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犯罪不被发现,他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在伦理犯罪之后,产生沉重的罪恶感,并残酷地惩罚自己,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反而为自己开脱:“他的确无罪,他不是在最后一刹那间已回心转意了么?”(433)。在翻船事件以后,克莱德本应该去投案自首,可是他又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做出错误选择,藏匿起“手提箱”、“三脚架”等犯罪证据,以防罪行暴露。但是,破坏伦理秩序的犯罪是逃不过社会的惩罚的,隐藏销毁证据反而加速了他毁灭的进程。在逃离犯罪现场的路上,克莱德内心充满了恐惧,小树枝吱吱的声响,猫头鹰的叫声都会让他如“受惊的野兔”般慌乱。之后,“法律!被捕!被揭发!死!”充盈着他的内心。这种由犯罪所带来的心灵恐惧是一种伦理恐惧。“所有类型的恐惧都往往由处于危险或面临着危险的感觉而来,人们对造成或可能造成危险丧失了控制力,既不能对危险事物做出有效的预见,也对行将到来的危险失去抵御能力,无力摆脱危险的局面”(转引自张玉龙、陈晓阳2012:62)。尽管克莱德想方设法摆脱法律的制裁,但是他对谋杀罗伯塔将带来的后果丧失了控制力,伦理意识告诉他杀人是违反伦理道德的严重犯罪,他无力摆脱这种犯罪所带来的伦理恐惧,这种恐惧是对克莱德精神的折磨,是一种心理惩罚,是伦理道德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最终他阴谋暴露,被捕入狱。入狱后,求生的欲望驱使他编造各种谎言为自己开脱罪责,不过,“俄狄浦斯的自我辩解是在道德上感到恐惧的情绪的宣泄,企图通过为自己辩解来减轻恐惧”(聂珍钊2014:180),克莱德的辩解只是一种求生本能,希望减免罪责,免遭牢狱之灾。由于克莱德的犯罪证据不断被发现,他的辩解越发苍白无力,最终他被定罪,判处死刑。
克莱德谋杀罗伯塔是对社会伦理道德和伦理秩序的挑衅和破坏,“谁破坏了新的伦理道德关系和秩序,即使是无意的,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心灵带来痛苦,要遭到严厉惩罚”(同上:185),更何况克莱德实施的是一种有计划、蓄意的破坏,遭到严厉惩罚是必然的结果,“死刑”就是对他的终极惩罚。在克莱德被判死刑后,对于他来说,用尽心机追求的财富、地位、爱情都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众叛亲离。他叔叔明确地和他划清界限:“我可不帮他,那是他自作自受。我决不为犯这种罪的人花一分钱……就算他是我的侄子也不行!”(485)他所迷恋的桑德拉也抛弃了他,跟随家人远离是非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众叛亲离实则是“一种道德惩罚,是比死刑更为严厉的惩罚”(聂珍钊2014:225)。
克莱德的被逮捕、审判、判罪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伦理秩序重归正轨。在这个过程中,克莱德的伦理意识也开始回归。首先是亲情意识的回归和道德情感的复苏。克莱德被定罪后,他的母亲坚持不放弃他,尽管家境举步维艰,她借助一家报馆提供的费用来探监。由于叔叔拒绝帮助克莱德,母亲四处奔走,通过举行演讲会来筹借上诉的费用。“以理性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道德情感,如母爱和亲情”(聂珍钊2014:250),克莱德母亲对克莱德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到道德情感的驱使。目睹母亲为挽救他的性命所做的一切,克莱德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对母亲的道德情感也开始复苏,意识到:“他过去对她犯了多大的罪孽啊?多么不关心她啊!啊,他意识到多么大的罪孽啊?”(638)反省自己的过往,他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悔恨和负罪感,克莱德从内心发出这样的感悟其实是亲情意识回归的体现,人性回归的体现,是理性意志重新控制非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体现。除了道德情感,促使克莱德人性回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的伦理教诲。克莱德出生在宗教家庭,做出了这一系列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事情之后,最终回归到宗教的精神救赎。被关押起来的克莱德与外界隔离,孤独绝望,加上死牢戒备森严,他被迫在自己的精神领域里寻找安慰和解脱。克莱德的母亲拜托邓肯·麦克米伦牧师拯救克莱德的灵魂并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克莱德接受牧师的传教,希望牧师坚定的信仰和力量能帮助他消除种种不幸。牧师虔诚的宗教信仰对他的内心有所触动,他开始思考宗教中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反省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如果他过去的生活能更正直些,对他母亲所说过的,开导过的话更注意些,没有到堪萨斯市那家妓院去,没有那么邪恶地去追求霍旦斯·布里格斯,或是在这以后,没有那么邪恶地去追求罗伯塔,而是一直安心工作,勤俭节约,毫无疑问,人家多半都是这么做的,那他的处境不是比现在好得多么?(671)
这些反省标志着他理性意志的回归和人性的复苏。
克莱德的公开认罪是人性因子的最终回归。在麦克米伦牧师的布道劝解下,克莱德也曾想到在牧师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恶,但是他畏惧认罪带来的后果,因为在被审问时,克莱德做了许多伪证,之后上诉的证据就是凭借这些伪证,一旦公开忏悔,就必然会被定罪,所以他依然选择隐瞒罪行。基督教教义认为,犯罪的人需向上帝公开承认和忏悔罪行,否则身体和心灵都将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可见,克莱德虽然认同基督教所宣扬的伦理规范,但是在精神上并没有完全皈依宗教。最终,桑德拉的一封信彻彻底底击碎了克莱德的一切美梦:“永远无法理解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675)。这封信让克莱德意识到他为了追求桑德拉,铤而走险,但是桑德拉对他完全无情无义,弃他于不顾,他的全部希望化为乌有。在绝望中顿悟,他终于敞开心扉,坦白自己和罗伯塔、桑德拉的关系,承认原来一直否认的罪行,忏悔自己的罪过。
克莱德坦白并忏悔罪行是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之间博弈的结果,是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最终回归到理性意志的控制下的体现。克莱德上诉失败,法院维持了原判,对克莱德执行死刑,从而,克莱德触犯伦理禁忌,打破伦理秩序,终于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克莱德的死刑就是对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在执行死刑前,克莱德与母亲诀别:“我是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去死的,我不会难受的”(695)。人性的回归让他痛彻自己的罪过,甘愿以死弥补对罗伯塔、对社会犯下的罪行。
4. 结语
“文学作品不仅需要树立让人效仿的道德榜样,而且也需要给人警示的形象”(聂珍钊2014:250),而《美国悲剧》正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文学作品,整部小说详细讲述的就是一个伦理秩序是如何被破坏,如何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秩序的破坏者——克莱德从伦理意识薄弱、理性意志涣散,逐渐变成兽性因子压倒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战胜理性意志,从而沉迷于欲望中不能自拔,作出错误的伦理选择,最终导致伦理悲剧,以死刑换回伦理秩序的回归。克莱德的悲剧是不幸的,但其悲剧又是注定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环境下,受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自律意识的缺乏与自由意志的泛滥使悲剧的发生成为必然。克莱德的悲剧反映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疏忽,唤起了人们对伦理道德的理性思考,也警示和昭示我们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建设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附注
① 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Farrell, J. T. 1946. Theodore Dreiser [J].ChicagoReview(3): 127-44.
Gerber P. 1991. “A Beautiful Legal Problem”: Albert Levitt onAnAmericanTragedy[J].Language&Literature27(2): 214-42.
Lord, D. 1941. Dreiser today [J].PrairieSchooner(15): 230-39.
McAleer, J. J. 1968.TheodoreDreiser:AnIntroductionandInterpretation[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Rhodes, C. 1996. Twenties fiction, mass culture, and the modern subject [J].AmericanLiterature(68): 399.
Sally, T. 1990.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AnAmericanTragedy[J].StudiesintheNovel(4): 429-40.
A. H.马斯洛.1987.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程朝翔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
埃·弗洛姆.1988.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M].北京:三联书店.
侯建新.1993.西方两性关系史评述[J].天津师大学报(4):53-72.
蒋道超.2007.从小说创作看美国性伦理与政治意识间互动的演变[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4-22.
刘红卫.2013.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与“激情之爱”——《背叛》中“婚外情”的伦理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6):26-33.
毛凌滢.2008.消费伦理与欲望叙事:德莱赛《美国悲剧》的当代启示[J].外国文学研究(3):56-63.
聂珍钊.2011.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6):1-13.
聂珍钊.2014.文学论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奥多·德莱赛.2001.美国悲剧(赵小兰、王成云译)[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赵梅.1997.“选择权”与“生命权”——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论争[J].美国研究(4):55-87.
张玉龙、陈晓阳.2012.恐惧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0-64.
(责任编辑 玄 琰)
陈晞,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电子邮箱:chenxi@hnu.edu.cn
张玉,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电子邮箱:xiaoyu4229@163.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编号13&ZD1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I106.4
A
1674-8921-(2014)11-0014-06
10.3969/j.issn.1674-8921.2014.1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