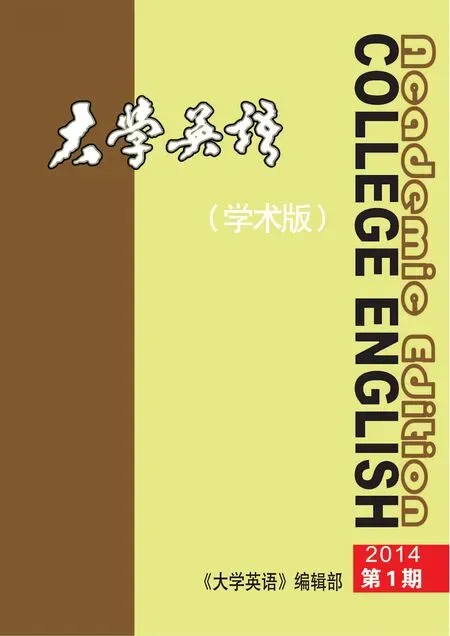回归与覆灭——评《织工马南》和《无名的裘德》中的边缘人物
李 莹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 100192)
引言
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和托马斯·哈代都致力于描写英国19世纪的乡村生活。二者文风在诸多方面颇为相似,以至于当哈代匿名发表了他第一部小说——《远离尘嚣》之后,众人纷纷猜测此书是出自乔治·爱略特之手(Page 2011:10)。这两位杰出的作家在其作品中都展示了边缘人物的命运,将他们最深切的同情赋予了这些地位卑微且为世人所不容的普通百姓。然而,因为两位作者对人生以及人性持有不同态度,两部小说中处于社会边缘的主人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最终的结局也大不相同。在本文中,我将从他们的边缘身份、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和两位作者对同情心的态度这三方面入手,将两部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做出比较,以揭示这些人物的不同命运。
一、边缘身份
在两部小说的开头,织工马南和裘德都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这种排斥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们都不得不远离故土,从一个地方迁居到另一个地方。乔治·爱略特在生活中与已婚男子同居,本人就是边缘人物。在波拿巴(Bonaparte)看来,乔治·爱略特认为基本上每个人都生来就处于孤独状态,很可能都会孤独终老(Bonaparte 1975:102-03)。《织工马南》是乔治·爱略特关于自我放逐的第一部作品(Beer 2005:445)。在被一段貌似亲密的友谊深深伤害之后,马南离开故乡——灯笼广场,来到了一个叫拉维罗的小村庄。“他住在一间石砌的小屋里,以织布为生。石屋就在拉维罗村附近的坚果树丛中,与久已荒废的石坑相距不远”(爱略特1982:2)。这片树丛是他与人世间的分界线。在被好友背叛,被上帝抛弃后,他独居于村庄边缘,就像被废弃的石坑一样,远离世间。他故意切断自己与众人的联系。除了织布生意上的事,他不与村里人有任何接触,“脸色苍白,个子矮小”(爱略特 1982:1)。他的织布机那种“可疑的声音”(爱略特 1982:2)吓跑了小孩子,也使大人们心存疑窦。他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损害,导致他后来对金子极度迷恋。然而,他对那只水罐的喜爱流露出他对友谊与交流的渴望,也预示了他最终将重获信仰以及世人之爱。
裘德不像马南那样故意远离人类社会。他心怀大志,不断努力学习以求挣得一个好前程,但他的努力一次又一次被周围环境挫败。他是一名孤儿,被姑婆收养。这位老妇人并不喜欢这个孩子,甚至希望他随他父母而去,并让他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可能是因为这种孤独,他将自己沉浸于书中的世界,并对一切像他一样无助的生灵都怀有深深的感情,不管是饥饿的乌鸦还是哀嚎的猪。于众人而言,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多余的人。乃至于他在临终时发出绝望的呼喊:“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哈代 1999:352)?裘德是一个不详的名字,与叛徒犹大 (Judas Iscariot)相似,也会使人联想到流浪的犹太人,而不管哪一个名字都与无家可归和贱民身份有关(Millgate 1982:350)。小说各章以不同地点为标题,进一步印证了他漫无目的的流浪生活。他的流浪使他流连于一个又一个简陋小屋和临时居所,但他从未找到过一个家(Page 2011:10)。甚至临时居所也与市中心相距甚远,让小时间老人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裘德似乎总是坐在火车上,而苏在站台上孤独的身影总是浮现在读者眼前。哈代将空间地点作为故事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的隐喻(Page 2011:51)。裘德和苏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在开始下一段旅程时从未有过清晰的目的。但他们漫无目的的漂泊被作者当作一种情节手段,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疏离与错位之感(Peck 2002:211)。
在世纪之交,哈代终结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其作品中开始崭露出现代主义的元素。他不像爱略特那样对生活怀有乐观的憧憬,而是对既定的权威思想和社会传统持怀疑态度。因此,他的作品中弥漫着分崩离析的破碎感。他站在社会边缘写作。其作品中一直有一种居于世事之外并质疑传统价值观的感觉。与之相反,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她站在社会与文化认可的价值中心写作(Peck 2002:206)。虽然她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她用人性与道德准则来取代上帝的律法。在她的文学世界里,中心不曾瓦解。她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包容、接纳、和睦和同情的氛围中。从前的边缘人物被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拉回到人群中来,再次融入人类社会。而哈代书中的世界是荒凉黑暗,充满敌意的。他笔下的主人公被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所吞没,徒劳地反抗传统价值观,但永远不能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因此,他们只能永远居于社会边缘,不能融入传统社会,直至最终毁灭的那一天。
二、环境影响
乔治·爱略特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作为这个有机体的个体细胞,根植于自身所处环境,与其不可分割,也不能单独拿出来加以分析(Bonaparte 1975:77)。当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被斩断,他们就可能会被疏离或异化。织工马南曾是一名热情而虔诚的年轻人,满怀兄弟之爱。他远离故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子边缘定居。他长期的自我封闭导致了村民们对这个外来者的多方揣测和马南自己对村民们的无端怀疑:
他从来不请来客跨进自己的门槛,也不到村里去,上虹居酒店去喝一杯,不到轮车匠的作坊聊天,除了职业上的需要,或者添置一些必需品,他也不同任何男人女人接触。拉维罗的姑娘们很快就明白,他决不会促使她们中间的一个人违反本愿去嫁给他——好像他已经听到她们说:她们决不会嫁给一个活死人。(爱略特1982:5)
当马南昏厥过去时,村里的姑娘们误以为他死了。甚至教区执事麦塞先生也认为:“灵魂出了窍,去了又来……这种事情倒是会有的”(爱略特 1982:6)。这样,马南在人们眼中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神秘人物。村民们蜂拥到他家里向他索要他们认为具有神奇魔力的药草。人们把他当做女巫一样的人,给他身上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巫术色彩。
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15年之后,马南的判断力大大受损。当他发现金子被盗时,他立即怀疑是杰姆·罗德尼偷的,仅仅因为他来他家的次数比别人多了点。他一直像一只昆虫一样独自生活,身边只有他的织机和金子相伴:
他的信仰之火已经完全熄灭,他的爱情之田已经荒废,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扑在干活和金钱上;……随着他无休止地在织布机上干活,那架织布机也反过来对他发生作用,这种单调的活儿使他更需要过单调的生活。他守着那些金钱,亲眼看到那些金钱越积越多,他那些金钱也把他的情爱的力量汇合在一起,变得像那些金钱一样,全然与世隔绝了。(爱略特 1982:47)
马南不再是社会的一份子,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变得面色苍白,形容消瘦。然而,即使他的生活中只有毫无生命气息的织机和金子相伴,他对于爱的渴望也从未停歇。
对于乔治·爱略特而言,自然具有道德含义,与人类自身幸福和灵魂健康有关(Cooke 2010:391)。当一个人与他所生长的环境之间的联系被斩断,他生命的意义也随之消亡了。随着原有的联系、纽带、责任和义务的消失,人的生命将失去寄托,理想破灭,人随之变成一种自私的,没有价值的生物。马南捡到的孩子成为联系他和社会的新纽带。他的生活在这个孩子到来之后也开始了一个新篇章(Cooke 2010:306)。乔治·爱略特并不想说人是环境的牺牲品,是被命运摆布的生物。人的周遭环境亦包括他自身承载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能够帮他抵御周围环境的侵蚀(Cooke 2010:258)。即使身处社会边缘,被村里人误解,织工马南仍然心怀人性之爱。在抚养这名“孤女”的过程中,他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打开心扉,接受别人的帮助,于是,在慢慢恢复了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之后,他又回到人群中来。哈代小说中的环境恰恰与之相反。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被吞噬到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成为命运的玩物。他们徒劳地想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但注定要失败。他们注定永远处于社会边缘,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乔治·爱略特的小说中,人与环境不可分割,但这种纽带在哈代的小说中被切断了。哈代书中的主人公永远在与环境抗争。哈代最后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个人努力的嘲讽以及对生命存在式荒诞性的描摹(Adelman 1992:11)。对人类而言,自然和生命本身的道德性是无法理解的,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范畴(Lawrence 1972:419)。当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裘德就难以理解自然的意义。小裘德为了谋生去做稻草人。这样一个角色貌似有违自然规律。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他对饥饿的小鸟的仁慈会损害人类的利益。“人间万事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合拍共韵,协调一致。天道悠悠,竟然如此狰狞,不禁使他生出反感。对这一群生灵仁慈就是对那一群生灵残忍,这种感想毒害了他那万汇归一的和谐感”(哈代 1999:11)。在他小小的心灵中,自然的秩序是相互矛盾的。乔治·爱略特书中那种和谐的气氛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断裂,再难恢复了。
裘德相信的每一件事——大学、教会、社会传统,最后甚至是苏,都把他压垮,逼入绝境(Adelman 1992:80)。裘德想要做神学博士的雄心壮志被圣书学院的回信泼了冷水。信上说要他“谨守本位”(哈代1999:99)。他的不懈努力不能使他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信中的建议纵然使人难过,但却预示了他的悲剧。裘德和苏去展览会后,他们的同居关系公诸于世。此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开始陷入令人窒息的气氛的包围”(哈代 1999:259)。面包房和杂货店的小伙计见到苏不再殷勤地举帽行礼。在镇上居民看来,让他们在教堂里重描《十诫》真是匪夷所思,难以接受,因此,他们的工作也丢了。他们每一条回归社会的路都被堵死了。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他们的关系也再不能见光,只能永远居于传统社会秩序之外。任何对社会法则的越界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好像社会法则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改变的命运(Lawrence 1972:420)。在哈代的小说中,无论个人如何挣扎也难以逃脱环境的束缚。织工马南编织的网可以被撕破,那只与世隔绝的蜘蛛能够重回社会,为人所接纳。然而,在哈代的小说中,如果主人公们不向现有社会秩序屈服,他们永远只能被排斥在传统社会之外。他们就像被诅咒的该隐,永远只能游走于社会边缘,蜗居于社会底层。
三、爱与同情
乔治·爱略特的主人公生活在充满邻里之爱、亲人之爱的氛围中。同情心成为联系边缘人物与人类社会的纽带,并将前者带回到后者之中。英文里的“同情心”一词有2个译法:sympathy和compassion。我们通过分析这两个英文单词的形态即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含义。sym-和com-都表示“相同的”;pathy和passion都表示“感情”。因此。 sympathy和compassion表示“相同的感情”,我们亦可以将其翻译成“共情”或“同理心”,意指“和别人分享同样的感情”。同情心可被定义为一种道德情感。当他人遇到困难,或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或行为动机 (Öztüfk 2011:35)。乔治·爱略特 “从华兹华斯处承袭了这种同情心”(Davis 2007:544)。在其早期作品中,她将这种情感投射到普通、卑微,但诚实、热情的老百姓身上。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多少文化,举止粗鲁,甚至头脑简单,但她在读者心中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温暖的位置,让读者发现这些无知的乡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魅力(Cooke 2010:117)。
尽管在别人眼中的马南神秘可怕,甚至带有巫术色彩,但他把自己全身心的爱都倾注到他捡来的孤女身上。这个无意间闯入他房间的小姑娘“多少是个来自那遥远的生活里的信使。她打动了他在拉维罗从来没有激动过的心——这是旧情的颤动”(爱略特1982:134)。爱蓓是一条情感纽带,连接马南业已忘却的过去和现在。他来拉维罗后那么多年第一次进教堂,就是为了这个小宝贝的洗礼。他的同情心在蛰伏多年后被爱蓓唤醒了。如果当初他将这个女孩拒之门外,他自己也会永远不能回归社会。“他本来躲开别人,一直过着越来越偏狭的孤立生活,现在这样一来,随着岁月递增,这孩子已在他和别人的生活之间建立起一道道新的联系”(爱略特1982:151)。他这种无私的爱与奉献也为他赢得了同样具有同情心的村民们的尊重和钦佩。就这样,这位多年独居的边缘人物重新回到了人群当中。
在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中,同情心可以修复边缘人物和人类社会之间业已断裂的纽带,从而使他回归社会。但哈代笔下的主人公则在周围人的冷眼旁观中绝望地挣扎,以求得他人的认可和接纳。并非是哈代自己拒绝这种已维系人类社会千百年的情感纽带。他也非常珍视这种同情心,并将其赋予给自己书中的主人公,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回报。乔治·爱略特在其作品中将这种为他人而活的利他主义情感与基督教教义等同起来(Cooke 2010:235)。哈代这位无神论者同样认为:人类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可以明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也必须在他们短暂而疲累的人生旅途中相互安慰,相互扶持(Dave 1985:185-6)。哈代详细描写了裘德和苏的利他主义行为,并非是让他们在物质或精神上有所回报,而是想激发读者的同情与怜悯之心。
裘德在幼时就是一个孤独、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孩子。他走路时小心翼翼,避免踩到昆虫。他对饥饿的鸟儿充满感情。这些举动都引发了读者的无限怜爱。他迟迟不娶苏是因为他担心表兄妹之间的爱情受人诟病,也害怕他们家族中的婚姻悲剧再次发生。读者很清楚他压抑了自己对苏的欲望,但没有看低他,相反觉得他诚实可信,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利用苏对他的情感(Öztüfk 2011:115)。苏一直试图反抗社会道德标准,尤其是婚姻法则。但她的母爱如此强烈以至于她放弃了对她自己理想的追求(Öztüfk 2011:121-22)。甚至当她的孩子被小时间老人杀死时,她都没有责怪他。尽管这个孩子像一个复仇天使一样,她还是爱他。苏认为这个结果是上帝对她的报复:“他们送了命可教我懂得了该怎么活着啦!他们一死,我就过了洗心革面第一关”(哈代1999:316)。哈代此刻用充满同情的口吻描述了这对夫妇的痛苦,让读者也为之动容。作者描述的利他主义行为越多,在目标读者群中产生的同情越强烈,我们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仁爱,具有恻隐之心,愈加乐于助人(Öztüfk 2011:41)。这样,我们可以想见,裘德和苏必须一生游离于人群之外。只有这样,别人的冷漠和他们俩的善良才能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才能从这场悲剧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因此,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构想注定了他们在书中的结局。
结论
《织工马南》和《无名的裘德》都描绘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物。然而,作者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他们的人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马南撕开旧时织就的网,大踏步走向新生时,裘德在约伯式的绝望呐喊中孤独地死去。乔治·爱略特总是将仁爱与同情赋予最普通的人群。她讴歌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信任,而这些情感是构筑她理想世界的基石。但当我们把爱略特式的美满结局与哈代式的悲剧结尾相提并论时,我们不会觉得后者逊色于前者。哈代让笔下的人物在无边的黑暗中苦苦挣扎,但依然保持善良与同情之心。两下对比,使读者对人物产生无限同情,心灵也得到净化。维多利亚时代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个人作为社会这一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与社会不可分割。爱略特正处于这个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对整个社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可以在同情和关爱的氛围下回归整体。而哈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世纪末的仓皇、悲观与失望使他笔下的社会充满了冷漠与隔阂,从而使裘德终生不能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身份”一词在英文中是“identity”,其动词形式为“identify”,含有“相等同”的意思。马南在爱与同情的呼唤下,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获得他人认同,进而重新获得了他的社会身份。而裘德终生未能获得他人认同,因此,至死都未能获得他的社会身份,从而永远成为边缘人物。然而,不管是大团圆式的结尾,还是主人公凄凉早逝,不管边缘人物是回归还是覆灭,这两部作品中体现的歌颂的仁爱与同情都会长存于读者心中,永不磨灭。
Adelman,G.(1992).Jude the Obscure:A Paradise of Despair[M].NY:Twayne Publishers.
Beer,G.(2005).George Eliot and the Novel of Ideas[A].In J.Richetti(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onaparte,F.(1975).Will and Destiny:Morality and Tragedy in George Eliot’s Novels[M].NY:New York UP.
Cooke,G.W.(2010).George Eliot:A Critical Study of Her Life,Writings and Philosophy[M].Cambridge:CUP.
Dave,J.C.(1985).The Human Predicament in Hardy’s Novels[M].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Davis,P.(2007).The Victoria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Lawrence,D.H.(1972).Literature and Art[A].In Edward D.McDonald(ed.)Phoenix: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Lawrence[C].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Millgate,M.(1982).Thomas Hardy:A Biography[M].Oxford:OUP.
Öztüfk,R.(2011).Evolutionary Aesthetics of Human Ethics in Hardy’s Tragic Narratives[M].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Page,N.(2011).Thomas Hardy[M].NY:Routledge.
Peck,J.&Coyle,M.(2002).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NY:Palgrave.
乔治·爱略特著,曹庸译 (1982).织工马南传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托马斯·哈代著,洗凡译 (1999).无名的裘德 [M].南京: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