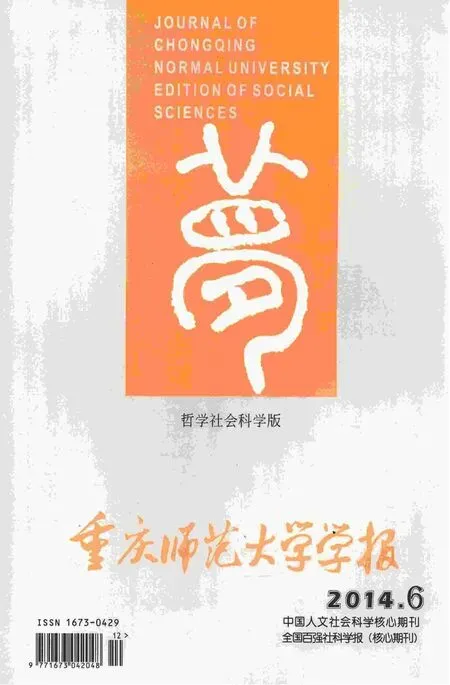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
杜芝明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400015)
“西南蕃”民族称谓出现于唐代,流行于两宋,此后较少出现。相对于“西南夷”、“西南蛮”等民族称谓,“西南蕃”是在“蕃汉”对称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蕴涵意义重大。学界对此有关注(如史继忠[1]、莫俊卿[2]488、杨武泉[3]50、程应镠[4]34、胡起望[5]212等先生),但不系统,不深入,可商榷。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对“西南蕃”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以就教于各方家。
一
“西南蕃”是伴随“蕃”作为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出现而出现的,而“蕃”的内涵经历长期演变才最终作为民族总称谓出现。
从《说文解字》[6]47(上)《经籍籑诂》[7]403(上)《王力古汉语字典》[8]746等文献看,“蕃”本义为“藩篱”,引申为“拱卫”“捍卫”,与其他字组合,内涵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诸侯国。武帝时,博士狄山就和亲指出,“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9]3141“今齐列为东蕃,而外私肃慎,捐国隃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10]2547齐国乃“东蕃”,是“华夏”东部藩篱之国,起着抵御少数民族的作用。
二是星象方位。“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为衡。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蕃四星……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亦曰四辅也。”[11]291-292太微与南蕃、东蕃、西蕃等星之关系,是天子、诸侯两者关系的反映。
三为少数民族。“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者,此经总揔而言之,皆曰蕃,分为三服,据职方而言也。”[12]892在服事制度中,“蕃”强调与“九州”对应的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蕃”为少数民族总称谓是伴随“汉人”作为族称而出现的,而“‘蕃汉’对举,在唐朝已普遍使用”[13]237-240。
宋代,“蕃”、“蕃汉”、“蕃部”等使用更加普遍,周边少数民族皆可称之为“蕃(部)”[14]。天圣六年(1028)“诏陕西部署司缘边蕃部使臣、首领等因罪罚羊,并令躬自送纳……”[15]2484《宋会要》直接以“蕃夷传”代替了正史中“四夷传”,这是“蕃”作为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充分体现。
综之,周代,“蕃”与“九州”相对,泛指九州之外少数民族;战国,诸雄并立,方位与“蕃”结合往往指称与少数民族接壤的诸国;秦汉,多以“蕃臣”指地方诸侯;隋唐,“蕃”作为少数民族总称谓已普遍出现,并常与方位词合用。
二
“蕃”与方位结合指称少数民族在唐宋较流行,“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贡奉之事。”[16]3903其中,“西南蕃”称谓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宋代。
唐代,史家对“西南蕃”没有界定,但空间有二:一是黔中道的蛮州,“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左右大首领、继袭摄蛮州巴江县令、赐紫金鱼袋宋万传。”[17]482蛮州为宋之势力范围,有宋鼎、宋万传,从宋鼎为“西南蕃大酋长”看,西南蕃活动区域当不限于此。一是海外,“主客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后、诸蕃朝见之事。……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18]1195-1196显然,“西南蕃”在海外,地域无从得知。而《唐六典》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19]129“七十余国”无黔中道民族,但包括《宋书》《南史》所载之“西南夷”。故“西南蕃”是《宋书》《南史》所记载之“西南夷”即海外诸国。
宋代,“西南蕃”有明确的地理空间,“西南蕃,汉牂牁郡地也。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20]10《乐书》载:“西南蕃,汉牂牁郡地也。东距辰州,西距昆明,南距交阯,北距充州。”[21]这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西南蕃只是位于汉牂牁故地,空间上小于汉牂牁郡。而唐置珍、费、夷等州明显位于充州北部,与《乐书》载“四至”存在出入。第二,《乐书》的“四至”应从《旧唐书》“牂牁蛮”抄入,“牂牁蛮……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16]14243《旧唐书》反映的是牂牁蛮位置,非“牂牁郡”范围,《乐书》删去里数使由“位置”变成了“范围”的描述。故“西南蕃”位于“汉牂牁郡地”,为“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除北面外,其范围为南交阯、西昆明、东辰州,尤以黔南诸羁縻州的龙、罗、方、石、张、韦、程等西南五(七)蕃为著。此外,有张、二王、腾、谢等蕃部,“其称大小张、大小王、龙、石、腾、谢等,谓之西南蕃,地与牂牁接”[22]。范成大以“等”、“谓之西南蕃”等表述充分说明该区域包括了多姓少数民族。“地与牂牁接”,方国瑜先生指出:“牂牁……所包之区域,在各时期不同……唐宋时期之牂牁地名,亦限于汉时所设之且兰、毋敛二县。”[23]515范成大所指只是黔南诸羁縻州,非黔州所领羁縻州全部,即且兰、毋敛(今贵阳、都匀区域)之南。
此外,“西南蕃”还包括其他区域,“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汉以来王侯国以百数……昆明,在黔、泸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17]5275“昆明为部族之称,亦用作地名,而在各时期以昆明为名者,不止一处。”此“昆明”与《乐书》《旧唐书》所载皆为昆明部族,其区域与牂牁部族接,“唐设普宁州、明州隶黔州都督府。宋时以黔州都督地为绍庆府,设羁縻州县,惟昆明部族不在其内,而称罗殿国也。”[23]515-516即今黔西北、滇东北地区。明人薛瑄说:“(先公)以北方罢学改官四川马湖府平夷长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蕃,去中国绝远。”[24]唐宋以后,“西南蕃”在文献中出现少,马湖地区被称为“古西南蕃地”当本之唐宋,而《宋会要·西南蕃传》也有戎州石门、马湖一带少数民族的记载。[20]36故宋时,滇东北、黔西北、川西南皆为西南蕃部所居,其族群包括了石门蕃部、马湖部、罗殿、罗氏等。
《宋会要》“西南蕃传”内容包括了川峡四路的“边夷”。“益、梓、利、夔州路缘边居住夷人或有铜鼓、铜器,并许依旧于夷界内使用,州县不得骚扰。”[20]20南平军,“皇朝熙宁七年(1074年),招收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25]373南平军,唐开南蛮立南州,宋时“军之境土,南则牂牁郡之境,北则巴郡之故疆也”[26]。南平军非宋人界定的“西南蕃”区域。泸州少数民族,政和五年(1115年),“梓州路转运司言:‘晏州夷族罗氏鬼首吕告向化。’诏补武略郎、西南蕃大巡检使。”[20]22“西夷”,乾德四年(966年)七月,王全斌言:“西南夷首领兼领霸州刺史董暠等上章内附。”[20]22
大理、自杞等少数民族(政权)被称为“西南(诸)蕃”,“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蛮氈。出西南诸蕃,以大理为最。”[27]106“西南(诸)蕃”包括了大理、毗那、自杞等少数民族,与范成大《志蛮》内容相符。范成大将区域内少数民族分为羁縻州洞、傜、僚、蛮、黎、蜑等六个族群,其中,“蛮。南方曰蛮,亦曰西南蕃。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27]101范成大一方面将大小张、大小王、龙、石等“谓之西南蕃”;另一方面将该部分少数民族以“西南蕃”名之,皆为化外“真蛮”,包括了大小张王等蕃、罗殿、自杞、罗孔、特磨、白衣、九道、苏绮、罗坐、大理、交趾等。范成大虽然没有直接以“西南蕃”称之,但却纳入到了“西南蕃”的论述。
综之,“西南蕃”作为少数民族泛称,活动区域包括:一是贵州全境,包括汉牂牁郡,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这是西南蕃活动的主要区域,尤以黔西北罗氏、黔南西南五(七)蕃等为著。二是川峡四路的“边夷”,如泸南少数民族、马湖、董氏等。三是云南省、广西西北部,主要是滇东北的石门蕃部、大理及广西西北部的自杞等。四是《新唐书》所记海外诸国。
三
民族地理观是“‘华夷之辨’思想在其地理空间上的认识和阐释所形成的理念、观念和方法”[28]。史家关于“西南蕃”的论述皆是唐宋人民族地理观的反映,而认识的差异性又源自现实以及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的影响。
唐人对“西南蕃”的认识较模糊且无传,《旧唐书》将“西南蕃大酋长蛮州刺史宋鼎”的内容放入“东谢蛮”。后唐,宋氏势力壮大,“后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来朝。其后孟知祥据西川,复不通朝贡。”[17]5276宋人在《宋会要》中单独为“西南蕃”立传,并在“四夷朝贡”中将其与其他少数民族并列。此后,除《宋史》“西南诸夷传”“黔涪施高徼外诸蛮传”“泸州蛮传”跟“西南蕃列传”相近外,更无文献对“西南蕃”单独立传。
在“四夷”体系、西南民族地理格局中,“西南蕃传”的出现是对汉代史家单独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书编纂体例的继承,也是对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与王朝来往密切、地位重要性的反映。
关于“西南蕃”的地理空间,《宋史》“西南诸夷传”“黔涪施高徼外诸蛮传”的总论与《宋会要》并无二致,应是元人从《宋会要》中抄入,“西南诸夷,汉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汉牂牁郡,唐南宁州、牂牁、昆明、东谢、南谢、西赵、充州诸蛮也。”[17]5276两处界定基本一致,但前者为行政区划,后者为族群,且内容上相互衔接[23]760。“昆明,在黔、泸徼外,今西南蕃部所居也。”[17]5276北宋郑獬也称呼“西南蕃”所居住区域为“南徼”而非“西南”,“尔(按:蕃王龙以岳)以豪武,荐居南徼之外……忠孝之心万里洞见。”[29]范成大也将大理、自杞等南方少数民族以“西南蕃”名之。史家对“西南蕃”空间的论述,体现了对汉代史家以(巴)蜀为中心划分西南民族地理方法的继承,但又有自己特点。
首先,“西南蕃”只是“西南夷”之“南夷”。该划分民族的地理方法可追溯至《华阳国志》,该志分为蜀、巴、汉中、南中四个区域进行论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30]229常璩排除“西夷”,将位于蜀汉之南的“南中”从“西南夷”中单独划出,就使北南对应明显、东西划分模糊,进而强化了“南夷”即南中作为独立民族地理单元的地位。唐代,张守节直接将“西南夷”定在了“蜀之南”。[9]2991
其次,除“汉牂牁郡地”外,也有“黔、泸徼外”“南徼”等表述。这是以直接统治区域(即正州)为中心、以“汉-夷”划分民族的地理方法,强调的是“边州”(黔、泸州)之外。宋人将“西南夷”之“南夷”以“西南蕃”形式独立出来,并常以“南徼”“徼外”描述,反映的不仅是巴蜀之“南”,更是直接统治区域之“南”。
这样的思想源于唐宋史家整齐划一的华夷“五方之民”民族地理观。唐宋史家构建的四夷体系是华夷“五方之民”格局中最整齐、规范的,《晋书》《隋书》《北史》《梁书》等严格按四夷(四方)地理格局安排内容。《太平寰宇记》全书以“诸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纲,四夷空间整齐划一,华夷“五方之民”地理思想得到集中体现,“古西戎之域,盖自古肃州以南,甘、凉、洮、凤、龙、茂、隆、蜀、邛、雅、黎、巂等州之西,并西夷也。”[31]3445这样的方位观在宋人中比较普遍,“自洮、岷至威、茂外境为西番,自沈黎至施、黔之外为南蛮,亦有自西域通货且贸易皆会于沈黎者。”[32]史家整齐划一的方位观,往往强调整体而忽略局部,因此唐宋史家将蜀之南的“西南蕃”作为“南蛮”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西南夷”之“西夷”排除在“西南蕃”之外是应有之意。
“西南蕃传”内容包括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之“西夷”“南夷”的主要少数民族,这就导致内容与宋人界定的“西南蕃”地理空间存在冲突。就此问题,李焘明确指出:“保、霸二州,密迩维、茂,盖西夷也。《国史》附此事于西南蕃传,且云西南蕃乃牂牁郡故地。按居牂牁故地者实为南夷,其族帐首领皆姓龙,与诸董绝不相关。《国史》误矣。诸董可号西蕃,若牂牁故地族帐,则不可号南蕃也。”[15]1309“诸董可号西蕃”反映了李焘的西蕃民族地理观,这是以王朝统治为中心、划分四方民族的华夷“五方之民”民族地理观的体现。“若牂牁故地族帐,则不可号南蕃也”,反应了李氏认同《宋会要》对“西南蕃”的界定。“南蕃”多指域外民族,故有“不可号南蕃也”之语。李焘认为将保、霸二州纳入“西南蕃列传”乃“《国史》误矣”,这实际是两种不同思想的反映:首先,李焘的思想与《宋会要》对“西南蕃”的空间界定所反映的民族地理观是一致。其次,宋代史家力图继承司马迁所建立的西南民族地理观,为西南少数民族单独立传(“西南蕃列传”),但具体内容只是宋朝羁縻统治下的西南少数民族,对于邛部川等其他少数民族,《宋会要》将其与“西南蕃”并列。
在继承汉代史家西南民族地理观的基础上,宋人以疆域为标准将“西南夷”之“西夷”划分为两部分:保、霸、茂等羁縻州少数民族被纳入“西南蕃传”,位于宋实际控制区域内;黎州蛮、邛部川等民族与“西南蕃”并列,位于宋实际控制区域之外,是宋人汉唐旧疆思想的体现。
唐宋史家继承了秦汉史家为西南少数民族单独立传,以及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夷”“西夷”的民族分布布局基本理念和划分方法。[33]宋人不仅为“西南蕃”立传,其不仅包括了“南夷”,也包括了“西夷”部分内容,而且“西南夷”“西夷”“南夷”等称谓常为宋人所沿用。
从常璩《华阳国志》以《南中志》形式将蜀之南少数民族独立出来,到唐代司马贞直接将“西南夷”定在“蜀之南”,再到《宋会要》《乐书》等直接将“西南蕃”定在“汉牂牁郡地”,汉代史家所载之“西南夷”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齐划一方位观影响下,“西夷”被排除在外,“南夷”却作为独立民族地理单元、“南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西南蕃(夷)”形式出现。“西南蕃”虽在“蜀之南”,但“西南”已不是巴蜀之西与南,而是统治中心之西南,这既是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方民族的地理方法,又是以王朝中心划分民族的地理方法。
南北时期,“西南夷”地理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宋史家继承了这一思想。《后汉书》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撣国王献乐及幻人……”[34]1685撣国,在今缅甸。《宋书》将空间具体化,“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35]2377《南史》《新唐书》《岭外代答·海外诸蕃国》等所载“西南蕃(夷)”的空间与《后汉书》《宋书》同,皆为疆域外民族;从方位看,其仍处于“中国”的西南方,体现了以疆域划分民族的地理思想。
[1]史继忠.试论“东谢”、“牂牁蛮”及“西南蕃”等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1创刊号.
[2]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O].北京:中华书局,1999.
[4]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5](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G].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6](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K].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清)阮元.经籍籑诂[O].北京:中华书局,1982.
[8]王力等编.王力古汉语字典[K].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汉)司马迁.史记[O].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汉)班固.汉书[O].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唐)房玄龄等.晋书[O].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O].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4]陈武强.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J].青海民族研究,2006,(4).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O].北京:中华书局,2004.
[16](元)脱脱.宋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后晋)刘昫.旧唐书[O].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宋)欧阳修.新唐书[O].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O].北京:中华书局,1992.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5)[O].北京:中华书局,1957.
[21](宋)陈旸.乐书(卷159)[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五)[O].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明)薛瑄.敬轩文集(卷22墓表·汾阴阡表)[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王存.元丰九域志[O].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宋)王象之.舆地纪胜[O].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印刻社,1991.
[27](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O].北京:中华书局,2002.
[28]黎小龙.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巴蜀“北僚”和“南平僚”[J].民族研究,2014,(2).
[29](宋)郑獬.西南蕃附进蕃王龙以岳十九人推恩制[G]//郧溪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O].北京:中华书局,2007.
[32](宋)佚名.条陈边防之策[G]//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63).续四库全书本.
[33]黎小龙.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J].民族研究,2004,(3).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陈禅传[O].北京:中华书局,1965.
[35](南朝·梁)沈约.宋书·夷蛮列传[O].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