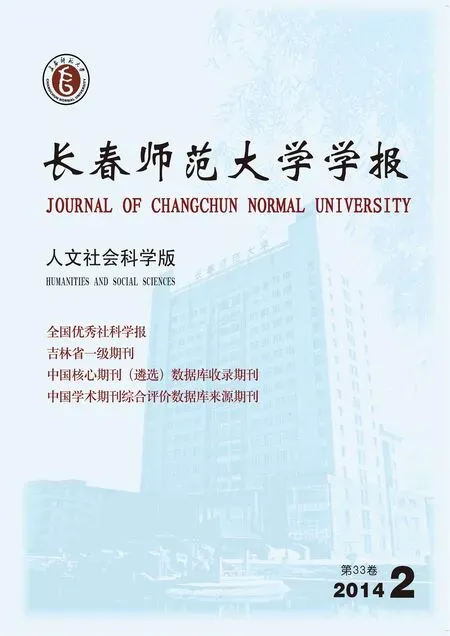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字”、“词”关系刍议
——“字本位”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崔金涛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字”、“词”关系刍议
——“字本位”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崔金涛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字”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核心,但随着西方语言学的传入,“字”及其研究日益被边缘化。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有助于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字本位”在成功避免了切分“语素”或“词”的窘境的同时,也过于轻率地否定了“词”在汉语中的客观存在。作为汉语的基础性结构单位,单音节的“字”可以通过语音、语义两种途径来构造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
“字”本位;“字”;“词”;语音构词和语义构词
“字”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中心问题。对“字”的研究通常称为“小学”,具体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自西方语言学传入以来,“字”从语言研究的中心退到了边缘,仅被作为纯粹的文字形体来看待。①随着“字”丧失了作为一级语言单位的资格,传统“小学”,除了“音韵学”仍然被看作是语言学之外,“文字学”和“训诂学”均被冠以“语文学”或者“文献学”之类的名目,从而基本上被排除在了语言学的研究之外。这种情形一直到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正式提出“字本位”的语言理论之后才有所改变。徐先生还“字”以语言学的资格,我们深表赞同,因为这样有利于中华本有语言学传统的继承,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目前汉语学界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困难。但首创者难为功,作为一种新生的理论,“字本位”本身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字本位”包罗甚广②,这里只选取“语言单位”一个角度,对这一理论的优势、不足及其解决之道进行分析,以求解剖麻雀,以见全体之效。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相应的讨论。
一
“字本位”理论在“语言单位”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较好地避免了“语素”与“词” 切分的窘境。按照目前最通行的说法,“语素”指“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词”指“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仅从定义上看,二者作为语言单位的特征非常明显,但事实上,不论是“语素”还是“词”,在汉语中都不是一望而知的,因而需要一些严密的操作方法来“发现”,诸如所谓“替代法”、“插入法”(或称“扩展法”)、“剩余法”者即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衡量,目前学界对“语素”和“词”的界定就显得不够明确,也不甚经济。在形态较为发达的印欧系语言里,“语素”的发现通常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将某一词汇的原形(如book)与其相应的语法形态(如books)进行比较,就可以较为简单地把一些不成音节的“语素”(如-s)离析出来。至于“词”,那就更容易寻找,比如在英语中,只要一组相连的音素具备一个明确的主重音,就可以判定它是一个“词”。但是反观汉语,确定一个“语素”或“词”却并非这样容易。例如,普通话中常见的“儿化”现象,其中的“儿”并不代表实际的音节或音素,而仅仅是一个卷舌的标记。尽管我们知道,“面”绝不是“面儿”、“粉”也不是“粉儿”,但在“面儿”和“粉儿”中却找不到一个相当于了“儿”的音素。至于“词”的切分,更是要比“语素”复杂得多。首先,我们在运用某一标准切分“词”时,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例外。比如在“鸭子”这个结构中的“鸭”不能单用,“子”也不能单用,所以“鸭子”是“词”,但又存在着诸如“鸭蛋”、“鸭肉”、“鸭血”、“鸭舌”、“鸭掌”、“鸭胗”这样一系列的形式,但似乎没有哪位学者认为这些含有“鸭”的组合形式是“词”,似乎也没有那一本权威词典收录过这样的“词”。其次,就是某一结构符合此一标准,却不合彼一标准,这样便出现了不少两难的情况,比如“道歉”,其中的“道”和“歉”都没法单用,所以根据自由与否的标准,“道歉”应该是词,但是“道歉”中间又可以插入诸如“一次”、“两次”这样的数量结构,而按照是否可以插入成分的标准(即所谓是否可以“插入”或“扩展”的标准),“道歉”又绝不是“词”,于是便发明了“离合词”的概念来弥合这种矛盾。
相对于“语素”和“词”切分面临的这种窘境,“字”是绝对清晰可辨的,根据徐通锵的定义,“字”的最基本特点是“1个字·1个概念·1个音节的一一对应”③。由于汉语的音节结构非常简单,再加上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的作用,这种三“1”对应的格局使“字”在汉语非常容易切分、辨认,基本不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如果我们拿一段话给一个没有受过语言学训练的汉族人,问他其中有多少个字,恐怕没有谁会回答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问他其中有几个“语素”或“词”,答案十有八九是不知道或者言人人殊。因为,这样的问题,恐怕连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也未必答得上来。只要我们联想自己学习或升学的经历,都会记起这样一种颇为尴尬遭遇:我们经常拿不准一句话里究竟有几个“词”或“语素”。可见,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汉族人来说,“字”是一个远要比“语素”和“词”来得现实得多、也确定得多的“语言单位”,当然选择“字”作为汉语描写和解释的起点,也会比用“语素”或“词”来得可靠得多。
母语者的语感是否能够作为检验语言学理论合理性的标准?起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在论及类推现象时曾经指出:“一个正常的说话人,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不会去描写他的言语习惯,而且如果我们愚蠢得竟然去追问他,他也决不可能说出正确的条理来的……我们随时得记住,说话人缺乏高度专门化的训练,是不会描写他们的言语习惯的。”[1]布氏这种否定母语者语感在语言描写中的地位、强调专门化技术作用的观点,发展到了后期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那里,就产生了对描写技术的过度依赖,以至于出现了像布洛克(Bloch)那样变乱日语“五十音图”的极端事例[2]。这种所谓“全新”的“发现”,虽然在描写主义语言学家那里获得了热烈的欢呼,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单纯依赖语言描写技术的深刻怀疑:究竟是某一语言的母语者的语感正确?还是某种仅仅依赖描写技术而得到的“科学结论”更正确?随着乔姆斯基(Chomsky)学派的兴起,这些重要问题已经有了比较确定的答案,在生成语言学家那里,母语者的语感再一次成了检验某一语言学理论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尺,而语言学的中心任务也从利用技术程序去“发现”某种陌生语言的结构系统,转到了如何更好地说明和解释母语者的语感上。
二
“字本位”理论在“语言单位”方面最显著的不足是,在强调“字”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简单取消了“词”这一级语言单位。应该说,徐先生这样的处理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
叶斯柏森(Jesperson)把语言中的形式分成惯用语和自由用语两大类。对于“惯用语”的特点,叶氏指出,“语言中有些东西……具有惯用法的性质”,“惯用语……是怎么样构成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惯用语在语言的实感上必须永远是一个不能作进一步的分解的,即不能像自由用语那样可以分解的单位。”[3]根据叶氏的这段论述,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汉语中,不论古今,都存在同样性质的单位,而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正好与之相当④。一般认为,古代汉语是单音节的“字”占绝对优势的语言,但不容否认,其中也存在一部分双音节甚至多音节的词汇单位。《说文·玉部》:“玫,火齐,玫瑰也。”“玫”下紧跟“瑰”字,云:“瑰,玫瑰。”按,这是《说文》非常重要的一条体例,即如果是双音节词,则在组成该词的前一个字下列出全词,并注出全词的意思,而后一字则仅把该词写出,不再做任何解释。由此可知,对于许慎来说,“玫瑰”实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双音节词,并不是“玫”、“瑰”可以拆开来理解的“字组”。《说文》是汉语文字学最重要的典籍,既然许慎设立了这样一条条例,并贯穿全书,足见上古汉语中存在双音节词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中古以后,汉语的词汇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双音化过程,其词汇主体由单音节“字”变为双音节“词”,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字”在双音节的“词”(即叶斯柏森所说的“惯用语”的一种)中的组合能力与它在由“字”组成的“词组”(即叶斯柏森说的“自由用语”的一种)中的相应表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双音节“词”中,单音节的“字”具有非常强的组合能力,基本上只要意义允许,就可以和其他单音节的“字”组成具体某一个“词”。例如“金”既可以在前组成“金光”、“金身”、“金色”,也可以在后组成“泥金、烫金、赤金”,而与之组合的“光”、“身”、“色”或“泥”、“烫”、“赤”,或为事物,或为动作,或涉及人类,或涉及非人的自然,实在无法从中找出某种规律,用以描述它们与“金”的相互选择。但在句法层面,“金”一般不具有独立活动的能力,我们通常使用“金子”或者“黄金”的说法。比如,我们可以说“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金子”,却不能说“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金”。另外,在双音节的“词”和“词组”中,单音节“字”的意义的组合方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打印”,尽管它含有“打”和“印”两个“字”,而且二者都具备造句能力(如“打人”或“印卷子”),但“打印”的意思绝对不等于“打”加上“印”,这里“打”仅是“印”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又如“司机”,“司”的意思是管理或负责,“机”是机器、机械,但“司机”并不是管理机器之类的意思,而是指驾驶车辆的人。
综上所述,汉语中多音节的“词”和单音节的“字”都是客观存在的单位,绝对不能由于强调“字”的基础性地位,而主观上无视“词”的客观存在。诚如周荐先生所说:“汉语的‘词’诚然不同于西语的word,汉语中的‘合成词’(或复合词)固然迥异于西语中的compound,但是汉语中词这一级单位及其下位单位的存在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宣布汉语中的‘词’就是汉语中的‘词’,不是西方语言的word;汉语中的‘词’的所指就是汉语词汇层次中的这一个。”[4]其实,即使是徐通锵先生本人,在处理与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相关的语言现象时,也并没有真正做到“去词化”。在“字本位”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字组”(或“辞”)这样的概念,而“字组”中又有“固定字组”一类。徐先生所说的“固定字组”正好相当于叶斯柏森所说的“惯用语”,也就是一般所说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
三
如果既承认单音节的“字”在汉语结构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又坚持“词”作为比“字”更高一级的多音节固定单位的合法性,那么就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由“字”到“词”,究竟有哪些重要的组合规律?
综合前辈时贤的诸多相关探索,由“字”到“词”的组合规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语音途径,一为语义途径,可以姑且称之为“语音构词”和“语义构词”。“字”作为一级语言单位,具有自己独立的语音和语义,在构造上一级语言单位时,自然也就可以通过语音和语义两种途径来进行。
先看语音构词。在讨论语音构词现象时,必须首先排除像“布尔什维克”、“咖啡”这样的情况。众所周知,这些看上去每个“字”都只有音节作用而无实在意义的所谓“单纯词”,实际上仅仅是假借汉字进行记音的产物,其根本性质属于多音节的非汉语,根本不能作为讨论汉语结构系统本质特征的依据。除去类似的音译外来词的情况,汉语的语音构词可以再细分为分音和叠音两个小类。所谓“分音”,指的是本来是“1个概念·1个音节对应”的1个“字”,由于汉语音韵结构的变迁,为了适应演变后的音节结构而分化成了双音节的“词”。例如“寻”,本“徐林切”,平声侵韵,以m收尾,义为“寻觅”,如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以前)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随着咸、深二摄并入山、臻二摄,闭口韵在汉语普通话中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为了适应新的音节结构,“寻”字分音而为“踅摸”(音xué ·mo,义为“寻找”),原本作为韵尾的m独立成为一个音节mo。又如“沓”,本“徒合切”,入声合韵,以p收尾,义为“多言”,如《孟子·离娄上》:“《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孟子》所引之《诗》,出自《大雅·板》。陆德明《经典释文》云:《说文》作“呭”,云“多言也”。由此可知,孟子所说“沓沓”亦为“多言”之义。随着入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消失,为了适应新的音节结构,“沓”字分音而为“嘚啵”(音dē ·bo,义为“絮叨、唠叨”),原本作为韵尾的p独立成为一个音节bo⑤。所谓“重叠”可以有完全重叠、部分重叠两种。完全重叠者自古有之,如《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中“关关”二字即模拟雎鸠鸟雌雄和鸣之声,故朱熹《诗集传》云:“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又《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集传》云:“丁丁,伐木声;嘤嘤,鸟声之和也。”可见“丁丁”、“嘤嘤”都是拟声词。部分重叠者亦自古有之,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集传》:“窈窕,幽闲之意。”可见“窈窕”是摹状的叠韵联绵词。又《邶风·谷风》:“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陆德明《释文》:“黾勉,犹勉勉也。”孔颖达《正义》:“言己黾勉然勉力思与君子同心,以为夫妇之道不宜有谴怒故也。”陆德明说“犹勉勉”、孔颖达说“黾勉然”,可见“黾勉”是表示勉力而为之情状的双声联绵词。
有关语义构词,汉语学界一般都在“构词法”的名目下进行讨论。因为较为常见,不做过多分析,这里只是指出“构词法”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以供学界同仁参考。首先,根据“构词法”对汉语的复合词进行分析,一般并不能顺利地预知其真实意义,上文所述的“打印”、“司机”就属于这种现象。现代汉语中有“温床”一词,义为“对某种事物产生和发展有利的环境或重要条件”。这一意义并不是“温”、“床”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中间经过了若干次隐喻之后才最终形成的。又如“墨绿”,义为“深绿色”。“墨”作为一个名词性的成分充当“绿”的修饰成分,但是这种普通名词作状语的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具有句法上的能产性,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无法直接说“墨绿”就等于“墨”加上“绿”。其次,单音节的“字”在构造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时,未必采用其常用义项。如“马”,作为一种动物,广为人知,而它的另一个义项“大”却很少有人注意,但恰恰是这个义项构成了两个相对较为常见的双音词:“马蜂”和“马勺”。《尔雅·释虫》:“蝒,马蜩。”郭璞注云:“蜩中最大者为马蜩。”足见“马”之有“大”义,其来有自⑥。又如“国”和“家”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意义,非常常用,但作为“诸侯国”和“卿大夫的采邑”,却非常生僻,所以本来是联合式的“国家”也就经常被理解成了只有“国”而没有“家”的偏义复词。
以上所论,仅是个人管窥蠡测的一得之见,之所以不揣固陋拿出来讨论,正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以激起学界有关“字”本位语言理论的兴趣,从而使这一可贵的语言学探索不会随着徐通锵先生的过早去世而衰歇,它丰富的理论意义与潜在的实践价值理应得到充分的显露与发挥。
[注 释]
①其实当我们追问,汉字作为一种纯粹的形体符号何以也具有语音、语义时,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它记录的汉语中的那一级语言单位带给它的。因此,即便把“字”局限在文字形体这样一个狭窄的领域内,也根本无法否认在汉语中存在一级“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事实上,自甲骨文以来,汉字作为一种文字系统的性质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一直没有改变。
②在徐先生提出“字本位”理论之后,汉语学界和理论语言学界都提出了不少质疑和批评。平心而论,在这些质疑和批评当中,有不少带有想当然的色彩,比如说徐先生分不清语言单位和书写单位的基本界限,显然就并不符合徐先生本人的原意。另外,作为一种全面研究汉语所有现象的语言学理论,“字本位”涉及了从书写系统到语音、语义、语法,乃至修辞、语言心理等诸多层面的语言事实。因此,仅从汉语的某一现象(比如语法上的“自由”与否)入手,是根本无法彻底否定这一理论的合理性的。
③有关“字”的定义,徐先生自己有过不同的提法,这里采用的是《说“字”——附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鉴别标准、基本特征和它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语文研究》1998年第5期)中的观点。
④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词”既可以是单音节的,又可以是多音节的。由于我们承认单音节“字”的基础性地位,那“词”理应指非单音节(也就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那些固定单位。
⑤有关“沓”与“嘚啵”的关系,俞敏先生亦有简说。详细情形请参看《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53页的相关分析。
⑥《尔雅》所谓“蜩”,即后世所说的“蝉”,所谓“马蜩”就是个体较大的蝉。今北京周边称较大的蝉为“马嘎”(音),当为古语词之孑遗。
[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01-502.
[2]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30.
[3]叶斯柏森.语法哲学[M].何勇,夏宁生,司辉,张兆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22.
[4]周荐.论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J].中国语文,2003(2): 148-155.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WORD: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ZI-based Theory
CUI Jin-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ZI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but ZI and its research ar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s. Mr. Xu Tongqiang's ZI-based theory helps to completely reverse this situation. ZI-based theory manages to avoid the segmentation dilemma of MORPHEME or WORD, but simply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WORD in Chinese. As the basic structure unit of Chinese, ZI(one syllable expresses one meaning) can construct WORD(two syllables or more syllables express one meaning) by two ways of phonetics and semantics.
ZI-based theory; ZI; WORD; phonetic word-formation and semantic word-formation
2013-12-21
2010年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一般项目(2010JGA094)。
崔金涛(1977- ),男,河北香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从事训诂学、经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H14
A
2095-7602(2014)02-0054-04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