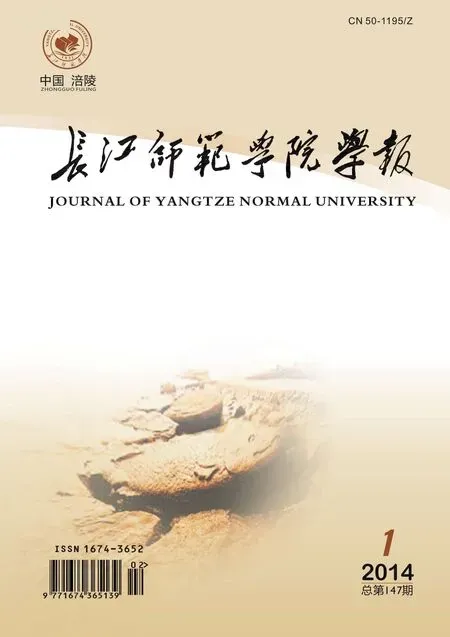石砫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
祝国超,周 凯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000)
石砫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
祝国超,周 凯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408000)
石砫土司作为重庆民族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统治石砫土司地区800余年。其间,石砫土司正确地处理了与中央王朝、周边势力、辖地百姓的复杂关系,民族间形成了政治军事互信、经济文化互动、民族和谐相处的信任和谐局面。这种和谐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为我们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史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就要正确地处理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努力促成民族间的信任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石砫土司 民族间信任和谐 民族关系
民族间信任和谐是指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和谐共处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族间政治互信、经济互助、文化互动、社会和谐,实质则是 “民族间在民族权利、民族利益和民族发展均衡的前提下出现的彼此信任、地区和谐的良性局面”[1]。中国和世界民族关系发展史证明,民族间信任和谐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及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元明清三朝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2]1在土司统治下谈民族间信任和谐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土司统治意味着战争、杀伐、酷刑和奢糜,他们据地称雄、强悍桀骜、肆为不法[3]210, “游猎,酒酣, 辄射人为戏。”[4]335那么,石砫土司统治有没有信任与和谐可言呢?这里就此作些探讨。历史上石砫土司共设三家:土宣慰司使一 (马氏,后降土通判),土宣慰司同知一 (陈氏),土宣慰司佥事一 (冉氏)[3]403、406、407。石砫土司以马氏为核心,陈氏和冉氏协其两翼,其中马氏自南宋建炎年间 (1127—1130年)至1949年,前后传承29代[5]21,统治石砫长达800余年。石砫土司在攻城杀伐、残酷压榨当地人民的同时,与中央王朝、周边势力、辖地百姓之间形成的民族间信任和谐局面值得深入地研究。
一、石砫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信任和谐
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历来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6]5。面对强大的中央政权,地方土司要保障“世有其权”就必须想办法取得并保持与中央王朝的信任关系;而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7]7310,所以对于内附土司多 “以原官授之”[4]221。双方信任源于一个 “利”字——在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共同利益需要下走到了一起。“这种政策既受制约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8]360,而双方信任关系的维持则依靠土司制度的相关规定。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土司的授职、承袭、进贡、纳赋和征调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种以社会规范制度、法律法规制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 (契约信任)。制度 (契约)信任是当事双方建立信任的重要机制,也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保障机制。波兰著名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 (Sztompka)在其 《信任:一种社会学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建立在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信任会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而受到侵蚀和损害,但是当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制度和结构不断建立之后,一种新的关于制度的信任就能产生,并且最终导致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新恢复和不断增强[9]。
石砫土司怎样取得并维系与中央王朝的互信呢?
第一是谨遵承袭规范确保信任。元明清三朝都有明确的中央王朝册封土司的承袭制度。石砫土司严格遵循承袭之法,取得了中央王朝的信任。在历史上石砫土司形成了 “嫡长子承袭”、“叔侄相传”、“子幼母袭”、“兄终弟及”、“族属袭替”等多种承袭形式[5]46-47,避免了土司争袭之乱,没有像其他土司因违规承袭而受到惩处①如洪武年间保靖土司因承袭违法而被“逮问”,结果“死狱中,革副宣慰”;正德年间容美土司百里俾弑父杀弟,结果明廷“下镇巡官验治,磔死”。见祝国超《明代中央政权对土司的政治控制探析——以土家族土司为例》,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11期。,保持了土司职权传递的持续性。石砫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在土司承袭方面业已形成的信任和谐关系,既确保了石砫土司 “世有其权”,也有利于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
第二是积极进贡纳赋巩固信任。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纳赋,其意义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它标志着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臣服与尽忠。石砫土司积极地履行贡赋义务,取得了中央王朝的信任,避免了因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而被加兵讨伐的危险,确保了石砫土司 “世有其权”,甚至获得了 “比他土司加厚”的待遇。
第三是推动文化传播增进信任。推行文治教化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思想控制、促进国家认同与民族信任的一贯做法。石砫土司自明代开始,积极地响应中央号召,自觉地接受汉文化熏陶,兴儒学,考科举,移风易俗,推动多文化、多宗教在石砫土司地区的交流交融。用儒家 “仁义礼智信德”为子女取名,修建 “三教寺”传播儒释道文化都是明证。汉文化在石砫土司地区的深入传播,满足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要求,增进了土司族人对中央王朝的统治信任和谐,推动了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互信,促进了石砫地区的稳定发展。
第四是参与军事征调提升信任。军事互信是最高级别的信任。石砫土司积极地参与军事征调,与中央王朝建立起稳固的军事信任关系,最终成为明王朝赖以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特别是秦良玉的白杆兵 “为远近所惮”[4]215,以一次抗倭、两次征 “蛮”、三次征“贼”和三次勤王的辉煌历史而被载入史册②李良品教授曾对石砫土司军事征调问题有过详尽的研究,见李良品《石砫土司军事征调述略》,载《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4期。但是彭福荣先生对“抗倭”一事有不同的看法。他梳理有关秦良玉的生平事迹、史志文献、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等,“始终不能找到秦氏抗击倭寇的直接证据。”因此认为秦氏抗倭之论难以成立。见彭福荣《秦良玉抗倭辨析》,载《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4期。,得到《明史》的浓墨重彩,崇祯皇帝更是诏见平台,亲赐良玉诗四章。对秦良玉又是 “封夫人,赐诰命”,又是 “授都督,充总兵官”,反映出明王朝对石砫土司的无比信赖。
石砫土司抓住哪些机会一步步地获得中央王朝的军事信任呢?
石砫土司的设立本就是为了军事节制九溪十八峒。元末明初石砫土司 “虽然有一定兵力,但势单力薄”[10],所以洪武八年 (1375年)九溪十八峒 “苗蛮不靖”,“杀戮村民,虏掠一空”[11]313;之后石砫土司强军保境,逐渐强大,到秦良玉时步入鼎盛时期,明王朝对其从不信任到信任直至 “离不开”。自明初以来的200多年里,石砫土司虽有 “奉调征讨”九溪十八洞 (1375年)、征散毛峒 (1391年)、征施州船山洞苗族之乱 (1466年)、征大雪山 (1594年)等 “征蛮”以及多次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不过是中央王朝“以夷制夷”、利用土司之间的相互对抗消减对朝廷威胁的操纵之法[2]36的受害者而已,反映了中央王朝对土司军力的不放心、不信任。直到1599年石砫土司“裹粮自随”大败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虽因 “督臣(李)化龙匿不以闻”无功默然而返,但此次 “征蛮”展示了实力,终因 “战功第一”和 “忠义可嘉”引起了明王朝的高度重视。1620年,清军进犯沈阳,兵部调 “石砫宣抚司兵四千人”[12]5143援辽,浑河一战付出了秦邦屏 (秦良玉之兄)和 “白杆兵”千余人战死的巨大牺牲。兵部尚书张鹤鸣说:“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4]215在随后镇守清军西图关内的要道榆关 (山海关)战役中,明朝廷把守关重任交给石砫土司秦良玉,足见朝廷对石砫土司的高度信任;1621年,石砫土司平定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明朝廷对秦良玉 “封夫人,赐诰命”,又 “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可见双方的信任和谐;1629年,清军进抵北京,“各镇自保不暇,逗留不前”,而秦良玉 “独慷慨誓众,裹粮率师,昼夜兼行”[13],进京勤王。石柱土司的忠君爱国令崇祯帝感动不已,“诏见平台,赐蟒玉,又御书诗四章赐之”[13],赞其 “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双方出现 “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间信任和谐局面。
总之,石砫土司通过在职位承袭、进贡纳赋、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忠顺,以及军事征调方面的忠勇,维系并一步步增进了与中央王朝的互信,促进了民族间信任和谐。这种信任和谐甚至还殷及子孙。“(马)应仁有罪应死,贷谪戍”[4]271就是一例。即使到了后来的改土归流,石砫马氏土司亦因 “历世忠顺”,更有秦良玉 “忠勇著天下”而获得清朝中央政府甚至民国政府的特别 “加厚”,保留 “通判”之职直至1949年11月石砫解放为止。《石砫直隶厅志》记载:“国家声教远讫,先后皆改土归流,石砫土官马氏历世忠顺,明季女土官秦良玉忠勇著天下,载明史,故地虽改设直隶厅,后裔犹世袭通判职,比他土司加厚焉”[14]。可见地方土司与中央王朝建立长期信任和谐是多么重要。
二、石砫土司与周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谐
石砫土司能够存续数百年,除了与中央王朝达成信任和谐外,自然也离不开与周边土司、地方政府和周边割据势力的信任和谐。石砫周边土司林立,土司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攻伐,关系错综复杂。如明初就有九溪十八峒 “乘乱不靖”,1375年马克用率兵征伐,导致 “贼”“深恨石砫兵强,潜走结散毛峒蛮”;中央政权、地方政府和周边割据势力也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石砫土司利益。如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石砫女土官覃氏行宣抚事。土吏马邦聘谋夺其印,与其党马斗斛、 (马)斗霖等,集众数千,围覃氏,纵火焚公私庐舍八十余所,杀掠一空”[4]271,面对地方土吏的严重威胁,女土司覃氏不得不向朝廷求援。而朝延 “命四川抚,按谳其狱”,结果仍 “事未决”[4]271,最后靠族人出面才勉强解决问题。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石砫土司与周边土司和地方势力亦战亦和几百年。它们之间靠什么维系利益平衡呢?这里以联姻为例予以说明。婚姻关系是重要的民族关系,联姻是封建利益集团避战言和、维持民族友好的重要方式,石砫土司也深谙此道。《马氏家乘·十世斗斛公传》记载:马斗斛 “妻覃氏,忠路土司女”[11]315,即忠路安抚使第七代土司覃大宁之女,因为石砫土司与司治湖北利川的忠路土司接壤,通过联姻以求避战言和、保持信任和谐;马千乘妻秦良玉也是忠县万户侯秦氏之后;播州土司虽远在贵州遵义,也被石砫土司纳入到其政治视野之中,通过联姻结成政治联盟,互为羽翼。《明史·四川土司传二》有较详细的记载:“会杨应龙反播州,覃与应龙为姻,而(马)斗斛亦结应龙,两家观望,狱遂解。覃氏有智计,性淫,故与应龙通。长子 (马)千乘失爱,昵次子 (马)千驷,谓应龙可恃,因聘其女为千驷妻。千驷入播,同应龙反。千乘袭马氏爵,应调,与酉阳冉御龙同征应龙。应龙败。千驷伏诛,而千乘为宣抚如故。”[4]271-272石砫土司不仅与周边土司缔结婚约,也曾与地方割据势力缔结婚约以求庇护。谭弦,明末清初地方割据势力,在夔州、万州、忠州等地拥兵20万。《马氏家乘·十四世洪裔公传》有载:“弦夫人马氏,公之姊也。”[11]319可见,联姻是石砫土司为了自身利益特别是势力弱小时避战言和、取得暂时信任和谐的重要方式。
三、石砫土司与治所百姓之间的信任和谐
土司手握生杀大权,好杀伐抢夺,有残酷压榨百姓的一面;但百姓乃衣食父母,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石砫土司也与治地百姓之间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谐关系。
石砫土司 “仁而有勇,轻征薄赋”,以仁心立信于民。石砫土司地方不大,但经元明清时期的大量移民,姓氏多达数十,其中大姓十三,加上马氏共十四族。土司马克用令十三族皆各 “立寨栅屯兵”。凡境内高峰绝岭,星罗棋布,皆各族屯兵边所[11]313。各寨共相声援,互为犄角,共同维护地方安全。同时,根据 “选贤用能”的原则,广泛任用乡里才德服众之人参加社会管理,沟通了管理渠道,夯实了统治基础,利用贤德之人的才德和威望取信于民。石砫土司将治所土民分为三类——舍人、里人和把人,选拔才德优秀者参与地方事务管理。舍、里、把人 “三家并用、惟贤取”,“有大事,三里峒寨头目得与参议”[11]313。石砫土司平等地对待土民、土兵,马克用 “仁而有勇,轻征薄赋,与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11]313,以仁心立信于民。以马宗大为代表的石砫土司大力兴办文教,让土民学习文化知识,促进了土民间的交流与互信。
石砫土司 “令出法随,虽亲不贷”,用制度取信于民。土司虽可 “杀人不请旨”,但是石砫土司的管理还是尽量做到了约文在先。《马氏家乘·始祖克用公传》就记载了马克用与众民约:“世官世民情同父子,世世相守毋相残害”。秦良玉规定:“凡犯有奸、淫、烧、杀罪之一者,杀无赦。”[15]84面对张献忠的大军进攻,“有议降者,有议迁者”,为了同心御侮,秦良玉发布了 《固守石砫檄文》,与民约:“毋惑妄论,毋听谣言,毋许越界,毋许私徙。临阵身必先,杀贼志必果。勿奸淫,勿劫掳,勿嚣张,勿浮动。”违反规定怎么办?《檄文》约定:“遭所约则赏有差,悖所约则杀无赦。”并且 “令出法随,虽亲不贷”[15]296。大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
总之,石砫土司精于治理,赏罚分明,平等待人,以仁心立信于民,用制度取信于民,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民族间信任和谐。万历二十二年 (1594年),马千乘之父马斗斛在石砫开矿被查亏损而贬戍口外,当时马千乘也被收系。“土吏马邦聘谋夺其印,集众数千,围覃氏”,朝延 “命四川抚,按谳其狱,事未决”[4]271,族人凑足赎金,马千乘得以出狱掌印。这件事情说明马氏土司与族人关系不错,是双方互信的结果。石砫土司形成的信任和谐局面,极大地促进了石砫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使石砫土司迅速崛起成为土司中的佼佼者。“不数年,庶富为川东冠。忠路、酉阳、唐岩、沙溪等司皆推石砫为司长,音问不绝”[11]313。民族间信任和谐促进人心归附,虽有张献忠洗川,石砫军民一心,终未陷于 “贼”。
四、石砫土司统治下的民间交流与互信
民族群众之间的互信往往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通过民族间频繁的社会交往而建立。
文化认同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重要条件,不同民族在文化交流交融与互动中相互了解、彼此认同,最终走向信任和谐。石砫土司广修 “夫子庙”,尊儒遵教促进汉文化的传播与认同;广建寺观,“三教寺”是全世界集儒佛道三教于一体的唯一宗庙,也是唯一经皇帝御批和尚可以婚配的寺庙,对促进不同宗教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互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交文人,以马斗慧为代表的马氏土司诗人群对推进民族互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济上互通有无,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重要表现和促进方式。石砫土司地区的场镇是各族人民经济贸易、互通有无、增进信任的重要场所。《石砫厅志·疆域志》有载:临溪场 “市大人稠,冠众场之首”;西界沱 “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都邑也”[14]。黄水坝场是古川楚盐道必经地,明代中后期 “已成为黄连集散地,重庆、万县、武汉、江西等地药商纷至沓来”,“估客往来络绎不绝”[5]102。场镇贸易搭建了民族间文化交融与互动、经济交往与互信的平台,不同民族群众在互通有无中增进了解与友谊,提升了信任和谐水平。
总之,石砫土司作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统治石砫土司地区800余年。在漫长的土司统治时期,石砫土司正确地处理了与中央王朝、内外土司、辖地百姓的复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民族间信任和谐的局面。这种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及其规律,为我们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民族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就要正确地处理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努力促成民族间信任和谐的良性局面。
[1]公 铭,陈永亮.文化交流交融与民族信任和谐——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年会民族理论专题会议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2]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龚 荫.中国土司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4][清]张廷玉.明史[A].李良品.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5]彭福荣,李良品.石砫土司文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6]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7][明]宋 濂.元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尤 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9]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
[10]李良品.石砫土司军事征调述略[J].军事历史研究,2007(4)
[11]马氏家乘[A].彭福荣,李良品.石砫土司文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12][清]谈 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清]王槐龄.补辑石砫厅志(卷七)[Z].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14][清]王萦绪.石砫厅志[Z].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
[15]秦良玉史研究编撰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曾 超]
K28.719
A
1674-3652(2014)01-0005-04
2013-12-26
国家社科基金“乌江流域民族间信任和谐与社会稳定发展研究”(12BMZ023)。
祝国超,男,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周 凯,男,重庆黔江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