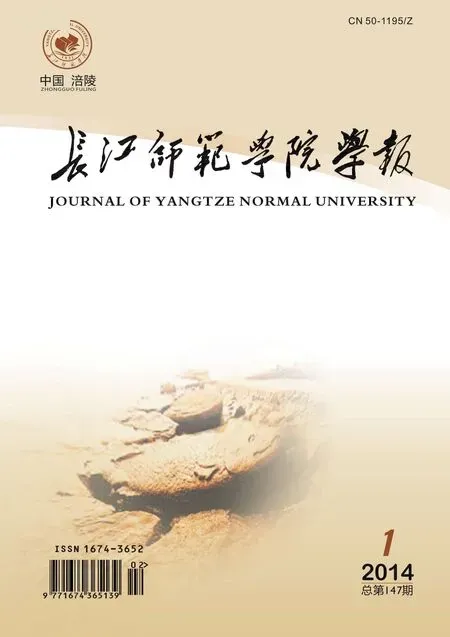试论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多民族国家意识的象征
谢国先
(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中国土司文化研究
试论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多民族国家意识的象征
谢国先
(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在各自土司等上层人物带领下,程度不同地参与国家事务。在保持各民族自身群体意识的同时,他们的多民族国家意识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贡物、从征、尊印可视为象征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多民族国家意识的具体行为。朝贡和从征既显示出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尊印则体现出少数民族对国家权威的高度认同。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多民族国家意识;象征
多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内各民族共同的国家观念,是不同民族对同一国家权威的认同。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是各民族在长期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就中国西南地区而言,大部分少数民族在明末清初的改土归流以后才完全进入封建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但这些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意识早已形成并得到不断的强化。这里略谈这种国家意识在明代西南土司阶层的具体表现,以期有助于对当代中国各民族共存关系的认识。
古代中国中央王朝虽然一直向西南少数民族推广中国一统的思想,但因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长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即维持少数民族上层世袭的统治地位。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实际上达到了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强化多民族国家意识的目的。这主要表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
一、贡物
明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向中央进贡方物,或一年一贡,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地贡物有所不同。四川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贡马,云南土司贡马、贡象,湖广土司贡大木。贡物为地方特产,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政治意义。土司进贡,朝廷回赐,固然具有朝贡贸易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可高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通过进贡活动向中央王朝效忠,主要还是要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利。正因为如此,朝贡者积极而为,甚至突破常规,或朝贡次数太频繁,或朝贡人数太多。“嘉靖七年 (1528年),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所过扰害,凤阳巡抚唐龙以闻”[1]5330。
因为交通条件的不同,北方蒙古贵族朝贡规模比南方各民族土司朝贡规模大得多。景泰三年(1453年)也先派三千多人到北京朝贡,朝廷苦于接待和封赏,皇帝只好叫也先 “自后可少遣,遣时与总数文书,否,守关者闭不纳”[2]799。
一些特殊贡品的采办和运送给地方更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万历二十五年 (1597年)刑部侍郎吕坤曾上疏,其中论及采木时说:“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 ‘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价虽一株千两,比来都下,为费何止万金。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损其数,增其直,多其岁月,减其尺寸,而川、贵、湖广之人心收矣。”[3]3962-3963吕坤之言虽有道理,但朝廷营建不停,土司献木不止。湖广之永顺、保靖,四川之永宁、酉阳,都多次贡献大木。数量或数十,或数百,往往见于史载。
贡物与回赐也可能变成敷衍,流于形式。明末谢肇淛即说:“今诸夷进贡方物,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进祖母绿、血竭、鸦鹘石之类,其真伪好恶皆不可辨识,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也矣。”[4]1565虽为敷衍而未终止,就是因为朝贡本身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朝廷对民族地方宣示主权、民族地方首领向朝廷表达忠心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从征
明代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率领土兵参加国家的军事活动,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表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由地方武装 (多为少数民族武装)参与国家号令的征伐活动,在军事上有利有弊 (有时甚至弊大于利)。这种策略的长期贯彻,就是因为朝廷和土司都能各遂其愿。
土司兵起初仅用于镇压邻境的反叛,后来也出省作战。明末朱国桢总结说:“土司惟川湖、云贵、两广有之,然止用于本省,若邻省未尝上中原一步。亦流贼时征入,用之有功。嘉靖间,南倭北虏,无不资之,且倚为重。”[5]3373用一个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去镇压另一个少数民族的反叛,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一贯做法。正统四年 (1439年)广西南丹土官 “莫祯奏:‘本府所辖东兰等三州,土官所治,历年以来,地方宁靖。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时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钤制其出没。每调军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接纳者,又先泄露军情,致贼潜遁。及闻招抚,诈为向顺,仍肆劫掠,是以兵连祸结无宁岁。臣窃不忍良民受害,愿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总理府事,而臣专备蛮贼,务擒捕殄绝积年为害者。……’帝览其奏,即敕总兵官柳溥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尔其酌之。’”[6]5496朝廷 “以夷攻夷”,其情形大抵如此。朝廷要安宁,土司要官位。输忠效命,有利可图,这是土司的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动力。
土司派兵参与国家的军事活动,既表现出他们对中央王权的拥护,也利用从征机会建功邀宠,耀武扬威。所以明代即有人指出:“土司兵最不宜调,其扰中国甚于胡虏。嘉靖 (1521—1567年)间倭警,调麻阳兵、调瓦氏狼兵,俱贻害东南最惨,而终不得其用。顷救朝鲜,又赦播州杨应龙之罪,调其兵五千,半途不用遣归,以此恨望再叛。正德(1506—1521年)间贼刘六、刘七之乱,亦调永顺、保靖两宣慰兵协剿,一路聚集,人不能堪。流贼戏谓我民曰:‘吾辈来,不过为汝梳;彼土司兵乃为汝篦矣。’盖诮其搜刮之愈密也。”[7]2874《明史》总结说:“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柱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8]1505以抗倭时使用土兵为例,“节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东南民既苦倭,复苦兵矣”[9]3602-3603。 在这方面, 多次被征调而屡有功劳的保靖、永顺土司兵也不例外。“时保 (靖)、永 (顺)二宣慰破倭后,兵骄,所过皆劫掠,缘江上下苦之”[10]5354。
朝廷以土司兵参加军事行动,虽然利害相半,但仍然久行不废。在这种军事行为中,朝廷对土司的驾驭,土司对朝廷的忠诚和期待,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尊印
明代继承传统,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各土司均需由朝廷颁发印信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统治权力。明代中后期吏治败坏,经办土司承袭的地方流官往往索贿迁延,或避嫌辗转;加之土司婚姻多变,宗支复杂,认定不易,保勘繁难,因而应袭之人有等候十余年才得承袭者[11],也有请求二三十年而不得承袭者[12],甚至有的候选人告袭至死也未得佳音[13]。虽然各级流官不断上书要求中央王朝简化土司承袭手续,但直到明末也未出现真正简便易行的承袭方法。就连应袭之人纳米不纳米、赴京不赴京之类的规定也几反几复。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央王朝力图通过土司承袭这一事件强化土司之权乃皇帝所授这样一种观念,它与君权神授的说教是一致的。土司的权威得到皇帝的认可,也就是皇帝的权威通过土司的统治而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印信成为君授权威的象征。因此,明代西南南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在内部攻讦和反流官的斗争中,往往把印信作为争夺的主要目标。
在云南武定府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土著上层之争和土流之争均以印信为焦点。《明史·云南土司》说:“嘉靖七年 (1528年),土舍凤朝文作乱。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举兵与寻甸贼安铨合犯云南府”。当时武定府尚未改流,但土知府凤诏母子已缺少实权而由流官同知掌印。凤朝文即以维护彝族利益为号召,反叛劫印。嘉靖十六年 (1537年),“命土知府瞿氏掌印。初,府印自洪武以来俱掌于土官。正德间有司议以畀流官同知,土知府职专巡捕、征粮而已。及凤诏死,瞿氏以母袭子官,所辖四十七马头阿台等,数请以印属瞿氏。吏部覆言,系旧制,宜如其请。从之”。土流之争体现为府印之争。嘉靖四十二年 (1563年),瞿氏老,以儿媳索林袭职。因婆媳不和,瞿氏欲以养子凤继祖代替索林。“不克,乃具疏自称为索林囚禁,令继祖诣阙告之。继祖归,诈称受朝命袭职,驱目兵逼夺府印。索林抱印奔会城,抚按官谕解之”。索林归武定后,谋诛继祖,继祖遂叛。“索林复抱印走云南,巡抚曹忭下令收印……”。土官之间的权力之争具体化为府印之争。万历三十五年 (1607年),继祖侄阿克等为乱,“连破元谋、罗次诸城,索府印。会流官知府携印会城,不能得。贼以无印难号召,劫推官,请冠带、印信。镇抚以兵未集,惧,差人以府印授之。贼退入武定,立阿克为知府”[14]5421-5423。综合 《明史》、《滇云历年传》 及《滇史》的记载可知,阿克等进围省城,所求无非印信而已。另据 《明史·云南土司》记载,弘治十六年 (1503年),入据孟养的麓川思氏后裔思陆“觊得宣慰司印,部执不予。于是仍数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无宁岁”[15]5460。印信实际上是地方统治权力的象征。但这种地方统治权力并非天上神灵所赋予,而是人间皇帝所恩准。从他们对印信的争夺可以看到,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已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印信的持有即意味着获得了中央王朝的支持,后者对于号召人民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与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相类似的态度,不是西南少数民族思想意识的局限,而是中国王朝观念 (国家意识)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深入人心的结果,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表现。明代西南各民族土司在其反叛活动中所期望的往往是中国皇帝领导下的地方统治权,并非指望成为与中国皇帝分庭抗礼的另一权威。
中央王朝在西南各民族中的神圣地位也导致了来自中央王朝的印信的神圣化。《滇略》说:“岁首官府开印,则自胥曹而下至于舆隶厮养,咸以红笺乞印一颗归贴门上以辟不祥。外逮塾生村氓,无不转托衙役代为请乞,动千百计。相传民间有妇为魅据者,百方祛之不效。州守闻之,令取妇衣钤之以印,是夜遂绝。然以朝廷之名器下同法司之符箓,亦亵甚矣。”[16]朝廷名器而有法司符箓之功,其社会心理基础决不仅如钤印驱魅那么简单。人们甚至认为对印信的盗用还可招致灾难。《明史》说,广南府一带,“道险多瘴,知府不至其地,印以临安指挥一人署之。指挥出,印封一室。入取必有瘟疠死亡”[17]5410,传统的灵物信仰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
明代西南其他地方少数民族在反叛活动中对印的争夺,情形与云南相似。宣德元年 (1426年),广西崇善 (今广西崇左)赵暹 “执故土官,夺其印”[18]5510。嘉靖四年 (1525年),四川茫部 (今云南镇雄)土舍陇寿、陇政兄弟争袭仇杀,陇政诱杀陇寿,“夺其印”,后来茫部改流为镇雄府;嘉靖六年 (1527年)沙保等谋复陇氏,攻陷镇雄城,执流官知府,“夺其印”[19]5363。嘉靖十五年 (1536年)贵州平浪 (属今贵州都匀)地方少数民族 “争印煽乱”[20]5484。万历元年 (1573年),广西洛容(属今广西柳州)韦朝义 “夺县印去”[21]5494。不论是少数民族内部个人之间的争权,还是少数民族上层与流官争权,印信都成为具体的争夺目标。
明代西南各地少数民族多次发起反叛,其中固然有图谋称王者,但更多的却是为了获得中央王朝认可的政治权利。反叛者企图掌握作为国家授权的象征——官印,足以证明反叛者追求国家许可的地方统治权利,这与志在推翻皇权的军事行为并不相同。夺印行为表明反叛活动的领导者是在认可国家权威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和地方群体、民族群体的利益。
朝贡、从征、尊印表明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具有强烈的多民族国家意识。地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朝贡、从征、尊印等向朝廷输诚效忠,朝廷则通过朝贡回赐、从征奖励、颁印授权等手段对这种意识加以肯定和强化。多民族国家意识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深入和普及,是明末清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治基础,也为今天我国多民族和谐共存创造了历史条件。
[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湖广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明]郑 晓撰,杨晓波校点.今言类编(卷四)[A].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一)[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6吕坤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明]谢肇淛撰,傅 成校点.五杂俎(卷之四)[A].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明]朱国桢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之十二)[A].明代笔记小说大观(四)[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18][2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广西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明]沈德符撰,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补遗[A].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〇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〇五张经传李天宠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明孝宗实录(卷四一)[Z].中央研究院缩印本.
[12]明世宗实录(卷八六)[Z].上海:上海市出版局,1984.
[13]江应樑.近代的傣族土司及其政治制度[A].民族学报(第三辑)[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
[14][15][1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云南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明]谢肇淛.滇略(卷四)M].四库全书本.
[1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四川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传·贵州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责任编辑:曾 超]
K248.7
A
1674-3652(2014)01-0001-04
2013-11-26
谢国先,男,四川雷波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