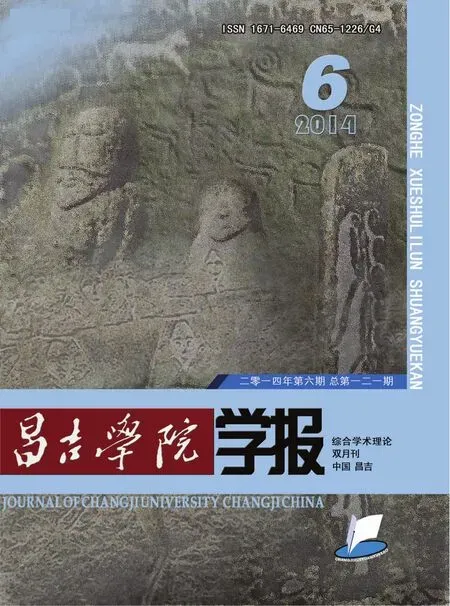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创作综论
刘 钊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金仁顺、朱文、卫慧、棉棉、赵波、魏微、朱文颖、周洁茹、戴来、陈家桥、丁天等“70年代生作家”亮相于文坛,被指称为浸染着浓厚的都市商业文化气息的“另类”写作。由于其中女性居多,文坛又有了“70后美女作家”的称谓。从概念上讲,这些命名虽有炒作之嫌,但也呈现出这一创作群体某些整体性特征和相对集中的城市生活主题。然而,作为一颗冉冉升起于东北边陲的文学新星,金仁顺个人的成长经历、所处地域与国际化都市的文化差异性,使她的创作一开始就不完全等同于“70后”写作。她的创作主题除了城市生活外,有一半取材于朝鲜民族的历史叙事,还有一些是写东北乡镇场景与生活的。她获得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长篇小说《春香》更不失为新历史小说的成功之作。除了题材广泛是其他“70后”作家无法比拟的创作优势以外,她以自己冷静的语言和有节制的叙述,严肃、理性地解剖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后复杂的人物关系,体现了独特的文学体认与追求。她在以长篇小说《春香》为标志的朝鲜民族古典民间故事的重述中,建立了理想的道德新秩序,实现了一位作家由揭示“已然”世界向建构“未然”世界的重要思想转折。
一、表征现代文化的都市场景
“70年代生作家”的小说“依托于现代都市的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以自我的生存经验作为小说的底本,改变了经典文本的背景设置、叙事方式的审美情趣,追求一种玩世不恭、狂放颓废的写作。”[1]她们作品中的都市年轻人被称为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的一代人。他们自觉地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蔑视传统的道德规范,多角恋、同性恋、混乱的性关系成为不可缺少的情节,俨然成为一种城市生活的标签。金仁顺出生于1970年,也许是这个年份与60年代太接近的缘故,也许是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经济发达程度有限的吉林长春的原因,也许是在从事专业创作前担任严肃文学期刊编辑的经历,她的创作展现出与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另类”写作大相径庭的风貌。
对于一位忠实于自我、忠实于写作的作家来说,读者总是能够从他(她)的创作中索解他(她)的生活轨迹,金仁顺就是这样。尽管她一直把城市生活作为叙事的中心,但以此为中心辐射开去的边远山区的煤矿(《五月六日》)、松树镇(《松树镇》)、莫莫格镇(《莫莫格》)、三棵树镇(《爱情进行曲》)等城镇场景,记录着她从孩童至大学的成长记忆,其个人成长的历程被粗线条地勾勒出来。这种选材方式在“另类”作家中较为少见,也表明金仁顺不是一位有意与历史隔离的作家。她尊重个人成长史,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但她同时又不盲从于历史和现实。她不回避城市生活中人们滋生蔓延的欲望,又不似其它“另类”作家们那样,仅仅将城市生活中绚烂浮华的横断面展示给人看。她是一个用文学的方式冷峻地思考和应对现实的作家,并以犀利的刀剖析着隐秘的人性弱点。
为了表现都市的繁华与消费社会的物质景观,卫慧、棉棉等人常把自己的叙述场景放置在酒吧、咖啡厅这些代表都市文化的高消费场所。金仁顺的作品中也离不开咖啡厅、餐厅,这也许是一些评论家将其归入“70后”作家群的原因。但她的叙述又不是侧重描写酒吧与咖啡厅的幽暗、混杂、低迷,更不是刻意夸张地叙写年轻人在那里酗酒、做爱、吸毒、殴斗的“另类”行为,甚至她绝少将笔墨停滞在年轻人挑衅滋事、无理取闹的空虚的精神状态中。在金仁顺的笔下,这些代表城市文化身份的场景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物质发展的表征,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道风景,是她的那些渴望倾诉、渴望对话的人物活动的必要场所。《彼此》中的女主人公黎亚非在结婚当日得知新郎郑昊刚刚与情人厮守了一整天,从此成为黎亚非婚后生活中无以排遣的浓重的心理阴影。在一次外出途中,她与长久以来手术配合默契的主治医周祥生共同目睹了一场车祸,他们惊魂未定地坐在古堡咖啡厅里,惨烈的车祸和特殊的环境使一贯沉默、压抑的黎亚非向周祥生倾诉了自己解不开的心结,由此触发了两人后来情感的进一步发展。《桃花》中季莲心与夏蕙母女俩关系原本紧张。夏蕙的父亲突然去世后,季莲心安置了一个仅供自己生活的小空间,住校的女儿与她的会面只能例行公事地被安排在剧院或咖啡厅里。金仁顺最有创意的咖啡厅是“玻璃咖啡馆”(《玻璃咖啡馆》)。因为它透视性好,三个逃课的女中学生用望远镜看到了咖啡馆里一对青年男女对坐交谈的场面。由于青年男子与一位女生心仪的偶像很相似,她们对与其对坐的女人徒生嫉妒,而那女人透明背包里的卫生巾,在她们眼里就是勾引男人的武器,所以她们决定去报复那个女人。《水边的阿狄丽雅》中的吴芳在相亲中总是要讲好朋友朗朗的故事,她从面前的一杯绿茶算命开始说起,而她的倾听者陈明亮常常是手中端着一杯咖啡……除了咖啡馆,金仁顺笔下的人物还经常出入于中高档的餐馆,《仿佛依稀》中背叛家庭的父亲苏启智请求与多年未见面的女儿相见,女儿新容把这场必然无奈又艰难的谈话放在了西式餐厅必胜客。
咖啡厅、西餐厅是喧嚣的城市中静谧又免俗的一角,悠扬的轻音乐和缠绵的灯光成为人们展露自我心灵的衬景。金仁顺小说的主人公们经常出入于这样的地带,与他们的城市文化人身份极为相符。黎亚非和周祥生都是医生;季莲心是戏曲演员,夏蕙是在读研究生;苏启智是大学讲授古典文学的教师,新容是杂志社的主编;会用绿茶算命的吴芳是研究生,被她的故事所吸引的陈明亮是中学教员……这些具有专业训练或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物,与那些都市里不谙世事又自认为深沉的“另类”年轻人群完全不同。他们有稳定的职业,有条件支付城市生活中较高层次的物质消费,却未必追求所谓的城市时尚。所以,现代城市生活带给他们的窘迫不是物质上的拮据,而是困顿的情感关系带来的精神漂泊感。相比之下,同样是空虚、失落,“另类”的年轻人依赖酒精麻醉自己,通过发泄求得暂时解脱;金仁顺笔下的年轻人(其实很多是中年人)依靠咖啡因刺激自己打起精神去面对复杂的生活。因而,咖啡厅是儒雅、老成的职业人精神的栖息地,是他们生活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人建立相互关系的“道具”。
二、析解两性关系的爱情题材
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不像亲情、友情那样具有包容性。现代婚姻和爱情中强烈的排他性决定了两性关系必然成为现代人必须面对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正是金仁顺剖析现代人精神境遇的一个切入点。在她的小说中,爱情关系似乎随处都可以建立起来:大学里的同学、师生;一起共事的同事;经人介绍的相亲;事业有成的男士在酒店、餐馆里与服务员或女大学生邂逅;萍水相逢后的相互约定;母亲与女儿的男友……在她的民族古典题材小说《春香》中,李梦龙看到情人春香的母亲香夫人时也是一见倾心。的确,爱情的本质是可以冲破年龄、民族、种族、国家、地域等因素的限制的,渴望爱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金仁顺借一系列以“爱情”冠名的小说,展现了两性关系的复杂性。《爱情进行曲》、《爱情诗》、《爱情试纸》、《未曾谋面的爱情》、《爱情走过夏日的街》等作品,描述了城市中多种多样的爱情关系,且不回避多角恋爱与婚外恋情,这是“另类”写作反传统道德观念的一面。但是,她的人物不滥情、不滥性。她写了爱情,又不唯爱情,因为爱情不是孤立的,它牵扯人的信念、忠贞、荣誉感、道德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内容,是透视坚韧也脆弱的人性的窗口。她通过爱情关系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道德观念的转变所带来的人与人关系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现象。
有人说金仁顺的小说相信有爱情,但又觉得爱情是不可靠的。这正是当下现实生活中一种无奈的常态。“金仁顺并不追究爱与欲的对抗,她的叙事理想就是通过两性之间的碰撞与勾连,打开人物彼此被日常伦理封裹的内心世界,让它们在幽暗的空间里闪耀独有的人性光泽。这种人性光泽,汇聚了真切的爱、自由、诗性的遐想,也渗透了欲望本能、背叛和生命的隐痛。它是一种生命的真实存在,却又被现实秩序封存在表象深处。”[2]在《爱情进行曲》中,李先从读大学直到毕业参加工作,一直在追寻着朱萸的影踪,并曾经不惜为她跳楼。外表随便、甚至让人感觉轻浮的朱萸一再拒绝李先的追求,念念不忘已经意外死亡的同学叶木。因而,叶木和李先成为她共同的记忆。大学毕业8年后,当她终于放下叶木时,已经有了女友的李先毫不犹豫地表示仍然爱着她。作者通过这段持久的、彼此铭心的叙述,证实了爱情的存在,但它似乎又是飘渺的,只存在于遥远的、不可触及的彼岸。现实中,烈火干柴般的爱情容易拥有却很难永久保持耀眼的光芒。当二人朝夕相处时,很快干柴就燃成了灰,顷刻间灰飞烟灭。《云雀》中事业有成的韩国中年男子姜俊赫就是这样,他到中国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婚姻。当他知道与自己同居的女大学生春风与男同学约会时,他并没有勃然大怒撵走春风。“你年纪小,我不欺负你,你也别因为我年纪老,就欺负我。”[3]这是姜俊赫挽留春风时说的话,它让读者领悟到两性之间除了两情相悦之外,还有惺惺相惜。人除了有爱与被爱的需要,还要协同作战应对人类的孤独。
金仁顺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却极少是温暖的。她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彼此》中的黎亚非,摆脱了第一次婚姻的心理阴影后,将与默契的周祥生结婚。结局却令人意外。与周祥生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前夫郑昊来到她的住处。当她得知郑昊独自承担了二人离婚的全部责任时,她与郑昊结下的郁积几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然而,周祥生坐在车里目睹了郑昊在黎亚非的住处留宿一夜的事实。黎亚非结婚前夜重复了郑昊曾经的错误,让周祥生体会了她曾经的“新婚礼物”,所以她和周祥生新婚典礼上相吻的双唇注定是冰冷的。就黎亚非来讲,这本来是一个渐明渐温的心灵故事,她情感历程的新起点却又必然地回到了原点。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婚外恋故事,深刻地阐释了人类情感恒定的逻辑关系,即越是迫切地想得到爱情,越容易被它在不经意间伤害。人在情感体验中遭遇的这种尴尬与伤痛往往是难以面对又必须面对的。金仁顺正是通过揭示这种残酷的情感,使她的作品超越了赞美爱情或泣诉爱情的层面。“像刀一样插进现实生活中”,这是她对很多70年代作家写作面貌的概括,也是对自己创作的评价。与男作家“用刀子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活儿”不一样,“女作家的写作大多数是从‘私生活’角度出发,刀子就是她本身,狭窄然而锋利。有时候对于她手下切出来的现实的切面,对于从那些切面里流淌出来的眼泪和鲜血、爱与绝望,她们自己也会受到惊吓”[4]。可见,金仁顺冷静、自觉地将写作视为刀子,用冷峻、锋利的刀刃刺破了一个个温馨浪漫的爱情之梦,审视、解剖着爱情中不可回避的血与泪、落寞与悲哀。她讲述的形态各异的爱情故事大多像《彼此》一样有一个重合的场景——受害者往往又是事端的挑起者。在恋爱的终点与起点相吻合的那一刻,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读者都徒然生出无限的无奈与悲凉,加重了叙述的悲剧性氛围。《冷气流》中的万依为了避免被自己的傻妹妹撞见,总是与李小心在壁橱里做爱。两人分手后她发现李小心诱奸了妹妹并使妹妹怀孕,便去找李小心算账。这时,她又意外地发现自己多年不见的女同学正在等待李小心一起去登记结婚,理由正是李小心在壁橱里做爱的习惯让她感到新奇、刺激。这使万依悲愤交加。然而,当李小心出现时,她亮出的刀终于因为她的紧张和饮酒过量而未能如愿地刺进他的身体。同样,夏蕙在亲眼目睹了母亲季莲心与自己男友西蒙的床上表演之后,她也拿着尖刀果断地刺进了母亲的腹部,让它随即绽放出一朵“桃花”。这朵“桃花”,因为父亲屈辱的婚姻生活而开,也因为母亲一再夺己之爱而开。这时,“从夏蕙的五官、身材、表情里面,老夏活回来了。一反往常的窝囊相,变得锋利、尖锐了,就像二十八年前的某个夜晚,这天夜里,老夏再一次变成侵略者,不过,这次不是身体,而是一把刀。”[5]父女两代人积怨下来的对季莲心的仇恨就这样终于爆发了。
三、去政治化的性别书写
金仁顺笔下这些愤怒至极亮出尖刀的人物都是女性,她们以这种极端暴力的行为指向伤害她们的对象,这与李昂的《杀夫》、池莉的《云破处》有某些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她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不仅“杀夫”,也有夏蕙这样的“弑母”,太姜那样的“弑父”(《盘瑟俚》)。由此可见,金仁顺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立场,但不持女性主义旨归。她指向的矛头不仅有男性社会对女人的戕害,还潜入人性深层,挖掘出两性共同的丑陋人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女主人公们并不追求女性主义者的新锐,不以颠覆男权社会为己任,这比一些肤浅的“另类”写作增添了严肃的社会意义。她的女主人公们在极力地调解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即便如此,她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精神打击,让她们不堪重负。当然,她笔下的男性也同样承担着情感的负累,是另一种痛。因此,她着力揭示的是女性的、也是男性的,实则为人类的纠结和伤痛。这种写作姿态决定她在情节的处理上警惕着女性主义者极端的行为误区,即她叙写的是暴力的动机和结果,回避了暴力描写本身血淋淋的场面。比如,太姜对毁了母亲和自己一生的父亲痛恶至极,将嗜酒如命的父亲按进酒缸,使其溺水而亡。同样,万依、夏蕙等人的暴力行为是人大悲大怒达到顶峰时刻的本能反击,行为的影响却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是说,她的小说并不追求李昂和池莉“杀夫”的性别政治效应,而是保持着一种平和的性别姿态;不回避女性的视角与立场,又不去刻意角逐女性主义的政治话语权。诚如她所言:“作家的性别问题算是个问题吗?只要写小说,性别视角自然就呈现其中,但这跟作家要表达什么没多大关系吧?跟如何表达可能有些关系。”[6]
因为金仁顺不是过分地强调自己的性别,她对女性情感细致入微的观照才自然而然地呈现敞开状态,避免了女性主义写作中常常出现的偏执。她的叙述视角是灵活多变的,叙述人的性别也男女都有,但以女性居多。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以自我的身份体验了男性的背叛,如《人说海边好风光》中的李江波、《仿佛依稀》中的苏启智、《听音辨位》中的博士、《酒醉的探戈》中的朱光明、《秘密》中的朋克等。他们背叛爱情与婚姻,给女性带来难以平复的情感重创。例如大学教师苏启智解除了与妻子、女儿的家庭关系,与学生徐文静结了婚。这种打击改变了女儿新容与母亲原本坦然自如的生活节律,从此她们整日在局促、压抑中过活,被抛弃的感受难以释怀,造成新容对交友与婚恋的怀疑和躲避。虽然苏启智患癌离世后,新容与母亲豁达地接受了徐文静,但已人去事非,悔过和遗憾不能治愈过往的伤害,宽容和谅解也不能抚平当初的伤痕。或者还有一种自认聪明的报复,如罗晶发现导游杜新颖与丈夫的隐秘关系后,放下了对自己肉体的禁锢以找寻与丈夫不忠行为的心理平衡,同时,她又巧妙地离间了丈夫和杜新颖的关系,可谁又能说他们之间的裂隙可以黏合无痕呢!金仁顺在情感的伤害与被伤害中,总是站在弱者一方的立场上。不幸的是,被伤害的往往是女性。这使她的作品因倾向于弱势群体而产生理智、悲悯的艺术魅力。
四、基于民族古典题材的女性历史想象
有评论家以“孤独的棋手”形象地评价金仁顺的创作,说她像一位棋手一样冷静地俯视着人世百态、人间冷暖[7]。但是,当面对现实这盘棋时,她难免有所犹疑、举棋不定,原因就是,现实复杂、僵滞的两性关系所演绎出来的人们的精神困惑并没有因为她笔下的人物举起刀而迎刃而解。为此,女性的自我救赎在现实生活中显得软弱无力。然而,当视野由无解的现实转向古典题材的“高丽往事”这盘棋时,她立刻就卸除了现实的僵局,变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她说:“古典题材的小说,我偏爱的是它写法上的不拘一格,故事可以脱离日常,违反规则,这类小说又跟我的民族身份息息相关,写作的时候有种释放的快感。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对我而言,相当于‘放假’或者‘回家’。”[8]在这个与现实的时间、空间跨度很大的叙事场域中,她找到了破解两性僵局的棋法。
金仁顺的朝鲜民族古典题材创作开始于1999年,陆续创作了《伎》、《高丽往事》、《盘瑟俚》、《小城故事》、《引子》、《乱红飞过秋千》等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创作起步晚于现实题材的创作,恰好说明她的创作个性逐渐形成而与“70后”作家群体的“另类”道路越来越远。从那时起,她寻求现实救赎与创造理想新世界的创作思路互为表里,并驾齐驱,在时间与空间的突围中尝试破解两性在现实生存中的困境。正是因为在现实题材中她冷静地持着解剖的刀,将现实解剖得太透彻,她才回到本民族的古典叙事中舞动起浪漫的旗帜,以自由无羁的想象为女性开创自己的理想世界。在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春香》时,她说:“这部小说里面,男人全是女人的配角。正好跟古代朝鲜,女人无条件地成为男人的陪衬形成反差。香榭里的人,被丈夫抛弃的银吉、小偷的女儿小单、歌妓的儿子金洙,凤周先生虽是贵族,落魄到流落街头,也很难有什么尊严可言。他们都是与现实生活充满对立的人,是弱势群体,但在香榭里面,他们过着幸福的、几乎可以说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组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小世界’”。[9]她的创作意图很明显,她不仅要用自己的文字创造古代朝鲜族卑微的女性历史的新篇章,还要为这群底层人物建造一个富有、美丽、幸福的乌托邦家园。
《春香》问世之前,她在上述古典题材创作中已经有了一系列关于李朝南原府为背景的叙事,香夫人、春香、李梦龙、卞学道等人物形象再次出现并在《春香》中得以成熟。在《伎》中,男主人公李梦龙怀疑“女人的爱情是可靠的吗?”[10]这与金仁顺现实题材创作中的认识是一致的。为了实现嫁入豪门的理想,香夫人和春香用尽心机,通过了暗行御使大人李梦龙的考验,并使李梦龙为春香举行了耗资巨大的结婚大典,成为李朝最著名的婚典之一。虽然此时的春香因为不能过上母亲香夫人那样的自由生活而感到遗憾,但她毕竟走上了令人羡慕的“灰姑娘”般世俗女人的成功道路。然而,在《春香》中,虽然香夫人、春香、李梦龙三个人物的关系没有改变,小说的情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香已经不再是《伎》中的春香。她已不屑于追求爱情,而将自己的热情完全投入在研制草药中;她的理想不再是嫁一个白马王子,摆脱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是继续建造母亲的“香榭”,让香榭中的所有人永远过着富足的生活。这是一种具有乌托邦思想内涵的反叛现实的设想,它的途径不再是女性举起无力的刀尝试破坏坚韧的事实,而是插上想象的翅膀穿越古代朝鲜族女子地位低微的传统自由地飞翔。为此,《春香传》中贵族施予民间女子的爱情“神话”模式坍塌了,进而为彰显出的女性主体性所取代。当春香和李梦龙感人备至的爱情故事传到京城李梦龙的耳朵里,李梦龙回到南原府为春香背诵她写给自己的情诗,春香坦然地说:“真有趣,我连听都没听过。”[11]金仁顺虽然没有否认爱情这份美好情感的客观存在,但是,她借春香之口向女性群体大胆地宣言:“在丢失了爱情的岁月中,我们不做一个男人家里的女人,而是成为许多男人梦里的女人。”[12]由此,女性被动、屈从的地位被碾碎,富有现代意味的女性主体性油然生发出来。因而,春香拒绝了李梦龙公子的求婚,继续留在母亲的香榭里,以美貌保障她在贪于美色的达官贵人之间斡旋并攫取财富,以她研制的特效药来保护生活在香榭里的所有人的平安。
如何让传统社会地位卑微的女性得以生存,且不重蹈女性悲剧历史命运的覆辙,金仁顺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她通过香夫人、春香母女两代人的形象塑造,为女性寻求生存之路。香夫人的美貌使她的名声之大可与南原府比肩,所有知道南原府的人就知道有香夫人,致使京城的官吏都慕名而至。香夫人在春香的生父去世后还能支撑着香榭的秩序,除了她的美丽还有她的智慧。智慧使她在达官贵人之间左右逢源,一次次规避了不幸的降临。因此,美丽和智慧是女人做许多男人梦中人的资本。但是,春香除了有与香夫人一样的美丽和智慧,还有香夫人所不具备的才能。香夫人为了让春香学习知识,特意为她请来凤周先生做她的老师,也让金洙和小单做她的同学,陪她读书。她为春香创造了从小在香榭自由自在的生活环境,使她无拘无束地在外公的药房里玩耍,阅读了外公撰写的全部药书,对医药产生浓厚的兴趣。她一直在研制一种奇异的药,它可以让自己不喜欢的人喝了之后失去记忆。香夫人为了阻止卞学道娶春香的邪恶念头,自己与卞学道一同喝了春香研制的药,牺牲自己保护了春香。由此可见,金仁顺在建设女性理想的生活时,不仅强调女人的美丽,还强调女人要有制服男人的智慧与才能,才能来自于知识。在《春香》的结尾,作者改写了朝鲜经典《春香传》的结局。春香并没有与李梦龙私定终身,也没有喜结良缘。春香的这个选择撕毁了千百年来朝鲜民族民间传说的浪漫想象,建立起作者新的理想,即为女性搭建一个香榭。“香榭的名声也许为外界所不齿,但这是一个能够让人尽情呼吸、自由生活的地方”。[13]春香从来就不认为母亲香夫人以美色换取巨大财富是耻辱的,所以,她违背了母亲希望她嫁给上层社会的意愿,要以母亲养育她的方式养育母亲,以母亲维护香榭的方式维护香榭,使女性和底层人可以永远安居在乌托邦乐园。
五、结 语
自上世纪90年代末“70后”作家群的概念出现后,批评界一直想为这个因年龄而聚合的创作群体总结出共同的创作特征。金仁顺本人并不排斥自己被纳入“70后”这一作家群体。但是,当金仁顺古典题材小说创作出现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她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了,也预示着她必将成为“70后”中卓尔不群的一位作家。这不仅源自她开始创作时就与一些“70后作家”崇尚的“另类”写作不同,更重要的是她的民族身份在她的性别身份之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资源。这位“另类”群体中的“另类”,不为商业利益所驱动,不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不追求作品的数量,对影视剧等大众文化样式持有警惕的态度,对于时下趋之若鹜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十分谨慎,她说:“我从来没有过‘大’的念头,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写短篇了。”[14]这进一步证实了她一贯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态度。正如董之林在反思包括“70后”女作家在内的小说创作时所期望的那样,“说不定哪一天,女性写作给读者带来关于历史更多的想象和惊讶:原来历史是这样的,至少在女人眼里是这样的”[15],这个期待在金仁顺的《春香》创作中实现了。她在商业化写作的喧嚣之外,表达了叙述历史的愿望。她的成功转型既有现实给予的启悟,又离不开朝鲜族文学经典的丰富给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在阅读金仁顺这一代人的创作时不免会滤去“70后作家”、“另类”写作、美女作家等不乏商业意味的概念回归到文本本身。金仁顺在现实题材中冷峻地剖析“已然”的生活现状,在古典题材中极力创造女性为主体的“未然”的理想世界,形成了解构与建构合璧的主题走向,完成了她创作中一次重要的思想转折。这正是金仁顺在“70后”作家群体中的意义,即以一贯严肃的写作姿态,坚守着纯文学的创作阵地,并以不断地追求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1]王丽霞.多语喧哗的审美状态——九十年代城市小说虚实形态略论[J].理论与创作,2005,(4).
[2]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J].文学评论,2011,(4).
[3]金仁顺.云雀[A].金仁顺.彼此[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83.
[4]金仁顺.之所以是我们[A].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5]金仁顺.桃花[A].金仁顺.彼此[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63-64.
[6][8][9][14]姜广平.身居东北的南方叙事风格——与金仁顺对话[J].文学教育,2011,(4).
[7]于若冰.金仁顺:孤独的棋手[J].当代作家评论,2004,(5).
[10][12]金仁顺.伎[A].金仁顺.玻璃咖啡馆[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47,42.
[11][13]金仁顺.春香[M].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220.152.
[15]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J].文学评论,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