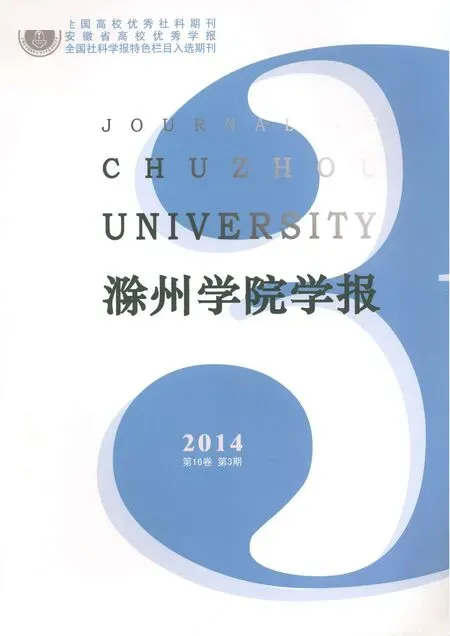安徽当代知名作家的文学史意义
——以耿龙祥、鲁彦周、公刘等为中心
黄晓东,明飞龙
安徽当代知名作家的文学史意义
——以耿龙祥、鲁彦周、公刘等为中心
黄晓东,明飞龙
安徽当代作家耿龙祥以其短篇小说《明镜台》闻名“十七年”文学史;鲁彦周以其小说《天云山传奇》奠定了在“反思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并闻名全国;公刘以其紧贴现实与政治的新诗写作成为当代著名诗人;潘军则以其先锋实验在先锋大潮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正是这些独具个性的文本写作以及最终形成的知名作家群体,奠定了安徽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耿龙祥;鲁彦周;公刘;潘军;文学史意义
安徽当代知名作家“评价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就是评价作家的文学史价值。因此,本文将以耿龙祥、鲁彦周、公刘、潘军等安徽当代知名作家为中心,考察当代文学史上包括当代文学史教材中如何对其文学创作进行阐释定位并评价其文学史意义。当然,对文学史著中相关的叙述与评价是否妥当作出分析,也是本文写作的内容之一。
一、耿龙祥《明镜台》的文学史意义
安徽作家耿龙祥已经于2007年在安徽安庆过世。他一辈子的创作并不多,但是他发表于1957年的短篇小说《明镜台》却“知名度”很高,一般的当代文学史在“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大都会提及这个文本。不仅如此,众多的“当代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选”也将其收入其中,因此其经典文本的身份已然确立。那么小说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只有两千来字的《明镜台》讲述的是在“革命”刚刚胜利的1950年代,革命干部“我”受命为厂里的墙报“明镜台”写作一篇“想当年”的文章。于是“我”想起了当年革命受了伤,在大别山“埋伏”下来,当地大娘照顾“我”如亲儿子,伤愈后又送“我”出大别山。临别时大娘说“希望你……”。大娘希望什么?作者暂时无法继续写下去。这时作者又将故事拉到当时:在“我”构思“想当年”结尾的时候是一个大雪天,“我”家里保姆的女儿取牛奶去了,要走两小时的路,“我”的妻在打毛衣,她就是不让保姆去迎接她取牛奶的女儿,最后保姆女儿掉进了水沟,送进了医院。但是妻子却说“那个小姑娘的手里有没有拿奶瓶?这要真是阿早(保姆的女儿),我们宝宝明早上吃什么呢?”。故事最后这样结尾:“从此‘我’就对我自己,对我妻子,都有了意见——我们都是国家的干部,而且是在工厂里工作,然而我们把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忘记了。我要找时间跟她好好儿谈一谈”[1]。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主题与结构,不禁想起萧也牧同一时期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它们都是对“革命”之后作为干部的“我”如何对待新的环境,如何对待“保姆”,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当年大娘的“希望”的一种思索。这两篇小说作者的命运也颇为相似。《明镜台》因为发表在1957年第1期《人民文学》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作者被划为“右派”,直到“文革”结束才复出,《明镜台》也获得“平反”,成为“重放的鲜花”。对耿龙祥及其《明镜台》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涂光群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述,这里不再赘言。
在“新时期”之初的当代文学史著中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算是较早对《明镜台》作出分析的。其中认为耿龙祥《明镜台》是“短小精悍的讽刺小品,别具一格……触及到我们生活中一些消极阴暗的东西”。而对于《明镜台》在文学思潮中的意义,该史著则认为:在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文学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开始初露苗头,作家们“不甘心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作浮光掠影的描绘和虚假的粉饰,也不愿在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或者对这些问题作隔靴搔痒的回答。他们敢于反映真实的生活,敢于抒发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在恢复,发扬和深化”[2]。也就是说,《明镜台》与当时很多的文本一样开始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提出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明镜台》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秦兆阳的《沉默》等一道汇成了“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其后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对《明镜台》的阐释并未有大的变化。虽然洪子诚在《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将1949年至“文革”结束这一时段的当代文学划分为“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非主流”指的是在当时要求“一体化”的政治规范内,那些表现出“异质”“另类”“启蒙”“先锋”“自由主义”特征的写作。洪著中认为耿龙祥的《明镜台》正是构成这股“非主流文学”思潮中的一个代表性文本。
也有一些文学史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们将《明镜台》等“百花文学”时期出现的“干预生活”、揭露现实中所存在问题的文学思潮与同一时期“苏联”的“解冻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接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耿龙祥的《明镜台》等文本与“苏联”的“解冻文学”有了联系,这是“比较文学”的视角。持这种观点的文学史著如朱栋霖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书中对此种联系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国恩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的《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章在分析《明镜台》等文本的同时,指出苏联“解冻文学”的特征主要为“写真实”以及对“人”和“人道主义”的呼唤,而这对当时中国“百花文学”中“干预生活”创作思潮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系。检视最新的当代文学史著,我们发现对《明镜台》的研究未有最新的评价出现,如2011年朱栋霖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17-2010精编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将《明镜台》等文本置于“探索‘生活’的边缘”这一视角之下进行分析,但是定位仍然是“干预生活”的小说。因此,耿龙祥《明镜台》的文学史意义可以定评为在当时“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所出现的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以及对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类小说文本。尽管这股创作潮流在随后政治氛围的逆转之下迅速消失,昙花一现,但与“文革”之后的“反思文学”某种程度上其实接通了脉络。
二、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的文学史意义
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并且因为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出现,使鲁彦周以及这个文本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小说在“新时期”之初声讨“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出现,但是究其根本,其故事模式今天看来完全可以概括为“政治加爱情”,如果抽去具体的年代和革命具体的内容,其情节构成和文化内涵与现代文学史上曾经非常流行的“革命加爱情”模式也是颇为相似的。故事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新时期”一个叫周瑜贞的姑娘在天云山区与男主人公罗群的偶遇开始叙述,然后通过女主人公宋薇的回忆将故事的时空拉到1950年代:女学生宋薇和冯晴岚到天云山区考察,考察队的政委罗群由于和宋薇相互爱慕而坠入爱河。但是爱情却很快遭遇到了政治,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罗群被划为右派,在政治的压力和打击之下,宋薇和罗群结束了恋爱,嫁给了领导吴遥。爱情故事还在继续,女学生冯晴岚顶着压力并秉持自身的政治判断,嫁给了“右派”罗群,并在当地的小学从事教育工作,生活得含辛茹苦,贫病交加。文革结束之初,在生活迎来曙光的时候,宋薇的丈夫吴遥却在罗群的“平反”问题上百般阻挠。此时的宋薇感情却占了上风,她毅然与丈夫决裂,去援助生活在贫困与政治双重压迫之下的罗群夫妇,但是冯晴岚却因为操劳过度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对小说文本《天云山传奇》进行文学史定位的过程中,仍然遭遇到了政治。例如,在《文艺报》1982年第6期上刊发了署名蒲晓的文章《对影片〈天云山传奇〉的一点异议》,尽管是针对电影,但也就是针对小说。该文中的“异议”主要是:一,故事没有很好的体现党在“右派”改正过程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正确的政策,尤其是吴遥形象的塑造。二,吴遥形象的塑造,相对于“三突出”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三贬低”。因为像吴遥这种阻挠“右派”平反的人是有的,但是把吴遥塑造成先把人家打成右派,又夺走人家未婚妻子,这样的干部是难以找到的,因此吴遥这一形象缺乏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样导致故事前半部分叙事的成功、后半部分的失败。针对这样的“异议”文章,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立马就有“反弹”的文章出现,如童庆炳的《可怕的政治偏见》、孙冶方的《也评〈天云山传奇〉》等。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交锋之中小说文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198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天云山传奇——从小说到电影》一书,书的第三部分为评论集,登载了钟惦棐、周介人、谢晋等人的评论文章,论及了小说文本及其影视的改编,其中也包括鲁彦周本人的文章《〈天云山传奇〉创作的前前后后》。
1979年发表于《清明》创刊号的《天云山传奇》在当代文学史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新时期”较早出现的由公仲主编、丁玲作序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中,已经开始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评价“新时期”短短几年的文学创作。编者对“新时期”的文学从思潮的角度做出了总结并且指出:“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的延续和深化,而在文体上“伤痕文学”以短篇小说为主,“反思文学”则以中篇小说为主。同时,在该史著中编者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纳入到“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的同时,对其在文学思潮中的价值作出了概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等一系列小说无论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人物的塑造,艺术表现手法等诸方面,都比‘伤痕文学’成熟得多。这些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较强的现实感。‘反思文学’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3]。对《天云山传奇》文学史意义的评价近三十年来一直未有大的变化,例如在王万森等人2006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中仍然持如上观点,只是对反思小说的文本的界定加入了古华《芙蓉镇》、谌容《人到中年》及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这一点也是当下文学史的共识。该史著还强调指出《天云山传奇》是最早对“反右运动”进行反思的优秀小说。这样,对该文本当代文学史意义的评价也基本固定下来。
三、公刘在当代新诗史上的意义
当代诗人公刘“新时期”之初到《安徽文学》杂志工作,2003年在安徽过世,因此我们将其纳入安徽当代知名作家之列。公刘的新诗写作开始于1940年代,但其创作的两个高潮主要为1950年代的“南下”“北上”时期,以及“文革”结束后作为“归来的诗人”时期。公刘1950年代写作的第一个高潮期是在西南边陲,在洪子诚、刘登翰所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将其与白桦、顾工、周良沛、杨星火等人一道归入“西南边疆诗群”。而在程光炜所著《中国当代诗歌史》中亦是将其纳入“西南边陲诗的异地想象”这一论题之下。而在这一诗歌创作潮流之中具代表性的诗人史著都首推公刘。公刘此一时期写作的“边陲诗”最具影响力的被认为是《西盟的早晨》,诗中“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几句,为众多文学史在评价公刘时所引用。《西盟的早晨》其实不是一首单纯写景的诗,而是一首颂扬边陲军人的诗,因此这首诗在1950年代广为赞誉,并获得艾青的好评,认为公刘是将自然环境、战斗任务、诗人最清新的情绪完全糅合在了一起。可见公刘诗歌创作在当时的新诗潮流中是和时代政治文化的要求相一致的,因为即使在《雨后小景》这样的诗题之下仍然是对边陲哨兵的颂扬和赞美。类似的表现宏大主题的诗作还有《母亲澜沧江》、《兵士醒着》等文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抒写的具有异族风貌的《茶园情歌》、《三个卖棉花的哈尼姑娘》、《格朗和情歌》等文本虽然疏离了宏大的时代题旨,但其和同时期的边疆诗人闻捷所写作的《苹果树下》等文本一样,反而更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公刘对时代主题的抒写一方面是时代的驱使,另外一方面从创作心理学来说,与作家的创作个性也有重要关系。正如公刘在《说说我自己》一文中所概括的,他的性格与为人绝对的清高,但是又绝对的“入世”。正是如此,在1956开始的“鸣放”的氛围中,他创作了寓言诗《刺猬的哲学》、《乌鸦与猪》,成为此后其被划为“右派”的罪名之一,这两首诗还被与流沙河的《草木篇》相对应,称为“禽兽篇”。其右派罪名中还有几首当时创作的短小含蓄的爱情诗,因为其表达了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主题”。例如,《小夜曲》、《迟开的蔷薇》、《还把贝壳遗落在沙滩》、《羞涩的希望》等。1957年诗人被划为右派之后,就停止了公开写作,直至新时期之初复出,成为“归来的诗人”,但公刘在当代新诗史上知名诗人的地位却是在“十七年”时期奠定的。
新时期之初,与众多“归来的诗人”一样,公刘一边开始了对此前的当代史的反思,一边继续对现实生活进行关注和“干预”。此间诗人先是创作了《爆竹》、《星》欢呼文革的结束,创作了《白花红花》献给周恩来的八十诞辰。其后开始陷入对历史的“沉思”,写作了《告别庐山雾》、《庐山剧场》等。而悼念张志新烈士的《哎,大森林!——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刑场》则是诗人新时期写作的一个高潮,诗歌的结尾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时代的警示。前一个文本中诗人把张志新比喻为森林里的啄木鸟,正是它们保护着森林的存在,诗人写到“海底有声音说:这儿明天肯定要化作尘埃,假如,今天啄木鸟拒绝飞来”。而后一个文本中对张志新临刑前刽子手为防止她呼喊,先割断她的喉管这一残忍行为,公刘写到“难道万物都一起哑啦?哦,可——怕!……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哦,可——怕!”。如前所述,诗人的写作始终紧贴时代紧贴政治,例如早在1940年代就创作了《什么是革命》(1947)、《中国要爆炸》(1947)等文本,此后的创作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政治和历史的大逆转时期过去之后,诗人的写作也逐渐陷入了一种困境。正如洪子诚等人所言,公刘“通过激情宣泄方式对社会政治问题做近距离透视的作品,在当时曾获得热烈的社会反响。但是,社会生活、思潮后来发生的变化,以及诗歌艺术出现的‘转移’,使这种看取现实的角度和方式难以为继”[4]。程光炜的观点则更为明确:“公刘的‘政治意识’过分强烈,他的思想态度、艺术才情也许更适合与历史转折期的社会情绪。从他身上,暴露出过于接近政治问题的风格上的弱点——当然,这也是他同时代诗人艺术上的‘宿命’”[5]。这些也正是对公刘新诗史意义较为恰当的评价。
四、潘军在当代小说史上的意义
潘军的文学创作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82年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啊!大提琴》在《北京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小说的内涵看仍然属于当时流行的“伤痕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凌石的小提琴手因为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拒绝演奏《苗岭的早晨》而被调离“前途无量”的小提琴手的席位,去改拉大提琴,他的女友也因此而离开了他。1987年潘军将早期的十个文本结集为《小镇皇后》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这些小说文本中仍然以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写作的主题与艺术规范。但是从这些早期文本中仍然可以看出其对小说艺术的追求与尝试。例如在故事结构上营造戏剧冲突,设置悬念;叙事中大量出现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以及意识流的运用。正是对小说艺术的兴趣与追求,使其在此后以“技术实验”为主的先锋小说写作中如鱼得水。
潘军真正进入当代文坛正是从先锋小说写作开始的。继1987年在《北京文学》第10期上发表中篇小说《白色沙龙》之后,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此后其写作了《南方的情绪》、《流动的沙滩》等大量具有先锋特征的文本,直至1992年在南京《钟山》杂志连载了长篇小说《风》,其先锋写作才告一段落。其先锋文本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表达了对生活以及文学的一种遐想及妄想,如小说《流动的沙滩》、《悬念》等;小说主人公对自我存在的切实性产生了怀疑和恐惧的心理以及因此所进行的一种探险,如小说《南方的情绪》等;小说表达对历史的真实性的怀疑与探寻,《蓝堡》、《结束的地方》和《桃花流水》等文本都选取了历史作为故事的背景表达“我”对历史存在的切实性产生的一种怀疑;小说的人物经常会扮演类似“侦探”或“窥视者”的角色,在文本《南方的情绪》和《爱情岛》中,叙述者“我”一开始就都被一个谜或者谜一样的事物所引诱而去进行一种揣测和侦察。在这些文本中先锋小说常见的叙事特征也都显露无遗:如《白色沙龙》中叙事的粗鄙化,尽管从中可以看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子》;《流动的沙滩》中元叙事的大量运用,这种叙事策略早从博尔赫斯及马原就已经开始;历史化的叙事策略,《蓝堡》、《夏季传说》、《风》等将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对第一人称叙事的偏好等。当然,潘军的先锋小说也有自身的写作个性:例如文本中对心理真实的追求,也即在心理描写中往往透露出叙述者本人真切的个人体验,正是这些个人的生活感受与心灵体验与读者构成最为直接的对话,正如鲁枢元所评价的,“潘军小说心理所占的比例很大,但很多先锋作家则是排斥掉这些,排斥掉主体和心灵,讲究零度情感,特别重视言语的操作,而少了精神层面的东西”[6]。再如对性描写的节制也是其先锋写作中的个性特征之一。先锋写作使潘军成为当代知名作家,其在先锋小说潮流中的意义可以概括为承前启后。“承前”指的是在1990年前后很多先锋作家都开始出现了写作的转型,开始收敛了技术试验的锋芒,或者退出先锋写作,正如文学史家所言:“1989年前后与‘新写实小说’的联合就是先锋小说撤退的一个突出表现。苏童、余华、北村等人都已开始热衷于故事性文本的创作,叶兆言甚至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作家”[7]。但是,在此期间潘军仍然在执着地进行着他小说形式的实验,写作了先锋色彩浓厚的文本《流动的沙滩》、《蓝堡》及《风》等。“启后”指的是在先锋小说潮流的第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潘军的写作也渐渐地开始走出“历史的迷雾”,和这一阶段出现的晚生代先锋作家,如韩东、林白、陈染等人一道,开始了对“现实”的言说,潘军小说的故事性也有所增强,如他的以当代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杀人的游戏》等文本就是如此。这些小说在保留着一些此前的个性特色(如将叙事与个人体验和人生感悟相结合)的同时,仍然将先锋小说的一些叙事策略(例如元叙事)恰当的沿用到小说的叙事中去。潘军对先锋中形式实验的执着精神,以及在整个先锋创作潮流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最终使其获得“先锋作家”的称号,并在先锋潮流中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位。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其后他对城市状态的书写以及回忆性三部曲《独白与手势》等文本,因为一如既往的个性化内涵而奠定了其当代知名小说家的地位,2003年也因此被出版界称为“潘军年”。
综上所述,正是耿龙祥、鲁彦周、公刘以及潘军这些当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知名作家的出现,使安徽当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有了自身的一席之地。尽管与“文学陕军”“文学鲁军”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依然对“文学皖军”(姑且称之)的未来依然充满期待。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1949-197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7.
[2]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2.
[3]公 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458.
[4]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4.
[5]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8.
[6]潘 军.坦白——潘军访谈录[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18-119.
[7]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99.
The study on AnHui famous writers'literary significance
Huang Xiaodong,Ming Feilong
Lu-Yanzhou'sTianYunshan legend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in reflecition literature trend;Gong-Liu's poety paid close attention on politics and reality and became famous poet;Pan-Jun's Pioneer fiction played a continual role in the trend.These famous writers established AnHui literature's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history.
Geng-Longxiang;Lu-Yanzhou;Gong-Liu;Pan-Jun;literary significance
刘海涛
I206.6
A
1673-1794(2014)03-0057-05
黄晓东,铜陵学院文艺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安徽铜陵244000);明飞龙,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江西赣州341000)。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338)
2014-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