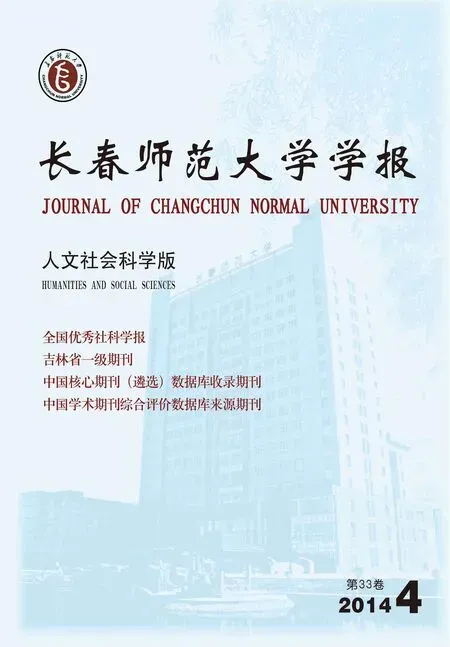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初探
王彦华,颜铁军
(吉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初探
王彦华,颜铁军
(吉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泛指吉林省西部蒙古族聚居地所产生和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是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中的一个类别。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具有创作时间集中、题材内容集中、人物对象集中等特点。对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的欣赏不仅会引起我们情感上的共鸣,还能够启发我们对人生幸福的思考。
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叙事民歌;短调;悲剧性
郭尔罗斯位于吉林省西部地区,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三原(东北平原、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重叠”、“三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和嫩江)交汇”、“三山(长白山、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环抱”之中。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泛指吉林省西部蒙古族聚居地所产生和流传的蒙古族民歌。
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题材极为广泛,内容也非常丰富,无论是社会斗争、农牧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事件等,在民歌中均有所见。从演出的内容来看,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可分为好日民道(婚礼歌)、玛克塔林道(赞歌)、苏日嘎林道(教诲歌)、聂勒音道(宴歌)、依那嘎道(情歌)、萨那林道(思念歌)、高木达林道(怨恨歌)、嘎斯楞道(苦歌)、呼和特音道(儿歌)、太嗨梅林道(祭祀歌)、博道(蒙古萨满教歌)、安代道(安代歌)等。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不仅是高木达林道(怨恨歌),在其他题材的民歌中亦有大量的悲剧性内容。
一、创作时间
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的创作时间比较集中,多数产生于二十世纪初至40年代。[1]2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的创作时间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二姑娘》、《金姐》和《龙梅》分别创作于1920年、1930年和194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只是自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创作的。蒙古族民歌就如同是宴席上的醇酒、奶茶中的咸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伴当。正如蒙古族著名作家苏赫巴鲁在诗中所言:“牧草数不清,民歌唱不完,马背是翅膀,民歌是语言”。蒙古族还有另一特点,即习以传唱、不善传抄。①这样一来,虽然有许多优美动听的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牢牢地挂在歌手的琴弦上,满满地吞在肚子里,但却往往随着歌手的殁世而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二十世纪以前也存在着大量的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只是因为无人记载、传抄而永远地消失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和听到如此多的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要归功于一大批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专门从事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的抢救、挖掘和整理工作的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们(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苏赫巴鲁先生)。从他们工作的时间和可能采访的对象来推测,这些民歌恰好主要产生于二世纪初至40年代。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历史时期,民歌的内容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连,所以这个时期创作的民歌注定具有悲剧性。
二、悲剧题材
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在题材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婚姻爱情方面。例如,著名的民歌《二姑娘》所描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悲剧。二姑娘是一个姑娘的名字,是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公太爷图普乌勒济图的二女儿。她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会作诗写文章。长大后,父亲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势地位,把二姑娘嫁给了敖汉旗王爷的贝子为妻。二姑娘嫁到敖汉旗后,因长相不漂亮而与王爷的贝子不和睦,婆家人也都看不上她。其丈夫性情暴烈,冷酷无情,经常对她拳打脚踢,甚至棍棒相加。二姑娘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度日如年。每次回到娘家,二姑娘都会向母亲诉说自己的委屈和痛苦,其父亲由于受王室贵族封建礼教的限制,又胆小怕事,非但不为女儿出气撑腰,还要求女儿不许有离婚的念头,更不得做出有损娘家门风的事情。父亲为了改善两家的关系,经常派人到敖汉旗府上给亲家送去金银财宝等厚礼,但二姑娘的处境却依旧如故。后来,在1891年的动乱中这个出身豪门而命运不幸的女人含恨离开了人世。《龙梅》、《八月》、《腊月》、《水灵洪格尔》等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也都是以不幸的爱情婚姻为题材创作的。我们知道,能够作为悲剧民歌创作题材的不仅只有爱情婚姻。事实上,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不幸之事都可以成为悲剧性民歌的创作题材。例如,创作于1921年的《可怜的秋香》、创作于1922年的《卖布谣》和创作于1935年的《铁蹄下的歌女》[2]11-18等中国近代歌曲就是以旧中国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命运为题材创作的悲剧歌曲。那么,为什么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在题材的选择上多集中于爱情婚姻方面呢?笔者认为,这与郭尔罗斯的地域环境有关。郭尔罗斯位于吉林省西部、蒙古高原东侧,荒烟蔓草,地广人稀,再加上蒙古人世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国家政治生活对郭尔罗斯蒙古族人的影响。因此,个人生活几乎成为蒙古人生活的全部,而在个人生活中男婚女嫁又是最为重要的话题和组成部分,因此爱情婚姻上的不幸便成郭尔罗斯蒙古人生活中的最大的不幸。
悲剧性民歌还体现在近现代郭尔罗斯人的阶级斗争上,民歌《鹦哥与罗成》、《陶克陶胡》就是这样的作品。鹦哥与罗成自幼父母双亡,为了养活妹妹,十五岁的罗成到黑帝庙做了庙奴。兄妹二人从卓索图盟逃荒而来,成了王府清除外地人行动的对象。在行动中,鹦哥被王府的两个卫兵强暴。为了给妹妹报仇,罗成联合几个拜把兄弟组成了反抗蒙古贵族的义军。在与王府卫队的斗争中,罗成击毙了强暴妹妹的仇人,但也命丧沙场。陶克陶胡出生于蒙古没落贵族家庭,眼看郭尔罗斯的草场不断被卖掉,毅然站出来反对王爷继续放荒而遭到呵斥与毒打,从此陶克陶胡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在斗争中他先后丧失了四个儿子,尝尽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三、悲剧人物
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所描述的悲剧性人物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例如《二姑娘》、《龙梅》、《水灵洪格尔》、《八月》、《腊月》等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所描述的都是女性。从爱情题材的角度出发,若两情想悦却又不能厮守终生,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因此,与女性相关的男性也应当是悲剧性的人物。那么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为什么只描写女性而不描写男性呢?笔者认为大概有三点原因:第一,与女性地位有关。一般来说,悲剧的发生往往都集中在弱者身上,而在旧社会女性是最典型的弱者,他们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爱情不能圆满,婚姻不能自主,常常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从此开始自己悲剧的命运。因此,女性必然成为歌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第二,与民族心理有关。在蒙古人眼里,男人是草原上的骏马,是蓝天上的雄鹰,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儿女私情这类“小事”不应被男人牵肠挂肚。男人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强者,因此无论如何不应成为悲剧中的人物。第三,与受害层次有关。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爱情面前男女永远都是平等的。因此,一个真正的爱情悲剧的发生对于双方当事人的伤害程度是一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男女双方都是爱情悲剧的受害者,但二者在受害层次上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女性往往是直接受害者,而男性是间接受害者。正是因为有了姑娘的被迫远嫁,才有了男子的单相思苦,这就如同水中的圆晕,女性常常是这一水晕的中心。因此,女性必然会成为众多悲剧人物的核心。
四、悲剧意义
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中绝大部分描述的都是真人真事。正因如此,人们在欣赏这些民歌的时候,才会倍加为民歌中的悲剧人物感到不公和同情。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扼腕叹息的层面上,还不能发现悲剧性郭尔罗斯民歌的真正价值。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理性,思考是人类的本能。当某种现象出现后,人们总是要对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停地加以追问。因此,在欣赏悲剧性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为民歌中主人公悲剧命运感慨的时候,人们也不禁要问造成各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与人世间一切悲剧一样,所有悲剧的发生都是由主人公未能在相互矛盾的两种价值追求间作出明确选择造成的。
具体而言,民歌中所描述的悲剧多以父母包办婚姻、迫使女子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为起点。在这里便存在两个同样正确但又相互矛盾的价值追求。一方面是惟父母之命是从的孝道追求,另一方面是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个人价值追求。而悲剧中的女主人公们都未能在二者之间作出果断明确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无法冲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方面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宣言,始终纠结于社会责任理性和生命自由本性之间,这便注定了她们悲剧的命运。
反过来,倘若人们能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价值追求之间作出明确选择的话,或许其结局就不会是悲剧性的了。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江梅》[1]62-64和其木格、高娃演唱版本的《金姐》[1]42-48中的主人公江梅和金姐是很好的例子。
江梅是姑娘的名字,如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美丽芬芳。十八岁那年,父母把江梅嫁给了一个姓赵的买卖人家为妻。不和睦的婚姻使江梅终日闷闷不乐,人也逐渐变老。正在这时,江梅遇到了一个叫高尼格尔的人,他是驻扎在扶余城内军队的一个连长。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最后彼此牵手离开了扶余城,跑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金姐也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自幼聪明伶俐,美丽大方。十七岁那年,她与一个名叫乌龙阿的做买卖的小伙子相爱了,但贪图钱财的父母不允许金姐嫁给乌龙阿,硬把她嫁给了一个姓白的富户人家为妻。乌龙阿得知此事后,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一蹶不振,生活也陷入了颓废之中。此时,东院有一个名叫水梅的姑娘看到了乌龙阿可怜的样子,便时常加以劝慰,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怜之情。乌龙阿明白了姑娘的心意后,又想到金姐成家已成定局,便与水梅姑娘海誓山盟订下终身。有一天,金姐回娘家串门,知道了乌龙阿与水梅姑娘相爱的消息,便抱怨乌龙阿另寻新欢。听完金姐责怪的话后,水梅姑娘向金姐作了耐心的解释,金姐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乌龙阿和水梅姑娘。再想想自己已经是有夫之妇了,乌龙阿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既然他和水梅情投意合,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金姐摆上了酒席,三个人举杯畅饮,相互祝福,彼此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这两首民歌中,主人公们也都同样陷入了两难境地,但不同的是她们都能很快地作出明确的选择。在前一首民歌中,江梅选择了爱情而放弃了礼教。后一首民歌中,金姐选择了顺从而放弃了爱情。正是由于主人公们都能很快地作出明确的选择,最终都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而获得了各自的幸福。
[注 释]
①解放以前,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民间艺人不知道“哆来米发梭拉西”是什么。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所有的民间艺人都走着同一种途径:心里有了一个调调,就哼出来,经过反复的哼唱和调整,把一首曲子磨得熟练了,便操起琴来,凭着“耍耳音”的原始技能,再用四弦琴或马头琴演奏这首曲子。直到1982年,蒙古人仍然沿袭着这种原始的创作方式。参见额鲁特·珊丹著《郭尔罗斯英雄史诗及叙事民歌》,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第177页。
[1] 宝音朝古拉.阿尔斯楞.郭尔罗斯蒙古族民歌集[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2] 上海文艺出版社.音乐欣赏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1.
2014-02-14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122)。
王彦华(1976-),女,吉林白山人,吉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硕士,从事声乐教育理论研究;颜铁军(1975- ),男,辽宁昌图人,吉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声乐艺术论研究。
J607
A
2095-7602(2014)04-01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