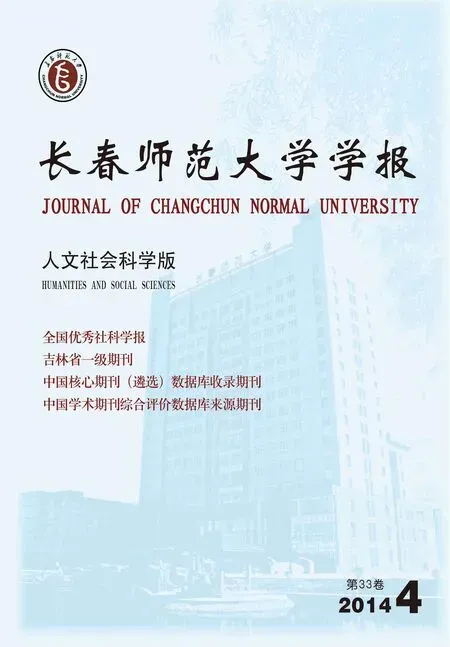谜中之谜
——论《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时间与文学性的关系
谢安安,唐建清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谜中之谜
——论《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时间与文学性的关系
谢安安,唐建清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许多人曾对《小径分岔的花园》的主题进行过解析,认为它讲述的是时间。但是笔者发现时间作为线索更为合理,对时间的描绘帮助博尔赫斯更好地揭示了文学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对谜底的解读,借助后现代文学观来解析《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时间与文学性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时间;文学性;谜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是享誉世界的拉美文学作家之一,被誉为“后现代之父”[1]。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尤其精彩,精巧的构思与无限的智慧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他与贝克特分享了由英法等六国先锋派出版商创设的“福门托奖”。短篇小说集《杜撰集》在六国出版后,他的名字与卡夫卡和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联系在一起。[2]《小径分岔的花园》(一译《交叉小径的花园》)更是他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时间的主题、迷宫的结构、虚构和异国文化元素一直吸引着人们探究。
在中国,《外国文学》于1979年就刊登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但国内对博尔赫斯的研究多出现在2000年之后,以意象研究或影响研究为主。其中包括一些针对《小径分岔的花园》这篇作品的文章,如朱雪峰《流沙上的花园——从<小径分岔的花园>索解博尔赫斯的迷宫》(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玮婷《变动的历史——<从小径分岔的花园>解读博尔赫斯的史学观》(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关于其文学性解读比较具体的有如下几篇:张素玫、祁晓冰在《博尔赫斯的叙事游戏——<交叉小径的花园>解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中曾将博尔赫斯的叙事手法与迷宫结构结合起来,对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进行剖析;孔岩的《博尔赫斯小说的文学性解读——以<交叉小径的花园>为例》(《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较早地关注到了小说中形式、不确定性所代表的文学性,并将博尔赫斯反传统的时间观同文学的多样性相联;唐蓉博士的论文《时间之书——博尔赫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已经发现博尔赫斯借时间问题来探讨文学性,将时间主题按照博尔赫斯的文体分为散文、诗歌、小说三类,并通过博尔赫斯的文学经历归纳出哲学不是博尔赫斯的目的,科学也不是博尔赫斯的归宿,文学才是博尔赫斯的本质。但作者将时间主题的案例和文学的历程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单元,文本分析与时间指涉文学性这条线索融合的稍显松散。
时间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领域内最令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对时间的复杂设置和精妙运用是现代小说浓墨重彩之处。纵横交叉、纷繁复杂的时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小说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对文本时间的解读也是理解小说内容本身的一种重要途径。博尔赫斯一直很关注时间,他对时间的思索也很耐人寻味,他曾说“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颤抖的、严峻的问题,也许也是抽象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3]在博尔赫斯的诗集中,有50多篇与时间主题有关。他的散文中也有30多篇是在讨论时间及其衍生出的话题,诸如《时间的新反驳》、《循环时间》都是直接以时间为谈论对象,口吻很像哲学论著。但是博尔赫斯曾声明他并不是作为哲学家来关注时间的。“我是个文人,我尽可能利用哲学里的潜在文学价值。我本身不是哲学家,只不过我对世界和我自己的生命感到莫大的困惑。举例说,当人们问我是否真正相信宇宙过程会一再重复,永无休止,我觉得我同那种事情毫无关系。我试图把灵魂嬗变或者第四维度的美学潜在价值运用到文学上面,想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4]即他对于时空的关注始终建立在如何更好地为文学写作的服务之上。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小径分岔的花园》文本为例,借助后现代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博尔赫斯的文本本身来具体阐释博尔赫斯的时间哲学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一、作为谜底的小说
如果我们按照博尔赫斯预设好的思路去阅读,他在书中借艾伯特告诉我们猜谜的规则就是谜面不能出现谜底:
“……《花园》手稿中惟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
“一点不错,”……“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5]
如果说时间是书中那部《小径分岔的花园》的谜底,那么博尔赫斯这部小说的谜底又是什么呢?按照博尔赫斯的逻辑,当然时间就不能作为谜底(主题),它只能作为谜面。笔者认为博尔赫斯这部小说的重点在于谈论文学。
博尔赫斯将《小径分岔的花园》定义为侦探小说,主人公余准和艾伯特的身份都与文学无关,但他们的相遇相知是依靠余准的曾祖的文学作品。是迷宫与小说的同构让这两个人有了深层的交流,两人之间的对话围绕玄学和神秘主义,大段地论述时间问题,但是象征的迷宫是通过文学才揭示出来的。博尔赫斯整篇围绕时间的猜谜实质是在揭示文学创作的秘密:
“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5]132。
在这个过程中,余准所见到的曾祖父的作品实际上已经经过了至少两批人之手的“篡改”,一是艾伯特提到的抄写员——代表了文学的传播途径。他或是无心或是有意的疏漏错误已经影响到了流传出去的作品,读者之一就是艾伯特,这是彭冣和读者之间的第一道隔阂,象征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直接交流的不可能性。艾伯特自身意识到了这点,因而他说“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5]130;二是读者自身的期待视野会与原作者的意图背离。对话中,艾伯特承认他“猜”出彭冣的用意,恢复他“认为”的顺序。而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读者是不可知的。翻译也是文学交流上的障碍,这体现在艾伯特念读彭冣的小说时余准的心理活动——“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这句话透露了文化差异背后人与人交流的不可思议。这种“误读”现象正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和近年来时兴的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视角,博尔赫斯却早在1941年就注意到了,并通过主人公之口阐述了审美体验。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都以精巧著称,因此他对于形式和修辞都有着独具匠心的构筑,整篇小说看似在一个还原真相的侦探过程中进行,实则我们一直在博尔赫斯的语言游戏中徜徉。从小说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完整的真相,因为“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在结尾时我们又被暗示其实我们对主人公的悔恨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这些显然出于作者别有用心的欲言又止的留白让我们不禁想起伊格尔顿的“未定性结构”以及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的“空白”。伊瑟尔在他的《阅渎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一书中指出“虚构本文中的空白引起并导致读者的建构活动”,而“引起期待功能以将之转变为空白,这是典型的现代文本”[6]。此外博尔赫斯还引用了框架结构的经典作品《一千零一夜》,并在自己的小说中也设置了大套小的格局:迷宫中的迷宫(阿什格罗夫本身就是个迷宫,而艾伯特又在其中建立起了迷宫花园),小说中的小说(彭冣的小说在博尔赫斯的笔下)。而且艾伯特揭示:迷宫与小说是同一个事物,这就更加可疑:作为幕后作者的博尔赫斯要建造的迷宫是否就是小说本身。因此《小径分叉的花园》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指向文学的书写,说明时间在小说中的作用仅是谜面,真正要从中解读的是文学内涵。
二、时间的循环或分岔——文学的多样性
叙述迷宫的确是时间的迷宫,博尔赫斯的迷宫依靠着时空才能搭建起来,但是赋予了时间的并置和多重性的可能的却是文学——作者设想的多系列的时间是在文本中实现的,毕竟现实生活仍在单向度的时间维度里。传统的西方时间观是理性统治下的线性时间观,是不可逆的流动的时间。康德与胡塞尔都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传统时间的绝对性,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概念,认为时间应该由主体体验而获得。柏格森的“绵延”时间理论区分了客观空间中被钟表记录的“物理时间”和个人直觉体验的“心理时间”。而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时间观的突出表现为两种:循环时间和分岔时间,在显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人生深刻的洞察力同时,与他的文学背景和文学接受密不可分。除了本土文化的熏陶,在博尔赫斯之前,英国作家康拉德、意识流大师詹姆斯·乔伊斯都曾运用相似手段打破小说创作中时间对叙述的限制。这位青年时期曾在欧洲求学交游,成长在欧美文学冲击下的拉美作家必然受到其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循环是解读博尔赫斯的一个关键词,文学批评家穆列洛在论博尔赫斯的讽刺艺术时就曾为书取名《循环的夜》(L. A. Murillo, The Cyclical Night: Irony In James Joyce and Jorge Luis Borg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有学者在论述《虚构集》的叙事时借用博尔赫斯的“帕斯卡圆球”来形容它的艺术特色(张丽娜:《帕斯卡圆球中的无极之境——博尔赫斯<虚构集>叙事研究》,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时间的循环是以对称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我们阅读到的文本叫做《小径分岔的花园》,它直接对应艾伯特按照彭冣描述而复原的花园。在文本中,“小径分岔的花园”又是彭冣写的那部小说的标题,而这部小说的手稿又被艾伯特存放在他建立的花园之中。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从小说到小说、从花园到花园的环形,即博尔赫斯尝试虚构的文本与现实世界中的作者、读者间的距离。其次,博尔赫斯将人物之间的关系设定成了一环套一环的追逐,《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余准是间谍,被追杀,而艾伯特又被余准追杀,这种人物关系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曾出现(如:上帝操纵棋手,棋手摆布棋子[7])。小说主人公余准在谈及自己的命运时说过,“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5]125对称的花园和人物的命运似乎有着某种冥冥中必然的安排,而我与父亲的命运相似暗示了生命的循环。循环时间在拉美作家的作品中并不稀奇,另一位享誉世界的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就运用循环混合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这其实和印第安人的时间观联系密切,它的形成与自然界的季节性周期变化有关:日月星辰、四季更迭等等都有着周而复始的循环感,人的生死是生命的轮回、灵魂的转世,死亡不过是循环的一个阶段,人是生命到死亡、又回到新的生命的往复过程。
但是马尔克斯用循环来探讨生命永恒的孤独,博尔赫斯则从循环中得到了文学启发。他也将循环和永恒联系在一起——“永恒地回复到永恒中去”[8],成就了文学的无限。艾伯特拿到了彭冣的手稿,从《一千零一夜》推断出要将一部书成为无限的可能性:
“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5]130
进而悟出了小说与迷宫的同一,像迷宫一样神秘莫测。而走出一个迷宫的办法——在月台上的孩子们给余准的提示是每逢交叉路口向左拐,一直向左拐,不就绕成了一个圆环吗?冥冥之中又和拉美人命运的循环相扣,象征了我们的人生本就是在一个循环的迷宫之中。
博尔赫斯更令人震惊的时间观表现在他对时间绝对性的否定上,他认为时间无限分岔。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艾伯特的一席颇为复杂的深奥的“时间说”令人印象深刻:
“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5]132
这一时间观的直接影响是“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应用到文本中对应着“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冣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5]130于是艾伯特将小说的几个片段读给余准听,以证实他的观点。时间分岔对应了文学上开放的结局,它摒弃了传统绝对单一的秩序,挑战了传统叙事的时空观,它以自己的方式认可了生活如水流一般不断向前、不会终止的真理。正如戴维·洛奇所言,“我们应当把小说的结尾和文本的最后一两页区别开来。前者是对读者头脑中有关小说内容产生的疑问所作的圆满解答或故意不解答,后者则常常是作为一种后记或附言,是话语接近尾声时的一种平缓减速。”[9]
博尔赫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小说正在崩解。所有在小说上大胆有趣的实验——例如时间转换的观念、从不同角色口中来叙述的观念——虽然所有的种种都朝向我们现在的时代演进,不过我们却也感觉到小说已不复与我们同在了。”[10]的确,随着写实主义的衰落和元叙事的兴起,我们读到的小说有时如同文论一般艰涩,有时如同诗歌一样充满隐喻,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文体模糊的时代。一切都是可能的,“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5]465博尔赫斯看到了开放的趋势,杂糅了不同的美学风格。在短短的篇幅内,将多元叙事和哲学沉思相关联,充分展示了小说这一语言艺术。
三、后现代的特征:虚构性与互文性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座迷宫。这个迷宫——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着空间,而作为文本,它的谜底在艾伯特的解释下又变成了时间——花园小说二者合一象征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博尔赫斯用虚构的文本来完成的,即我们要寻找的答案。
时间可以作为我们确定一个事件的佐证,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加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就会让叙述的事情可信度陡增。博尔赫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开篇就引用了真实的人物利德尔·哈特讲述一战期间的一场战争:“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5]124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事件和这个著作都是子虚乌有的。博尔赫斯在开篇就对历史进行了虚构,或者不如说,即使是历史,也不过是一种虚构。虚构在后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被突出强调,“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11]博尔赫斯将《小径分岔的花园》收录在《虚构集》中,且为彭冣的书房取名“明虚斋”,已经暗指虚实相与,一切皆为构造。
时间分岔的设想恰好帮助了作者的虚构,整个故事情节及故事背景则给我们一种真实感。一战的背景下,青岛大学的英语老师为德国人当间谍,在天津当过传教士的汉学家艾伯特把他们聚集起来很合理却又有着很大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刚好暴露了作者的刻意为之。巧合“在小说创作中很显然是作为一种结构手段来利用的。然而,过于依赖巧合会破坏叙述的真实性。”[9]165这本是一份证言,却恰好少了开头两页,让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故事情节;主人公跳上车,恰好错过了马登上尉的追捕;下车的地方,小孩子恰好给他指向了艾伯特的花园;艾伯特恰好研究了余准祖父的迷宫;艾伯特的名字与英国炮兵阵地的名称恰好巧合……正如艾伯特所说: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5]132
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环节错过,或者时间分向了其他方向,那么我们看到的故事就会不同。“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不仅告诉读者结局的多样性,同时也更进一步印证了作者的虚构。
谈及虚构,博尔赫斯让余准讲述《小径分叉的花园》也是别有用心,主人公“余准”是《博尔赫斯全集》中的译法,这个名字西文英文皆作“Yu Tsun”,按照“汉语拼音——韦氏拼音对照表”,其汉语拼音应为 “yü cun”,我们按照发音作适当联想,不难发现它和《红楼梦》,人物贾雨村的“雨村”不谋而合。笔者认为博尔赫斯可能深谙其中的语意双关,借指“假语村言”,这便涉及了另一个文学性特征——互文性。余准的曾祖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红楼梦》无论从文字的叙述上还是宁荣二府的格局上都与博尔赫斯的“迷宫”概念不谋而合,因而《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提及《红楼梦》绝非偶然。博尔赫斯曾读过英文和德文两种译本的《红楼梦》,并评价说“这部书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好”。博尔赫斯本身是推崇短篇小说的人,《红楼梦》作为长篇小说在其心中得到这样的赞赏,可见博尔赫斯对它的喜爱非同一般。文中提及处理彭冣的手稿的“遗嘱执行人”是“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如果没有刊行,也就没有艾伯特拿到手稿去研读,并形成这个故事,这和《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引出全文的效果也是相同的。这又恰好说明叙述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虚构的表现。
四、结语
博尔赫斯曾说“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思考时间,时间问题,当然还有我的个性。至少我认为这些事物是一起存在的,因为我认为时间是组成我的物质。说实在的,我没有特殊的有关时间的理论。我只是感觉而已。”[4]11如果说博尔赫斯对时间是一种感觉,那笔者对谜题的解答也或多或少是一种感觉。笔者认为博尔赫斯在这个以时间为谜面的谜题中奉献给我们的是文学的谜底。当然,作为后现代的一位开山祖师,博尔赫斯的文本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我们的一切解读也都存在着谬误的可能,但是体味其中的真意仍然带给我们无穷的趣味。博尔赫斯曾说这是一篇侦探小说,那读者就是寻找真相的“侦探”。
[1]王钦峰.谁是后现代主义小说之父?——论博尔赫斯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首创之功[J].国外文学,2011(1): 41-49.
[2][美]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博尔赫斯传[M].陈舒,李点,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403-404.
[3][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作家们的作家·前言[M].倪华迪,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4][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美]理查德·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0.
[5][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31-132.
[6][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43-250.
[7][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林一安主编.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M].林之木,王永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156.
[8][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M].王永年,徐鹤林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291.
[9][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50.
[10][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凯林-安德·米海列斯库编.博尔赫斯谈诗论艺[M].陈重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55.
[1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5.
Riddle of Guessing Ga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iness and Time in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XIE An-an, TANG Jian-q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Many people have analyzed the theme ofTheGardenofForkingPathsand concluded that its theme is “time”. I find tha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use “time” as a clue in this fiction, the description of time is just an approach helping Borges reveal the literariness behind “time” .This thesis, by examining the text and interpreting the riddle,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the literariness inTheGardenofForkingPathswith some postmodernism viewpoints, in order that we can understand Borges better.
Borges;TheGardenofForkingPaths; time; literariness; riddle
2014-03-08
谢安安(1989- ),女,吉林长春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唐建清(1957- ),男,上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I783
A
2095-7602(2014)04-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