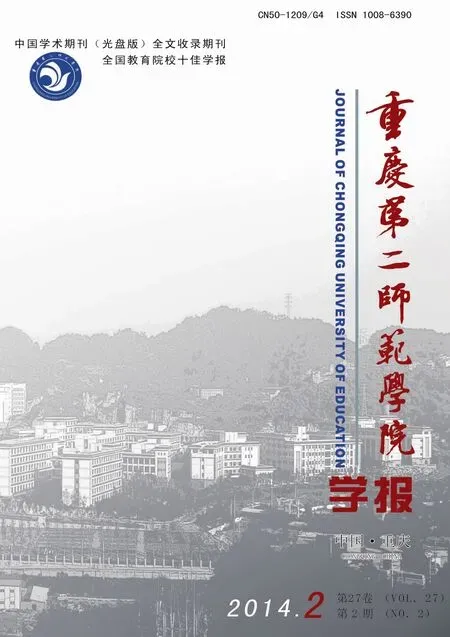学前儿童第一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探微
黄林林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州 510507;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一、语言学研究维度下学前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一)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自然机制观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年-1952年),是二十世纪享誉全球的意大利幼儿教育学家,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她的教育法建立在对儿童的创造性潜力、儿童的学习动机及作为一个个人的权利的信念基础之上,她所创立的独特幼儿教育法,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在儿童语言习得方面,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一种天生的语言潜能,她称之为“语言的特殊机制”,并把这种“创造语言的机制”比作儿童内部的老师。这位老师在恰当的时候教儿童学习语言,儿童首先掌握单音,然后是音节,循序渐进,正如语言本身一样合乎逻辑,接着是单词,最后是语法。自然就是老师,儿童在她的教诲下学习语言。可见,“儿童内部的老师”就是“自然”。实际上,这一“自然”就是先天的语言潜能。[1]“如果儿童没有自己的内部教师,他就不可能学会说话,正是内部老师让他听成年人的相互交谈,而促使儿童准确地掌握语言,我们(成年人)对此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儿童先天的语言潜能为儿童制定了语言学习的整个计划。”[2]在蒙台梭利看来,儿童不是生下来就具有先天的、现成的语言,而是因为具备了“语言特殊机制”才可以“吸收”周围的语言,而猩猩等灵长类动物哪怕放置在人群中,也不能掌握语言,就是因为不具备先天的“语言特殊机制”,这种“自然机制观”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生成系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乔姆斯基(N.Chomsky)的先天语言习得机制说
普遍语法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语言设计三要素》(N.Chomsky 2005)中,Chomsky提出语言器官和人体其他器官一样,具备生物系统的普遍属性,个体的语言发展主要由基因天赋、外部数据、原则这三种要素相互作用决定的。[3]Chomsky 认为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体现,为人类所独有。儿童一出生,人脑中就存在一个具有“遗传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正是因为这种天生的语言习得能力,只要将儿童置于语言环境中, 就能听到、说出和理解语言,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语言能力。Chomsky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为什么儿童能够在短短数年里学会使用如此复杂的人类语言和说话。他从研究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思维建构的高度出发,认为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心理客体,但最终是一个生物客体。语言机能就像身体的各种器官一样,是一个语言器官,其基本特征由遗传基因决定。Chomsky虽然也承认经验和环境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但在语言习得的根本原因上,他仍坚持遗传的语言习得机制才是语言习得的根本原因。
二、生理学研究维度下学前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一)Leneberg的语言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Lenneberg(冷宁伯格)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著名教授,他在《语言的生物学基础》一书中提到语言获得的最佳时期:从神经生理角度来讲,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大约从 2岁开始延长到 12 岁结束。这一时期,人的大脑既灵活又具有弹性,语言功能尚未侧化移至左半球,整个大脑参与语言学习,因此这个阶段可以轻松自然地吸收新的语言信息。[4]Lenneberg 关键期的模式为语言的获得提供了解释:一是练习假说。在生命初期,人有一种较高的获得语言的能力,如果该能力在生命初期没得到训练,它将消失或者随着成熟而下降;如果该能力得到训练,则进一步学习语言的能力将在整个生命期间保持完整。二是成熟假说。在生命初期,人有一种较高的获得语言的能力,它随着个体成熟逐渐下降或者消失。[5]Lenneberg认为青春期之前这段时期称为语言习得的关键期(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二)Oyama等人的语言敏感期假说(Sensitive period hypothesis)
1978年,Oyama(奥亚码)进行一项研究,通过研究不同年龄组的人到达目的语国家之后,其讲话能力和理解目标语(英语)的能力与他们到达目的语国家时年龄的关系,得出结论:语言的获得与年龄的关系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现象;Oyama 指出偏爱“敏感期”这一术语是因为“敏感期”“准确地反映了年龄等现象逐渐的、自然的过渡状态,以及这些现象在感受上的敏感变化”。[6]Long 以及其它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支持敏感期存在的观点,而且已有证据表明,对于语言能力不同的人来说:在目标语的获得过程中不只是存在一个敏感期,而是存在几个敏感期;在第一和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均受敏感期的制约,获得语言的能力不是突然地全部丧失,而是逐渐下降的过程,大多数个体从 6 岁开始下降,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从青春期开始下降。[7]
(三)周加仙的二语习得敏感期的脑与认知机制研究
在国内,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加仙博士就二语习得敏感期的脑与认知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8]她首先对语音学习的敏感期进行研究。语言环境与遗传因素对婴儿语音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婴儿在胎儿期就开始了母语语音的学习,他们能够区分不同语言的语音,具有普适性的语音辨别能力是世界公民。婴儿从6 至10个月大时,对母语中同一音位范畴内的不同语音和外语中语音的分辨能力下降,而对母语的语音分辨能力则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最初10个月的特定语言经验会使大脑对该语言的语音很敏感。[9]科学家的研究表明, 婴儿出生后6至12 个月就是婴儿区分各种不同语音的敏感期。其次,周加仙博士根据韦伯· 福克斯等( Weber Fox )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语法加工敏感期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语法加工受第二语言起始年龄的影响,早期接触语法可以形成高效的语法加工策略,而晚期接触语法则形成效率较差的加工策略。
三、心理学研究维度下学前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一)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学派
皮亚杰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儿童语言和思维等问题是他认知发展研究的中心内容。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派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是天生的心理认知能力与客观经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认知能力的发展决定了语言的发展。儿童大脑在某个发展阶段,儿童的语言表现是由存在于他大脑中的一套先天的语言机制所控制的,而不是仅仅对成人语言的模仿,尤其是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不仅对儿童的认知过程起调节,而且也对儿童的情绪、动机和行为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语言能力不能独立于认知能力而存在,语言能力的获得要以一定的生理成熟和认知发展为基础,并在非语言的认知基础上能动地建构起来,语言的习得是一种认知结构的动态建构过程。[10]相对于天赋论和环境论,皮亚杰更倾向于认为儿童语言发展是儿童与环境互动的结果。皮亚杰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就是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原始形态或过渡形态表现为出声的自言自语,也即是“自我中心语言”,且这种语言是儿童特有的自我中心思维特点的表现,该语言与社会化语言相对立。
(二)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
行为主义的习得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心理学家斯金纳和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他们认为人的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语言能力来自一系列的“刺激-反应”,经强化而形成习惯,儿童学说话就是对环境或成人话语所给予的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果反应正确,他就从成人那里获得物质的和口头的奖励,使反映得到强化而形成语言习惯。[11]斯金纳在《言语行为》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对人的言语行为进行功能分析。他通过对动物的实验,用他所创造的特殊术语如刺激、强化、短缺等来描述、辨识出控制言语行为的各种变量,并详细描述这些变量如何协同作用来决定言语行为。他认为如果想要精确预测人类会采取什么样的言语行为,只要了解那些控制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即可,而说话者在言语行为本身能有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2]总之,斯金纳和布龙菲尔德的观点承认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还有外部环境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但是该理论将儿童等同于实验室里的动物,忽略动物本质和人的行为之间的本质差别,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和排斥儿童内在的语言能力,机械主义的倾向严重,也使之在五十年代后期遭受到了批评。
四、社会学研究维度下学前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一)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学派
以Lantolf[13]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学派(Sociocultural Theory)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来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14]关于儿童心理和认知发展的研究。Vygotsky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相联系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儿童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身的心理结构。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15]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是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发展的一项辅助工具。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意义就是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学派
语言社会化理论学派(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是以Watson-Gegeo 和Neilsen[16]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视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母语习得研究,也能用于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该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
五、研究述评
在学前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几十年间,研究问题经历对“母语习得”的研究、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到“多语习得”研究;研究内容从研究“习得什么”到“如何习得”再到“习得差异”;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发展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研究维度从“语言学”发展到“心理学”再到“生理学”和“社会学”等。
诚然,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是“语言习得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台梭利的“语言特殊机制”还是乔姆斯基的“遗传的语言习得机制”,都承认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特殊的语言机制,这种机制是先天的、遗传的、自然的,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把“遗传的、特殊语言习得机制”看做是儿童语言习得的根本原因;生理学们倾向于研究“语言习得与个体生理成熟程度的关系”,语言发展过程是按照明确的时间表顺序的,而其关键期大约从 2岁开始延长到 12 岁结束。无论是“关键期”假说还是“敏感期”假说都承认了第一和第二语言习得都存在着“临界期”,而且语言的获得与机体的成熟程度有关系;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则是“语言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更重视“语言习得的过程”研究,认为语言就是习惯的总和;社会学家们重点分析了“社会互动对语言习得和认知水平发展的作用”。社会文化理论学派的理论来源是认知心理学,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社会化理论学派的理论来源则是语言人类学,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17]
各学派学者们倾心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语言习得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这些理论有完全对立的、有部分相同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然正是多种学派的纷争,使得研究更全面、准确、透彻。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学术争鸣,正如北外文秋芳教授所言:“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反对谁,而是根据研究目的赞成谁。”[18]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儿童教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17-318.
[2][意]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M].任代文主译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432-437.
[3][16]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68.12.
[4][5]Lenneberg E H.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In M. Lester (Ed.), Readings in Applied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Orlando[M].1970: 2-20.
[6]Oyama S.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speech. Reprinted in Krashen S D,Scarcella R C,Long M H,(Eds.), Child-adult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Rowley,MA: Newbury House,1982:39-51.
[7]Long M H. 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on language development[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0, 12: 251-285.
[8]周加仙.语言学习敏感期的脑与认知机制研究——兼谈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和实践[J].全球教育展望,2009,(9):20-24.
[9]Gopnik, A., Melt zoff,A.N.and Kuhl, P.K.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 What Early Learning Tell s Us about the Mind[M].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1999: NY.
[10]匡芳涛.儿童语言习得相关理论述评[J].学前教育研究,2010,(5):45.
[11]刘晓东.儿童教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2):325.
[12]王宗炎.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上、中、下)[J].国外语言学,1982,(2):15-21,(3):37-41,(4):37-15.
[13]Antolf J P, Thorne S L.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17][18]尹洪山.从社会文化理论到语言社会化理论[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1):95-98.
[16]Watson K A, NEILSEN 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SLA[M]//DOUGHTY CJ,LONG M H.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