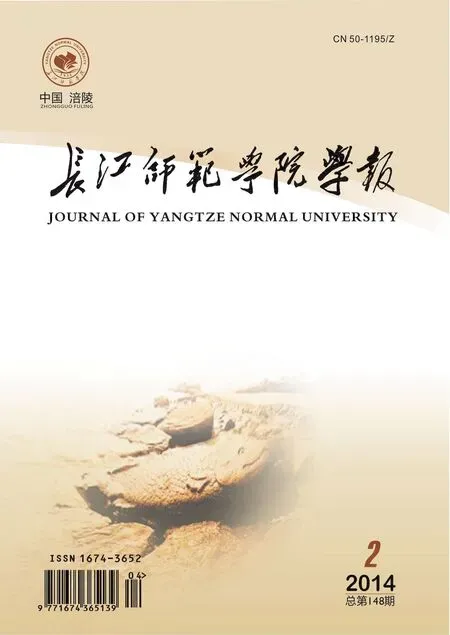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刘杨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社会学研究
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刘杨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影响日益明显。对于中国而言,要在文化传播中塑造有魅力的国家形象,首先要重视文化输出式传播,同时也不能忽略塑造国内文化形象。而在已有基础上,要更好地在文化传播中塑造国家形象,要充分重视到传播渠道与传播效率的不对称性;文化传播中原创性、时代性要进一步提升;文化输出不能只满足于量的扩张,更要有精品意识,从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真正通过文化传播塑造立体的国家形象。
全球化;文化传播;国家形象;中国
随着科技日益进步和发达,信息传播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可以说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加速着全球化的进程。在这样的语境中,国家形象不再仅仅通过经济交往和政治交流实现, 文化传播 (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有学者意识到 “文化传播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当代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全球传播,是一种国际化形象”[1],也就是说,当代文化传播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文化精神的传播与交流,并在传播中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因此,在当前全球化日益紧密、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有效的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乃至重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传播和输出国家文化形象,通过文化节、孔子学院这些文化传播途径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和构筑国家形象,但要真正地从文化上建构起立体的国家形象,单靠这些渠道是不够的,因为其传播面毕竟有限,而且受到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因而要双管齐下在文化传播中更为有效地塑造国家形象。
一、重视文化输出式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中,一国文化形象的形成首先要通过有效的文化输出为异国接受者所承认,进而使其认可文化输出方的国家形象,但在文化输出式传播中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播效率的高低。如何尽可能地在跨文化交流中给接受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是否成功。在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纸质媒介的传播效率显然已经不能与时代相适应,即使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样的重要报纸,其能提供的信息量也十分有限。新的媒介如影视媒介、网络媒介的成熟和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宣传和建构国家形象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例如中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街头的播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很好的例证,它可以在公共空间中展现中国国家形象,对受众的影响也会更大。
同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文化传播中要注意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影视媒介为例,有学者指出:“影视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不仅可以通过票房收入与广告收入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本国民族文化,有利于塑造和宣传本国的国家形象,起到联络各国人民情感、提供相互学习机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作用。”[2]而在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影视的传播渠道和接受面都不断拓宽,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影视媒介更有效地提升国家形象的魅力。我们认为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就值得研究和借鉴。近年来,韩国在文化输出中十分注重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建构立体的国家文化形象,韩国服饰、韩国饮食乃至民俗大多是通过韩剧传播的,而文化资源整合和输出导致的泛东亚地区的 “韩流”涌动有力地塑造和输出了其国家文化形象。
二、积极塑造国内文化形象
有学者指出国家形象 “可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3]。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的文化输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断来中国经商、旅游,他们所面对的中国,他们所认知的中国国内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转化为国际形象。那么我们在通过文化输出式传播塑造一个强大的国际形象的同时,也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忽视国内形象的建构。因为在信息化的时代,外国人可以将在中国国内的感受和见闻,在第一时间通过一条微博、一则短新闻、乃至一段视频在国外网站、媒体上传播,而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他国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如此来看,若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反差明显,文化输出反而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近三十年来,中国国内形象从外国人作为 “他者”介绍和建构,到如今有意识地在各个领域自我重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主体性,但是国内文化形象的提升所需要走的路还依然很漫长。如今 “Made in China”的产品遍及世界,但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却缺乏原发性、有价值内涵的优秀企业文化;外国人在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媒体报道地沟油等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标志着在经济发展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而这些都与我们输出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也有可能会带来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价;而国内刊登有关社会问题负面报道的报纸,其所刊载的文章也常常被国外一些舆论加以利用和渲染以作为批判中国的材料。我们的政府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从根本上解决不利于中国国内形象构建的问题和负面文化因素,切实改善中国的国内形象,这样在信息化的时代才能无损于国家形象。
三、文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文化传播中中国国家形象的魅力和吸引力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热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但要更进一步借文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的影响力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一)传播渠道与传播效率的不对称性
自2003年起,中国通过政府层面先后在法国举办了盛大的中国文化年,在美国举办了中国文化节,在 “中印友好年”中文化交流也是重要内容,2006“中国意大利年”中在意大利办了系列展览宣传中国文明、文化,2007年,中国在俄罗斯也成功举办了“中国年”文化交流活动。与此同时,国家汉语考试(HSK)也渐渐热门起来,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越办越多,2012年中央电视台非洲频道也在肯尼亚顺利开播。凡此种种,都是通过官方渠道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问题在于 “文化年”的时间有限,孔子学院的受众范围有限,在塑造国家形象的立体性、持续性和国家形象的广泛传播性上都显得美中不足。
在当下,文化传播并不意味着仅仅要通过政府间渠道传播,近年来中外民间友好团体也致力于通过民间渠道扩展文化传播。从理论上来说,相较于官方有限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载体,民间和大众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手段应该更具有多样性,但是从传播效率 (以及传播的实际影响力)来看,往往会因为经费、资源的有限而无法承担起推广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一重要使命。有学者提出:“文化传播有两个层面:一是借助媒体对外传播,如对外广播、国际卫星电视、海外版报纸等,这是一种单向传播。二是通过各种国际文化活动进行对外传播,如学术交流、艺术交流、海外文化展等,这是交互式的双向传播。”[4]对于一般层面的异国人士,大众传播为他们了解他国的国家形象提供了最直接的渠道。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5]也就是说在 “媒介即是信息”的时代,适时拓宽政府以外的文化传播渠道,更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同时可以打破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而造成的传播障碍。从这个角度上看,如何在民间与大众文化的传播中有效地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仍需研究的课题。
(二)文化传播原创性、时代性不足
文化传播从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而 “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进一步说,异质文化的互补、交流、理解也应该是其题中之意。我们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信息化的语境并非追求文化同质化,而是要在传播中更突出民族化特色,并借此构建出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形象。
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化传播显然在能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原创性上稍显不足,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影视乃至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发展,有的时候在“后殖民意识形态”的陷阱中不自觉地以所谓 “西方”为价值标准或作为判断尺度,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普利策奖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忽视了东西方价值理念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仅以影视文化为例,国产大片在频繁生产中丧失了自我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品格而沦为对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模仿,或者满足后殖民者所想象的古老中国的审美取向,过分突出武打和古老中国的形象,这样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异质文化者的欣赏,只不过满足一下他们的猎奇心理。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在文化传播中,亦步亦趋地模仿而产生的文化产品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超越,反而会陷入机械复制的陷阱。
另一个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传播中时代性也存在着缺陷,许多文化遗产已然面临着断承,更遑论结合时代特点改造输出。在奥运会、世博会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忙于报道赛会进程或介绍各国展馆,反而在塑造文化形象最为有力的时机较为普遍地缺乏配套的文化传播;在海外,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传播渠道传播的只是中国古代文化、民俗的精华部分,对于当下中国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和富含现代性的文化形象建构则显得捉襟见肘。
(三)文化输出质与量不平衡
有学者提出 “一个主权国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实现他国文化追随和仿效来提高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7],而事实上在文化传播中,近年来中国文化输出量逐年增长,如今已然扭转了数量上的 “文化逆差”,但是文化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却没能同步提升。当然,我们承认这其中包含着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但跨文化交流本身就是要在这种差异性中展现一国文化形象的。当下好莱坞的大片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国产大片在美国的票房号召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文化产品则主要在华文世界和一些文化较为贫瘠的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和受到认同,这还未能与中国的经济形象相匹配。近年来,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致力于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是大国形象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上的大国形象,还应该包括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上不仅仅要致力于抢占市场份额,更应在这样一种柔性的文化传播中,输出甚至改变中国的国家形象。
基于这样的考虑,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文化传播中应更重视质的突破。例如一些孔子学院现在只有1至2名中方教师,传播中国文化的范围和能力都很有限,是不是能在以后的办学中加大合作力度,扩大实际影响;中国的影视产品缺乏精品,叙事模式和价值理念都显然滞后,是不是能在技术发达的时代产生一流的、赋予中国时代精神的大片;重要的门户网站在文化建设和传播方面多是刊载一些娱乐新闻,今后是不是能利用网络媒介加强系统性的文化介绍和输出。应该说,凡此种种都可以在今后的文化传播中多加关注,以期实现在已然达到一定传播数量的积累的前提下,提升文化输出中的精品意识。
总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任务不仅仅包括 “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的强势,吸收、借鉴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因素,并与之形成互动、互渗和互补的文化传播态势。”[8]更重要的在于,要在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整合我们的文化资源、拓宽传播渠道,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时代传播多样性的便利,另一方面坚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讲而从文化层面建构更为立体的、具有民族特色和魅力的中国国家形象。
[1]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
[2]温朝霞.跨文化传播视阈中的国家形象塑造[J].探索,2009(3):121.
[3]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 (3):16.
[4]刘乃京.文化外交——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J].新视野,2002(3):67.
[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6][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2.
[7]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63.
[8]庄晓东.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04(2):62.
[9]李 凤.文化研究与审美批评[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6).
[责任编辑:田 野]
G125
A
1674-3652(2014)02-0098-03
2014-01-10
刘 杨,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