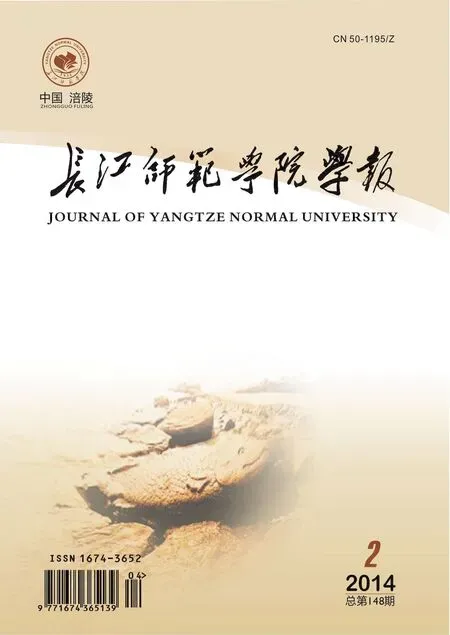论洛夫诗歌的自然意象
张春艳,方 忠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论洛夫诗歌的自然意象
张春艳,方 忠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自然意象,是洛夫诗歌中出现次数最多且最具诗人匠心的意象。在众多的自然意象中,月意象和雪意象是洛夫着力塑造的两类意象。它们融古典情思与现代诗歌技巧于一体,是诗人人生观与创作观的体现。不同创作时期,洛夫诗中的自然意象的选择与表现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别,这是诗人创作理念的调整,也是其思想成熟的标志。
洛夫;自然意象;创作理念;调整
洛夫,是华语诗坛一位重量级的诗人。在意象的经营上,洛夫独具匠心,创作了一批个性突出、意蕴丰富的意象,其中自然意象占洛夫全部意象的一半以上。自然,是人类永远的审美对象,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象源泉。“人类所面对的一切美的形式,都来自于大自然,色彩、线条、体块、音响、节奏、变幻,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感官的贡献。”[1]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原乡,人类以和谐共生的姿态与自然相处,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赋予自然物以新的情感内涵,创作出一批具有情感符号特征的自然意象。洛夫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繁复多彩,意蕴丰厚,涉及花草树木、鸟兽鱼虫、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四季晨昏等各个方面。例如,爆裂的石榴意象、成熟的葡萄意象、广阔的大海意象、暝色起愁的黄昏意象、弥漫的雾意象、闪烁的星意象、代表生命最初形态的种子意象等。
一、个性化的自然意象
个性化意象的营造,是诗人风格特征的最佳体现,如同夜莺之于济慈,荒原之于艾略特,香草之于屈原,菊花之于陶潜,月亮之于李白,太阳之于艾青,丁香之于戴望舒,麦地之于海子。洛夫诗歌中最具诗人个性的是月意象和雪意象。
(一)月意象
月亮作为一个古老的意象,在历代诗人的笔下已凝定为一个固定的情感符号。她的出现总是披着绰约、朦胧的色彩,伴以婉约和谐的姿态,并以其玲珑剔透的光彩和宁静安谧的神韵,创造出空间澄净、内心虚静的审美境界,引发诗人空灵的悠古情怀。洛夫诗歌中的月意象在沿用古典意涵的同时,还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月,最初并不是以乡愁的面目出现于洛夫诗歌中,而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客观对应物。“月是月,光是另一回事”(《无聊之外》)①本文引用的洛夫诗歌均出自2009年台北普音文化出版的《洛夫诗歌全集》。,洛夫早期的诗作充满着炮弹与鲜血、生存与死亡、存在与幻灭的各种冲突,但是不论战争多么残酷,生命如何痛苦,明月仍当空自美,美得那么冰冷,那么无情。在这些诗中,月亮充满着一种诡异的气质,她静静地观看人类经受的各种灾难与痛楚,甚至抱以不怀好意的怪笑。面对亘古不变的月亮,诗人们总是感伤于生命的短暂和世事的变幻无常,但是与古典诗人不同的是,洛夫将永恒的月亮视为时间的杀手,她吞噬了悠悠岁月,扼杀了菁菁年华。月亮,在洛夫诗中还充满了肃杀之气。在 《月亮·一把雪亮的刀子》中,诗人以雪亮的刀子比喻皎洁的月亮,使以柔美、温和、母性著称的月亮变得杀气腾腾。这把 “刀子”是 “割断/明日喉管的/刀子”,诗人以月的阴晴圆缺来写时光流逝,岁月无情,月亮如刀,刀刀催人老。在 《时间之伤》里诗人更是这样写道:“月光的肌肉何其苍白/而我时间的皮肤逐渐变黑/在风中/一层层脱落”,诗人将月人格化,她苍白的肌肉与 “我”逐渐变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轮冷酷的月亮与时间同流合污,剥蚀了“我”曾经丰腴的肌肤,使 “我”深受 “时间之伤”。洛夫诗中的月意象并未完全摆脱古典的韵味,温婉柔美的月光也常出现于他的诗作中。“他嗅完一朵初绽的菊花似乎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月亮总是无声,总是不痛不痒地/抚着他的额。露水渐渐转白”(《岁末无雪》)。作为不介入人事悲喜的客观存在体,此诗中的月亮虽然仍旧无声,仍旧 “不痛不痒”,却在岁末百无聊赖之际,以轻柔的光辉抚摸诗中人苍老的额头,陪伴他品尝午夜的孤寂。这样的月亮,少了些诡异、冰冷的味道,却多了一些柔情与澄澈的质感。沿用古典诗中乡愁的意涵,洛夫诗中的月亮也系满了游子怀乡的思绪。“不是霜啊/而乡愁竟在我们的血肉中旋成年轮/在千百次的/月落处”(《床前明月光》);“最终/被选择的天涯/却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语词/仍悬在/故乡失血的天空”(《漂木·漂木·1》);“其实,我们从不知道回家的路/路在云中/在闪烁的星光中/在狂涛中/有时又藏在细碎的浪花里/路在四月的贸易风中/在秋夜的月色中”(《漂木·鲑,垂死的逼视·1》)。两次放逐的人生体验,成为洛夫心中忧郁难解的幽闷,乡愁是诗人口中不断吟哦的旋律。不论身体如何迁移,住在诗人心中的明月,却永远悬在故乡的天空上,成为洛夫一生的系念。《漂木》中的月亮不再凄楚,反而透露出一种看透宿命、把握当下的心甘情愿。在洛夫笔下,圣洁、超越的月亮回归了人间,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平添了一份亲切、一份人情。“一半月亮/沿着苍古的河岸/在搜寻曾经/一度圆过的自己/一拐弯/迎面又撞上了自己的另一半”(《梦见》),落入凡间的月亮,开始寻找失去的另一半,在追求圆满的过程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在洛夫笔下,解开圣洁面纱的月亮,甚至具有了形而下的欲望:“李白从河里捞起的/只是一件褪了色的亵衣/用力拧干,最后/拧出了一小杯月光”(《漂木·浮瓶中的书札·致诗人·5》),坠入凡尘的月亮也具有人间的七情六欲,在洛夫看来,李白诗中的月亮未尝不是一种欲望的表达。洛夫诗中静谧的月光所营造的空灵之境,也带有几分禅宗的色彩。在澄澈明净的月光下,一颗清静无为的本心自然闲适,与万物同在,与宇宙共生。“不相信山中月光的皮肤是冰凉的?/你听,一个挑水的小和尚/一路喷嚏而去”(《夜登普门寺》),幽静的古刹在冰冷月光的照射下,透出丝丝凉意,这种 “凉”是穿透骨髓的清净,是 “表里俱澄澈”的明心见性。“月落无声,雪落无声,我在万物寂灭中找到了我”(《大悲咒与我的释文》),在万物寂灭中,洛夫让自己回归素朴的原点,以心中一片皎然,呼应天地安静的脉息。月,是洛夫安放心灵的寂静之所。
(二)雪意象
雪,也是中国古典诗中常见的意象,岑参有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高适有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别董大》),柳宗元有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总之,雪在诗人的笔下姿态各异,妙趣横生。洛夫笔下的雪意象,更是其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一种象征。相对于月意象来讲,雪更多地承载了洛夫的天涯乡愁。洛夫爱雪,湖南的雪、韩国的雪、温哥华的雪,都出现于诗人笔下,他的书房——“雪楼”,即是以雪命名。洛夫对雪的喜爱自童年时期就开始了。童年生活中,故乡茫茫的白雪,成了诗人记忆中永远无法消退的画面。因此洛夫诗中的雪,经常与故乡、童年回忆交织在一起,而诗中的乡愁也总是弥漫着一种冷白的色调。“回首,乍见昨日秋千架上/冷白如雪的童年/迎面而来/啊!雪的肤香/秋千架上妹妹的肤香/如再荡高一些,势将心痛/势将看到院子里渐行渐速的/蓟草般的乡愁”(《时间之伤·雪地秋千》)。“童年在院子里堆的那个雪人/无论如何是溶不了的”(《读雪》),洛夫诗中的雪带着香气,那是妹妹肌肤的香气,更是乡愁的味道,它弥漫在诗人身边,虽历经数十年,依旧难以消散,且如蓟草般迅速蔓延、增生。那个融化不了的雪人,是诗人心中无法淡忘的故乡情结和对童年遥远的追思。对于漂泊天涯的游子而言,乡愁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随着洛夫移居加拿大,心中的乡愁不仅没有消减,反而与日俱增。“我,天涯的一束白发/雪水洗白的/……/渡船由彼岸开来/你说回家了,烟,水,与月光/与你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每一幅脸都已结冰/下雪了吗?/我负手站在窗口//看着雪景里的你渐渐融化”(《漂木·浮瓶中的书札·致母亲·2》),诗人将自己比喻为被雪水洗白的 “一束白发”,乡愁似雪将诗人满头的青丝变为白发,这是日日思念故乡的结果。在岁月的冲刷之下,童年的欢乐或许会远去,母亲的面容或许会模糊,但记忆中的这一切却依然存在,它已经被刻入骨髓深处,成为天涯游子骨血内难以磨灭的基因。雪,在洛夫诗中不仅是乡愁的代名词,更以其惨白冰冷的形象,成为高贵洁白、孤独寂寞的象征。“当蠹鱼吃光了所有的文字且继续产卵/他开始发愣/沉思/默想他雪一般的身世,惨淡/如一张白纸”(《好怕走在他的背后当他沉默如一枚地雷》),人生惨淡如白纸一般,没有轰轰烈烈的辉煌,也无凄凄惶惶的落魄,生命单调如雪,这是寂寞者的空虚,更是空虚者的寂寞。而惨白人生的背后,未尝不是诗中人不惹纤尘的纯洁个性,因始终纯洁如一,故显得单调苍白。正如洛夫在 《杜甫草堂》中所写的一样,“泪湿的衣襟,诗稿,微秃的前额/以及随时可能在骨髓里升起的雪意/都已是失去了名字,容貌,气味的/辉煌过也苍凉过的/风/的/昨日”,杜甫骨髓里升起的雪意是他冰清玉洁的人格,是他忧国忧民的高贵情感。在诗人笔下,清冷的雪象征着一种不被玷污的灵魂。洛夫诗中的雪,因触之冰冷,常能给人清净、镇定之感。“一根先验的木头/由此岸浮到彼岸/持续不断地搜寻那/铜质的/神性的声音/持续以雪水浇头/以极度清醒的/超越训诂学的方式/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漂木·漂木·4》,雪可以冷却心中的欲望,抚平躁动的情绪,“以雪水浇头”,混乱的思绪得以冷静,灵魂也因此从兽性的骚动提升至神性的层次。在洛夫诗中,茫茫的白雪与 “白色的空气”、“白鹭”、“纯白的鹭鸶”、“白杨等意象,共同营造出一种“白色的喧嚣”。这种 “白”蕴含着清韵空灵之美,透露出辽阔悠远的情思。时空在这一片纯白静谧的无声世界里,似乎已经静止,瞬间成为永恒。在雪地里,过去的一切被掩埋,包括 “情绪的蝎子/思想的蟑螂/久久藏在潜意识里的一截毒藤”(《初雪》),甚至是过去的自己,所谓的 “澡雪精神”便是如此。“五十年来第一次我被慑住,被蛊惑/被一双野性的手猛力拉过来/又远远推开/这是亘古的一声独白/百年孤寂后面还有更多的孤寂,更多的百年”,这是一种广阔无垠的空无之境,是一种纯洁无瑕的天地情怀。雪,炫白了世界,开启了诗人封闭的心灵,使他得以与过去对话,向未来展望。在茫茫的宇宙时空中,诗人与天地同孤寂,与亘古共永恒。
二、不同时期的自然意象
洛夫是一位不断求新求异的诗人,每写一首诗对他来讲都是一次新的出发,在诗人看来,“写诗必须要不断占领,不断放弃”。在自然意象的选择与营构上,诗人亦是如此。洛夫曾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分为五个时期:抒情时期 (1947—1952年)、现代诗探索时期(1954—1970年)、反思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时期(1971—1985年)、乡愁诗时期 (1985—1995年)、天涯美学时期 (1996—今)。随着洛夫人生经历的变化和诗风的不断调整,诗中的自然意象也在发生变化,不同时期的诗歌呈现出不同的自然图景。
抒情时期的自然意象以明朗为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营造的是一幅阳光明媚的自然风景。《灵河》中较常出现的意象为充满诱惑的果园、柔软的阳光、炸裂的石榴、迷蒙的烟雨、暧昧的四月等。作为诗人的处女作,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洛夫写给初恋女友的情诗。爱情初临时的欣慰与甘醇弥漫于诗句之间,使自然意象笼罩了一层愉悦、明媚的色彩。初入诗坛的洛夫,并未摆脱大陆二三十年代诗风的影响,抒情性是他诗歌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的作品集 《灵河》,因过度抒情常使读者产生一种软绵绵的感觉。1976年诗集再版时,诗人将原来的诗篇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特别是在意象的经营上,有些改动已全然找不到原诗的影子,例如,《禁园》原有的诗句 “风在轻轻地推着门,不敢掀起/我怕鸽子衔走梦的余粒……”,被全部删去,轻柔的风、衔梦的鸽子这些单纯、细腻、略带忧伤的诗句,只属于青年时代的洛夫。战争打破了诗人年轻的幻想,洛夫的诗歌也因此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现代诗探索时期的自然意象告别了前期的明朗、单纯,而变得衰败、焦虑。“从夹竹桃与凤尾草病了的下午走出”(《石室之死亡·9》),“而雪的声音如此暴躁,犹之鳄鱼的肤色”(《石室之死亡·12》),代表生命力的植物展现出病态的一面,雪没有了 《灵河》时的纯洁无瑕,而变得暗淡、沉重。太阳没有了女性的阴柔,而充满了男性的力量,阳光不是轻轻地缠绕着常春藤,而是骤然将树影劈开。“石榴首次爆裂时所生出的那种欲望/升起于你们的对视”(《石室之死亡·55》),石榴这一意象在 《灵河》中也多次出现,如 “哦,石榴已成熟,这动人的炸裂/每一颗都闪烁着光,闪烁着你的名字”(《石榴树》)。从炸裂到爆裂,诗歌的力度有所增加,后者更能体现出果实成熟后丰满欲裂的状态。其实,诗人此处并不仅是在写果实的成熟,而是欲望的书写与展现,如果说 《灵河》时期是纯洁的相思爱恋,那么此时便是一种性爱的渴求与表达。这一时期是诗人对生命全面探索的时期,也是诗人生命中最冷澈、最飞扬的时期。切身的战争体验,让诗人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自然意象也多了一份诗人对生死的思考。“清晨为承接另一颗星的下坠而醒来”(《石室之死亡·51》),清晨本是希望的开始,星的坠落是绚烂的终结,而此处,清晨为迎接一种死亡而醒来,在诗人看来,死亡的终点即为生命的起点。
反思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时期,诗人意识到,西方现代主义虽为其诗歌创作的想象与灵感开启了一扇窗口,但作品实验性较强、诗风晦涩也拉开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七十年代洛夫重新认识和评估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洛夫曾说,“我是在现代诗探索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个,但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也是做得最彻底,最具体的一个。”[2]自然意象是古典诗歌的主要意象,洛夫对古典诗幽玄而精致的意象语言较为偏爱,诗人这一时期的自然意象遂带有一种空灵、冷凝的艺术美。《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撑着一把油纸伞
唱着 “三月李子酸”
众山之中
我是唯一的一双芒鞋
啄木鸟 空空
回声 洞洞
一棵树在啄痛中回旋而上
入山
不见雨
伞绕着一块青石飞
那里坐着一个抱头的男子
看着烟蒂成灰
下山
人不见雨
三粒苦松子
沿着路标一直滚到我的脚前
伸手抓起
竟是一把鸟声
此诗很容易令读者想到 “月出惊山鸟”、“鸟鸣山更幽”、“竹杖芒鞋轻胜马”等古典诗句。诗人入山寻雨而无所得,竟抓住了一把鸟声。这首诗写了诗人由追寻到失落,再到豁然开朗的状态。唯一的芒鞋可以看出诗人的孤寂,“一棵树在啄痛中回旋而上”是生命在痛苦中成长的状态,诗人追寻此物而得彼物,鸟声是诗人意外所得,他的出现是一份突然降临的惊喜,令迷惘的诗人顿然醒悟。诗人将情感化为冷峻的意象,感性随之有了深度。诗中的 “雨”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意象,它体现了一种不断运动、不断更新、充满生机的 “道”。
乡愁时期诗人的创作思路依然沿用上一时期的,只不过在题材上以乡愁为主。这一时期的自然意象除了具有空灵、冷凝的特点外,还平添了几分怅惘与愁思。洛夫乡愁诗的创作并不自这一阶段始,《魔歌》时期就已经有乡愁诗问世,但这一时期的乡愁诗较之以前,情感更真挚、深重,尤其是大陆探亲之后的作品更是触人心弦。在自然意象的设置上,诗人较多选择带有大陆地方色彩的自然意象,如白杨、西湖、烟雨江南等,“极目不见何处是烟雨西湖/何处是我的江南水乡”(《车上读杜甫·3》),“那年,在江南/只有杨柳默然垂首/因它已哭满了/一池塘的泪”(《边陲人的独白》, “为了你的焦渴/西湖与漓江蓄了满眼眶的水/是耶非耶……李商隐曰: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是耶非耶”(《是耶非耶》)。诗中的江南,不只是诗人的生活体验,也不只是单纯的故乡记忆,而是酝酿于心灵深处的一种情感,是深藏于诗人意识里的中国情结。江南是故园的缩影,它牵动了诗人心中千丝万缕的文化乡愁。
天涯美学时期指诗人1996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之后的创作期,包括 《漂木》《背向大海》等作品。漂泊海外的孤寂心境、个人命运的悲剧情怀、超越时空的宇宙境界、放逐天涯的失乡之痛触发诗人开启一段新的精神之旅。这一时期的自然意象,跟 《漂木》的篇幅一样,辽阔、壮美,具有一种苍茫而宏大的气势。“落日/在海滩上/未留一句遗言/便与天涯的向日葵/双双偕亡”,《漂木·漂木·1》开头就为全诗奠定了一个壮美的格调。落日与海滩置于一起,一个是永恒的时间之维,一个是无限的空间之域,甚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气势。与落日偕亡的是一株向日葵,这株向日葵不是栽植于田园,也不是长于野外,而是生于天涯。何谓天涯?洛夫眼中的天涯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仅是空间的概念,更是时间的概念,是心灵与精神上追索。“当河谷上空一只鹰鹫/俯冲而下/叼去了/河面上一层薄薄的月光/时间噤声/故事正要开始”(《漂木·鲑,垂死的逼视·2》),鹰鹫从高空俯冲而下,刁起的不是水中的鱼,而是水里的月光。鹰俯冲所带来的距离感,与天上之月和水中之月所造成的空间感合为一体,空间被极度拉大。鹰冲破水面的刹那,不是打破平静,而是带来瞬间的静止,时间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一段故事即将开始,关于流浪,关于漂泊,关于寻找。
总之,自然意象是洛夫对自然和生命本真的一种体验,是诗人的古典情思与现代诗情的碰撞与汇通。无情的自然在诗人笔下变得有情,人的生机与自然的生机融合无间。在人与自然的交汇中,洛夫的诗情诗韵得以丰富和升华。洛夫不同时期诗歌创作呈现出的不同图景,体现了诗人 “不断放弃,不断占领”的创作理念,也反映出随着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的变化,洛夫的价值判断与美学追求在矛盾与冲突中的成熟。
[1]吴 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9.
[2]龙彼德.洛夫访谈录[J].诗探索,2002(1—2).
[责任编辑:黄志洪]
I106.2
A
1674-3652(2014)02-0089-04
2013-12-24
张春艳,女,江苏徐州人,主要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方 忠,男,江苏南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