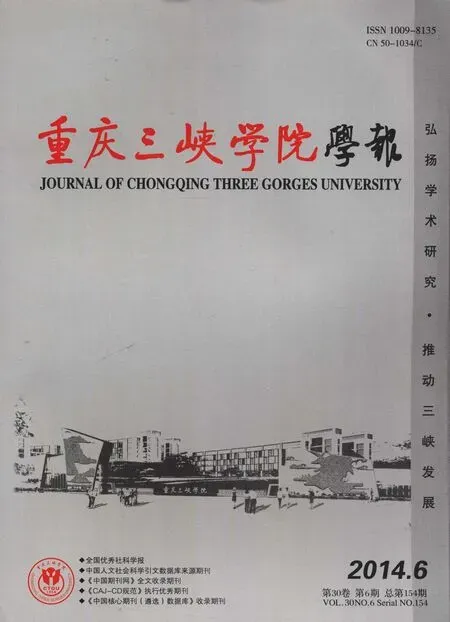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影像资源的效用及限度
刘志华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 400715)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影像资源的效用及限度
刘志华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 400715)
图像时代文学作品的影像化倾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供了可兹利用的丰富资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文学文本意义丰富性的消解与遮蔽。明确影像的效用及其限度,把握好相关影像资源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化解图文的矛盾,才能把影像资源作为文学教学有益的补充。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影像;效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提醒人们,世界正在“被把握为图像”[1]72。随着信息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世俗化生存的加剧,今天的世界已全面进入图像时代。文学文本也开始大量向影像转化,文学与影像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密切。文学存在样态及传播渠道的变化,势必影响到文学的阅读与接受,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生普遍是受阅读文学作品的影响而走进电影院的,或是基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而对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产生兴趣。那时,人们往往把影像作为文学的延伸阅读或印证式鉴赏,影视更多要借助文学经典来抬高自己。今天,这种情况已发生根本性逆转。学生普遍对阅读文学文本缺乏浓厚兴趣,往往通过影像了解作品概要,更喜欢影像的直观、时尚与“生动”,不再迷恋文字作为“冷媒介”的“深度”和对想象力的激发。面对影视文本,觉得津津有味,面对文字文本,却提不起阅读兴趣。即使是那些时尚化的配合影视作品播出的影视同期书,多数也是书店橱窗的摆设,随着影视作品热播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很少有人真正阅读。
今天,互联网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人们读图倾向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提供了更多可兹选择的影像资料。现代文学中经典作品大多有影视改编,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伤逝》,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腐蚀》、《春蚕》,巴金的《家》、《寒夜》,许地山的《春桃》,沈从文的《边城》、《萧萧》,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老舍的《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茶馆》,张爱玲的《金锁记》、《半生缘》、《红玫瑰白玫瑰》、《色·戒》等,都被搬上了银幕,部分作品还被多次改编;钱钟书的《围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还被演绎成电视连续剧。当代作家杜鹏程、柳青、杨沫、王蒙、张贤亮、王安忆、余华、刘震云、刘恒、贾平凹、王朔、莫言、陈忠实、毕飞宇、赵本夫等的作品都有影视剧改编。当代文学中大量的作品是通过影视走进人们视野的。王朔被称为“触电”最频繁的作家,十余篇小说的影视改编为他赚得了知名度;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主要靠电影《红高粱》家喻户晓;对海岩文学作品的了解,多数读者也是从影视开始的。
另外,作家的人生故事也开始大量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新浪网、凤凰网等制作了大量的访谈节目和传记片。中央电视台的“人物”、“艺术人生”、“见证”、“子午书简”等节目颇具影响。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系列节目就把鲁迅、郭沫若、沈从文、丁玲、徐志摩、萧红、郁达夫等的情爱故事搬上荧屏,对了解作家性情与创作观念,是难得的资料。互联网的便利使我们不必走进电影院,甚至无需耐心等待电视台的节目播出,这为我们带来了资料的丰富和读取时间上的便利。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而言,借助新媒体和互联网,可以大量利用相关影像进行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把以前单纯的教师讲解的平面化教学变为视频、声音、图像的立体化课堂,大大增加了课堂教学中的信息量和直观性,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今天,通过影像来集约作家作品信息,不失为教学与时俱进的需要。
二
影像资料在给现当代文学教学带来内容的丰富与形式多样的同时,影像阅读也可能给大学文学教育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是影像与文字在表意方式上存在差异,影像作品对文学作品的诠释可能存在大量意义贬损或者附赘情况,有可能干扰甚至扭曲受众对文学作品的认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属于“冷”媒介,“冷媒介清晰度低,需要人深度卷入、积极参与、填补信息”[2]7,因此文学阅读需要想象力与语言难度的双重克服。而影视依靠的主要是表演、台词、音响、氛围烘托和蒙太奇等剪辑手段,是技术化和群体创意的产物,依托的是导演、明星的人气效应。影视作为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其与文学表现在“语言”和方式上存在差异,这会带来二者在内涵诠释深度上的区别。文学的本体是语言以及对语言的创造,而影像主要依赖的是对技术的运用。文学的语言内部张力更丰富,读者二度创造的空间更大;影像的直观性,在调动读者想象力方面比之文学来说有所欠缺。所以,文学作品常常在影视改编中造成意义的流失,甚至为了迎合观众而进行情节演绎和附赘。特别是今天的很多影视作品,走明星路线,对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往往迎合世俗和时尚趣味。如电视剧《京华烟云》、《啼笑因缘》,与小说相比,都存在过分煽情的倾向。而对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导演所重的是小说中的情欲纠葛,白灵等重要人物都未出场,很难见出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内涵。当然,也不乏《芙蓉镇》那样改编成功的案例,其丰富的人文和人性内涵,似乎比原作的意义更为丰富,但这样的作品需要高超的导演和出色的演员,类似的影视作品凤毛麟角。就整体而言,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基于影视受众的大众化和表现方式的具象化,大多都很难企及文学文本意义和内涵的丰富性。王安忆就批评说:“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3]88
二是影像的直观容易导致人们感觉的迟钝与心灵的粗鄙化,这与文学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文学是探讨人类可能性的艺术,是伟大心灵在不同时空中的幽思感叹,文学可以抵达镜头无法触及的地方,抵达人的精神高处和内心深处。读者通过和伟大心灵的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影像主要依赖于视觉印象的直观,故是人类童年期的最爱。读图较少深度情感的掺和,尤其缺乏心灵的共振与摇荡,容易造成心灵的惰性和情感上的从众,使人沉迷于世俗趣味。人自由敏锐的心灵往往容易被影像的平面化直观性所俘获。心理学研究证实,长期置身图像环境的人对世界的感受能力会有所下降,而且图像往往带着物的痕迹,容易造成人的诗性感悟力的衰退,从而影响到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欲望。“影视表现手法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众化要求,造成了文学文本想象空间被挤压,掏空了文学的诗性和美感,使文学本性中的崇高越发不能承受影视化接受之轻。”[4]现代人喜欢影像直观带来的视觉快感,常常忽略了对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开掘,从而造成对世界诗意把握能力的退化,这是需要加倍警惕的。
三是影像的时尚追求与文学的精神性之间存在矛盾。影像以吸引人的注意力为第一要旨,往往追慕时尚,打着时代的烙印和追逐商业利润的痕迹。即使是改编于上世纪的影视作品,时代印痕也非常明显。当今的电视媒体,被称为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受众的宽泛,他们必须尽量调和满足多数人的口味,追求审美的社会平均数。影视的大众文化特征,其对世俗欲望的渲染、炒作,煽情就成为惯用的招数;媒体的行为往往带着明显的商业目的,那些用“文化”或者“艺术”精心包装的东西,其背后多为利益所限,往往与艺术无关。如2004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28集电视剧《林海雪原》,就给杨子荣、少剑波增加了许多三角感情戏,以至于被网络戏称为“林海情缘”。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借王琦瑶与几个男性间的情感纠葛,重点是对城市与人生命运的思考,表现上海的市民化和对日常生活的偏爱。而被关锦鹏改编成电影,则变成了“一女四男”的情爱戏,小说被置换成了一个旧上海的情欲故事。文学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价值,是尽量远离现实的理想高蹈。虽然受消费文化滥觞的影响,文坛也出现了大量的时尚化读物,但文学的世界主流还是其对高贵精神的捍卫和对人性丰富可能的透视,尤其是对人类诗性的坚持。作为文学教育者,我们不排斥影像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但我们更应坚守文学的精神矿藏,尤其是不能通过影像读图来替代文学文本的阅读体验。
四是文学作品在影像改编中容易出现时代性的误读现象。影像比之文学而言,具有更强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也造成一些影像对文学作品意义的理解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阿Q正传》经过1958年和1981年两次电影改编,前者明显是在附和政治革命,后者又过分夸大人物的喜剧元素,尤其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意识的迎合,体现为另一种形式的教化。而到1999年改编成《阿Q的故事》电视剧的时候,后现代的戏说背离了原著的精神,恶搞与戏谑一起上阵,阿Q被打扮成一个后现代的“英雄”。一些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更是被大众趣味或者社会潮流牵着鼻子走。电影《白鹿原》走的是感情戏的路线,而电影《高兴》把农民离乡进城的艰难与悲情打上时代的亮色,把悲剧演成了正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影视剧改编,比较重视悲剧情愫与启蒙情怀,而当下则过于强调欲望叙事与迎合社会主旋律。如果仅仅通过影像资料来理解文学作品,或者把影像等同文学作品,势必导致对文学作品的误读。影像对文学作品的故事性诠释较为容易,但对文学的美感和更深层次的内涵,尤其是诗性韵味的表现,却有相当难度。面对影像质量的参差不齐,我们应披沙拣金,发现那些好的作品,但绝不可以把影像读图视为一条代替文字阅读的捷径。
三
如何利用新媒介时代影像资源获取的便利,同时克服其负面效应来指导学生进行文学阅读呢?我们不妨做以下一些尝试。
首先,把影像作为一种资料补充,重点在激发学生对文学文本的审美阅读兴趣。教师的课堂不能是枯燥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阅读”殿堂,尤其是对那些出身在新媒体时代的指上一族青年学生而言更是如此,但也不能成为“看戏”的剧场,更不能把讲台变成资料剪辑和展示的操作台。好戏连台,看似热闹,其实并不能带来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有主体的介入,以自己的方式引导学生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感知和阅读,尤其是强调把对文学作品的技术性阅读和感悟性阅读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将文学作品作为艺术交还到学生手中。文学的阅读既需要一定的知识,更需要生命和情感的参与和体会,借助影像的目的是把学生引入文学博大的殿堂,而绝不是把学生从文学丰富的文本世界引向一个直观的图像世界。
其次,教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要熟悉,能够引导学生对影像文本与文学文本进行比较性阅读,明确影像文本的成功和局限之处。教师要能够让学生在图像与文字的双重阅读中游刃有余而不至失之偏颇。我们强调文学文本阅读的同时,并非排斥对影像的阅读和借用。二者应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互相激发艺术的想象与体验。因为当代很多文学创作与影视关系密切。王朔坦言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影视的影响。他的小说《我是你爸爸》最初就是冯小刚一个电视剧的设想;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实际上是张艺谋、杨凤良、谢园、顾长卫等的一次集体创作的结果[5]。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催生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并非特例,这也启发我们对文学的接受与观照方式有进行调整的必要,纯粹学院式的文学教育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看来难免有些理想主义,也可能存在诸多盲点。
第三,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文学和影像阅读。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文学阅读和影像阅读的知识教育,让他们能够在各自的知识规范中进行阅读,明确彼此的界限和特点,做到不互相僭越,彼此替代。读不懂本身,一方面可能是作品的难度所致,但也很可能是阅读方式的问题,尤其是相关背景知识的欠缺。影像本身切合了新媒体时代的特点,也契合这个时代人的存在本质,是人的审美欲求与技术的合谋。而文学本身,虽有希利斯·米勒等终结论的说辞,但在深刻性方面依然体现出难以替代的优势。相信随着影像技术的提高和美学观念的进步,影视对文学作品意义的诠释空间也会大大拓展,影视反刍文学不是没有可能。张艺谋曾说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6]10,其实,反之亦然。在今天,如果文学对影像的力量视而不见,难免给人文学有自欺和自负的嫌疑。
[1][德]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M]//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4]储兆文.影视化接受:文学不能承受之轻[J].唐都学刊,2004(5):103-105.
[5]王朔.我看王朔[N].北京青年报,2001-01-11.
[6]李尔葳.张艺谋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张新玲)
Ut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Image Resources in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U Zhi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The tendency of video material of literature in image times provides rich resources for the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has reduced and obstructed the richness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nly by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ut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video material, a good mastery of the re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and video material and a sound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of illustration and text can we effectively use video material in literature teaching.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ideo; utilities;
G642
A
1009-8135(2014)06-0141-04
2014-07-10
刘志华(1972-),重庆铜梁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美学。
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影像资源的效用研究: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为例”(2012-GX-037);西南大学教改课题(2010JY06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