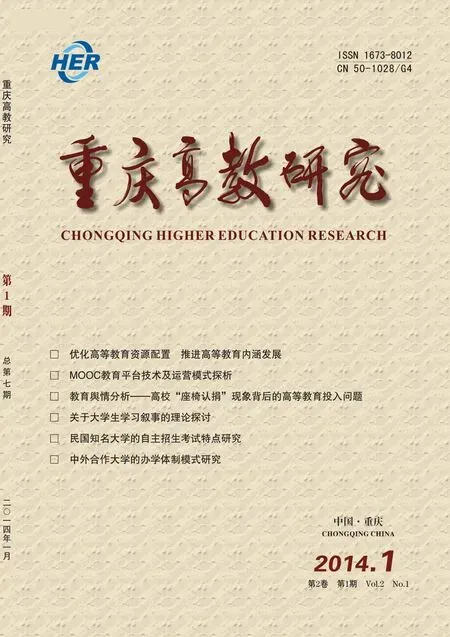高等教育评价模式的比较分析
洪 敏,吴云香
(1.复旦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433; 2.上海财经大学 发展规划处, 上海 200433)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的竞争力对于高等教育的依赖性逐渐加强,高等教育竞争力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评价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从国际范围来看,如何评价一国高等教育,已有诸多实践。根据视角的不同,对一国高等教育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一是知识资本视角,其代表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侧重于对高等教育蕴含的知识资本的评价;二是人力资本视角,其代表是21世纪初期安东尼·马斯拉克等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侧重于对高等教育蕴含的人力资本的评价;三是系统效能视角,其代表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21世纪大学协会的《U21国家高等教育排行榜》,侧重于对高等教育系统效能的评价。
一、知识资本视角
“知识资本”是西方经济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知识资本是知识价值的经济化表述,这一概念本身反映了知识与经济的联系。列夫·爱德文森(Leif Edvinsson)是全球知识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知识资本分为两部分:人力智力资本和结构智力资本。前者包括专利、技术和其他固化了的智力,后者是一个结构化的体系,即经过人员流动,个人的智力转变成为集体财产的知识资本。通过创造更多市场价值总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知识资本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后来“知识资本”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
作为培养知识资本的主要源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为知识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使得知识资本与高等教育紧密相连。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的产出之一,知识资本成为一些高等教育评价的重要价值取向。其突出代表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自1980 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竞争力评估标准。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是否达到繁荣和增长的可持续水平的经济环境及其稳定性的情况。在该报告中,竞争力被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制度、政策和要素的组合”。报告认为,高等教育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国竞争力有12个一级指标(支柱),其中直接涉及高等教育的一级指标有“高等教育和培训”以及“商业成熟度以及创新”[1]4-7。“高等教育和培训”下设3个二级指标,即教育数量、教育质量和培训,各占33%的权重。“教育数量”下设3个三级指标,分别是:中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教育支出;“教育质量”也有3个三级指标,分别是:教育体制质量、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以及管理学院质量。“商业成熟度以及创新”下设的二级指标“创新”包括如下7个三级指标: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公司研发的话费、大学——行业研发联合、政府对高级技术产品的采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和发明专利。
报告认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和培训对想要超越简单的生产加工、产品和提升价值链的国家至关重要。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培育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够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工人资源。”[1]7报告对于知识创新的作用更是不惜笔墨。“从长远来看,生活标准只有通过创新来提高。当国家奔向知识前沿,整合和采用外援技术的可能性趋于消失时,创新对国家来说尤其重要。”[1]7
根据12个一级指标的不同得分计算权重,报告将不同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其中,高等教育作为“效率提高因子”的一部分,是一国进入效率驱动型阶段的关键指标之一;“创新”成为一国进入创新驱动型阶段的关键指标之一。这就敦促各国从一国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去审视、重视和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性也因此得以提升。
知识资本视角下的评价注重高等教育的知识资本方面,它具有如下优点:首先,这种评价凸显了高等教育生产知识资本的作用,将高等教育竞争力纳入一国竞争力的范畴,提升了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地位;其次,这种评价将培训纳入高等教育竞争力的范畴,认为培训是高等教育的延伸,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内涵;再次,这种评价将创新纳入高等教育竞争力的范畴,通过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大学——行业研发联合、发明专利等指标,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外延;最后,这种评价注重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无论是从一国竞争力看高等教育竞争力,还是从高等教育竞争力看一国竞争力,都反映了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可分割。这为系统效能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评价模式埋下了伏笔。
二、人力资本视角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2]。这一理论批判过去仅仅关注物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数量,却忽视劳动者智力因素的影响,认为“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人力资本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的作用更大”[3]42,“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比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3]46。贝克尔还认为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这种投资可以提高人力的智力、知识和技术水平。正因如此,一些高等教育评价将人力资本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其突出代表是安东尼·马斯拉克的评价指标体系。
2005年,俄罗斯学者安东尼·马斯拉克等为测量各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从人力资本视角构建一个有13个指标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并利用联合国教科文整理1994年的统计数据,对全球39个国家进行了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排名。在13项指标中,其中4个指标比较常规,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经费和生师比,它们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要素,其余9个指标均与人力资本有关,其中1个指标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数量(在该指标体系中人力资源包括学生和教职工),其他8个指标均针对毕业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即未加权的毕业生人数占人力资源的比例、加权毕业生人数占人力资源的比例、人文学科毕业生比例、自然科学毕业生比例、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毕业生比例、医科毕业生比例、工科毕业生比例和商学毕业生比例。
也就是说,在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中,人力资本指标比重将近70%,成为评价一国高等教育系统优劣的最重要考量指标,可见对其重视程度。舒尔茨曾指出:“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做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做出贡献。”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国经济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的倚重。通过投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帮助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的角度彰显了高等教育的价值。
三、系统效能视角
系统理论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他认为,系统就是“过程的复合体”,“具有集合性、层次性、相关性等三大特征和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环境适应性及综合性等五大要点。”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系统或整体均有纵向层次和横向层次:纵向层次意味着每一级指标就是—个层次,而横向层次则指各个指标之间互不包含与兼容,指标与指标之间层次鲜明[4]。
系统效能是指系统在规定的条件下满足定量特征和服务要求的能力和水平。它综合反映了系统的可用性、可信性及固有能力。应用到教育领域中,系统效能理论认为学校也是一个系统,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这一大系统则综合反映了教育系统的可用性、可信性及固有能力。也可以说,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一个大系统,其下还有一些子系统(一级评价指标),每个子系统下又有子子系统(二级指标及下一级指标),而同时学校本身也是一个整体,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能够测量学校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协调和内部结构的稳定合理的状况。
在实践中,也有高等教育评价采取系统效能的视角,其代表是21世纪大学协会发布的《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
21世纪大学协会(Universitas 21,简称U21)成立于1997年,由欧洲、北美、东亚和大洋洲21所研究型大学组成,旨在协助成员学校实现全球化的教育与科研。2012年5月,U21发布《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下简称《U21》),其评估对象包括全球48个国家。《U21》构建的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估体系有4个一级指标:资源、环境、连接性和产出,比重分别为25%、25%、10%和40%。其中“资源”下有5个二级指标,包括高等教育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高等教育总支出占GDP百分比、高等教育生均支出、高等教育研发支出占GDP百分比和高等教育研发人均支出;“环境”下有4个二级指标,即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女研究员比例、数据质量和政策监管环境定性测量;“连接性”则包含高等教育中国际学生比例和国际合作文章比例两项二级指标;“产出”下有9个二级指标,为高等院校论文总数、高等院校人均论文数、影响因子指数、一国好大学密度、一国好大学卓越研究指数、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符合条件人口的比例、24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比例、研究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和24~65岁中有高等教育学历与中等教育学历人口失业率比值[5]。
这种评价模式继承并发扬了以往高等教育评价对于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视。《U21》的评价中一级指标“产出”高达全部权重的40%,其下设的9个二级指标中,有5个指标是对知识资本的评价,主要是对高校论文、好大学、好大学卓越研究指数的评价,另外4个指标是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数量及比例的角度评价了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
与此前的评价模式不同的是,《U21》明显体现出系统效能的理论视角。譬如,在“环境”这一指标中,既有从性别角度评价高等教育的系统内部情况,也有从数据、政策等方面评价高等教育的外部运行情况;一级指标“连接性”更是直接测量高校与国际的联系互动。
进一步分析发现,《U21》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实际上反映了高等教育投入——中间过程——产出的全部过程。在一些子指标的构建上,也蕴含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如通过“连接性”这一指标突出了国际视野,通过“环境”中一些子指标如女性比例体现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
或许可以说,系统效能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评价模式是对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的高等教育评价模式的扬弃。
四、结论
(一)国家高等教育评价模式有不同的评价视角
国家高等教育评价模式的不断发展从侧面反映了人们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在一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渐认可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富有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这一观点。目前高等教育评价模式采取的不同视角,主要是知识资本视角、人力资本视角和系统效能视角。
知识资本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评价突出了高等教育促进知识创新的功能,与“大学是产生高深知识的地方”这一古老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评价模式侧重于培养人、并将人的培养转化为生产力,突出了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颇有威斯康星理念的痕迹;而系统效能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评价则凸显了系统的思维和高度,彰显出一种更为广阔、宏大的视野,表明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里二者之间的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并且,一些先进的价值观念,也反映到评价之中。三种评价模式的立足点也不尽一致。知识资本视角与人力资本视角的评价均立足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微观考察其内部情况;而系统效能视角的评价则立足于社会系统的高度来评价高等教育,更为宏观。一言以蔽之,三种评价模式,各有侧重。
(二)系统效能视角将成为高等教育评价的发展方向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本视角与知识经济视角的评价的局限性逐渐显露。知识资本视角的评价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评价,而是寓高等教育评价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之中,独立性欠缺。而人力资本只是高等教育价值的一部分,单以此来评估高等教育质量不免狭隘,并且它也没有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在系统性方面存在缺陷。比较而言,系统理论视角的评价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种评价更全面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情况。系统理论视角克服了评价对象与评价者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对二者中介即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环境的评估,试图更全面地反映这一系统的状态。高等教育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是互动的。一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价指标,必须既要有对该系统内部评价的指标,也要有其与整个社会系统互动的评价指标。
其次,这种评价更迎合教育国际化的背景。当今,各国之间的教育合作日益深入,教育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评价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为此,评估主体从各国内的各所高校,变成一国高等教育整体;高校与高校之间的比较,变成国与国之间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较量。
再次,这种评价正面的价值导向更加明显。高等教育的功能除了教学、科研之外,还具有社会服务的功能。促进社会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处、倡导男女平等价值观念、开拓国际视野等,在系统效能视角下的评价中多有体现。
基于此,系统效能视角的评价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注重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可能成为下阶段高等教育评价的发展方向。当然,目前三种评价模式并不能相互取代,而是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质量做出衡量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Schwab K, Sala-i-Martin X, Blanke J, et al.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9-2010[C].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9.
[2] 百度百科. 人力资本[EB/OL].(2013-05-30)[2013-09-15]. http://baike.baidu.com/view/743635.htm.
[3] 林荣日. 教育经济学[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4] 杨伦, 王莹. 构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J].江苏高教, 2009(2):34-37.
[5] Univeritos 21.u21 Ranking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EB/OL].(2013-05-28)[2013-09-16]. http://www.universitas 21.com/artide/projects/details/153/executive-summary-and-full-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