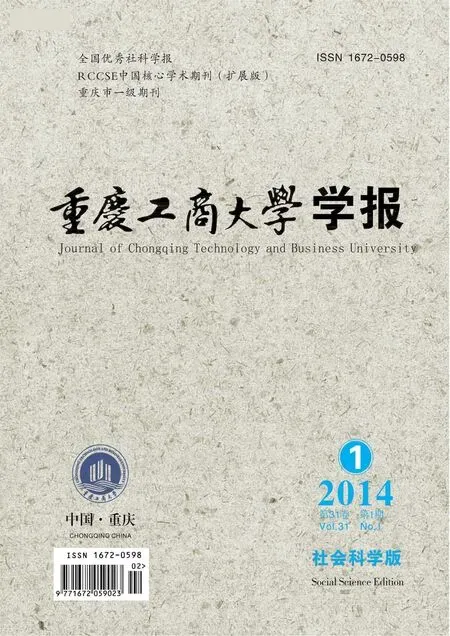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常启云
(1.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2.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南阳473100)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常启云1,2
(1.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2.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南阳473100)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网络舆论;舆论安全;公共舆论场;网络民意
我国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问题增多、群体矛盾极易产生的时期。当前,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折射出改革阵痛、体制弊端,显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的同时,也使得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一项崭新而又紧迫的热点话题。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传播如何促进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及其舆论的形成?二者如何转化?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及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合力形成的舆论压力,作为执政者该如何作为?本文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将传播学与社会学相结合,采取跨学科视野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
一、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
所谓舆情是某一群体或阶层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尤其是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有的以情绪、意见和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或隐或显的民意。它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抹杀的社会集体意识,带有一定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舆情的主体是民众,研究考察的是民众的情绪和意见。舆论是公众对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问题等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形成的大体一致的意见、立场、态度和观点的总和,具有公众性、公开性、评价性和权威性。依据舆论主体形式的不同,舆论包括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两种类型。舆论重在“众”和“论”,可以被“压制”“制造”,甚至被误导。同时,舆情与舆论又不可分割:民意是二者共同的底蕴,社会热点问题是二者共同的客体;不仅如此,舆情和舆论又可以相互转化,当民众的意见、情绪和态度公开表达出来形成公共的意见和看法时,舆情就转化为舆论;与此同时,舆情向舆论转化后,又会受到舆论的刺激而使之得以强化,进而再转变为新的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舆情与舆论两者之间不断地相互转换。
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和舆论,说到底就是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网络“意见”,借助网络平台的迅捷性、海量性、可复制性,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很容易在网络上形成网络舆情气候,并最终转化为舆论,并在不断挖掘出来的新信息的刺激下,实现着社会舆情与网络舆情、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的不断转化。概而言之,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一般有三个发展阶段:
(一)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相关网络舆情的“导火索”
一般来说,群体性事件是指社会生活中因群体利益受损,社会矛盾激化,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发生的聚众性对立行为。它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多以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种种群体行为为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是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相互耦合的结果,而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既是事件发生事实的反映,某种程度上又是促使其发生的直接诱因之一。正如克兰德曼斯所述,“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不是自发的,而是行动者、媒体和社会成员共同阐释和重新定义形式的过程”[1]。任何事件只有当它被感知并能够赋予其意义,能够被人们理解和解释时才会成为问题,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某种程度上就是其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
(二)网络媒体的特性促使有关群体性事件迅速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
信息海量、广泛覆盖、传播便捷、平等自由的媒体属性使得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交际的重要信息载体,其全时性、高效性、交互性也为网络舆情的酝酿与发酵提供了自由空间。哪里有事件发生,其所在地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关于事件的文字、图片甚至视频发送到网络上,这种无需把关、直接传送的信息传播方式能够真正在第一时间发布来自现场的报道。这里暂且不论有关事件的披露是否客观、正确,也不论其何种动机,总之,这样的帖子的出现,客观上成为相关事件在网络空间被知晓、被关注的开始,成为特定事件舆情传播的“种子”。尽管最初的“种子”帖子在其后的舆情演变中可能被网民忽略或者淹没于其他竞争性议题中,而那些真正在网络上产生影响、受到关注的帖子,经过其他网民特别是意见领袖的重写、充实、修改、推荐,很快会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得以迅速吸引人们的眼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中群体性事件议题的产生过程,本身可能是一个二级甚至多级传播的过程。与此同时,如果涉及事件的相关人员对事件的网络传播加以回应,这种应对反应也同样会被上传至网络中,又会对事态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作用之中,游走在网络与现实“双重世界”的网民会让事件很快由现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引发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互动,形成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气候。
不仅如此,网络技术也会给热点议题的传播提供便利。当一个议题受到网民的持续关注,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这些议题随着跟帖数或点击量的不断上升,并最终进入排行榜,从而引发更大的点击量,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网络媒体和社会传统媒体又会进行相互间的议程设置,进行观点和意见的交相碰撞、相互推动甚至共振,其结果就会形成好像龙卷风一样的舆情气候。
(三)群体性事件的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
由于群体性事件往往发端于社会的丑陋面和诸多的负面信息,而网络媒体不加过滤,有意或无意地放大渲染,过度宣传社会阴暗面,会对民众的思想形成强烈冲击,产生情绪低落、埋怨、激愤等负面舆情。这些负面舆情又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升级,使参与网络跟帖和讨论的人数逐步呈几何状递增,尤其是其讨论的问题越是与广大公众利益相关时,讨论进行得就会越来越激烈。同时,由于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影响面大,给予决策者思考的时间短,且网络的匿名性削弱了信息发布者的责任感和受到社会惩戒的担心,有时会发布不真实、不适当甚至恶意歪曲事实的信息或者情绪化的、偏激的评论,对信息量有限的网民产生误导,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甲地骚乱、乙地声援、丙地联动”的情况,使事件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加严重的方向发生变异。
社会危机通常表现为矛盾的尖锐对立,网络舆情危机是网络舆情集中爆发的外在表现。无论是网络舆情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恶化,还是群体性事件的恶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群体性事件在一定规模或气候的舆情影响下,事件的双方最终会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且持续受到越来越多的网民及社会公众的关注,从而形成更加严重的舆情危机,造成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的严重对立。而此时,危机中的各种因素相互制衡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左右着舆论的发展方向,使得多种多样的网络舆情在相互讨论和争论中,经过交流、融会、取舍和整合最终走向或单极聚化,或两极分化,或多极裂化,或零极淡化。于是,舆情也就最终转化为舆论。
二、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化
当互联网迅速发展并成为人们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且是比较开放的意愿表达方式时,舆情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力变得非常之大。然而,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网民关注和提出的话题、见解极具自发性、个体性和分散性,这种自发、个体、分散性的网络话语如何能够吸引公众视线,集结并上升为公众广泛关注的、焦点性公共话题?对公共话题各种见仁见智乃至截然对立的见解、观点又如何能够趋于一致,最终汇集成为体现民众呼声的公共舆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得不归功于网络舆情向舆论的转化。
一般而言,舆情向舆论的转化,应当是一种常态。当民众的态度和观点被公开表达出来并形成了群体的共同看法时,舆论研究强调的“公众”和“公开”意见的定义条件就得到了实现,舆情就会转变为舆论。网络上产生和传播的舆情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向舆论的更快、更多、更容易和更复杂转变,进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恐怕是个走丢了的孩子。我当时看着他也是不知为什么眼前就浮现出了我小学第一任同桌的形象。我俯下身问他:“小弟弟,和妈妈走丢了吗?”
网络舆情向舆论的转化过程,其实质就是网络舆论由最初的网络议题发展成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直至形成网络舆论的过程。舆论形成的标志是达成共识,社会认可,群体制约。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是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传播中经过意见聚合的过程形成的,网民通过自由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跟帖、回帖和点击看帖,形成网络舆论场。在网络舆论场中,围绕着公众关心的话题,网民的意见逐渐聚合,促使网络舆情转化为网络舆论。由此可见,要实现这种转化,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公共话题上的聚合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在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冲突频繁发生,人们也逐渐习惯于借助网络发表意见、交流观点、聚合思想、维护权益。因此,每当群体性事件一发生,有关该事件的信息就会在第一时间一方面进行人际传播,一方面进行网络传播。而群体性事件又大多与政府行为、贫富差距、伦理道德、社会公平与正义及国家民族利益密切相关,很容易聚焦网络公众的视线,聚合人气,使这些话题迅速成为各大网站的主题。伴随着网民对话题的点击次数以及发帖、跟帖数量的急骤增加,在网民积极的网络参与中,这些公共议题被鲜明地凸显出来,从而实现网民在这些公共话题上的聚合,为网络舆情向舆论的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重要平台
网络舆情由众说纷纭的或隐或显的网络意见发展成为大多数网民的公开一致意见即网络舆论,离不开论坛帖文、新闻跟帖、微博内容等形成的公共舆论场。“所谓舆论场,是指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2]舆论场的构成包含三个要素: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即舆论场和社会整体环境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大小;舆论场的渲染物或渲染气氛[3]。这三个要素为舆论产生聚合了大量外力作用,当它们刺激舆论主体时,容易使人们迅速萌发一种信念,并把人们的见解统纳到相同方向。这时,信念和见解就会铸成坚不可摧的意志合力,舆论也就展现出来。以微博、微信、QQ、人人等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社交媒体尽管形式各异,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均是在虚拟的人际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交流群体,每一个交流群体便形成一个舆论场,具有意见交互通道开放畅达、网民相邻密度和交往频率高的共同特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舆论场在总体上构成了网际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的宏观时空环境,即大的舆论场。这样,在大大小小的舆论场的作用下,不同观点层出不穷,不断地辩论交锋,在这种辩论交锋的过程中,整个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信息连同其细节均能被层层展现。同时,伴随事件过程的进展,网民对事件公共议题的各种见解也会逐步深化和不断拓展,对问题的分析更趋于理性,逐步呈现出问题越辩越明的效果,从而形成趋同意见,最终使包含各种观点及争论的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在辩论中逐步从多元走向趋同。
(三)意见领袖的出现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引领者
“一切舆论的形成都要经历个人意见、社会讨论、舆论领袖评价指导、获得权威性等无数力量互通互导、犬牙相制的过程。”[4]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其形成及转化也同样如此。由于网络中信息的海量性加上网上信息良莠不齐,当网民遇到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就迫切需要有一种权威的声音为网民答疑解惑。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由于事件本身议题的特殊性及高显著性,使得当地政府、专家学者、传统媒体成了天然的“意见领袖”。在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传播中,来自政府的声音、专家的意见、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包括网络论坛的版主帖子等均以其较高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在舆论形成及转化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导向作用。这些意见领袖时刻关注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断传播其权威性的观点和看法,与众多网民的意见形成互动。这种互动,一方面不仅能回答网民遇到的问题,而且能使网民们不但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不仅为网民设定了讨论的议程,而且还提供了可用来探讨议题的框架,从而影响其他网民的观点和行为,引领着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方向,甚至影响着事件本身的发展进程。
(四)媒介间的议程互动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催化剂
当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向舆论的转化及舆论之间的相互转化之所以更快、更多、更便捷,这其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议程互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本身就存在着相互设置议题的现象。网络的便捷性、大众化,尤其是手机、Ipad等移动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闻事件一旦发生,就会首先通过这些便携的移动媒体进行首次传播,在“把关人”和新闻选择因素作用的影响下,一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在网络媒体率先披露后,也同时会成为传统媒体的信息来源,从不同角度和深度以不同形式的新闻体裁对该新闻事件进行二次传播。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的介入又会强化新闻事件的传播,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网民参与网络讨论的积极性,使众多网民或集中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或不断爆料事件细节及进展情况,展开后续报道。如此循环往复,网络舆情和舆论正是在这两种媒介间的议程互动中不断实现转化,从而将事件推向深入。由此,一方面,传统新闻媒体舆论与网络媒体舆论之间的共振能够使有关新闻事件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并最终形成舆论的合力,从而加速网络舆情向舆论的转化速度和频率。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以其强大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功能把控着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方向。
三、面对网络民意,政府该如何作为
社会转型带来了利益多元化、社会公民化、观点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技术进步使得网络媒体正成为人人得以共享的信息平台,成为表民情、畅民意、集民智的舆论场所,二者的共同作用深刻改变着各级政府的执政环境。因此,面对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如何转变思维方式,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应对的问题。[5]
(一)适应网络,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
表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和基础。各级政府也只有充分维护公众的表达自由,尊重公众表达的权利,让公众真正能够畅所欲言,才能真正知晓民情民意,对症下药,引导好网络舆情和舆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自由发表观点的重要渠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微信、QQ、博客、微博客、闪客、拼客、哄客等“客文化”如细胞一样占据着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组成若干个相对独立但彼此紧密联系、信息高度畅通的网络社会,充分发挥着“集结号”和“照明灯”的威力,使得其所到之处没有黑暗,只有阳光和透明,能够让所有的暗箱操作都暴露无遗。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爆发时,任何政府官员即使有动用权力封锁此类新闻事件的“心”和“胆”,也没有封锁此类新闻事件的“术”和“力”。任何只顾强行封锁消息,一味辟谣和否认,反应迟缓,敷衍塞责,忽视网络舆情和网络民意的做法均是不可取的。因此,要想对网络舆情和舆论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首先必须要发扬民主,维护公众的自由表达权,理性对待多样化的网络舆情和舆论,充分维护好这一“信息交易平台”和“观念的自由流动市场”。
(二)适时引导,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网络是一个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最为直接的民情官意的互动站。网络媒体常常反映出许多在其他媒体上很难见到的、来自社会基层的各种信息,它可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保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了解到真实民意,通过梳理与分析,为其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但网络是把双刃剑,泥沙俱陈,既有建设性、批判性的理性观点,又有偏激性、不负责任的冲动言论,甚至谎言、谣言满天飞,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政府的决策,甚至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网络的这种“双刃剑”的特性使单一性案件既可能通过网络的放大和推波助澜衍变为群体性事件,也有可能经过及时的介入、正确的处理而减轻矛盾、制止谣言、化解民怨。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适时引导,努力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当代政府的分内之责。
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任务首先就是要加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程度,使之能自觉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依据和标准,对相关事物做出顺应时代潮流、切合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舆论。其次就是要大力引导社会主流舆论。由于舆论本身是多种意见的集合体,是不同舆论相互影响、渗透、转化而成的大体一致的公开性意见,这种意见无论是对组织还是个人,都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作用。因此,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就是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类舆论载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作用,积极打造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以主流引领支流,以主流遏制“逆流”,努力使各种舆论“能够同现实的意识形态协调,趋向于它,至少不要影响现实意识形态对全局的控制,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三)适度干预,保障国家舆论安全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涵之一,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直接体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舆论传播活跃期,更是舆论冲突多发期,在舆论安全方面正面临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集中显现的社会问题导致舆论茫然,减弱甚至丧失舆论维护社会规范的功能;社会结构变动加剧、社会规范出现真空与舆论惯性的双向挤压下,舆论冲突此起彼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出现引发舆论分散,加大了社会控制成本[6]。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引发了传播技术革命,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构筑的网络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网络文化与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与重塑”[7]。当人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卷入“数字化生存”后,“舆论”这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从形成机制、传播方式到作用机理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维护国家舆论安全设置了更多难题。
由此可见,面对多样化的网络舆情和舆论,“每个国家都保证本国人民享有表达思想的自由,然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对它的大众传媒加以控制,正如对它的所有的社会机构加以控制一样。”[8]政府在保证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从维护政治秩序,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需要对不当舆情和舆论进行适当干预,防止某些公民由于滥用自由和权利而对国家、组织或者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发生,做到实现公民言论自由与社会管理秩序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政府在干预网络舆论时,应把握好干预的限度,既要防止专制和独裁,又要防止舆论泛滥。[9]
总之,我国转型期间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揭示改革阵痛、体现体制弊端的同时,也显现着网络传播在群体性事件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事件信息的网络舆情与舆论的传播、形成与高频率转化,昭示着网络舆情与社会律动和公众情绪息息相关,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是社会震荡的预警仪。网络上的风吹草动很可能会演变成为现实中的波涛汹涌。这些“风吹草动”和“波涛汹涌”时刻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效能,因为毕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1]Bert Klandermans.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M].Oxford Blackwell,1997:44.
[2]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4.
[3]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5-66.
[4]李兢兢.网络舆论自由表达的限制[J].新闻前哨,2004(7).
[5]贺翠芳.政府信息公开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62.
[6]赵强.中国国家舆论安全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9 (2).
[7]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55.
[8]刘伯高.政府公共舆论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17.
[9]胡圣方.国内网络群体性事件理论研究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3):33.
(责任编校:朱德东)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s and Opinions in the Mass Incidents
CHANG Qi-yun1,2
(1.ChineseMedia University,Beijing 100024,China;2.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enan Nanyang 473100,China)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hub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the amplifier of public opinions.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ss incidents reflects the throes of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shortcomings and is the results of long-term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ofmany complex factors,however,its direct caus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xtensiv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The internet dissemination ofmass incidents is the fuse to form the internetpublic sentimentand opinions,with the forming of internet public sentiment and opinions bymore and more network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mass events,the inten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mass incidents result in the risk of network sentiment and opinions and form network opinions.The gathering on public topics,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field,the orientation of opinion leaders,the interaction of the agenda between media and so on respectively provide the premise,the important platform,the usher and the catalys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twork sentiment to public opinions.Facing the surging network public willing,the ruling Partymust update governing ideas,adapt to internet situation,respect the free expression rightof internetusers,real-time guide network opinions,shape socialmainstream ideology,make proper intervention with network opinions and ensure national safety of public opinions.
mass incidents;internetpublic sentiment;internetpublic opinion opinion safety;public opinion release place;online grassroots opinions
G203
A
1672-0598(2014)01-0079-06
12.3969/j.issn.1672-0598.2014.01.013
2013-11-13
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2012BSH002)“风险社会语境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河南省软科学项目(132400410657)“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型、原因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常启云(1978—),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南阳理工学院讲师。